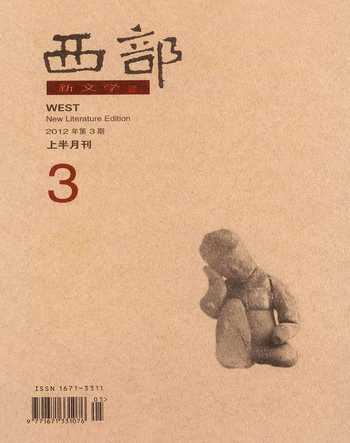老其满的玛利亚
李鹏海
一
2010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建、该院博士生导师杨镰率队的“塔里木生态环境与绿洲文明考察队”一行十七人赴沙雅考察。沙雅是他们这次考察的第一站。他们到后,提出第二天一早就去踏访八十多年前瑞典传教士恩瓦尔女士曾经生活了十九年的老其满村。
关于恩瓦尔的事迹或瑞典传教团的记叙文献甚少,只见于贡纳尔·雅林博士用瑞典文出版的《重返喀什噶尔》和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所著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年—1935年)》及《马仲英逃亡记》。2011年夏,瑞典汉学家杨富雷博士到沙雅县来,给笔者提供了一份非常简单的《诺维亚·恩瓦尔年表》。三种资料记载的恩瓦尔小姐在沙雅、库车生活的时间都不同。雅林博士记叙的是二十二年,赫定博士记叙的是十七年。而杨富雷博士从瑞典国家档案馆提供的年表中考证,恩瓦尔小姐是1900年到喀什的,1915年3月到沙雅。其前在喀什工作与学习维吾尔语六年,曾到伦敦学医一年(1906年至1907年),英吉沙工作一年,巴楚工作两年,1934年8月离开沙雅。1935年9月21日离开喀什回瑞典,同年10月15日死于距莫斯科仅十二小时铁路里程的火车上,葬于莫斯科西郊,与她的七十岁生日仅差三天。恩瓦尔在沙雅生活的实际时间是十九年零五个月。这与笔者采访的情况是相符的。
恩瓦尔女士全名是Lovisa Engvall (诺维亚·恩瓦尔),老其满的当地人都称她为玛利亚(即圣母)。老其满人、沙雅镇人、库车堆先比巴扎(星期一集市)一带的人都这样称呼她,其中带有无比的敬意和由衷的热爱。据瑞典汉学家杨富雷先生提供的资料,恩瓦尔小姐于1865年10月18日出生于瑞典中西部的小村庄Vall,离卡尔斯库市(karlskoga)很近,她的外祖母是瑞典教会中有名的传道人,恩瓦尔从小受到熏陶,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一个新的教派——行道会的信徒和传教士。
1900年,恩瓦尔万里迢迢来到了新疆,12月份抵达喀什。她是从中亚辗转到中国喀什的,同时到达的共有一百余人,是一个传教团,其中就有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热带医学博士古斯塔夫·拉奎特。他们在喀什集中半年学习当地的维吾尔语,然后被分派到喀什噶尔(喀什)、莎车、英吉沙等地,开始传教生涯。他们的传教活动是与他们开办启蒙学校和开展医疗活动同时进行的。恩瓦尔小姐是被分配到库车来传教的,时间是1915年3月。不知什么原因,她又住在了塔里木河边的老其满村。其前,她在喀什工作学习六年(1901年至1906年),熟练掌握了维吾尔文,并可以操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1906年底返回伦敦,学习护士和助产,获得了助产士与医学护士的双重学历。1913年她与她的仆人、当地的维吾尔人托克特·阿洪产生了爱情关系,教会要求她离开喀什回国,但她拒绝了。1915年她到了沙雅。
恩瓦尔小姐到老其满之初,是不受欢迎、不被接纳的人。她的到来给封闭的、平静的乡村小集市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有人甚至要求立即将这个异教徒、这个黄发碧眼白皮肤的女人驱逐出村镇。然而当地的一位依明保长保护了她,使她得以在此地安居下来。
老其满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以前,它是塔里木河北岸的一个乡村集市,又是塔里木河上的一个古老渡口,更是丝绸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从老其满沿河道逆水而行,可以到达姑墨,即今日的阿克苏、温宿一带;从渡口跨河南行,穿越原始胡杨林,进入浩瀚的沙漠,再沿着由南向北流淌汇入塔里木河的克里雅河、和田河,可以到达喀什噶尔、和田,继而到达印度及中亚。
老其满在遥远的过去一直叫其满,是维吾尔语,意为“花园”。面临滔滔的塔里木河和原始胡杨林,春天百花竞放,夏季绿树茵茵,秋季硕果累累……好一个绿洲上的大花园。不幸的是它处于渭干河的最末端,可供农田灌溉的水源有限,制约了发展。人口的繁衍与增加使其满村人无法生存的时候,就有部分农牧民向外迁徙,产生了新的村庄和集镇。现在库车的其满镇和与之相邻的新其满村都是该村的移民后代。迁居于别处的村民不忘其根,就称原来的其满村为老其满。《库车县志》及《库车县地名图志》中都有记载:“其满镇原系沙雅老其满的移民,已有数百年之久。”
考察队人员慕名而来缅怀恩瓦尔女士。沧海桑田,昔日的土墙茅舍早已不见,恩瓦尔女士昔日的传教站、住所都荡然无存。然而,恩瓦尔女士的仁爱之心,她的奉献精神,以及救死扶伤给群众带来的恩泽,却深深地铭刻在其满及库车、沙雅人民的心中。就像眼前依然挺拔的这棵大树一样,枝繁叶茂,直伸蓝天。这棵杨树就是她昔日在前院里亲手植栽的小白杨,近80年的风霜雨露磨炼了它,使它长成了擎天大树。它的根深扎在其满的泥土里,而且得到了充足的阳光及人们浇灌的滋润。它头顶一轮皎洁的明月,周围有徐徐清风,如同恩瓦尔的精神一样,茁壮成长。
考察队员们被这位异国女性的精神感动了。一个不同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的纤弱女士,从远隔重洋的瑞典来到了这里,孤身生活了19年,进入古稀且重病缠身的最后时刻才离开,怎么能不令人感动呢?
有人提议要在这棵大树旁竖一块碑以纪念恩瓦尔女士无私奉献的精神。提议立刻得到全体队员的赞同,大家立马捐款,不到20分钟就捐献了4000多元。
二
关于恩瓦尔女士的生平事迹,我只知道支离破碎的一点,那还是从一些书中得到的。斯文·赫定先生在《马仲英逃亡记》中有一小段记录:
他们指的是1933年3月8日斯文·赫定考察队的两名技工乔格·苏德布和卡尔·埃尔瑞本·希尔。他们都是瑞典传教士牧师的儿子。在第一天晚上来到了瑞典教会设有它的一个传教站的杜夏木贝巴扎(应该是堆先贝巴扎,即星期一集市),70岁的恩瓦尔女士孤独地住在那里已经17年了。她夸奖我们上一次考察队的队员们,说他们“那样的好”,又请求乔格在我们去喀什的路上把她带上。因为她认为她太老了,已经不能孤独地生活了。她有两年没有收到一封信了。现在在这里遇到两名年轻的瑞典人,特别是两个都是牧师的儿子,使她说不出地高兴。
我们非常愿意按照她的意思,把她带到喀什的教会去。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为还没有见到过恩瓦尔女士而感到遗憾。一个人如果有她为之奋斗的一种高尚的理想支持着,孤独地住在中亚的一个小镇子上17年,也许还可以忍受。但是,在战争期间,在不断受到抢掠和暴行的威胁中,住在那里,特别是对于一位妇人来说,却绝不是一件小事。然而,没有一个人敢碰她,甚至连最残忍的东干(指马仲英的士兵)流氓。就像有着看不见的卫兵似的,都过门而不入。有一名司机听说,有一个土匪的头子到她家去抢马,她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使那个家伙纯粹由于惊讶而忘却了他想要的马。
另一位瑞典东方学家贡纳尔·雅林在1979年出版的《重返喀什噶尔》一书中写道:
我们再一次起飞,看到了地面库车城里的灰白色房子,就禁不住想起了瑞典传教士诺维亚·恩瓦尔,她独自一人在库车等地居住和工作了二十二年,在那里治病救人。根据曾写过她讣告的奥尔格·罗本茨的文章,恩瓦尔在讲到她自己时曾说过:“上帝对我比我对上帝更加仁慈。”罗本茨说:“她属于人类中的这种人,她宁愿失败也不放弃自己的打算。其他人干涉她,想来救援她的所有企图,都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正是她这种性格中的特点,才是她在库车城(应为现在的沙雅县境内)生活多年,治病救人,与其他欧洲人隔绝的主要原因。”当她最终要返回瑞典时,得了一场大病。那时离莫斯科大约还有十二小时,她死在塔什干至莫斯科的列车上,后来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那是1935年10月6日,这一天离她七十岁生日还差两天。
在做民族团结工作调查中,笔者到老其满走访,遇到了当年收留恩瓦尔小姐的保长依明的孙子乃买提。他告诉笔者说,去她家抢马的不是土匪,而是比土匪还凶恶的马仲英的匪兵。那年马仲英部下的三旅旅长鲜福海带着匪兵来到沙雅,竟然一次性杀死三十七户不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人。一百多条人命瞬间丧生于匪兵的屠刀之下,惨不忍睹,这在《沙雅县志》中有记载。
一个年已70多岁的老妇人,竟敢打土匪头子一个耳光,这是何等的勇气和胆量!在1933年前后,新疆军阀混战,到处都可能发生民族仇杀的时候,一位伊斯兰的异教徒,而且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孤独无援的弱者,竟然能安然生活在异国他乡,她靠的是什么力量?自然靠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关心她,信任她,爱护她。
乃买提的爷爷,也就是巴依孜的父亲,叫依明,是当地的保长,人们都叫他依明保长。恩瓦尔女士初来时就住在他家里,后来也是在依明保长的帮助下,她修建了传教站和住房,并与他家为邻。
她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金发,白色的皮肤,挺直的鼻梁,一双深蓝色有神的大眼睛,身材不算很高,略有一米七左右。有人问:“你怎么会想到要来老其满?”她说:“是因为缘分。”其实,她是因为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在1933年之前根本不知道有一个恩瓦尔,可恩瓦尔却知道赫赫有名的探险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原来,早在1915年她再次离开斯德哥尔摩之前,就读了很多斯文·赫定博士关于新疆的著作和工作日记。文章中提到穿越沙漠的起始地都是老其满,一个花园似的村镇集市。恩瓦尔本来的目的地是库车,却鬼使神差地到了沙雅的老其满。
在一个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突然间闯入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异教徒,而且是一位肤色不同的异类女性,这犹如羊群里进了一只狼或是人群里进来了一个怪物,打乱了这里原本平静的生活。老其满是一个通衢大道上的小集市,来往过客的各色人物都曾暂时停足,本来并不奇怪,然而,恩瓦尔是要住下来传教,把她比喻成“怪物”或“狼”就不足为奇了。可想而知,她在老其满生存的艰难是非常人能够想象的。
传教压根儿行不通,谁也不听她的经文讲述。然而,她懂医术,可以给黎民百姓治病。这里缺少的正是救助病人的医生。
医生虽然稀缺,但恩瓦尔的义诊并不是一开始就很顺利。当时的渭干河绿洲上虽然没有一家医院,但有一些利欲熏心的蹩脚医生和一些装神弄鬼的巫医(当地人称“巴克西”),这些人虽然只能将小病治成大患,大病给人治死,但长期以来依然被当地群众信奉成救命的稻草。恩瓦尔的出现断了他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给恩瓦尔制造了不少麻烦。正如斯文·赫定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如果有她为之而奋斗的一种高尚的理想支持着,那么,什么样的逆境她都可以跨过去。恩瓦尔用她的爱心、耐心、忍心和仁慈消解了周围百姓的冷漠和疑心,逐渐地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1922年春天,她在沙雅镇建立了一个传教站(实为她的医疗站)。当年秋天,哈拉哈塔姆的群众也给她修建了一个传教站,哈拉哈塔姆就是堆先比巴扎(星期一集市)。星期一她到堆先贝巴扎上给人义诊治病,周二她又回到了老其满的拍先拜巴扎(星期二集市)她的寓所里来履行她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到了周五,她又出现在沙雅县镇的主麻巴扎(星期五集市)为人看病。周而复始,工作的日程排得紧张而有序。
在白天的忙碌中她忘却一切,全身心地扑在了病人身上,为她的病人焦虑,为药品的稀缺操心,也为她的成功而欢心。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听塔里木河的滔滔流水声传来的时候,她就难以入眠了。她想起她的祖国和故乡的亲朋好友。她的故乡美丽极了,那里有密布的森林,纵横的河流和清澈的湖泊。不论是城市、乡村,到处都是绿草红花,澄清的湖泊宛如绿色海洋中的珍珠,在皎洁的月光下生辉……她常常披衣而起,徐徐地在月光下踱步,无声地流下泪水。
她从一个水面积占全部国土面积百分之八十的故乡来到沙漠边的小镇里,反差是何等大哟!
她有不需付佣金的数名志愿者为她喂马,看守“传教站”,干些杂活,例如采买一些日用品、食品之类的东西和替她搬运杂物等。乃买提·巴依孜说,每当主麻日的凌晨,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买增(伊斯兰教职人员)就站在清真寺的塔顶上,用最嘹亮的声音向四方呼喊:昏睡的人们,快快醒来吧,向真主祈祷,求真主原谅你的罪过吧。这时,恩瓦尔早已在马背上做完十字礼拜,抚胸低唱着 “阿门”。而起得更早的是被疾病折磨的病人,他们已经在恩瓦尔的传教站门前排起了长队。有瘸着腿走来的,有车拉、马驮来的,也有被人抬来的病人,静静地等待着他们心中的“玛利亚”。恩瓦尔走到队伍的末端就下了马,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从人群中穿过。与此同时,街道两旁不论是看病的,护理病人的,还是经商的,无不匍匐于地跪拜,口里齐声颂唱“萨拉姆”!比见了最高级别的阿訇还虔诚……乃买提说到这时重复了一句:“真的,我一点也不骗你,这是我亲耳听爷爷说的。”
三
那天乃买提·巴依孜和我谈了很多,例如恩瓦尔给当地百姓们治病的许多故事,和巴克西(巫师)斗智斗勇的许多轶事等等,都无法在这篇短文里详细地记录下来。
确实如此,如果没有恩瓦尔赤心相待群众,膏血倾注群众,精神关注群众,仅靠她柔弱的身躯、靠一记耳光就能吓呆残忍而凶恶的土匪?就靠她孤独的一个异教徒就能得到穆斯林们的真诚认同?
近二十年里,她奉献了青春,献出了所有的一切,直到她1935年10月16日病死于返途的火车上,六天后埋葬于异国他乡的莫斯科郊外。一位新疆诗人在诗中写到:
你献出自己,提炼自己,浓缩自己
将自己变成一粒小小的药丸。
她将自己献给了老其满,献给了沙雅,献给了整个渭干河绿洲的平民百姓。
她传达了人类的文明,播撒了人间的正义,验证了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之间和睦相处的真理。
我敬仰诺维亚·恩瓦尔·玛尔女士。愿她的灵魂安息。
栏目责编:晓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