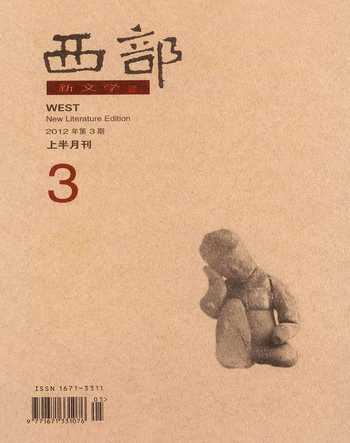偷娘
季栋梁
消息是宝平带回来的。消息是带给杆子的。麦子黄了,宝平请假回家收麦子。杆子把一包药塞进宝平的包让给娘捎回去。宝平把药送到杆子家,杆子娘留宝平吃过饭,捏着宝平的手说,收完麦出门时来婶家一趟。宝平帮爹收完麦子偷了个懒,缓了半天,睡足了觉,就往城里返。离杆子家远远的就隐隐听见了哭声,上了梁顶就见杆子家院子里高高竖起引魂幡,便知道杆子娘去了。宝平烧了灵前纸,磕过头,起来一问,杆子娘果然咽气不久。宝平好不悔疚,他要不偷懒,在家里不贪睡那半天,就能撵上个活口,杆子娘让他走时来一趟,定是有话捎给杆子。杆子大哥拉着宝平的手说让杆子连夜赶回来。
宝平赶回城里工地,正赶上中午歇工,固固刚吃过饭,躺在工棚里的床板上掏牙。固固牙稀,好不容易老板给了顿肉吃,就全垫在了牙缝里。村子里人说牙稀的人少弟兄没帮衬,固固很认同这个说法,他就他弟兄一个。
宝平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抓起固固茶缸子咕咚咚灌了一气,扯起固固说,快,快跟我去找杆子。
方圆几十号人出来都在一个建筑公司干活,建筑公司有几个工地,杆子在另一个工地。
固固说,一回来就日急慌忙去找杆子,啥事么?
宝平说,杆子娘死了,快点儿,他大哥让他连夜赶回去。
固固从床板上“嚯”地蹦起来,踏得床板哐哩哐啷的。
宝平就往外走,却见固固站在床板上不动,脸上凄凄的,泪水汪在眼眶里打转。宝平一拍脑袋方才想起杆子的娘也是固固的娘,舌头就像一截被拉得久了没弹性的猴皮筋,半天了,还长长地耷拉在嘴唇上。
之后宝平高叫一声,杆子的娘就是你娘哩。
又高叫一声,你娘也死了。
固固“哇”一声,就哭出声来。
宝平有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杆子的娘就是固固的娘,不过不做固固的娘已有十几年了,人都淡忘了,只记得是杆子的娘。
固固“嗷——啊——嗷——啊——”地哭着收拾东西。
宝平说,你收拾东西做么?
固固说,你去叫杆子吧,我要和杆子一起回去。
宝平说,你回去做啥?回去也撵不上活面了,最多能撵上个送埋,五黄六月的,人放不住,肯定都已经入殓了。
固固嗝儿嗝儿地说,我得回去。
宝平有些急了,说,要回去也得等上几天,再有五六天这个月就满了,你现在走了,这个月的工钱就一分都拿不上了,咱白纸黑字地给人家保证了的。
固固说,就是两个月工钱没了,我也得回去。
宝平说,你这人,看不见的亏都吃不完,看得见的亏还吃?等工钱拿到手,到七七上回去一趟,上个坟多磕几个头,多烧几张纸,娘也不会怨你的,有这个月的工钱,回去做上几套纸活,衣服、小车、童男童女、房子,娘得了总比便宜了老板好吧?
固固说,你别啰嗦了,快去叫杆子吧,给他说我和他一起回去,我去找老板请假了。
固固去找老板请假,老板很痛快地答应了。老板当然痛快了,省一个月的工钱哩。别看老板有钱,屁股下压的小车都过百万,可一分钱的便宜都想占。
请假出来,固固又去了农业银行,把打工几年存下的五千块钱全取了出来,装进防盗裤衩里。
当天傍晚,固固和杆子就上了火车。杆子一路哭着,上了火车也没停下来,却又怕人听见,搂着头,压抑着声音,结果就像蜜蜂嘤嘤嗡嗡的,夹杂着咯儿咯儿的嗝气声。两个人面对面坐着,杆子个头高挑、瘦削,就像杆子,大家都叫“杆子”。固固偷眼看杆子,杆子脸色有些泛黄,鼻台子上还没有黑色的胡子,只有绒绒的一层汗毛黄黄的,鼻梁两边,有些若隐若现的雀斑。杆子眉眼俊俏,面容狭长,就显得有棱有角,要城里人说就是帅哥了。固固知道杆子给工头报的是十八岁,其实也就十六岁。他上嘴唇沿有一颗痣,米粒大小,很醒目,和自己上嘴唇上的那颗痣一模一样。固固心里叹息一声,心想,要在城里,他还正背着书包,拉着女同学的手,唱着流行歌无忧无虑地上学哩。
杆子是今年才出来打工的,之前他们很少见面,村子隔着几道山岭,有二十里。一起打工,虽然杆子和他表面上就像和宝平一样哥长弟短的,可是,私下里还是觉得关系不同。比如,杆子虽然把他和宝平都叫“哥”,可叫他“哥”时,脸上表情是丰富的。比如,杆子不会抽烟,和人们蹴在一起时,别人发烟也接,但烟接到手里会看他一眼,好像他是他的啥人,害怕他骂似的。他心里说,我管毬你。比如,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杆子偷眼看他,当他猛然把目光投向杆子时,杆子的目光立刻像被惊吓着的小兔子慌乱逃遁。他能感觉到杆子见了他看他的目光有种别样的东西,他反感他这样的目光,更反感人忽然会说他们是弟兄俩。因此,他总是阴着脸。
固固也想好好哭一场,可面对着杆子他就是哭不出来,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他有些嫉妒杆子,他有那么方便的眼泪,想哭就能哭出来,涮涮涮的,而且是当着他的面、一车厢人的面都哭得出来,鼻涕涎水都吸不住,哭上一阵还眼泪巴茬望他两眼,哭上一阵还眼泪巴茬望他两眼。他心里冷冷地说,先是我娘后才是你娘哩,你倒比我哭得歪。可还是忍不住,摸出一沓从拉面馆装的餐巾纸递给杆子。杆子看他一眼,接过去擦满脸泪痕,却是越擦哭得越凶,发出嗷嗷啊啊的哽咽声来。
固固伸出手去,像爹摸他的头一样,抹了一下杆子的头说,别哭了,小心把眼睛哭坏了。这么说着,又拧开矿泉水递在杆子手里。杆子接在手里,抬起目光来看着固固。这次固固忙将目光转向车外。
又大又圆的月亮就像一个笸箩,拴在火车上,给火车带着在那戈壁滩上空滚动。月光像水一样漫过无遮无拦的戈壁滩,戈壁滩一片银白,固固知道那是月光落在了芨芨草上。这时间正是杨花坐籽的时节,浑身上下缀满白色的穗子。固固看看腕上的电子表,再过半个小时,车厢里就会熄灯了。他盼着早点儿熄灯,这样他和杆子就相处在黑暗中了,谁也看不到谁了。他实在不想和杆子那样的目光相对,更不愿杆子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注视他。何况他要好好地想一想接下来要做的事。
从记事起,固固一提娘,爹就说死了。固固说,别人的娘咋活着?爹说,别人的娘是好人,好人命长。固固说,我娘是坏人么?爹就不说话了,只顾吃烟。固固大一点儿的时候,知道人死了就埋了,埋了就有坟鼓堆,清明时节要上坟。可他从没见过娘的坟鼓堆。他就问爹,娘的坟鼓堆在哪里?爹说,坏人死了都没有坟鼓堆。后来张娃拉回来了。张娃因为偷了李全的羊,李全追到半路上,张娃失手打死了李全,结果被判了死刑,枪毙后拉回来埋了,有坟鼓堆。固固说,张娃都有坟堆哩。爹就大声咳起来,咳完又不说话了。固固就很茫然地看着爹。
爹有肺痨病,总是咳嗽,厉害的时候,身子弓成一张弓地咳嗽,这么咳了几年,人就一年一年地不行了。有一天,爹说要带他出趟远门,可到了董家塬,爹靠着一棵树坐了下去,说,去要碗水喝。固固说,才走了多远,我不渴。爹又说去讨个馍吃。固固说,才吃了多久,我不饿。爹翻翻眼睛就躺在树下不走了。固固说,爹,翻山越岭的,就是要在这树下躺一躺吗?爹不说话。固固说,家里有那么多的树,你却跑来在这棵树下躺着,躺在人家树下比躺在自家树下舒服啊?真是。爹不说话。固固又说,这树正对着人家大门哩,你躺在这里,让人家看见了咋想?还当咱打啥瞎主意哩。爹照样不说话。固固又说,咱又不饥不渴的,到人家门上要吃要喝,光彩呀?丢人不丢人?爹还是不说话,而且把头扭了过去。固固就站在那里打量这个叫董家塬的村子。
村里人都说董家塬好,说起董家塬就像说大地方一样,其实董家塬就是平整。董家塬当然平整,不平整能叫塬?在固固看来,董家塬风光就风光在董家塬人住的是房子。那当然了,这么平整的地方想挖窑洞没处挖,不住房住啥?不过固固也知道,这两年娶媳妇,人家就要几间房,不要窑洞。当然平整有平整的好处,地平了窝墒,庄稼就长得好。再就是路好,直溜溜平坦坦的,像磨刀石。固固扭头看看爹,爹搐一个疙瘩窝蜷在那棵树下。固固知道爹在耍脾气。爹有时候就像个娃娃,也给他耍脾气,一耍脾气,就搐一个疙瘩,给他扎势哩。固固站在树下想想,就过去敲开那扇大门。比起要馍吃,要水喝就不丢人,要水喝的不是讨吃,要馍吃的才是讨吃。可是即使这样,固固觉得还是很丢人,终归还是个讨么。门是铁大门,很气派。哐啷啷,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婶子。固固低着头说,婶,给碗水喝吧。那婶子看了他两眼,进去端了碗水出来递给他,盯着他看。固固觉得这婶子有些面熟,给盯着一看,觉得自己满脸都有虫子在爬。固固接过碗来“咕儿——”“咕儿——”地灌完,把碗擩到婶子的手中,掉头就跑了回来。他隐约听到婶子说了句啥,也没有回头。到了树下,却不见了爹。正纳闷时,爹从另一棵树后闪出来。固固说,我讨水喝了,咱们赶路吧。爹却又靠着树坐了下去。固固说,你这人真是,到底想做啥?爹不说话,又咳起来了。固固说,你老是这样,让人问住了就不停地咳,你这人,那肺痨病就是这么咳出来的。爹说,你少说几句怕哑巴了?让人耳根子清净清净不行啊。固固扫一眼那大铁门说,要坐咱换个地方坐噻,总这么坐在人家门前,让人家咋想噻。爹就靠着那树背对着那门坐着不动弹。固固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就往一边走。爹说,你去要个馍吃。固固说,不去,我不饿。爹说,我饿了。固固说,唉,你这人,你这人非把人丢尽了,家里没馍?爹大吼着说,我饿了!固固说,给你要去,要去。固固这么说着就向另一家走去,他想不能在同一家要吃要喝的。爹却说,你去哪儿?就这一家要。固固盯着爹说,你咋总是给一家人找麻烦,越来越不懂事。爹说,爹就要这家的馍,别跟爹拗着了,爹老了,没几天了。说着爹就咳起来了。固固只能再次来到门前,举手敲门时头低低地垂着,他觉得这实在是丢人。门开了,出来的还是那婶子。固固说,婶,给我个馍吃吧。话虽然说得不结巴,可他的脸已经红透了,像爬了多陡的坡似的。婶子说,正好家里有碗面,还热着,跟我进来吧。固固一点儿都不饿,可那婶子已经进门去了,固固只好跟了进去。到了屋门口,固固站住了,家里也老来讨吃的人,都是站在门墙的旮旯里,从来不进屋的,忌讳把穷气给人家带进去,冲了人家的运气。婶子拉着他的手说,进屋吃吧,外面风尘土扬的。固固跟着进了屋。婶子说,你坐吧,婶给你端饭去。不一会儿就端了一碗面上来,还端了一碟子菜。菜是杂拌儿菜,有韭菜、黄花、蒜苗、洋芋条,还有茄子和黄瓜,味道真好。固固越吃越香,一碗面吃光了,一碟菜也吃光了。固固有些不好意思。婶子始终看着他,目光很是慈祥。固固抹抹嘴说,婶,我还想吃个馍。婶子笑笑,拿了两个馍出来。他拿到手里就往外走,婶子说,塬下上来的吧。固固点点头。婶子又说,固固你认得么?固固点点头。婶子说,个头有你这么大了吧?固固说,和我一样大。婶子就盯着他看。固固怕被那样看着,忙忙往门外走。他想告诉婶子他就是固固,可又想告诉人家干啥呢?自己是来讨吃的,家里又不是揭不开锅了,本来就够丢人的了。固固出了大门走出一截,一回头看看婶子还倚门站着,就说,婶,你进去吧。说着便顺着墙根绕到墙背后去了。在墙背后,他听到婶子叹了口气,进去关上了大门,这才绕到了树下。爹又从树后闪出来。固固说,你也知道丢人,怕让人看见?你说你到底咋想的。他把馍递给爹。爹像真的饿了,蹴在那里,双手捧着馍一点一点地啃,掉落在掌心的馍馍渣子忙连舔带吸地吃了,就像吃酥得一碰就掉皮皮的点心。一个馍吃得剩下一牙儿了,爹才说,就是这馍。爹说,那家人阔吧。固固说,没看,只顾着吃饭了。爹说,有几间房子?屋子里都摆了些啥?固固说,没管,又不是咱家。爹吃光了一个馍,把另一个馍递给固固说,你吃吧。固固说,我都把一碗面一碟菜吃上了,还吃?爹说,你吃一个吧,这馍跟别的馍不一样,好香的哩。固固说,馍再香还能香成点心?爹就长叹了一声说,回吧。固固瞪大眼睛说,啥?你说啥?走了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要着吃个馍?我还当你带我去大地方呢!爹说,大地方的街石子街,没有票子吃不开,去大地方有啥意思。爹说着已经走回头路了,固固心里就很不高兴,觉得这趟门出得真没意思,他就有些乏了,走得疲沓沓的。爹说,这家人要记住。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固固觉得今天真是没意思,一来回走了四十来里路,啥事都没做成,因此,一回家他就上炕睡了。爹端上了一碗炒好的豆子,听别人说吸着吃豆子补气,爹就一颗一颗地吸着豆子咯嘣咯嘣地吃。爹把豆子往固固前面推推,固固没吃豆子。爹咬了两个豆子说,那婶子好么?固固说,好,可再好也是别人家的。爹说,知道那婶子是谁么?固固眼睛盯着窑顶,他懒得和爹说话。爹说,她就是你娘。固固听得这话一个鹞子翻身坐了起来,说,你说我娘死了,她咋又成我娘了?爹说,对我来说她死了,可对你来说她活着。固固说,你咋这样的人,哄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从小就哄我,把我哄到这么大了。固固就拼命回忆,可就是想不起来。他对娘没一点儿印象,要了碗水喝了,吃了碗面,又要了两个馍,他都没仔细看看,因为他不渴不饿又不是讨吃,却去要喝要吃的,就很害羞。爹唉了一声说,咱这里女人都想嫁到董家塬去,董家塬就是天上。固固瞪着眼睛想了半天,狠狠地说,我知道了,她真是个坏人。爹又说,爹陪不了你几天了,死了,你去找你娘,只要他们要你,你跟他们姓都行。固固说,我看你活愚了,有让自己的儿子跟别人姓的?你有几个儿子,还把你富有得不行了?还没老就糊涂成这样子。我跟人家姓了,谁给你上坟烧纸,你到那世还不穷死?爹说,穷死就穷死吧,反正这辈子穷了一辈子,也穷惯了。爹把那个馍掏出来递给固固说,你尝尝,你娘做的馍就是香,多少年了,还是那味道,你娘是村子上那时间茶饭针线做得最好的,你吃那碗面香吧?固固说,我不吃,饭也不香,你不要说了,她就是个坏人,坏女人。爹说,爹死了你就去找你娘,跟他们过日子吧,他们有钱给你娶媳妇,置家业。固固说,我不要媳妇。爹说,你不要媳妇,爹这辈子就白来这世上了。
爹把事说出来了,心里就没事了,躺在那里竟然唱起来:
想你者想得不能能,
趴在了地上画人人,
穿衣找不见扣门门,
吃饭寻不见嘴唇唇,
睡觉摸不见灯绳绳,
走路瞭不见圪塄塄,
没你难活得不行行,
整个成了个瓷人人。
爹心里没事了,可固固却心里有事了。
平时爹不咳嗽的时候也这么唱曲儿,固固也喜听,可现在他心里有事了,听起来就烦,说,别哼哼了,你心里不泼烦呀。
爹却说,不哼哼爹心里才泼烦哩。
青天蓝天嘛老黄天,
老天爷杀人无深浅,
董家塬的塬来平格坦坦,
刘家山的山来山套着山。
东山上糜子西洼里的谷,
黄土里笑来呀黄土里哭。
固固跳下炕就出门去了。一出院门,就不由得把头抬起来往塬上瞭。尽管董家塬很远很远,尽管一看心里就泼烦上好一阵儿,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不由得往畔上瞭几眼。去镇上赶集要经过董家塬。后来,几次赶集,固固都会看着那户人家,心里就乱七八糟的。赶集是快活的事,可自从心里有了事,他就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次,口渴得要命,他几次走到那门口,最后也没去讨水喝。爹总是要问,你去讨水喝没,你讨馍吃没?固固会恨恨地说,我就那么没出息啊。
后来,爹不停地给他叨叨娘的事。固固实在泼烦得不行,就说,你真没出息,她就是一个坏人,值得你给她说这么多的好话?爹就努力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一样说,我能这么想这么说,你不能这么想这么说。固固说,为啥?爹说,她是你娘,其实她也没错。爹咳了几声又说,你娘是扑着好日子去了,也没错,人谁不想过好日子?只有水才往低处流哩。再说爹那时间也不学好。固固说,你不学好?爹说,又赌又偷的,回来还打你娘么,不学好么,日子过塌了,把你娘过得心凉了。固固说,日子过得心凉了就跟上人跑了呀?固固想娘肯定是跟上人跑了。爹说,唉,你娃咋就这么个娃噻,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疙瘩,她的儿啊。固固说,我是她儿?我是她儿,她咋一次都没来看过我?爹说,来过不知多少次了,让我赶了,没让她见你,我威胁过她,她要见你,我就把你卖了,她怕这话哩。
固固又大了一点儿,爹还在叨叨。固固说,爹,你心里一直想着她,是吧?爹不说话。固固又说,你下辈子还想吃她做的馍,还想和她过日子是吧?爹忽然“哇”地就哭起来了。固固从来没见爹这么哇哇大哭的样子,气都憋住,脸憋得紫红。固固就捋着爹的背说,爹,等她死了,我把她要回来埋在你身边,你们下辈子就又能一起过日子了,要不回来我就给你买回来。爹咳了一阵儿说,你不能一口一个“她”地叫,她是你娘,你这样叫折寿哩。固固说,她要真念我是她儿子,她就不该折我的寿,哪有娘折儿子的寿的。爹就说,唉,你这娃跟爹那时候一样倔啊。固固说,她要再想让我叫娘,我就要把好多话问明白哩,我不能糊里糊涂地叫她“娘”。爹说,你想把啥问明白,爹说给你。固固摇摇头说,你这人哄人哩,问不出实话,再说有些话是心里想的,你知道她心里咋想的?爹说,你娘其实这些年也跟着老董东跑西颠地受苦了,还没享上福,老董让汽车碾死了,把个家也赔了个净光。
爹说没就没了,就像忽然刮来一股贼风,没来得及用手罩住灯,灯头摆了一下就那么灭了。抬埋爹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都来了。爹就固固这么一个孝子,顶着孝盆,跟着阴阳转了一天的经,没得消停。爹埋了之后,村里人都走了,宝平才给他说,你娘来过了,带着你那个隔山弟兄,还给你带了一笼子馍哩。便把馍给他放在面前。固固说,你咋不早说?我有好多事还想好好问问她哩。他给了宝平一个馍,自己拿了一个吃。那馍真还是他吃过的最香的馍。宝平说,你娘这馍做得有水平,像点心一样。
在给爹一七一七烧纸的时间里,固固几次想去看看那个是娘的女人,可是都没有去。他想把心里装着的事全问明白,却又怕见那个是娘的女人。有一次都快走上塬畔了,又踅了回来。娘却来看他了。他正在扫院子,娘就进来了。娘对他说了好多话,他偏偏一句话都没说出来,一件事也没问出来。他只是盯着娘看,看得娘在院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娘给他带来了两双鞋,一双做的,布鞋,一双买的,皮鞋。还给他带了身衣服,也是买的,是他从来没穿过的。娘给他做了顿饭,和他一起吃。天都快黑了,看来娘想留下来睡一晚上。他怕娘留下来,就躲到山野去了。娘走了,他站在山野里看着。凛冽的西北风刮得黄天昏地的,娘就顺着坡越来越小了,一点一点不见了。他忽然就哭了。爹死了,他都没哭出声来,可这天他忽然哭出声来了。
一七一烧纸,要烧七七纸。他一直想着哪天去找娘,把些事情问明白了。可是日子过得很快,四十九天就那么过去了,还没等他决定去找娘,大家就喊着出门打工,他也随着出外打工了。那年他虽然才十五岁,可个头窜得老高,老黄拍拍他的肩膀说,抱砖推车,能干。
下了火车,他看了杆子一眼,杆子的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固固买了些烧纸和面包提着。车站有蹦蹦车等着拉人挣钱,固固把自己和杆子的车钱一并交了。上了车,杆子给他钱时,他推了回去,说,哥请你坐蹦蹦车。杆子说,谢谢哥。杆子把两个眼睛哭得肿得像桃子。他心里一拧一拧的。到了董家塬,就看见高高撑起的幡杆和白的黄的纸花,像蝴蝶翻飞着。杆子远远地放声嚎哭开了,固固却是一声都哭不出来。他掐掐自己,疼,但还是哭不出来。进了院子,跪在棺材前磕过头,烧了纸,固固接过别人递过来的孝帽戴上,接过麻匹捆扎在腰里,就匆忙去找杆子大哥。听听阴阳念经,知道快要起灵了。杆子的爹已死了好几年了,现在只能找杆子大哥了,没了爹,一切都是长子主事哩。
杆子大哥正在跟阴阳商量着啥,固固就走了过去,叫了声“大哥”。杆子的大哥看看他,他说,我是固固,塬下的。杆子的大哥就明白他是谁了,说,跟杆子一起回来的吧,先去扒拉一点儿把肚子填饱,要起灵了。他摇摇头,扯着杆子大哥的衣襟,说,大哥,我有话跟你说。杆子大哥就随着他来到一堵墙背后。固固说,大哥,你知道我是谁了?杆子大哥说,知道了。固固递给杆子大哥一根烟,点了,说,事急,我也不绕弯子了。杆子大哥说,直说吧。固固说,大哥,你把娘还给我吧。杆子大哥看着他,眼睛瞪得牛铃一样说,你说啥?你说啥?固固说,你把娘让给我吧。这次他把“还”字改成个“让”字,觉得这样说好一些。又说,你爹身边有你娘哩,可我爹身边啥也没有。杆子大哥瞪着眼睛说,你是来吊孝的,还是来闹事的?要吊孝就好好吊孝,要闹事趁早走人,就凭你也来闹事,也不提提自己有几斤?说着转身要走。固固一个蹦子拦在杆子大哥的面前说,大哥,我不是来闹事的,我三岁上娘让你爹拐走了,你让我下辈子也没娘么?你就行行好吧。杆子大哥恼怒地说,你休想。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固固坐在那里想了半天,他想,还得从杆子身上下手,杆子和他算是亲着哩,其余的人家都是一个爹一个娘,杆子在这事上最有发言权。
杆子已经哭得浑身稀软,像是被人抽了筋骨一般,拉拽不起来。固固只能连拖带抱把杆子从娘的灵堂前弄到墙后,对杆子说,娘没了,你得帮哥,把娘让给我。杆子擦着眼泪说,你说啥?你说啥?把娘让给你?固固说,让给我,你从小就跟着娘一直到娘没了,可我从三岁上就没了娘,你想让哥下辈子也没娘么?杆子说,我把娘让给你,我下辈子不也没娘了?固固说,你爹身边还有个娘。杆子说,那是别人的娘,不是我娘,你休想把娘弄走。杆子还不等他说啥,嚎哭着走了。走出老远了,又回过头来举举拳头说,你休想把我娘弄走。
固固痴呆呆地站在那里,想了半天他又找到杆子大哥,扯到墙根下,掏出打工攒下的那五千块钱来说,大哥,你把娘卖给我吧,我从小没娘到现在了。杆子大哥甩开被他扯着的衣襟,火了,说,看你也老大不小了,做事咋就举着杵子打月亮不知轻重高低?要不看着咱们是隔山弟兄,我一个砍脖子让你娃摸不着东南西北哩。这事别再说了,再说我让人把你扔出村子哩。杆子大哥走了,固固对着他的背影说,我把你敬到了,做到仁至义尽了,下面我做了啥事,你可不要怪我。
起灵了,固固看着装着娘的棺材被八个小伙子抬着向山上走去。固固找了一根丧棒捏在手里,也跟着送葬的人群走。一路上纸钱翻飞,哭声遍野。固固想哭几声出来,可是他怎么努力就是哭不出来。他心里默默地说,娘,等我把你偷回去,我会好好哭你一场。
下了葬,送葬的队伍在杆子一个人的哭声里陆陆续续散了。固固没有随着队伍走,而是直接回家去。才走了几步,杆子却追了上来扯住他说,哥,回家吃了饭再回吧。固固甩开杆子的手说,谁是你哥?谁是你哥?然后就走了,他越走越快,就像后面有什么追着。到远处回头一看,杆子还站在那里抹泪。
回到家,已是黄昏,固固来到爹的坟前,看着爹的坟,孤零零的越看越凄惶。爹埋了后,他怕爹孤独,也怕自己打工走了,风吹雨涮地把坟堆抹平了,找不到爹的坟,就把院子里的一棵老柳树移栽了过来,每七都提桶水饮,那树竟然活了,而且旺生生的。
山野里最后一群羊归村,天空就像一盆清水里滴进了一滴墨水洇了开来,暮色就四合了。固固跪下来磕了三个响头,烧了一沓纸钱说,爹,固固说话算话哩。他开始起爹的坟。棺材已经朽了,碎得一块一块的。他想这事出得突然,想得也不周到,要不他会做一副气派的双人棺材,棺材头上有金童玉女,棺材盖上有盛开的莲花,棺材两边雕龙刻凤。可是现在事情紧急,只能将就一下了。等娘归阴三年的时候,他会做这样一副棺材,还要请六个阴阳、六对鼓乐,念三昼夜的黄经。
固固将坟坑往大里挖了一倍,然后开始往出清理爹。爹只剩下骨头了。爹的骨头蒙着一层灰尘,他就把爹的每根骨头刨出来一口一口吹干净,靠左边重新摆好。他说,爹,你就挤一点儿吧,我娘要来了。吹去灰尘的骨头是那样的洁净,在月光下云白水亮的。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便用那草帘将父亲的坟坑虚覆起来。抬头看看月亮,好圆好大,他知道今日不是十五就是十六,不管是十五还是十六,都是好日子。固固回了趟家,在园子里的桃树上砍了两个桃树枝子,剁出九个七寸长的木橛,然后提着锹往董家塬来了。
山色越来越重了,虽然月光很明亮,但毕竟夜不观色,山路就更加崎岖坎坷,不过固固凭着走山路走出的经验走得很快。到了董家塬,他看了一眼腕上的电子表,二十里的路程,他只用了两个小时。固固没有侦察,便直接冲着杆子家的坟地去了。人入土了,坟上就再不能去人,只有到了七七才能到坟上去,这时间坟地应该是没有人的。来到坟地,果然没人。有几道光从墓地射出来,这使得墓地显得十分诡秘。只有未曾烧尽的白纸在明亮的月光下,随着小风一跳一跳的,像一只白色的小兔子。固固并不害怕,因为这里有娘在。他想即使有恶鬼,娘也会拼命保护他的,再说他身上装着桃木橛,这东西避邪。不过那几道光让他感到阴森恐怖的。固固抛抛头发,踏进墓地,才发现那几道光是阴阳摔碎了瓷碗片儿反射的月光,心里一下子就宽了,定了。固固围着娘的坟鼓堆绕了几圈,把坟鼓堆的大小高低记在心里,就开始起坟了。起新坟要比起老坟省事得多,新坟的土是虚落的,只要往下刨就可以。很快他就看到棺材了。他将锹从棺材盖的缝隙插进去一撬,棺材就被打开了。当摸索着将娘抱出来时,固固没有想到娘竟然像个娃娃一样轻。
月光越发的明亮了,固固不敢逗留,他将娘背出坟圈外,放下说,娘,等会儿我背你回家。然后,他开始填坟坑了。坟坑填好,他围着坟堆绕了个圈,觉得和先前一样了,然后跪在那里叫,娘唉——回家了,娘哎——回家了,娘哎——回家了。叫过三声,他掏出七个桃木橛围着杆子爹的坟堆钉了一个圈,这样就把杆子爹镇住了。他不这样做,娘的魂魄就叫不走,叫走了爹也弄过杆子爹。杆子爹是个厉害人,家族又大。他边钉桃木橛边说,要怨就怨你的儿子,我敬过他了,这都是他逼的。钉完桃木橛,他把锹把放平挨着地,扫来扫去。觉得坟地里没留下什么痕迹,然后倒退着扫了出来。在坟地的大门口,又钉了两个桃木橛,便背起娘往回走。娘太轻了,他背着娘边走边唤,娘哎——回家了,娘哎——回家了。这样叫着,就觉得娘的魂魄跟在他的背后,而且隐约听到娘轻轻的脚步声,心里又安稳又踏实。
天阴了,山谷朦朦胧胧的。固固完全凭借着经验走,走起来就不跌跌撞撞、磕磕绊绊的,倒比月光清明走得踏实平稳,速度也就快多了。固固不停地叫着,娘回家了,娘回家了,还说,娘,回家多好,老天爷都帮忙哩。把娘的尸骨偷了回去,魂魄叫不回去,等于没将娘偷回去。
刚刚背上娘,觉得娘像个娃娃一样轻,可现在他觉得娘越来越重了。他心里说,娘应该好好压压他的,这些年了,娘没吃过他的一口东西,没穿过他的一件衣服,应该好好压压他。固固实在太累了,就借个土坎坐一坐,就让娘在背上趴着。他不敢走得太快,他害怕把娘颠散了,又怕把娘垫疼了。娘是老人,这几年一直有病,经不起颠簸折腾的。
到了埋爹的山洼,固固没有背着娘直接到爹的坟前,而是背着娘回了家。娘好久都没回家了,该让娘再看看这个家。他也想好好看看娘,他有许多话要问娘。尽管娘已经去了,但他还是要问,娘给他留下了太多的空白。自从他知道她是娘后,就想着有一天,他要把所有的话都问清楚,把所有的空白都要填满。不管娘回答不回答,他都要问下去,而且他不会哭,连一星眼泪都不会掉。只是这几年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找着机会问。他没想到娘这么快就走了。
已是半夜时分,有几声狗叫,夜更宁静了。回到家,他打开门。进门槛的时候,他说,娘进门了,小心碰头。他摸索着把娘放到炕上,点着了灯,将灯端到娘面前放稳,坐到娘身边仔细端详着娘。这才发现娘的脸上蒙着一层土,他舀了一盆清水,将娘的脸重新洗了一遍。娘的脸就很白净了。他看到娘上嘴唇上那颗痣,和他、杆子的一模一样。他明白他很像娘,以前他还一直觉得他很像爹。他把娘身上的土拍打干净,他把娘被弄皱的衣衫拉展。娘就像睡去了一样,那么宁静,那么慈祥。泪水就再也关不住了,像树叶上攒积了一夜的露珠刷刷刷地落下来,那么大,那么沉,打在鞋上地上,发出嘭嘭嘭的声音。他趴在娘的身边任泪水流着。许久之后,他抹了泪水,掏出烟来。他不知道娘抽不抽烟,村里许多奶奶婶子都抽烟,他就给娘点了一根,自己点了一根。抽着,他什么都不想问了,就想躺在娘身边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是,他又怕睡着了,鸡叫了就不好了,娘的魂魄就入不了坟了,就成了孤魂野鬼了。他就看着娘说,娘,你回来就好了,咱们一家人就全了,你们好好过日子吧,你就能给我爹做他念叨了一辈子的馍吃。我想问你的话不问了,我攒了多少年的泪水都流给你了,过去的就让都过去。杆子把我当哥,他看我的目光我能知道哩,我会把他当亲弟兄一样待哩,有我吃的就饿不下他。这么说着,他觉得娘有了泪水,眼角亮亮的。固固看看电子表,已经两点多了,不敢再耽误,四点钟鸡就要叫了。背娘的时候,他才想起娘浑身上下都穿着人家的衣服,他想给娘找件衣服什么的,却没有一件。从他记事起,家里就没有女人穿用的东西。忽然他想到自己手上的电子表,就很兴奋,虽然戴了一年了,可是他买的。他把表抹下来,给娘戴上,背起娘往坟地里来了。
埋了爹和娘,箍好了坟堆,固固躺在坟堆前说,这下好了,一家人全了,逢年过节我来和你们说话。固固抽了根烟,然后起身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朱阴阳家。朱阴阳在朱家洼。到了朱家洼,已是鸡叫两遍了。朱阴阳打着哈欠说,你半夜三更的啥事,你家里没啥事了。固固说,我想给我爹念经。朱阴阳说,你爹五周年过了,十周年还远着,为啥念经?坟里不安,家里不顺,遇啥事了么?固固说,不为啥,也没遇啥事,我就想给爹念个经,多少钱我出就是了。朱阴阳说,那我看看日子吧。固固说,明天就是好日子。朱阴阳还是看了看日子,说,明天真还是好日子。固固说,念三昼夜经。朱阴阳说,一昼夜经就行了,又不是啥日子,没名堂么。固固说,你就念三昼夜经吧,纸活做全套,给我爹我娘一人做五身衣裳。朱阴阳说,你娘是人家的人了,现在埋在人家坟里,做了也得不上。固固说,你就做吧,一定要把我娘的魂魂招回来。朱阴阳就明白了,说,你娃有孝心啊,现在像你娃这么有孝心的人不多了,日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固固放下了两千块钱说,明天就起经吧,把鼓、乐也一并带上,我先回去准备了。
三天经念完,烧引魂幡的时候,固固把朱阴阳扯到一边问,我娘的魂魄在我家吗?朱阴阳说,在,你看引魂幡一动不动的,你娘的魂已在你家的坟里安歇下了,要不然那幡会乱晃的。固固答谢阴阳时,还欠三千块钱。固固说,明年给你还清。阴阳说,就冲你娃有孝心,明年就明年吧。
固固并没有立刻回去打工,娘现在他家坟里,他得烧够七七纸,就像杆子家一样地过。七七纸都在黄昏烧。从家门口开始烧起,七天为一七,一七一烧,一七比一七远一些,就像送亲戚一样,一站一站地送,七七送到了坟上,就算送到家了。
心里事了了,日子就有了想法,眼里就有了活。地里是没一丁点儿活做,一年庄稼两年做,打工就把地撂荒了,把家也撂荒了,窑壁上的泥皮碱得一坨一坨,就像害了牛皮癣。固固就活泥把窑洞又泥了一遍。几堵院墙根子也被雨水泡得凹了进去,又背了土培填实。园子里的几棵树枝子长得纷乱,又把旁枝骟了骟。活只要做起来,就没个完了。
做着活,固固也哼着小曲儿:
荞麦皮皮担墙墙飞,
我一心一意想呀么想着个你。
心里头有谁就是个谁,
哪怕他旁人跑成个罗圈圈腿。
哼着小曲儿,不但解泼烦,也解乏:
石板上栽葱扎不下个根,
玻璃上亲嘴急呀么急死个人
不来这一回我见不上个人,
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烧完七七纸,固固在爹娘的坟前坐到深夜,他说,爹,娘,我明天就要走了,过年时我回来给你们烧纸,过节。
第二天早上,固固起来刚刚洗了脸,杆子就到了门前。他知道杆子也是烧了七七的纸。杆子说,哥,我今天进城打工,你走吗?
固固说,走,哥跟你一起走。
杆子就把一个包袱递给固固说,哥,是娘给你留下的。
固固打开包袱一看,是几双鞋,几身衣服,还有一对银手镯。
杆子说,娘以前老说你,一说就哭,这双银手镯是给你媳妇的见面礼。
固固锁了门,两个人就上路了。经过去爹坟上的路口时,固固带着杆子到了爹的坟前,对杆子说,磕个头吧。杆子就很顺从地跪了下去,磕了头。
杆子说,哥,你也念经烧纸了?
固固说,嗯。
杆子说,谢谢哥。
上了火车,杆子说,哥,那天我说那些话你不多心吧?
固固笑笑说,多啥心?你不那样说我才多心哩。
杆子说,咱们的娘,咱们一起敬着。
固固说,对,一起敬着。
杆子就说,我爹死后,他们都是一娘生的,对娘和我不待见。哥,我就活个娘,没了娘我还活个啥?说到这里,杆子又嗷嗷地哭起来,边哭边说,娘的七七刚满,他们就催促我出去打工挣钱,我还想多陪几天娘哩。
固固捏着杆子的手说,有哥哩,咱弟兄俩互相帮衬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么说着,固固的泪水又来了……
责编:柴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