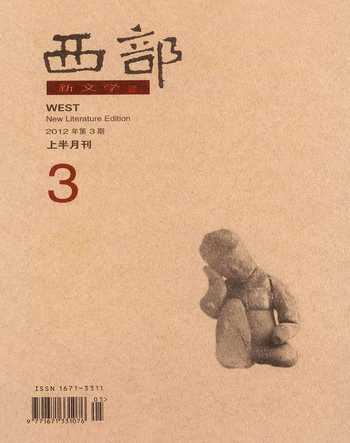泡在福马林里的时间
“莎士比亚说‘死亡是有去无回的未知国度……”“解剖学”的老教授说。
“老师,那您认为‘死亡的定义是什么?”
“那你认为呢? “
“如果我说水晶球是活的,您相信吗?”
“当然相信,因为死的东西,都一定活过。”
◆
“六男二女,其中二女必须相邻并排,请问共有几种排法?”把问题抛给女孩之后,我在一旁发呆。
女孩埋头走进“排列组合”的世界,她的额头微冒油光,脸上稀疏点布几颗痘子,长得是巴掌脸,但不属于可爱或美丽型,也说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眼睛、鼻子、嘴巴都长得不错,但排列组合起来就是差了一点儿。乍看之下有点像小了两号的梁咏琪,不过是捏坏了的梁咏琪。
女孩家住台北市的边陲地带,玉门街和酒泉街交口──这个地方好像也是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边陲。我每个星期二、五的下午,趁没课的时候来帮她补习数学。女孩家是卖流行饰品的,那种西门町一抓就一大把的日本流行文化的怪东西,她们店里最好卖的是钥匙圈,不是普通随处可见的那种,而是大小不一,里面用福马林泡着甲虫、白老鼠、青蛙、蛇、猫、狗、猪胚胎……让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古怪东西。
每次走进女孩家,经过女孩母亲开的店,看到这些钥匙圈,我都有种嫌恶的作呕感,仿佛是闻到福马林的刺鼻味,可是根本什么味道都没有啊,我知道那是视觉引发的伪嗅觉。
走进凌乱狭仄的店面,通过狭长阴暗的甬道,女孩就坐在甬道的尽头、用木板隔出的小间里等我。甬道里堆满各式流行饰品,但没有外面那种“尸体钥匙圈”。小间里,女孩桌上有一颗大约像垒球那么大的水晶球,每当女孩在练习解题时,我便会望着水晶球发呆,从水晶球里见到的世界像被重新排列组合过一样,不具真实感。
水晶球映出女孩扭曲变形的脸孔和深不见底的甬道,像是显微镜底下利用伪足运动爬行、不断形变的变形虫正要爬进(或被吞噬)某种类似腔肠动物的消化腔。
“算不出来。”女孩把问题推回给我。
“是谁发明‘排列组合这么无聊的问题的?”女孩嘟囔着,“想怎样就怎样,干吗还非得要去算有几种组合不可?”
“这种题目很简单,你只要把两个女的绑在一起当成一个,那这题就变成七个人的排列问题,但是因为两个女的可以互调,所以最后再乘上两倍就行了。”我把解题的过程从头至尾演算一遍给女孩看,女孩似乎对如何解题并不怎么感兴趣。
“老师你听过蚯蚓的故事吗?蚯蚓是阴阳人你知道吗?”女孩突然问我。
女孩有一种很荒谬的素质,她会在我上课上到一半时,硬生生地把我的话给打断,然后不着边际地胡乱倾倒些学校里的趣闻琐事给我;偶尔她也会打断自己的话,另辟一个与上一个话题没有任何关联的“超联结”;又或者在滔滔不绝的讲述中穿插一两个问句,但等不及我回答,她便又顺着这个话题的滑梯溜到另一个话题去了。
──蚯蚓是阴阳人,同时拥有雄性和雌性性器官,行“有性生殖”时,A 、B两只蚯蚓就会以“69”的淫荡姿势,你插插我、我插插你,插(被插)完了,就各自回家生小蚯蚓。A大蚯蚓生a 小蚯蚓、B大蚯蚓生b小蚯蚓,所以a 和b小蚯蚓基本上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姐妹(反正都是阴阳人)。
类似“蚯蚓是阴阳人”这类错置接舶的胡乱想象是每个高中男生都善做的事──将所有的东西都和性联结,于是乎从书本里、课堂上、隔壁女生班中便会摇晃歪斜地走出一个又一个荒谬无厘头至极的黄色笑话。而这些富于想象的歪斜笑话是彼时苦闷高中生涯里的全部。
这类只流传于高中男生的私房笑话,我本以为它们会随着高中毕业那些善于虚构杜撰黄色笑话同学的消失而退到大脑的最底层。其实不然,这个当时是绝妙有趣而今却觉荒诞可笑的想象联结,又在某个你无法预料到的什么时刻,藉由一个高中女生重新唤起,再度从大脑底层爬起,向你摆手。
我问女孩这是从哪听来的。女孩笑说这是全班都在传的笑话啊!说完后,女孩又吃吃地笑,似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或者是她压根就没想到关于女孩总是被告知的某些不合时代潮流的可笑嘱咐。
女孩不带深层涵意的笑声,让我仿佛又听到以前那几个每天讲黄色笑话同学的讪笑声。同样一个故事,不同的人说来,总带给我不同的联想。
我本来一直以为女孩这种近似于自言自语的无厘头说话模式,只是为了阻断我上课的节奏,就像我以前,每每会在考数学的前一个晚上暗暗祈祷数学老师被车撞、学校发生火灾、台风天不用上课。女孩是我的翻版,只不过我是来暗的,用意志力;女孩却是明着来,用的是行动力。
可是后来,我渐渐发觉到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是真正让我觉得女孩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不是女孩迥异于一般人的语言逻辑,而是一种超乎我理性认知所能解释的──像是女孩对我施展的淘气小诡戏,每次从女孩家回来,不知怎地,我便会在半夜睡着时,昏昧地走进女孩为我精心设计的荒诞诡谲又新鲜有趣的迷离梦境。
当晚,我作了个梦,梦里几十条蚯蚓在讲台前纠结缠绕成一团,我置身考场,考场里只有我一人,考试的科目是数学。从玻璃帷幕外射进的白光让我几乎睁不开眼,我吃力地从亮晃晃的日照中辨出考题:“十二条雌雄同体的蚯蚓杂交会生出几种不同排列组合的蚯蚓?”
我冷汗直冒,依稀知道这只是一场梦,我大可不必走进这荒诞的排列组合迷宫,我只要一咬牙便能从迷宫中穿墙而出,但迷宫里似乎有什么我非得挖出不可的秘密,吸引着我继续走下去。我在“迷宫”和“梦境”间挣扎,猛一抬头,蚯蚓变成女孩,有着蚯蚓身子的女孩在讲台上咧着嘴笑。在逆错的光影下,我觉得全身刺痒难受。
◆
福马林即甲醛的水溶液,甲醛的成分为HCHO;以百分之三十七至四十的比例调合,称为福马林,呈酸性。通常在学校的生物实验室里都可以看见一堆浸泡在瓶子里的各式标本,瓶子里浸泡标本的药水便是福马林,用福马林来浸泡标本的目的是防止腐化。
“解剖学”的老教授指着用福马林泡着不知名蛇类的透明玻璃瓶,解释福马林的成分和效用。这让我联想起小时候家里堆在厨房角落里不知装着啥东西的稀奇古怪的瓶罐瓦瓮。
◆
在女孩上课的那个小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某些好像早已消失、但却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什么时候、什么场合突然看见的老东西,像明星花露水,像弯弯香皂,像黑松玻璃瓶……我常望着这些东西发呆,然后突然想起小时候常看的五灯奖、六灯奖,我甚至不清楚现在还有没有“五灯奖”这个节目。
我想象着在一个浑沌的夜里,自己昏头昏脑地从床上爬起,意识模糊地打开电视,然后那句熟悉的“一个灯、二个灯、三个灯……请登上卫冕者宝座”传来,女孩就坐在卫冕者的宝座上咧嘴眨眼,朝电视外的我招手。
那天回家,我就真的做了那样一个梦,只是登上卫冕者宝座的变成了我。我坐在卫冕者宝座上,然后亮片从空中洒下来,我挥舞着手里的笛子向大家道谢。女孩就坐在我的右手边,她的手里也拿着一根笛子,她是我下一轮的“挑战者”。
有一次,我还看见被丢弃在一旁的《明天会更好》、《古月照今尘》、《像我这样的朋友》等在夜市上三卷一百元的合辑录音带,这些有历史的老东西常让我想起那个逝去的童年昏昧的午后。
小时候,我会趁家里大人都不在的时候,偷溜进终年卧病在床、意识不清、被大家称为活死人的祖父房里,翻箱倒柜找对我而言还不太有具体意义的东西──钱,但我总会在层叠暗影、尘垢蛛网的生锈铁箱和潮湿发霉木柜里翻找到些古钱币、泛黄照片、老旧书信……一些让你仿若寻获珍宝的老旧物品。
后来到祖父房里找钱的原始动机,渐渐被类似到蛮荒丛林里探险的异样情怀取代。是的,那是一次又一次的探险,像少年印地安娜琼斯在法老的墓穴里、在吸血鬼的棺木里。
祖父黝黑昏暗的房里,有一股呛鼻的尿臊腐臭味,好像有什么已死或正在死去的东西,地面是湿凉黑土,赤脚踩在地上有种陷落的感觉,仿佛一使力便可把整个地板给掀起。印象最深的是屋顶石棉瓦的那道裂缝,它会固定在某个时刻射进一道光森灿亮的光影,当灿白光影投射在黝黑昏暗的祖父房里,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道光影里尽是些悬浮粒子,诸如尘埃、菌类、孢子、细菌、病毒之类让你直觉刺刺痒痒的小东西。
而随着日照的迁移,光影会在房里跟着移动。每当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光影会在那一刻洒在祖父的身上,我常有一种祖父整个人泡在福马林里,然后在我背对着他翻箱倒柜时,他突然爬起来抓一下痒、转个身或叹口气之类的奇怪错觉。
总之,只要一到女孩家——不管是狭小充斥着次文化令人作呕饰品的店面、狭长阴暗的甬道,还是小间里不停出现,但记忆里不属于现在这个时空的古怪东西——我便仿若置身于蛮荒丛林,就像小时候在祖父的房里一样,我觉得房子里有什么我无法探知的秘密。
我想这栋房子里充斥的奇异氛围就是我屡屡作梦的原因。
女孩家只有女孩和母亲两人,女孩的母亲似乎是整天窝在店里。用铁架箍在墙上的电视随时都是开着的,没有客人的时候,女孩的母亲就手拿遥控器不停地变换频道。有好几次中午过后,我到女孩家时看见女孩的母亲松垂着手轻握遥控器在店里睡着,而墙上电视仍兀自跳闪播放着。外头曝炽日光和店内黑沉光线的落差,再加上电视画面跳闪的蓝光映在女孩母亲的侧脸,女孩的母亲像是“关怀原住民”之类电视节目里常出现的那种偏远山地部落里,有着七彩黥面整日坐在门口仿若死去的老妪。
我习惯不出声地悄悄侧身闪过她走进甬道,但她每次总会在因我身形瞬时遮覆而致使她脸上阴影闪动时,骤然自昏暗中醒过来说:“萧老师,你来了啊。”然后,又不停地按转手上的摇控器。
印象中,女孩从没同她母亲说过什么话,母女俩和我交谈的过程中也鲜少谈到彼此,我总觉得这对母女有我无法探知的龃龉心结存在。偶尔,我还是可以从她们同我闲聊时露出的线头,探查到她们日常生活的点滴,可是当我想沿着线头找到某些事件的源头时,裂缝便会往两头开去。同一件事,她们母女的讲法南辕北辙,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总之,横陈在她们母女之间的是晦涩难辩的认同断裂,而我是一座无法把她们衔接起来的架空桥梁,因为我不是一个双向的沟通者,我只是聆听和倾诉的对象。
而女孩嘴巴不停张合、爱说话的特质大概是来自女孩父亲的遗传吧!印象中女孩的母亲并不怎么爱说话,至少和她同年纪的欧巴桑(三八型的老妇女)比起来,女孩的母亲算是话少的了。至于女孩的父亲,我一次也没见过,我也没好意思问。
◆
“你们认为泡在福马林里的东西是死的还是活的?”“解剖学”的老教授问。“死的?活的?未知的?有希望的?”
“死的泡进福马林,它就会活了过来;活的泡进福马林,它就会死去。”
“很有趣的说法。就像群居的人会说,人是群居的动物;对未知感到恐惧的人会说,未知是令人感到恐惧的。照你的说法,等你死了以后,把你泡进福马林里,你也会活过来啰!”
“应该是另外一种不同于活着的活吧!”
◆
后来在很多时候,我常常在想女孩错置的虚构内容背后究竟是什么?是女孩有意识地带领着我走进迷雾的世界,还是我自己下意识不由自主地和她跳起双人舞。
有一次,女孩告诉我说,她曾和班上几个男同学把一个抓耙子女生用胶带和童子绳绑着,关进教室后面的杂物柜里。然后她们老师只是“嗯,又没来啊”。天晓得,她们老师把这个抓耙子女生当成另一个老是逃课没来的女生。
女孩说这话时,嘴角泛着笑意。女孩无邪的笑仿佛在向我宣告,这只是个稀松平常的恶作剧罢了,我似笑非笑地应和着,心底却觉得这简直就荒谬到了极点。我觉得被女孩关在杂物柜里的人是我。
祖父房里的味道、家具摆设,甚至连光影的变迁,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仍是一个午后,我又昏头昏脑地走进祖父的房里,不久,伯母突然嫌恶地捏着鼻子走进来,我吓得赶紧躲进一个木制衣橱里,伯母不知是拿了还是放下什么东西就又走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伯母竟然把门板给顺手带上锁住,而我就被关在祖父的房里一整晚上。
当晚,外头灯火通明闹哄哄的,我知道家里的人正心慌地在找我,而祖父房里暗黑寂阒无声,只有我和祖父无言地对望着。我频频望向祖父那没有表情的脸,好似在向祖父求援,而祖父的沉默也似乎在对我说:“我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你难道连几个小时都捱不住吗?”
就这样,我和祖父同外头的人进行了一场意志力的相搏。我不能叫出声,否则我就输了。
其实我比外头的人更为惊慌。我想当他们质问我为什么我会被锁在祖父的房里时,那种尴尬无法应对的处境恐怕才是我最深的恐惧。那一晚,我没有吃东西,可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饿,我只是愣愣地想,祖父有多久没吃东西了,印象里看到伯母或母亲扶起祖父的身子,然后一口一口喂食的画面已经是好久以前了。
那晚我就在糅和了“害怕被遗弃”和“恐惧被发现”的复杂情绪里,躺在祖父的床底下睡着了。后来我是怎么出去的,我竟然没有一点印象。我只清清楚楚地记得我被关在祖父房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
就像被强迫取出的录影带一样,记忆里的画面在此处戛然而止,任凭我再怎么想就是没有从祖父房里脱困或逃离出来的印象。我只记得那之后,父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
“被女孩关在杂物柜里的女生”、“被伯母锁在祖父房里的我”,我突然觉得我和女孩只是在不同的时空里,被迫穿上同样的戏服,然后搬演一出主客易位的同一出戏。当女孩啦哩啦杂地论述那个被关在杂物柜里的女生是如何如何云云时,我仿佛看见那个心慌想要发声求救却又哑然恐惧着的我。那是个已经剥蚀模糊不怎么清楚的年岁,但是在祖父房里被关了一晚的记忆却深深地刻划在我的脑海。
不知道是同我混熟了,还是意识到我是个好听众,女孩讲述的话题越来越辛辣。当我开始怀疑女孩说的都是些她自己杜撰的谎话时,是在第二次“屙屎事件”后。
有一次,女孩又喜滋滋地天南地北胡乱说些学校的趣闻琐事,突然说到有一回她们班上一个叫沈再勇的男同学,竟然趁半夜的时候,撬开导师休息室的门,然后跳到他们导师的办公桌上屙屎。隔天,他们导师一整天满脸大便色。
看着她无邪忘我地又说又笑,我觉得背脊发凉,因为这个故事她早已说过,但上次屙屎的主角是“颜忠敬”,和我们训导主任同名同姓,我不可能会记错。
自从第二次“屙屎事件”的主角换成沈再勇之后,女孩以前讲过的故事便不停回笼重复搬演,但是故事主角的名字都变了,颜忠敬、沈再勇、陈建宏……
我想女孩沉溺在不断繁衍、复制、虚构的欢愉里,即使有某部分是真实的,也经过她的想象力渲染和修饰。
几天后,女孩又告诉我,她们把班上另一个女生也给关进教室后面的杂物柜里,理由是不顺眼。说实在的,我已经有点厌烦女孩的胡乱想象,但女孩总是一副“我说的都是真的哟”的纯真模样,这使得我陷入极大的矛盾之中,就像我无法相信从三岁小孩口中会撒下什么弥天大谎一样。
同一天,女孩的母亲却告诉我,女孩有一次回家时身上尽是些绳索的绑痕。女孩的母亲怀疑女孩在学校受到什么欺负。我打了个冷颤,我有不好的预感。
但我真正确定女孩脑子有问题是在第一次期中考后,女孩的数学成绩是零分,我沮丧无法置信地拿起女孩的考卷。考卷上,女孩竟然把所有“排列组合”的答案通通写成“一”种,用常识想也知道不可能只有一种。但女孩却笑嘻嘻地说真理只有一个,所以任何排列组合也只有一种。
听女孩这么讲,我突然想起高中每天批评时事、对每件事都有意见的数学老师讲过的话──“排列组合”根本不合逻辑,男男女女一定会依彼此熟识程度和姐妹淘间的小心眼嫉妒排挤,而简化成只有一种。但这是个不合逻辑的世界,所以尽管正确答案只有“一”种,我们也必须说谎。说谎,懂吧!那是和整个荒谬世界对抗的最好方法。
我突然觉得女孩从头到尾都在说谎,她也在和这个荒谬世界对抗。
◆
标本制作程序
1.处死。
2.清除内脏。
3.刷洗尸骸。
4.将尸骸泡入5%中性福马林内两至三天。
5.将泡过福马林的尸骸取出,泡入大量清水中一天。
……
◆
对于女孩上课时不停地插话、转移话题,甚至虚构杜撰一些不存在的人和事物,我总是饶有兴味地点头虚应聆听,我猜女孩有太多的话不能讲出来,不管是对学校同学或女孩母亲都一样。只有我,我是女孩寂寞灵魂的出口。
只是这种看似永无止尽的“诉说与聆听”,终会因为某个施力点的不平衡而被狠狠地截破。
“连续生了五个男婴之后,请问下一胎生女婴的机率是多少?答案是二分之一。”
“如果已经连续生了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男婴呢?”
“还是二分之一。”
“怎么可能?你骗人。对了,老师我跟你说喔,我们班的宋仁杰和隔壁班的沈云慧去医院夹娃娃,当场被沈云慧她妈妈给逮个正着。事情越闹越大,最后,你知道怎么了吗?”
女孩又把话题岔开,另辟战场。我实在很佩服她去哪里找来这么多不存在的人名、地点、事件(也许存在,但一定经过女孩重新排列组合)来同我闲扯。这很好玩吗?还是我像个傻瓜?
“原来,沈云慧肚子里的小孩是我们训导主任的,呵呵呵……还有更夸张的,我们训导主任竟然就是沈云慧她妈妈的‘好朋友,嘻嘻嘻……老师,你知道什么叫‘好朋友吧?对了,那夹娃娃,你听的懂吗?你是医科的应该听得懂吧。”
后来渐渐地,我并不在意女孩说些什么,尤其是在听到女孩母亲说女孩身上有绑痕后,我便不自主地每每把女孩故事里的受害者自动换成女孩;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出神地望着水晶球──深不见底的甬道里,女孩变形虫似地不断蠕动爬行。
“对了,老师,你有没有听过‘蚯蚓是阴阳人的故事,这是我爸告诉我的,哪天介绍我爸给你认识,我爸也是医生喔……”
“你爸不是死了吗?”我脱口而出。
后来我回想起来,这是一句看似软弱但其实却是深具毁灭性的话。
前几天,女孩的母亲才告诉过我,女孩的父亲老早就死了,现在怎么可能又好好地活着?还有,“蚯蚓是阴阳人”的故事不是他们班流传的笑话吗?现在又变成她爸讲的。
“谁告诉你我爸死了,是我妈对不对。她骗人,我爸没有死。”女孩像是被最亲密的伙伴出卖一样,露出不能置信的绝望表情凝视着我。
“可是你妈妈说……”
这时,不知是从哪个方位透射进来的细碎光影正洒在我们上课的书桌上。
“我爸爸还活着,他就在我们家的顶楼。”女孩呐呐地说。“他被我妈妈泡在福马林里,有一天他会再活过来的。”
泡在福马林里???我脑中一片空白,我看不到我脸上的表情。
“我没有骗你,不信我带你去看。”女孩像是被冤枉的小孩,急着解释什么。
这时,细碎光影缓缓地爬上女孩的侧脸,我突然想起祖父死去那天,我第一次壮起胆要把手伸进祖父的口袋里,看有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宝贝,那时从屋顶射进的那道光影正投射在祖父的脸上,我忍住呛鼻的尿臊腐败味,掩住鼻别过头去,把手伸进祖父的口袋里——那个被大家说成“活死人”的祖父口袋里——我瞥见祖父的脚底有蛆钻出,不知怎么的,一股一定得确定祖父口袋里鼓胀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冲动,掩盖了一切,我从祖父口袋里掏出了几张模糊难辨的发黄证件。
突然,祖父伸出他那枯瘦的手抓住了我,他的脸部表情扭曲狰狞,似乎是极端痛苦的模样,我吓得抛下那些从祖父口袋里掏出的发黄证件,用力扯掉祖父的手,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我不知道这一切都看在父亲眼里。
到了夜里,我还不敢回家,我躲在我家后面一个当时被我们称之为“防空洞”的大水泥函管里。后来,我听到类似锣鼓、唢呐的声响从我家传来,才想到要回家。回到家时,我才发现祖父已经被抬出房间──祖父死了。
在祖父下葬后不久的某一天,父亲突然把我叫进他的房里,然后关起门来,拿出藤条朝我身上猛抽,边抽还边啜泣。父亲没有说明打我的原因,我也没有如往常一样,扯开嗓门大声呼救,我沉默地接受父亲的悲愤。我望着摆在父亲书桌上,从祖父口袋里掏出的发黄证件,我知道父亲将和我一辈子守住这个秘密。
只是那时的我,仍在心底低回着”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害死爷爷的”(即使我知道那的确是我,某种程度上的我)。
我静默无言地望着洒满细碎光影的女孩阴郁的脸庞。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潜进祖父房里探险的少年印地安娜琼斯。我突然又有种祖父在光森灿亮的福马林里爬起来抓痒、搔背或叹气的幻觉。
“我爸还活着。真的,我没有骗你,不信我带你去看。”
女孩的话“我爸还活着”不停地在我耳旁呜嗡呜嗡作响,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祖父被日照光影笼照,仿若整个人泡在福马林里的画面。原来“希望”和“记忆”都是福马林,女孩的爸爸活在女孩的希望里,祖父则活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瞬间,不知道是不是光影造成的恍惚效果,水晶球里不断蠕动爬行想要穿越隧道的变形虫,真的消失不见了,像被吞进腔肠动物的消化腔里,只剩下空荡荡似乎不断长出也不断萎缩的甬道,不停地晃荡晃荡着。
◆
生物实验室里,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在解剖青鞋,准备把它摆进福马林里制成标本,我却想着女孩说她爸爸被浸泡在福马林里的事。
“你就是萧国辉吗?来,告诉我水晶球为什么是活的?还有什么是一种不同于活着的活呢?”“解剖学”的老教授笑着拍拍我的肩头说。
许荣哲,曾任《联合文学》杂志主编,现任台湾最有活力的文学社团“耕莘青年写作会”文艺总监、四也出版公司总编辑、台湾文学创作者协会理事长、走电人电影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著有短篇小说集《迷藏》、长篇小说《寓言》、《漂泊的湖》、网络小说《吉普车少年的网交生活》、电影剧本《七月一号诞生》、《单车上路》、《孔雀牢笼》等。曾获中国时报、联合报文学奖,新闻局优良剧本奖等十余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