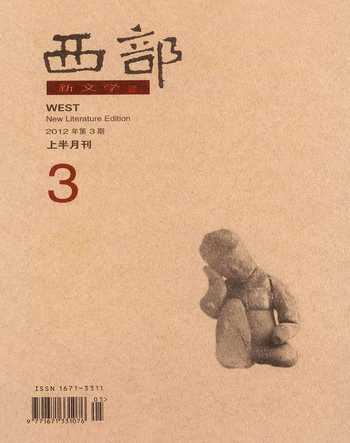他们说神
我觉得要理解台湾小说的多样性,不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是很难了解驱使小说脱离旧貌的策动力。我有幸在台北呆了两个月,在生活和言谈方面感受小说家们的性情、抱负,在口碑和批评家开辟的评价通道上,了解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多样化。我想促变的原因是,严肃小说一旦脱离动辄上万的印数束缚,小说家们就获得了肆无忌惮的自由,这与现代诗在大陆的发展状况尤为相像。同时台湾的评奖体系由于全部采用双向匿名(评委不知作者是谁,作者不知评委是谁),大大降低了成名作家逐奖的意愿,使得文学奖成了作家初登文坛的捷径,而胜出的根本在于开辟新路或写出新意,这恰恰是后进作家乐意发力的。与内地成名作家蜂群一般挤占文学奖这个通道相反,本辑收录的吴钧尧、许荣哲、凌明玉、黄克全四位台湾小说家,初登文坛时曾获奖无数,而现在,他们已非文学奖的常客,已是联合报副刊、中国时报副刊、《印刻文学》等重要文学园地的约稿作家。我想这个机制已能道出台湾小说多样化的秘密,即在联合报副刊等重要文学园地发表的难度,远高于获奖的难度,这使得成名作家与年轻作家各执一端,互不挤占对方的通道,文学奖和文学园地分工明确,一个发掘新人、发现新路,一个向大众推广风格已就的成名作家。 ——黄梵
他们说,我是神。
青屿村,位金门东北角天摩山下。天摩山一边向海,遥望山后、田埔,另边远眺太武山,以及官澳、西园、吴坑等村。面海的山麓,一尊风狮爷陡然醒觉。才醒着,听着风呼号,以及人声细细密密。人声,风吹不散,且跟风合而为一,风一来,声音渗透,慢慢地,比风还嘈杂、还殷切。我相信,我因此醒转;而且,我马上知道我是风狮爷,我也是神。
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陈龙收服郑克塽金门驻军,派任总兵官。金门风大影响生计,东半岛处风头,影响剧烈。陈龙问城隍,设仪式,布香案,得设风狮爷于青屿。陈龙委雕刻师傅,就一块经风化却仍坚实的花岗石碑雕凿。石上留有日月纹图,雕刻师傅料是古石,雕刻时,留日在额前、月在腹下,图样宛如雄狮鬈鬃。风狮爷咧嘴睁眼,双爪凝力,仿佛扑噬飞跃,架上三尺高的平台,威风凛凛。村人于风狮爷颈项围上红袍,风起,红袍如千百只蜻蜓同声振翅,风过,则如锅中热油突然爆开。
风狮爷座前,村人堆砌红砖,便于伏跪祈求,前头设一只香炉。
风吹沙掩,红砖几乎淹没了,炉中香已歪斜。平台上看得远,前见草屿湾,后见后山与料罗湾,水头村再过去是烈屿,再过去是厦门与同安。不知怎么,我竟对眼前与背后的地理了若指掌,若愿意,竟也记得一些历史。
对哪,我是神,这是神该有的神通。
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事物不甚明了,譬如,我竟无庙可住?我知道神该供于庙,香烛立左右,忠勇事迹绘制在两边的墙头,神安稳坐在案前,闻香火、听祈求。我看看左近,寸草不生,黄沙滚飞,甚至看不到人们从哪一条路走向我。
思索时,见一人从下头的村子赤脚走来。十二三岁的少年,左肩荷锄,扁担右肩扛,扁担头绑着两个麻袋。他步伐歪斜,脚印左右错落,踏上山,风更大,索性拖着锄头跟扁担走。沙地软,他拖曳的痕迹跟脚印,像画一般。他穿棉袄走近,扶着我脚边平台喘气,喘了一阵,朝我合十致意,一屁股坐在座前的红砖上。沙地上,一对脚印散乱,似碎月点缀,两道拖痕歪曲,宛如长河旖旎。不一会儿,风沙飞扬,河与月俱都消弭。
少年玩性起,拎扁担走下,在沙地乱画,这回仿真太武山势,山头雄浑,少年多做附会,太武山后,再画上一座、两座、三座太武山,退回我座前,欣喜望看沙地上绵亘山势。风呼呼来,沙阵阵落,黄沙如大雾,一一掩盖。我看得哈哈大笑,张开的嘴巴喝哧喝哧响,少年猛回头朝我看,我还是喝哧喝哧笑,少年跳上平台,搂着我的颈大喊一声后,赶紧跳下去,迅速拿起扁担跟锄头,往面海的山麓走。
村落有人听见少年吼叫,走出看,少年已匆匆走远,只剩我一个人,不,一个神,立在山头哈哈笑。
他们说听见风狮爷——也就是我——大口吃风的声音。村人提到有一回,他在庭院缝补渔网,渔网这头套挂廊下铁钉,另一头伸展庭院,抖开渔网,穿好白色线,搬板凳,在阳光下摊开,找寻漏破,准备缝;忽闻一阵喝哧,一声、两声,响了起来。本以为听错不理会,不料,喝哧声再响,他禁不住好奇,马上立身,针跟渔网从膝盖掉落,他不管,冲出大门,看见风狮爷在吃风。
有人问,风无形无影,怎知道风狮爷吃风?村人说,他跑出几步听,辨明喝哧声来自风狮爷方位,又跑几步,声音不断,他更确定了。上坡,沙沉,他跟随声音一步一步走,喝哧声终于变小,走到风狮爷座前,这才没了声音。村人听了,啧啧称奇,都说风狮爷显灵。少年也在人群中听。听得向往,末了,警觉到那是他开的玩笑,忍不住笑出来。少年一笑,头就遭殃,背后一个中年人往他头上一敲,少年回头看,畏惧地喊了一声爹。青屿乡居民多姓张,张春明揪着少年的耳朵,把他拎出人群,用力拧了几下才松手,骂他地瓜没栽好,跑到这儿干吗?
村人都围听风狮爷显灵,见着春明带走少年,同情地说,张辉白这下要倒霉了。张春明暴躁易怒,拧耳朵算小事,有一回还持扁担,追打儿子。那是秋天一个午后,张辉白脸肿唇破,沿着村落跑。张春明追着,大叱,你搁走,你搁走!妇女在屋檐下洗衣,看着张辉白小鬼般的一张脸,既苍白又诡艳;张春明怒睁双眼,如牛头马面破地狱而出,看到这一幕的妇女后来说,好像看见大鬼追着小鬼。
小鬼噤声跑在前,有几次因换气或惊恐张开嘴巴,妇人说,张辉白张嘴吐了好大一口血;大鬼挥扁担跑在后头,大跑几步,扁担过肩用力挥,敲得大地都在震动。不只一个妇女,而是很多个妇女都吓坏了,当张辉白第二回跑过她们,她们瞧着鬼来了,大喊救命、救命。午睡的丈夫或公公,本在妻子或媳妇一上一下的刷衣节奏中沉沉睡去,忽然节奏断,喊声起,下床一看,正看着屡追不上的张春明恼羞成怒,把扁担当绳索耍,朝前丢。扁担如陀螺快转,掷中张辉白,张辉白倒地不起,张春明从后头追上,村人愣了一下,急忙快步追上去。
张辉白被父亲逮个正着,张春明也被村人齐齐按住。事隔几天,妇人看见张辉白就说,他的命是捡来的。
张春明伯公看不下去,奉劝张春明,你一家老少都死了,剩儿子相依为命,你老了谁来养你,难道不是你儿子?
张春明双手捂脸,默不作声。伯公说一个人一款命,辉白也没有做错事,不能再这样打他。张春明哽咽。
六年前一个傍晚,张春明收成地瓜,以牛车装好,一家人亦步亦趋闲谈回家。六岁的张辉白尿急,跳下车,小跑到前头,脱裤撒尿。张爷喊说,小白聪明,故意到前头,撒尿完牛车经过,刚好可以跑上车。张辉白没想到这许多,他只是怕一个人落在后头。张辉白在右侧撒尿,牛车向右靠近。只这一点点偏斜,却使张春明家破人亡。
张辉白尿完穿裤,转身,正见夕阳沉,晚霞满天,他待上牛车,牛竟踏空,右肢深陷黄尘大地。牛挣扎,踏空的洞越来越大,张春明坐在牛车前,被牛的身体挡着,看不见踏空的洞,扬声吆喝,挥竹竿拍打牛的屁股。倏然,牛跟车、张春明夫妻以及父母,囫囵跌落。张辉白吓得大哭,村人赶到,看见道路凭空塌一个大洞,惊惶莫名,再探看,却见张春明一家人跌作一堆,身上堆满尘土跟地瓜,不知死活!村人放绳索救人。
张春明捂脸。不——,这不是我的手,这是谁的手,压在我脸上?我的手被压着了,被谁压着了?指缝间,微光照,这是黄昏,将见炊烟袅袅吹送的黄昏?张春明艰难地移动脖子,脸上的手无力滑落,张春明察觉自己躺在洞穴内,上头是一个圆洞窟,有人拉绳索跳下来,移开压在他身上的人。
村人兴奋大喊,春明没死!村人清走他身上的沙石、瓦片跟地瓜。
父亲、母亲跟妻子,躺在他左右。他们都死了。
牛,断腿断颈,还留一口气喘着。村人拿刀,往它喉咙一划。村人搬走死者,拉了好几十车砂石,就地埋牛,填平凹洞。张春明一家,只张辉白没跌落黄沙堆掩的老宅,张春明却欲将儿子跟牛埋在一块儿。
伯公说,辉白没做错什么,哪能这样对待他?
张春明捂住脸,双掌又湿又咸。
清初,郑成功伐树造船败退荷兰,岛上树,几乎砍伐殆尽;隔年,荷兰人报复郑成功,联同清廷攻占金厦,焚烧掳掠。清廷为杜绝沿海居民资助郑氏,迁居民于内地,金门二十年无人居住,风沙无眼,埋了屋子。青屿居民赖此径往来农务,多年无事,偏就在六年前,张春明的牛,踏破了沙内的屋瓦。
一连多天,村人都在说风狮爷显灵,喝哧喝哧大口吃风。张辉白听着时,不敢再吃吃偷笑,村人谈得认真,若知是他的恶作剧,若父亲再追打他,可没人能救他命。再者,村人提到晚上如厕,听到有人叹息,张辉白想,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禁挨近身子听。
村人阿雄说,临睡前,却觉得肚胀,想忍到天亮,一坨屎像田里花生发芽,就要移开土方,伸展而出,急忙撕几张手纸,跑到庙前粪坑。有人插话说,这款情形,阿雄你还能跑?阿雄修正,的确不是跑,当时连走路都有困难,夹紧鸡鸡跟屁眼,一扭一扭地走。众人闻言哈哈大笑。
阿雄往粪坑一蹲,响了一阵屁,再哗啦啦屙几条屎,就在这个时候,紧邻的粪坑有人叹气。阿雄连叫几声,是阿旺啊、阿火啊,还是春明啊?结果都没人应话。这时候风狮爷显灵,喝哧喝哧,阿雄好奇,拉裤头,人半蹲,看见不远前风狮爷身上发出阵阵冷光。村人问,怎知道光是冷的,而不是温暖的?阿雄说,当时浑身发抖,寒毛一根一根立,你说这光是冷还是暖?村人觉得有理,频点头。粪坑隔壁有人,想跟他说话壮胆,头探过粪坑围墙,往内看,却只看见一口粪池,哪里有人?阿雄急忙擦屁股,隔壁叹息又响,他拉好裤头,头也不敢回地跑了。阿雄说,这回,他肯定是用跑的。
有人忧虑说,不会是海贼吧?
春夏之间,海贼趁西南季风,从广东而上,到秋冬,再趁西北风从浙江来洗劫。金门四季,常无宁日。清廷底定金厦,初设总兵官,复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设通判,又四年置县丞,沿海军旅互相支持,加以处乾隆盛世,贼匪少。清嘉庆以后,国势衰,贼匪渐多。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海寇朱溃曾犯,厦门拨兵支持,终以退敌,村人常登上天摩山打探战情,一见闪失,马上撤村躲避。村人犹记彼时,命若紧弦,幼童感知气氛异样,便无由大哭。
正当村人陷入贼匪来袭焦虑时,有人说若是盗匪,不一刀杀了阿雄?有人附和干笑,多数人却眉头皱、搔耳摸鼻,若贼匪来,能躲哪儿?一伙人本兴高采烈谈风狮爷显灵,却疑心盗贼来,忧心忡忡。
张辉白没料到情势演变,更是惊慌,噤口不语。
三月,西南风起,青屿一区风势略微,将播种,张辉白持锄除草翻土。新雨后,天边阴,地头潮,走沙少,阵阵沁寒。才近午,张辉白已料妥农事,从沿海的田埔爬坡上天摩山。风不大,红披巾潮湿,如一只蚊帐罩着风狮爷。座前红砖吃水,无比红艳,张辉白想起村里娶嫁,他跟着孩童唱着,“新娘水当当,裤底破一坑……”近几年长大,不再跟着唱,他抖着风狮爷红披巾,想起童谣,边抖边唱。抖一阵子,披巾上的红,由暗而亮,放下后,不再死粘在风狮爷塑像上。
张辉白后来说,只是那么一个动念,他想看看风狮爷法身是否湿了,扯开披风,矮身歪头瞧去,却看见披风里躲着人。
“不,不——我根本不晓得那是不是人!我抬头看他,他低头看我,我愣了一会儿,大叫一声放下披巾。披巾干了,随风起扬,哪来的人?”张辉白说。
张辉白最早告诉他的玩伴阿清,阿清也这么问,哪有人没事看风狮爷的裤底?
过了没几天,陆续有人问张辉白,干吗没事看风狮爷裤底?
又过几天,张春明也知道了这事,瞪着他,气呼呼。张春明走到柴房拿扁担,走几步、又走几步,扔了扁担回客厅,拿一把竹尺,举高,朝张辉白的头打。竹尺划过张辉白耳边,如鬼怪吹哨,张辉白内心一惊,竹尺最后却拍在屁股上。张辉白挨打,知道父亲避重就轻,内心高兴,隔天看见阿清,却还是内心有气,追着阿清,大骂都是他乱说话。
两个人假打真闹,追追跑跑,来到天摩山左肩,村人很少来的竹林。天摩山几乎光秃,却只这处长着一排低矮竹林。村人说,那儿地阴,没事少去。两人嘻闹到此,忘了父长告诫,张辉白大胆欺近,竹林下,一个石砌坟墓,阴森森、哀惨惨。张辉白记得母亲说过,小时候扫墓,每经过那儿一次,他就哭一回。张辉白不太记得母亲生前说过的话,关于竹林与坟的话,却记得真切。两人没读多少书,却还识得墓碑上记着“张敏之墓”。
两人朝石墓丢石子,一颗、两颗。阿清说坟墓完全没动静。张辉白打了一下他的头,要什么动静,难道要死人爬出坟墓吗?两人哈哈大笑,见墓旁竹子粗壮,索性回家拿斧头,砍了两枝,当剑耍。风走竹林摇,叶细如笛,阵阵急响。两人收住手上竹竿,仔细盯着竹林闪闪飘摇。上午,日头海面升,竹林阴一阵、阳一片,光线交错、叠乱,阿清说,你可看见了,竹林里好多人走来走去呢。张辉白骂道,你胡说。望着光影闪动的竹林,忽然听到悠悠几声叹息。
他们说,我是神。
他们说,我们是神。可是,我们却连一头狮子都不是。逢年过节,村人提竹编的篮子,过祖厝与家庙,爬陡峻,到一立起的风狮爷座前,焚香祭祀,喃喃祈求。他们说,立雄狮,镇风煞,可是,风沙连年刮,小径年年改,唯一不变的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一头石砌的狮子系红披巾、上鲜艳的漆。我们并不忌妒一头狮子,因为我们是神,而且,曾经是人。
我们只是孤独。
孤独啊。
身为神,我们也惊讶,神会孤独,何况我们是三个人。于是,我的大弟,让他自己钻进风狮爷的红披巾,吓了村童一跳;我大声斥责他不久,却无意中长叹,让半夜如厕的人,如兔奔走。我们感到哀伤,看村人拉裤急走模样,又不禁掩嘴而笑。
我笑,大弟跟着笑,小弟围过来,问我们笑什么。我说你是神哪,自己掐指一算,不就知道了。他眨眨眼,明白所以,跟着笑。我们好奇被吓着的村民会如何传述这档事,挤近围观的村人跟着听。我们竟然听得津津有味,浑然忘了我们不再是人。我料想,是故事的魔力换转身份,我们回想住在青屿村的日子。那些日子,虽然多忧多虑,回想中,却滋味无穷。
我问大弟,记得当年的青屿吗?他说,他其实是记得的,真的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念头一转,百年前的村头景观一一浮现。青屿村当年,绿草如茵,山羊有黑有白,沿天摩山啃草,村外田,顺着丘壑起伏,村人挖凿一方一方池塘,养鱼苗、兼灌溉。
太武山下,山林一丛一丛绿。绿的是森林,空出的是村落,傍晚时,白色炊烟飘过绿色的山林,白、绿交织,仿佛翠笋,景致完全不同今日。
张敏,发什么呆,赶快回家吃饭去!我听见叔叔的声音,吓一大跳,我看见久违的叔叔,再看看少年之身的自己,知道自己被叙述的故事召唤了,回到百年前的青屿。我赶紧回家,看见父母、爷爷跟奶奶,一阵欣喜,热泪直流。我悄悄转过身,不让他们知道我已不是他们的儿子张敏,而是一个神。
两个弟弟随我悄悄进入故事,大弟朝我会心一笑,小弟咧嘴吐舌,我知道,我们都太想念亲人了。
隔天,我们兄弟三人扛锄头锄草,仿佛知道这只是一种角色,锄起草来,格外轻松。我数落小弟,说他以前老爱赖床,锄头得丢到床上给他,才气嘟嘟起床。让我惊讶的是,小弟听不懂我的话,还顶嘴说什么以前,现在不正锄草吗?大弟也觉得奇怪,以为小弟顽皮,不以为然。
我十三岁以后,就不再参与农务,无法再挥锄入田,扳开新土,呼吸泥土的沁凉气味。我还怕毛毛虫,父亲什么都不怕,拎起一条条又白又软的虫,摔一旁,再踩死。父亲的赤脚沾满虫尸,我倒抽一口气。我这一生,后来都在宫廷过,吃喝有人伺候,记得有一回,花园飞来一只喜鹊,呀呀叫两声,嘴里掉下一截东西。小太监尖声大叫,我走近一看,是条嚼得半烂的虫,余一半,还在地上挣。我想起父亲神勇,终不敢着鞋踩,拾一根棍子,戮死虫,省得它痛苦。底下众人,一半真诚一半马屁,都说大人神勇。
我趁父亲走远,跟兄弟俩提到这节往事,小弟狐疑不解,大弟想了许久,最终说,是啊,那件事情好玩得很。而衔虫入宫的,是一只喜鹊。这种鸟处处有,眼下就有一只,嘎嘎嘎,在左近的相思林上叫。我又说,记得吗?后来宫中树林,筑了好大一个喜鹊巢。小太监们不知道真没见过,还是故意装胡涂,拉着小弟去。小弟去,一眼就认出来了。
小弟闻言,拉我手,下一段坡道,往上头一指说,你瞧,喜鹊窝在这儿,却不是什么宫廷啊、太监的。
我一听,大感惊讶,来不及询问大弟这是怎么一回事,即被吵闹声吸引。
我们扛锄头,跑近看,是村人跟叔叔争执。叔叔说,海寇如狼,你退一步,他进两步。看见天摩山没有?叔叔指着不远前的山,我们若退,早晚会被逼得一个一个跳崖。
日前,海寇遣使,入金门东边各村,声明自动缴金,若敢抗拒,刀剑无眼。叔叔说,怎能与海寇妥协?主张连结各村,组织村勇,强化海防。主和、主战,意见不一,叔叔说跟海盗议和,不怕后世子孙抬不起头?叔叔与主战的村民团结抗敌,有一回埋伏在天摩山,海寇数十人深入村头,叔叔率众,切断海寇退路,十来个人围住几人厮杀,村民虽有受伤,海寇却伤亡惨重。
后来,张敏细数前尘,感叹说,正是成也海寇、败也海寇,叔叔声誉隆,与村民结怨,海寇买通叔叔仇家,诬陷叔叔串通海寇,走私牟利。海寇假造文书与金银,藏于家中,官兵得情报搜索,果得通敌证据。张敏想到此悲从中来,一日晚餐后,跪倒双亲足下,一家人都不知所以。张敏拉两个弟弟一起跪,他知道,就在明天,双亲与叔叔,将被判处充军,天涯地角,从此陌路。他跟弟弟张庆、张本,遭阉割,送入宫,当太监。
弟弟却白了我一眼,说,大哥近日怪,常胡言乱语。
我急得大喊,这是一出戏,两个弟弟已是神,莫入戏太深哪。我扳着张庆的肩胛说,醒来哪,难道明天,你要再尝一次宫刑,再喊哑喉咙?两个弟弟没有搭理我。我忽然想起百年后、青屿乡,我与大弟装鬼吓人。我们曾经是人,尽管为神,却是孤独啊。两个弟弟不愿孤独,故情愿入前世,再尝人间滋味。
日后,张敏专伺东宫,太子继位为明宪宗后,晋升司礼太监。张敏恭谨干练,不倚权胡为,百官敬畏。后宫争端多,贵妃为争宠,欲溺毙纪妃所生之子,张敏以幼猫充当皇子,溺死后花园,实则秘密抚养皇子。宪宗登基多年,虽妻妾成群,却苦无子嗣,感叹东宫虚悬。张敏说出往事,宪宗大喜,宠信日加。太子即位,为明孝宗,年纪幼,大小事由张敏定夺。
我,位极人臣,何妨陪两位弟弟做戏,再当一次人?
清风满月,虫鸣青屿,我知道过了今晚或者明日,我将蒙昧了神的灵光,眼茫茫,神荒荒,随尘世演义。日有阴阳、月有圆缺,太监是哪一种气候?就算我身为人,也还是孤独啊。
孤独是人,孤独是神。我只能选择当一个人而孤独,或者当一个神而孤独。
我选择当后者。但是,我该怎么回去呢?
我起身,套件上衣往外走。月光亮,人影长,月在西,不久,天就要亮了。我胡乱走,穿山林,过溪流,流水映光,洁亮如洗。我再走、再走,是山猫还是喜鹊被我惊动,嘎巴响起,或者山林有鬼,正瞵瞵看我?神,岂有惧鬼之理?我再走,也许躲起来,我就能免去这一个循环的章节。我走下一个洼地,这儿草多树少。咦,我来这儿做什么?我感觉到正有物事快速流泻,是什么呢?我再想起了百年后、青屿乡,百年后,我又怎么了呢?我知道我正遗漏一个重大线索,天亮后,我就要奔赴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那是什么呢?
我悲伏草地,哀伤痛哭,胡乱翻滚,草丛中竟有一个坚硬的东西,撞得我头疼。拨开看,却是一个石碑。尽管月光亮,我却不识得上头的字,只见日、月纹图。正纳闷时,却见它化作一头狮子,朝我嘶吼。
我醒了。身旁两个弟弟躺着,浑身冷汗,我急忙摇醒,他们愣了好一会儿,才回神说,梦见小时候的事,当时的一切是多么美好,却又多么凶残。
我们惨叹说,幸好是一个梦。
我们抬头——,不为什么,而是直觉地该抬起头,正见风狮爷看着我们。我没看错,那是一头朝我们微笑的狮子。
清明,是我们最悲伤的节日。你问我为什么?你何必问,我是神哪。
我讶异我的口气如此恶劣。察觉到时,觉得不好意思。风狮爷站前头,面无表情。我急着找话题,忙说,原来我以前就见过你啊。你身上的日月纹图,让我想起前世或者梦境中曾看过的一模一样的图案。风狮爷还是不搭理。清明雨纷纷,斜斜落,像一把大扫帚,急急刷。我们四个神,遗立荒野,睁着眼,什么都看见,却也什么都看不到。
一大早,村落炊烟升,村人煮饭,炒各种菜,料理包春卷菜肴。不多时,村人将如以往,鱼贯经过。村人过世或葬于天摩山下,或葬于自家田埂间,或葬得更远。葬田间者,每一天瞧子孙耕作;葬野丘的,子孙在清明或忌日祭祀,风沙抹逝,常找不到坟头。
张春明父子挑扁担、锄头出村。父母跟妻的坟头与路面齐,幸立石碑,得以辨识。张春明掘了够深的洞,与儿子一起扶正石碑,再谨慎挥锄掘土,掩上坟墓,不多时,黄沙上,再是三个坟头。父亲每掩好一个坟,张辉白就拿砖头用力压实。祖父母的坟距离母亲坟头三十步,张春明跟儿子说,别忘记,三十步。张辉白点头。到定点,张春明再掘土方,起坟头,挂墓纸,燃香。
张辉白只在祭祀时掀篮子,其余,则用棉布包覆。新雨后,沙吃水,风起不兴,若平时,得专人看顾,见风起迅速掩篮,免得菜肴入沙,折耗一锅好菜。
祭祀后,两人挑扁担、扛锄头,往村头走,换菜肴,拜庙,拜风狮爷。时近午,张辉白起火热菜,撕妥春卷皮,一层层铺好,向张春明喊一声后,熟稔地舀菜,洒花生粉,包春卷吃。
竹林下,石棺前,张敏、张庆、张本三兄弟,看村人三三两两,望白云层层叠叠,听海涛撞撞裂裂。直到死,直到成为神,还时时刻刻被提醒,他们曾为人,却又不像人。
我看着悬挂双腿间,雕刻师附会雕饰的巨大卵葩,长叹一声,转过身去,不再望着那悲伤的三个人、三个神,或者三个鬼。
说不定,不仅青屿村,包括山后、田埔、官澳、西园等村,都听到张辉白睡梦中惊喊。一根好大的棍子,朝我敲。绿色棍子。该不会,正是我跟阿清从竹林砍下的那一支?阿爸挥扁担打我时,我都没这么怕。棍子,有形的棍子打上头,却模模糊糊,变成一个巨大的袋口,笼罩我。我依稀跌入被牛踏坑的古瓦房。我这么想,就真的滑将下去。跌,跌,再跌,我不禁骂,再跌,我就死定了。等我吓醒,已在洞窟内。只我一个人在洞窟内。忽然,天下雨,而且是急雨,不一会儿,水淹过膝,再不久水淹及胸。这时,洞口忽现三条人影,我伸手,等他们救。
我跟阿清说这个梦,他说,都长这么大,还做噩梦,羞羞脸。
不知道阿清为何跟旁人提起我的梦。连阿雄都知道,他鬼祟地拉我到一边说,我也做过类似的梦,也见一支大棍挥来,我跌落、再跌落。我运气不好,没跌到洞窟,却是跌到粪坑,我喊救命,明明看见阿旺、阿火,还有你阿爸春明,都来粪坑屙屎,却没一个人理我。屎条、屎花一起打在我脸上,好恶心、好恐怖。
我稍后知道,阿清跟别人提我的梦,是因为阿清梦到一个棍子打来,他跌落天摩山。明明跌落山底,正庆幸毫发无伤时,尽头忽做起点,再往下跌。
伯公脸色凝重,在庙口提他的梦时,村人已交换彼此的梦,都啧啧称奇。有人跌进尿壶,不停看见老人套进萎缩的话儿撒尿;有人滑落蛇身,蛇蜷曲,成一个圆,不停绕一条蛇打滑。伯公说,他掉进一只香炉,伯公指着庙里香案说,就是那只香炉,他想爬起,却被下一炷香卡着,换位置,又是另一炷香拦路。
我挨近听,顺着伯公的手往上看,看到香炉,也看见后头立着神主牌,写着张公敏几个字。我想起竹林下、石碑上,也写有这几个字。我不敢问父亲。问阿雄、问阿清,都说不知道,只好问伯公,他说那是明朝人,官做得很大,有一次皇帝生病,张敏以太监身份代行皇帝职务,民间传说,张敏是“七日皇上”。
我一听大惊,张敏的后代是谁?伯公说,张敏三兄弟都当太监,时隔两百余年,侄孙辈是谁,都没人知。
村头噩梦,如同风狮爷喝哧喝哧吃风,话头过,村人渐少提起。
我身子拉长,体魄渐壮,既是少年,又不是少年,村人说,我正转大人。十一月,风吹西北,黄沙像布幕,扯掉一层又见另一层,我掩口鼻,一步步走上缓坡。风狮爷披巾被风扯破,风吹过,啪啦急响。我解下扁担、锄头、竹棍歇息。村人说,快转大人了,还带竹棍玩?以棍作画,比扁担轻省得多,我持棍回头看,沙地上,足迹陷,我把玩手中棍,琢磨该画或不该画,又该画什么?
就画风狮爷如何?
我兜圆圈当头,正要画上双眼,惊风来,披巾断,凌空起落。我呆了呆,追着披巾跑。红披巾打旋直升,如飞龙破云,滑溜弧行,如蜻蜓振翅。披巾被竹林挡住,挨着竹林刮。我忘了林下有坟,只觉红巾、绿竹相映,格外醒目。我踏上石碑,拦下披巾,喜滋滋地捧在怀中。
待留意跑来坟墓,看见坟上方有一个破洞。伯公说,这是张氏三兄弟衣冠冢,坟内并无尸骨,我喘了一会儿,放胆,以棍探路,踏上坟去。坟茔结实,却有破洞,我张望洞口,看似不深,究竟多深呢?我心想这就是梦中我跌落的洞口吗?
洞口边缘,裹一层蛇蜕的皮,我持棍一勾,拖出洞。蛇长几尺,恐比竹棍还高。大石当基础,碎石掩空处,洞口越遮越小。我小心地探棍入坟,棍身已没,却没到头。
最后,我松手,棍走,沉入坟墓,淡淡叮咚。
吴钧尧,《幼狮》杂志主编,曾获金鼎奖等多项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