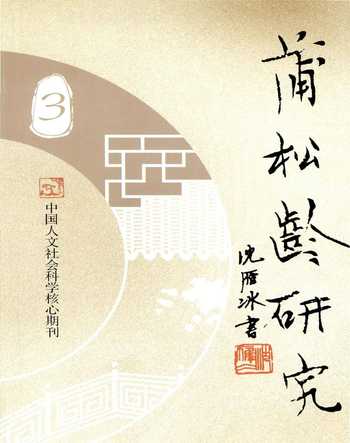伎艺戏法也在志怪
焦伟
摘要:《聊斋志异》为我们展现了民间众多伎艺戏法,有的被蒲松龄赋予新的艺术生命和时代寓意,也有的只是进行了生动的记载和描述,作为一个专题来看,民俗文化也是蒲松龄“雅爱搜神”重要领域,通过研究使我们更深刻体会其高超的创作技巧和艺术特色。
关键词:伎艺戏法;志怪;再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419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中,除了运用狐媚道僧的幻术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外,蒲松龄还根据一些见闻轶事,记载和描述了多种民间的伎艺戏法,如《偷桃》中的屠人杂技,《王成》、《促织》里的决斗博彩,《蛙曲》、《鼠戏》中的弄虫蚁,《口技》中的象声戏法以及《木雕美人》中的木偶戏等,还有《劳山道士》里的穿墙术、《戏术》中的套桶魔术也可归入。这些篇目中,有一些笔记体小文式作品,虽然不是简单记述,但也不能看作是小说体裁,为什么蒲松龄仍然收入其中而不忍删掉呢?笔者认为,这些伎艺戏法在民间流传很广、影响深远,甚至在当时不只是一个人向蒲翁讲起过,或者是蒲翁在各类典籍中多次阅读到,为此,加以著录和脱胎换骨地再创作,使之成为志怪的另一个领域,我们权且称之为伎艺志怪法。
其实,我国古代人民发挥聪明才智,费尽功夫和心思创作展演了很多独门特技的伎艺戏法,其中一些流传至今。如口技,古代称象声,喻为学什么像什么之意。到明清时代,已经成为独立的艺术样式。明嘉靖才子李开先曾为山东济宁一个叫“刘九”的盲艺人作传,说他“市语方言,不惟腾之口说,而且效其声音。”张岱《陶庵梦忆》记载,评书艺人柳敬亭在说景阳冈武松打虎时的情景:“说到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壁皆瓮瓮有声。”《口技》就是一部象声的独幕剧,售医女子为了增强看病医方的神秘可靠,让人相信她的医术高超,妄托仙姑下凡并请来会诊,先是邀请的神仙九姑、丫鬟腊梅登场,后又六姑、春梅及小郎子来到,“旋闻女子殷勤声,九姑问讯声,六姑寒暄声,二婢慰劳声,小儿喜笑声,一齐嘈杂。”四姑与丫鬟最后出场,“遂各各道温凉声,并移坐声,唤添坐声,参差并作,喧繁满室,食顷始定。即闻女子问病。九姑以为宜得参,六姑以为宜得芪,四姑以为宜得术。参酌移时,即闻九姑唤笔砚。无何,折纸戢戢然,拔笔掷帽丁丁然,磨墨隆隆然;既而投笔触几,震笔作响,便闻撮药包裹苏苏然。”蒲松龄在描写口技时用了“戢戢然、丁丁然、隆隆然、苏苏然”等象声词,生动逼真地再现了口技的玄妙之处,这位医女的嘴上功夫堪与柳敬亭相比。然而,行文到此蒲松龄并没有轻易结束,而是用王心逸见闻说明口技在京城很常见,从这里可以对比体会到蒲松龄高超的小说创作技巧和志怪的形象表现方法,正是有了王心逸提供的这类普通线索,使得蒲松龄不断进行再创作,加入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的情节和人物描写,成为生活气息浓厚的志怪体裁。正是蒲翁的高超的艺术创作,让人觉得医女借口技来做广告合情合理,而经过“静绕门窗、倾耳寂听”,让人不能不信其医术。更让人觉得我们读小说就如身临其境,现场观看一般,通过出神入化的描写,也体会到了口技给我们带来的乐趣。
《聊斋》的志怪,涉及诸多方面和领域,概而述之,有狐妖志怪、奇闻志怪、异象志怪、冥梦志怪等等。由于狐妖鬼魅形象众多,使我们没有去关注来源于日常生活的这些伎艺戏法。用形象反映生活,是蒲松龄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把脉其穷尽一生的一边科举,一边写作过程,可以说是异常艰苦的。“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聊斋志异·自志》)从其叙述的搜集材料、积累素材、不断加工的方式方法(“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邮筒相寄”),我们认为一部分聊斋故事或者是线索都是在坊间巷陌先有一定程度的流传,然后由文学家“一题到手,必静相其神理所止”,加工整理、寄托孤愤、再创作了几十年,直到终老成书。因为传奇法志异的特点,在再创作中缩减了对环境和生活的铺陈渲染,增加了人物情节和细节描写,虚幻色彩浓厚。而民间的伎艺把戏是最能反映百姓文化生活的,当然会成为志怪的载体,蒲翁对此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蛙曲》、《鼠戏》更是来源于百姓生活,且自古有之。据史料记载,教虫蚁的戏法至少远在一千多年的东晋就已开始,至宋代盛极一时,明清又有发展。从有关记载看,有“蚁戏”、“蛙戏”、“龟戏”、“鼠戏”、“蚤戏”、“鱼戏”、“鸽戏”等等。蛙戏的常见节目是蛤蟆教书。表演时,台上置一木墩,艺人对木匣轻喊一声,一只大蛤蟆跳出,坐在墩中。再喊:“老师来了,学生怎么还不来?”这时,又有大小不等的八只跳出来。艺人接下来发话:“老师该教学生念书了!”大蛤蟆一听,哇地叫一声,八只小蛤蟆跟着“哇”一声。老师“哇哇”两声,学生也跟着“哇哇”两声,一唱一和非常有趣。表演完毕,小蛤蟆一一来到“老师”面前点头鞠躬,感谢之态可掬。这在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里有生动的记载,“谓之蛤蟆说法,又谓蛤蟆教法。”《蛙曲》借王子巽说法,“曾见一人作剧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细杖敲其首,辄哇然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之乐,宫商词曲,了了可辨。”这显然是另一种蛙戏。戏法是用来挣钱的,给钱就可以表演出更复杂的音乐,配以锣鼓打点,可以清晰地听出曲调音阶来。而马戏、斗鸡等戏法则早在商周时期即有之,《西京杂记》叙说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俸谷一年费两千石”,河南嵩山脚下建于东汉初年的中岳汉三阙,就雕刻有马戏、蹴鞠、幻术、斗鸡等画像,说明这些戏法在古代社会一直延续发展并成为民间传统。
鼠类较之蚂蚁、青蛙等要聪慧得多,王兆云在《胡海搜奇》中说,“予在山东,则一人卖药,二大鼠在笼中,人求药,呼鼠之名曰:某为我取人参来。鼠跃出笼,衔人参纸裹而至。又呼其一曰:某为我取黄芪来,亦复如是,百不失一。”清代在苏州玄妙观,有一山东人表演的鼠戏,把形如伞盖的木架安放在地上,拼出一戏台,十余只鼠盘踞台上,锣一响,这些老鼠便上演戏剧,如《孙悟空大闹天宫》、《李三娘挑水》等。他们还能用爪抓住竹木刀枪,旋转而舞。看来,咱们山东在伎艺戏法上还有很多传统的。这跟《鼠戏》中的描写几乎完全一致。“一人在长安市上卖鼠戏,背负一囊,中蓄小鼠十余头。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俨如戏楼状。乃拍鼓板,唱古杂剧。歌声甫动,则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装服,自背登楼,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给老鼠穿上戏服,蒙上假面具,出来做一些高难度的表演动作,也真难为艺人们了。犬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朋友,比之其它动物更加聪明,善解人意。在《木雕美人》中,记载了训犬并给犬和木偶穿衣打扮的情景,“又以小锦鞯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学解马作诸剧,镫而腹藏,腰而尾赘,跪拜起立,灵变不讹。”这种小型木偶戏还带有剧情表演,“又作昭君出塞,别取一木雕儿,插雉尾,披羊裘,跨犬从之。昭君频频回顾,羊裘儿扬鞭追逐,真如生者。”
就像现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剧目一样,民间的伎艺把戏不但代代相传,还因为要到各地演出,进而加大了社会影响面。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就是由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再到大众传播,成为群众文化传播的媒介。民间流传故事的特点,一是讲求神秘性,必须吹得神乎其神,否则不吸引人、无震撼感;二是讲求故事性,没有曲折起落,受众就会缩小;三是讲求时效性,针对某些现象、名人轶事,层层加工。民间伎艺把戏之所以成为传播媒介,还有它的直观性,更加容易产生神奇的幻觉,导致人们对神仙鬼怪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时,为了加强故事的真实可信性,作者在书中使用了许多真人名姓,甚至不惜以我的身份来叙述,如《偷桃》:“童时赴郡试,值春节。旧例,先一日各行商贾,彩楼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从友人戏瞩。”据史料记载,屠人魔术本是西域胡人的把戏,因其台上太血腥曾遭禁演。故事的流传,往往都会视情景进行再创作,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添油加醋,甚至是剔除合理部分只留震撼人心的部分来吸引迷惑,以乱视听。蒲松龄在记载和创作这些伎艺戏法时,没有像民间那样凭空臆想、走火入魔,而是撷取精彩的场景,使人觉得志怪而不荒诞,奇异而不迷离。
至此我们可以加深对鲁迅先生评价《聊斋》的理解,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因此,在《聊斋》各篇目中不乏花妖狐鬼的奇幻之术,但有一些是“示以平常”带有杂技魔术的色彩,经过蒲松龄的进一步加工创作,把这些展现在写鬼写妖的篇章中,很可能把现实可信的部分在创作中简化或魔化了,如《种梨》,给人增加了神秘感但还能觉得可信,成就了“传奇手法志怪”梦幻现实主义艺术特色。从蒲翁创造的鬼狐妖孽各类角色中,很少出现像《西游记》中那种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腾云驾雾的神道、妖术和魔力,最多像把所有的瓮变没了,把别人的钱财挪移来家,还有青冢变华宅、树叶变霓裳等,狐妖的法术一般,与常人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区别,这大概就是蒲翁的写而不信的特点吧。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