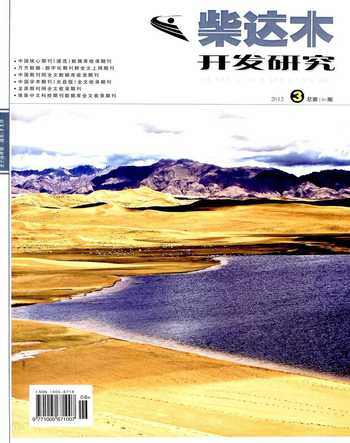浅谈青海蒙古族生态环保文化意识
呼和巴拉
青海蒙古族是13世纪20年代进入青海这块神奇土地的。16世纪初踏入青海境内的顾实汗各部落是今天青海近十万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主要是和硕特蒙古部。蒙古族是青海世居民族之一,在青藏高原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繁衍生息,用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生态环保文化。生态环保文化是青海蒙古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含金量较高、“储量”较丰富的文化“宝藏”,独具特点,有较高研究价值。青海蒙古族的生态环保文化的形成是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所决定的,它不仅表现在语言、习俗、宗教、生活娱乐等方面,同时也包含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大自然不断发生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生态经济之中。他们的生态伦理、文化习俗与生态经济原则和大自然发展规律密切吻合,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一、青海蒙古族生态环保文化源远流长
青海蒙古族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带,生态环境的脆弱、地理环境的恶劣,使他们在同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依赖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的生态观念及行为,从而使善待大自然、回报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成为了蒙古族人民的基本生活理念和追求。早在16世纪以前,蒙古族信仰萨满教时期就有崇拜天地,祭祀苍天的习俗。作为游牧民族,认为长生不老的苍天——呼和腾格尔,就是蒙古族的上帝,天有多大,大自然就有多大,草原就有多大。认为“上界是我的腾格里父,下界是我的大地母”,宇宙万物生灵都是腾格里的,由腾格里安排世上万物生灵的生存、发展和命运。他们遵循天命、崇拜天地、服从天意的信念是坚不可摧,牢不可移。在这种习俗中客观地还存在着一些原始宗教的色彩,可实际上这无不体现着对天地、对自然界秩序的尊重。所以崇拜苍天是草原游牧民族出于对宇宙秩序、自然规律的一种由衷的赞叹和深深的敬畏,是领悟自然,觉悟自己,把自己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完全融入大自然的一种潜在意识的反映。事实上,自然崇尚是蒙古民族自下而上生存发展的力量源泉和远大目标,是与大自然的发展一起勇往直前,永远向上的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保护自然、爱惜自然、珍惜自然、珍惜一切生物与生命是蒙古族生态环保文化意识的基本而重要特征之一。
蒙古族历来崇拜长生天——腾格尔,遵循天命,对大自然敬畏而顺从。在这种崇拜期盼中,表现出的恰恰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象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爱护大自然,并树立适应自然环境的思想和尊重自然规律的理念。蒙古民族生于草原,融于草原,就是在死后,还是回归自然与大地共存。古代蒙古族汗王或贵族身染重病于宫廷之中,在临近逝世时,则要移至毡帐布营之中,而表示生前不居砖石宮室。《元史》中说:凡帝后有疾危殆,度不可愈,亦移居外毡帐房。有不讳,则就殡殓其中。若以土葬,葬后则用马踏平此地,不留痕迹。之后青草生长覆盖,葬地仍如原先草原,毫无损伤。
青海蒙古民族在森林、草原、高原的独特环境中生存,主要靠的是狩猎和游牧。狩猎、游牧活动在天地之间,是天性,是与自然同存共荣的基本生存方式。蒙古族对整个大草原,整个大自然,甚至整个宇宙,都表现出虔诚的敬畏和爱恋之情。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于自身的生存,对畜牧业的发展,对大自然的保护等方面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措施,并有法律手段加以保护。1640年9月,以卫拉特蒙古巴图尔洪台吉和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为首的东、西蒙古29位首领,在塔尔巴哈台山会盟,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的法律条款把信仰习俗、民间禁忌升华为一种制度,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人们生活不断完善和发展,对蒙古社会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牲畜、草场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难看出,此《法典》中包含了如何处理好人与畜、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法制思想和法制观念。
青海蒙古民族根据所处的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地形外貌状况和不同地区差别,创造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生态环保文化适应方式。他们将人、畜、草、水这四个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基本要素科学地协调起来,当做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并且在游牧社会经济与草原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中,从未打破过生态平衡,能使游牧经济自身的自然规律长期生存发展,也就使草原生态系统以自身正常状态维持下去。
青海蒙古族在长期的生存发展实践中,创造出了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环境、可持续利用和循环利用自然资源的一整套生产生活方式和技能。这就是高原游牧方式。他们首先保持、维护一定区域面积的草场,使之持续承载各类动物包括野生动物的生存需要;很巧妙利用草原生态系统发展规律和平衡规律,确定划分四季草场,并控制一定程度上整个草原的载畜量;根据不同牲畜选择不同的草场和放牧方式,以赶牧、领牧、天牧、瞭牧为主的放牧方式,合理搭配,轮换放牧,使之既不超出不同季节草场牧草生产力的总量限度,又避免与草原生态环境中其它生物争食纠纷,同时对各类草场采取休牧、禁牧、轮牧、活牧的不同放牧方式,以缓解草场压力,实现了天时、地利、人和、草兴、畜繁的最佳结合。在草原上,人畜和其它动物一年的排泄物、各种残留物给草原土壤添加了一层宝贵的腐殖质、有机质和钙磷质等肥料。这些上等的有机肥料撒到草原上,确保了来年牧草茂盛、草原兴旺。人们还利用牲畜的粪便作为燃料,根据热力学定律,牲畜粪便这种物质经过燃烧利用后变咸了草木灰,这种对草木生长极为有利的肥料返回草场后,作为一种新的能量又参与到下一轮的能量循环之中,这中间既没有污染,又没有浪费,可以说是热力学第一定律一一能量守恒定律在草原游牧生态系统中比较典型的体现。
二、青海蒙古族生态环保文化的表现形态
(一)生产生活方面
1蒙古包的造型
蒙古包是圆形结构,拆搭方便,便于搬迁。大小尺寸比例对称,长短有度,造型美观,协调均匀。蒙古包制造材料全部直接取之于自然植物和牲畜。它的墙壁叫铁日木,以柳木条用皮绳(牛皮)缝编成菱形网眼的网片,可伸缩、可折叠。蒙古包的天窗叫俄日克,圆形透光、通风透气、调节室温。白天将俄日克的盖毡打开,烟气可自此对流,保持室内良好光线、清新空气,雨、雪天和夜间用顶毡盖住,达到保温的效果。蒙古包光滑溜圆的外形,有利于抵挡草原上的白灾(暴风雪)、黑灾(沙尘暴)、地灾(地震)的袭击,当白灾、黑灾袭击时,流线型的蒙古包对其具有缓冲作用。当地震时,本来很轻的铁日木很有伸缩性,弹力又好,几乎不存在任何危险。蒙古包没有棱角,包顶也是拱形的,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承受外力性能最强,抗御风暴有很大的柔韧性,可承受住冬春季节十级大风的袭击。在雨雪季节,只要将蒙古包的顶毡盖上,它就形成了一个圆球状的封闭体,雨雪很难侵入。圆形的包顶存不住雨水,再大的雨也能直接从顶毡顺壁泻流到地面散去。蒙古包的围毡具有极强的隔风保暖性能,并且可以按气候冷暖进行增减,冬季天冷可增加覆盖层,无论包外有多大的风暴、雨雪,只要包内有火,即温暖如春。蒙古包所需用的材料和费用很少,对自然环境没有影响。蒙古包的铁日莫、乌尼(承天窗的支杆)、哈拉兹(天窗架)的材料都是自然森林灌木中较为细小的柳木条制成,然后用剪下的羊毛擀成毡子,进行裁缝,蒙古包的内外盖毡、围毡便齐备了。再用剪下的羊毛、马鬃、马尾、牛毛,可以搓成围绳和围带子。所以一切材料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无须多少成本。蒙古包的这些特点,完全是物竞天择,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
2游牧方式
畜牧业生产是传统游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具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标准。它的形成主要是由特定的畜牧群体所处的栖息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所决定的。畜牧生产是以草和草场以及水源为基础的,因而随季节而移动,逐水草而游牧。从表面看,这种“被动行为”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毫无原则地漂移在草地空间之中,似乎带有“靠天吃饭”的性质,完全依赖大自然。其实不然,蒙古族对畜牧业很讲究规则,且十分严格。他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草原生态、草地的形状、草木的性质、长势、水源及其利用等都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和很强的使用技巧能力。他们对草原生态看上一眼,就能说出哪块草场应牧养什么牲畜,哪块草场适于哪个季节放牧。有经验的牧人,即使是在夜间骑马,也能用鼻子嗅觉到附近草的种类和土质及水源位置。这就是与自然并存中学到的自然常识和生存能力。
草场的选择必须根据畜种和季节的不同而选择利用。牲畜因种类不同,喜食的牧草种类也有所变化。青海蒙古族根据当地“春暖、夏热、秋凉、冬冷”的气候变化规律和“夏肥、秋壮、冬瘦、春乏”的畜种体质状况,按春夏秋冬季节把草场划分为春窝子、夏窝子、秋窝子和冬窝子。这样可以顺应季节、环境的变化,更好地利用天然的牧草资源——草原。在四季草场上放牧很有针对性,五种牲畜的食草习性不同而对它们选择的地形、草类草势,水源也不一样。春季产羔草场的草要好,且草软草矮,是“换青”季节。“四月草初长、牛羊未肥”,青藏高原的冰雪刚刚开始消融,畜群不愿吃隔年秋草,但新草又吃不饱,“草色遥望近却无”,畜群整天疲于追草,这叫“跑青”。这时一些老弱病残的瘦畜就因疲于奔走吃不上草而死亡。夏季草场非常好,但必须要靠水近,而水源都在山里面,这时牧草长势好,气温又热,需要选择凉爽、通风的地方放牧,时间要长,所以要进山放牧。夏天主要抓“水膘”,确保畜群的饮水,并适当舔食些盐或吃盐碱土、盐碱草。秋季草场草籽多,草质好,要让畜群少跑多吃,抓实膘,这叫“抓油膘”。牧人说:“夏抓水膘、秋抓油膘、有肉有油、冬春不愁”。冬季靠的是草高,不怕大雪盖住,气温很冷,牲畜要在阳面温暖处放牧,不饮冰茬水,确保怀胎母畜不流产。四季草场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短处。随着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草地、水源利用和保护的有效选择。
3狩猎采集
狩猎——采集经济的生态首先体现在对自然环境的无条件依赖。狩猎采集是青海蒙古族自古以来生活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整个蒙古族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一整套对动植物生态资源进行摄取和利用的知识和经验,也是熟悉自然、了解自然、逐步掌握自然规律,能够将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本领和技巧。
蒙古族的狩猎不完全以猎取动物,获取生活补给为目的,更重要的是保护自然生态平衡、保护草原。狩猎的动物主要有岩羊、黄羊、盘羊、鹿、野牛、野驴等食草动物,还有狼、熊、豹、猞猁、狐狸等食肉动物,有时也有秃鹫、鹰等对羊和羔羊有害的飞禽。他们狩猎有严格规则。在动物中进行认真挑选,有针对性地猎取那些越了冬不能过春,过了今年过不了来年的老弱病残和淘汰动物。不准打猎幼仔、母仔,尤其是更要爱护怀胎动物,若猎取这些野生动物会被视为无能,不道德而受到人们的歧视;打猎忌讳“断群”,猎取十头左右动物,总要放生几头;每次打猎中注意放生大批幼兽和带仔的母兽。蒙古人无论宰杀牲畜还是打猎野生动物,除获取它们的肉以外,利用它们的皮毛做穿戴物和日常用具。如皮袄、皮裤、皮帽、皮手套、皮褥、皮被、皮鞭、皮田袋、皮具套、皮鼓风袋、皮绳、毛绳等。这样即解决了食物补给问题,又为衣着用具提供了原料,体现了畜牧、狩猎业对自然资源能量的互补和利用。如宋使萧大亨对蒙古族狩猎的记载:“若夫射猎,虽夷人人之常业哉,然亦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搜群,惟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需而已。”所以,在蒙古族的自然资源观念中,普遍不存在囤积居奇和赖以发财的意识,人们狩猎基本上都是为了充饥和度荒,而且十分重视猎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在狩猎、采集经济中,狩猎和采集两者不能分开,也缺一不可。如劳动分工中一般多为男子狩猎,妇女采集植物。虽然在习惯上一般狩猎列在前面,但在实际生活中,采集占的比重更大,更为重要。采集也和狩猎一样,有季节,有时间,也有选择性,不能乱挖乱采,即要注意留根保籽,又要保护土壤不受损害。人们都在夏秋季节采集各种药材、野葱、野蘑菇、木耳、蕨麻(人生果)、地皮菜、沙棘果、枸杞果、锁阳等等,什么节令菜什么和怎么采都相沿成习,代代相传。狩猎、采集经济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栖息地的动植物资源所决定的,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谋食方式比较直观地反映了蒙古族对栖息地的动植物与能源流动的组织和利用,因此其生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狩猎采集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们从事这种谋食活动时,不直接改变即成的生态环境,也不打乱原有生物互相关联的链接关系,仅在其伴生生物的正常生息间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
4敬畏生命
青海蒙古族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认为这神奇的大自然不仅具有其生物生命特性,而且具有精神生命特性。认为大自然及其万物是其最基本、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有关生命的价值观念在蒙古族人的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包括人在内的无论何种生命形式都同样重要。他们以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资源、呵护一切生命为出发点,他们的观念与行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都以保护大自然、维护家园为前提,并以此为主导而展开延伸的。
在青海蒙古人的眼里,大自然的一根草、一把上、一块石、一滴水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额尔德尼——宝。对大自然只有珍惜、爱护的义务,没有任何糟踏、破坏甚至毁灭的权力。这就是与大自然同命运、共存亡的唯一条件。在蒙古民族的生态环保文化观念中,对草原、大自然的烧荒,染脏河水、犯地规,滥砍伐、滥打猎、肆意破坏资源都是一种重大的忌禁之事,是大逆不道的罪孽。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在其大可汗令中这样写道:不准脏污泉眼、河水,不准在流水、湖水里洗脸、洗澡、洗衣,否则天神不饶,将其以天条严惩。宋朝大臣彭大稚在《黑鞑事略》中记载:“蒙古习惯法:‘其禁草生而创地者,遗火而焚草者,诛其家。”足以可见,蒙古族早已把毁坏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不道德行为列为触犯自然规律的不法行为,严加制止。
(二)风俗礼仪方面
1祭祀
青海蒙古族几百年来一直保持和传承着各种祭祀风俗。祭祀活动是以崇拜大自然,敬畏生命为主要内容的。他们以祭祀形式祈祷长生天——腾格尔保佑宇宙自然间的一切生命太平无事,吉祥幸福,和谐泰合;祈祷“佛、法、神”三宝永久保佑草茂水清,森林常绿,风调雨顺,五畜兴旺,兽猛禽骄,人们安居乐业,时代祥和,春满人间。他们把这些活动一般选择在绿草如茵、牛壮马肥、风和日丽的季节举行。整个活动自始至终注意防火、防随意践踏草原、防污染水源、防随意倒垃圾,注意环卫。这些行为就是蒙古族适应自然环境、顺从自然规律、以赖大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生态观念和行为。这种看似迷信色彩较浓的宗教活动,实际上是人们以这种方式把草原丰盛繁茂,人间无灾无害,大自然平安祥和的思想精神寄托于上天腾格里,寄托于宗教理念上,表现出了他们的言行举止、思想观念、精神理想必须以大自然为核心,围绕大自然的有序法则去生存、去发展的自然性心态。
2禁忌
在青海蒙古族的民间社会生活中,沿袭着大量带有生态维护性质的禁忌习俗。这种习俗一直传承到今天,在人们生活中,在整个民族生态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蒙古族的禁忌习俗内容较多,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几乎无处不在,凡事都有。涉及到高山、湖水、草原、森林、土壤、植被、牲畜、野兽、飞禽:涉及到吃喝拉撒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居住、搬迁、转场、出行、打猎;涉及到婚姻家庭、丧葬习俗,甚至给人取名都有禁忌习俗。譬如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砍伐树木、打猎,伤害兽禽鱼虫、将神山上的任何物种带回家;禁忌将污秽物以及奶物倒入湖、泉、河里及在河流、水源边地堆放脏物、大小便、捕捞鱼、青蛙等:严守“不动土”的原则,严禁在草地上胡乱挖掘,以免使草地肌肤受伤;夏季禁忌大规模搬迁草场,因夏季牧草生长季节,不能让牲畜大面积践踏;禁忌在草地上挖水渠,因水道易于水土流失,造成对草场的破坏;禁忌捕捉和惊吓任何飞禽、拆毁鸟窝、捕食一切爪类或圆蹄类动物;禁忌捕猎因雪灾、旱灾、洪水、火灾等而被困的动物;禁忌摘断细枝嫩芽、砍伐新幼树木、砍断树根、烧毁树木。这些禁忌的形成,主要表达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敬、感激、畏惧和顺从之情。无论那种禁忌,其内容中无不渗透着生态意识,无不表现出对大自然崇拜敬情。这已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习俗规范和制约,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坚定信念。
3色彩
青海蒙古族生态文化形式中生态色彩意识很强烈,很浓厚。他们崇拜的色彩与大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常喜欢崇拜的是蓝红黄白绿五种色彩。他们崇拜的色彩中,蓝色应是首选的神圣色彩。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后建立蒙古汗帝国时,本民族取名为呼和蒙古勒——蓝色的蒙古。因当时信奉的萨满教以长生天——腾格尔为真主,整个宇宙都由长生天——腾格尔安排,一切万物都顺从腾格尔的旨意。不老长生天就是大自然的恩主,也就是蒙古民族的神主。天空博大无比,晴如明镜,湛蓝如宝石。所以,他们衷心跪拜在恩主不老长生天——呼和腾格尔之下,祈求为本民族赐名——呼和蒙古勒。呼和就是蓝色之意,这不是盲目崇拜上天的愚昧行为,而是对大自然神圣不可侵犯的纯洁、光明、勇往向上的崇拜。也是生于大自然、死于大自然、融化在大自然中的强烈生态意识的表达。
其次是红色。红色火辣、活泼、生命力强,红色代表太阳。太阳是大自然宇宙的成员,并且是最大、最高傲的星座之一,是不老腾格里的宠物。所以蒙古包的门必须朝东方太阳升起的方向开。萨满教盛行时,早上太阳刚刚出来,人们就朝着红似火的太阳跪拜叩头。现在也沿袭旧的习俗,女儿出嫁须在太阳露脸后才骑马上路;春节拜年,等太阳露出火红的笑脸时才串门拜年。
再次是黄色。黄色代表大地,大地乃万物之母。大地养育了数不清的万物生灵,蕴藏着数不清的宝藏。没有大地母亲温暖的怀抱,一切生命之物就无生存之路。她对大自然万种灵物恩赐永久、代代享福。加上青海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五百多年,对黄色更加尊敬、重用。家里的佛箱、佛龛、佛杯、经袋均为黄色:寺庙房顶、佛像以及佛寺用具都是金黄色;寺庙大活佛袈裟、经帽、衣物也是黄色的。因此,祭敖包、祭神山、祭泉源以及向活佛、喇嘛敬献哈达一般都用黄色绸缎哈达。这即有崇敬、珍爱大地资源生态之意,又有对佛教的膜拜虔诚之心。
白色是蒙古人最喜爱、珍惜的色彩。白色表示纯洁、圣洁、善良高贵、明朗。圣祖成吉思汗大军营帐门前常高高飘动着黑白两杆苏鲁定(用马鬃做的指挥旗),这白色苏鲁定象征着和平、安宁之意。在蒙古人眼里白色就是吉祥云朵,高贵不可侵犯,高洁不可旗污,就是恩重如山的五畜乳汁,只许珍食不可浪费。蒙古人的“查干浩勒”(白食),就是用牲畜乳奶制做的各种奶食品。这种白色食品营养很丰富,价值也很高是很好很有效的保健品。在每次重大节日和娱乐活动时,第一礼节就是“查尕-德吉勒奈”。意思是首先必须品尝奶制品,如奶乳、酸奶、奶果子之类的白食。如在娱乐宴会时,主持人或主人忘记了这一重要礼节,将会受到人们的责骂、批评的。这就是对作为生产、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生物——牲畜的崇敬、珍爱之情的表达。青海蒙古人把春节叫“查干一萨拉”(白色之月),把心底善良的人叫“查干萨纳台昆”(白心之人),把奶制品叫“查干-浩勒”(白食),把五畜叫“查干-哈毕尔尕台-玛勒”(只有付出而无索取的白福之畜)。
绿色表示暖和、协调、生命之意。它代表草原、森林和向上不息、生命力极强的一切生物。只要有绿色,就有生命、就有希望。草原是蒙古人生存的摇篮,没有草原,从古到今无法生存繁衍。故对绿色非常敬重,对凡是绿色的东西都会珍爱不惜。因而五种鲜艳的色彩就象五色彩虹装点着蒙古族的生活;象一条五色彩带装扮着他们生态环保文化丰富的内容,一直沿袭,传承到今天。
三、青海蒙古族生态环保文化的传承及延伸
青海蒙古族之所以能够在青藏高原扎根生活、繁衍生息、繁荣发展,其最主要原因就是它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与之相适应的具有突出特征的传统文化。这古老朴素的传承文化的重要内容——生态环保文化是该民族顽强生命力的传承延续,是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结晶,它影响着该民族的现在和未来发展。
古代萨满教在整个蒙古族生产生活中产生过根深蒂固的影响,而接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的青海蒙古族生态文化价值的核心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青海蒙古族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中,处处都体现着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之情。这与藏族等其它民族的民俗文化价值观一脉相承,它的价值取向是人类与大自然不可分割,大自然本是人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善待大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青海蒙古族的生态环保文化与整体蒙古族和其它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一样都体现出与大自然协调互利的价值取向。在其生态环保文化里,将自己看作是大自然之子,将天空大地看作是人类的父亲、母亲,动物是兄弟姐妹,人类与世间万物彼此像家庭成员一样生活在一起。青海蒙古族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感情,认为人与大自然是相互依赖的,大自然理应得到人类特别的保护与关爱。任何人只可以向大自然索取自己确实需要的那一部分,不论是食物、水,还是其他资源,同时也应该同样地向大自然给予回报,这就是爱护大自然,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协调发展理念。这一价值观念能够发展、传承、延续到今天的基本保障,就是青海蒙古族无论向大自然索取什么都得道歉、反思、反省、感悟的心态思想。这种观念逐渐形成为一种文化内涵,它使青海蒙古族得到发展、传承、延续下来,因为它是优秀的,是传承文化的精华部分,是整个青藏高原地区蒙古族等兄弟民族共同拥有而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与其他文化一样,长期在草原、高原上传承经久不衰,构成了一部青海蒙古族不断发展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处处维护大自然的生命的延续,保护大自然的发展规律,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大自然的一员,成为大自然的生态保护者。
参考文献:
[1]江帆,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04
[3]芈一之主编: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民出版杜1981
[4]苏日巴达拉哈,中国民族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5]白歌乐主编,蒙古族,内蒙古人民出版杜1991
[6]那仁图雅编著蒙古族民间禁忌(蒙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7]孟克德力格尔编著,蒙古族传统生活概观(蒙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8]青海民族学院蒙古语言文学系著,青海蒙古研究(蒙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9]纳巴生,学院,刘昆黎编著和硕特蒙古,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10]柴达木开发研究2004(1-6)
[11]达木林巴斯尔,道日吉等编著,蒙古族食谱(蒙文),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