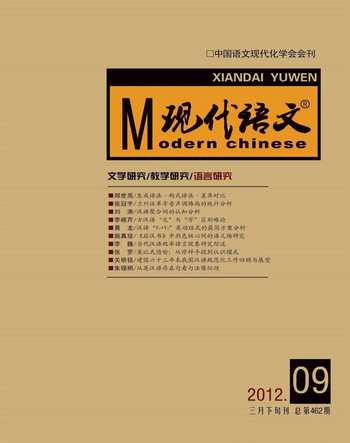《古字通假会典》指瑕
摘 要:高亨先生编纂的《古字通假会典》是一本重要的工具书,对语言文字研究的帮助很大,但其中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旨在对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关键词:《古字通假会典》《会典》声系通假
一、前言
《古字通假会典》(下文简称《会典》)“是一部帮助读者认识、判断古字通用现象的专著,带有工具书性质。它以收录资料为主,汇集了古籍中有关文字通用的大量例证,依古韵加以编排,以供读者翻检查阅、比较参考。”[1]
《会典》的体例是“按古韵十九部的顺序编排;同部之字,按所属声系编排。如红字属于东部工字声系,俊字属于文部夋字声系,等等”[2]。所谓声系,意指一字之基本声符。如《会典》之部又字声系的“郁”字。“郁”字从有得声,有从又得声。因此,“又”为“有”与“郁”的基本声符。再如“售”字,从雔省声,被归入“雔”字声系。所谓省声,意指声符被省简。但实际上,省声字的读音并未因声符省简而改变读音(或稍有不同)。因此,在分析省声字时,应恢复其原型声符来分析一字的基本声系。《会典》把“售”字归入幽部雔字声系,即是体现了这一声系分类原则。再如“姗”和“珊”字,均从删省声而来,所以《会典》把“姗”和“珊”列于“删”字声系下,莫不是以恢复原形声符作为基本声系为分类准则的。
由于《会典》采取的是古韵十九部分类法,与现今学术界通用的王力古韵三十部分类法有所不同。为了方便针对《会典》的讨论,我们对声系的归类仍沿用《会典》的韵部分类,但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采用王力先生古韵三十部分类法。两者有差异的韵部对应关系如下:

有个别字的声韵分部有所不同,这里我们不一一讨论。下文对《会典》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限于篇幅,有些问题我们只在结论中指出,而不在正文中讨论。
二、《古字通假会典》指瑕
1.宫字声系
《会典》第8页“东”部设有“宫”字声系。《说文·宫部》:“宫,室也。从宀,躳省声。”于省吾先生对许慎说法提出异议:“《说文》释躳为‘从吕从身(俗作躬),是以为会意字。然吕既不像脊骨,则躳字无由从之以会意,故躳之从吕,自系从之变,本应为从身声之形声字。《说文》又释宫为从宀、躳省声,殊不知甲骨文宫字本从宀从声。后也作从,亦是从之变。许氏不知古代本有字,既误释躳为会意字,又误以躳省声为宫之音符,所谓一错再错,而从来却无人道破这一点,今特为纠正。”[3]可知,“宫”与“躳”皆从吕(宫之初文)得声。按《会典》以基本的声符为一个声系的原则,“宫”字声系显然不妥,应改为“吕”(宫之初文)字声系。
又《会典》第31页“蒸”部下设有“弓”字声系,其下有“躬与穷、躬与共和躬与今”通假例。如上所述,“躬”字的声符作吕(宫之初文),并非从弓声。因此,“躬”字通假例应剔除于“弓”字声系。
2.容字声系
《会典》第10页“东”部设有“容”字声系。容,战国作,从宀从公,从公无意,当以公为声符,上古“容、公”均“东”部,公见纽,容,中古喻三,上古隶匣,见匣旁纽,故公与容音近。又,战国古玺所见作,从公声;信阳楚简榕所从容作,亦从公声。可见容本从宀,公声。迄今所见战国前古文字,容无从谷者,篆从谷甚为可疑。古文字从宀从穴每无别,因疑篆文容本是从穴公声之字,许慎云‘从宀、谷,不可从。”[4]“容”及从“容”之字的通假例应归入“公”字声系。
3.邕字声系
《会典》第11页“东”部设有“邕”字声系。《说文·川部》:“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籀文邕。”有不少学者对许慎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从川从邑不合理。《说文新证》云:“甲骨文从隹、吕(宫的初文)声,……吕形或省其一作口形。战国楚文字吕形讹为邑形,为后世隶楷所本。……故后世或作雝、或作雍,其实是同一个字。”[5]这一点可以从“雝”字的文字演变情况知道:→→→→→→→。据此可知,“吕”字在发展演变时,有讹变为“邑”的情况。故雝字声系当应纳入“吕”(gōng)字声系。
4.夅字声系
《会典》第13页“东”部设有“夅”字声系。“夅”实际上只是“降”字的省体。“降”字古文字作、,从阜、从二止,像二足向下之意,为会意字。董莲池云:“此夅之下乃倒止之讹,即本作而讹作了,字或即降字之省。”[6]在有一些从“夅”的形声字中,如“洚”和“绛”,其声符乃是“降”省形作“夅”。有的字书所列的“夅”字,实际上是一种晚出的形体。按《会典》体例,应把“夅”字声系改为“降”字声系(或降省形声系)。
5.匆字声系
《会典》第23页“东”部设有“匆”字声系。其下列有“匆”与“聪”和“聪”与“匆”等通假例。实际上,“匆”字是由“囱”字分化演变来的。东汉时匆字写作形,其上部后来变作“匆”。据此可知,“匆”为“悤”之变体。因此,“匆”字声系和“囱”字声系应合并为同一个声系。
6.丰字声系、豐字声系
《会典》第26页、28页“东”部分别设有“丰”字声系和丰字声系。丰字金文作,从壴,从。林沄先生认为,乃是“丰”字的繁体,在“丰”字里作声符。[7]这种说法,显然是很有道理的。这样看来,“豐”字声系应归入“丰”字声系。
7.字声系
《会典》第46页“青”部设有“荧”字声系。荧,西周金文作,像燋烛燃烧形,后变作,战国变作,其燋烛燃烧形已不显,又追加火旁以增其义。[8]因此,“荧”字应是(yíng)字的后起初文。《会典》应改为(荧之初文)字声系。
8.贞字声系
《会典》第61页“青”部分别设有“鼎”字声系与“贞”字声系。“贞”字古文字作、形,乃是一个从卜鼎声的形声字。其下部的“鼎”旁后讹变作“贝”旁。这种讹变在古文字中比较多见,例如“员、则”本都是从鼎,后来都讹变作从贝。“贞”字声系应纳入“鼎”字声系。
9.省字声系
《会典》第66页“青”部设有“省”字声系。“省”字古文字作、、,最初写作从屮从目,后来将上部的“屮”字改造成“生”字,使其作为声符。季旭升以为,“眚本义为省视,其后引申为视察灾病,再引申为灾病,秦汉以后为了区分此二义,于是把‘眚字原形保留给‘灾病义,‘省视义则把‘眚字生形的下横笔打斜,分化出另一个字。”[9]即、字。“省”字虽从“眚”字分化出来,但仍保留“眚”的读音。“省”字声系应改为“生”字声系。
10.旬字声系、匀字声系
《会典》第78、79页“真”部分别设有“匀”字声系和“旬”字声系。考之“旬、匀”二字,实皆从“勹”得声。甲骨文中表示十天的“旬”字写作,后来加上义符“日”,作,成了从日勹声的形声字。姚孝遂先生认为由(云)演化而来,即因之声,令上部出头,以表区别,形成“旬”一词。[10]可备一说。
除了演变成从日勹声的旬形声字之外,古文字中的“匀”字作、形,显然也是由“勹”(旬之初文)演变过来的。再从两者的读音考察,“旬”属邪母真部,“匀”属余母真部,读音很近,属于同音谐声系统,应无问题。概括而言,“旬、匀”应合并归入“勹”(旬之初文)字声系。
11.信字声系
《会典》第81页“真”部设有“信”字声系。“信”字战国文字有作、、形。后一例属于“秦”系文字,写作从人从言,前二例属三晋文字,写作从言从千。其实,这里的“千”旁就是“人”字,只是在“人”上加一饰点,变作“千”。《说文》认为“信”乃会意字,而从古音上考察,“信”应该是一个从言人声的形声字。“信”为心母真部、“人”属日母真部,读音相近。《会典》应把“信”字声系并入“人”字声系。
12.凡字声系
《会典》第83页“真”部设有“凡”字声系。细考“凡”字声系下所列的通假字,如“扟、讯、迅”等,并非从“凡”得声,而皆从“卂”得声。“卂”字在隶定时,有讹变成与“凡”字同形的情况。按照文字的正常演变形态,应以未讹变成“凡”的“卂”字为原形声符。故“凡”字声系应改作“卂”字声系。
13.奔字声系、贲字声系、卉字声系
《会典》第146、147页“文”部分别设有“奔”字声系和“贲”字声系。“奔”字金文作。刘钊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指出,“‘卉乃‘奔字截取部份构形而成的简省分化字。贲、奔古音相同。‘卉与‘贝组合成‘贲字后,又孳生出一批从贲得声的字,而实际上也就是从卉得声”[11]。这种说法显然很有道理。“贲”字乃从“奔”省声,故“贲”字声系应并入“奔”字声系。
另外,《会典》第627页“泰”部设有“卉”字声系,其下有“卉与贲”通假例。从上文可知,此处的“卉”字应为“奔”字之省,而并非花“卉”之“卉”。故“卉”与“贲”通假例应从“卉”字声系中删除,归入“奔”字声系。
14.免字声系、頫字声系
《会典》第154页“文”部设有“免”字声系,其下有俛与俯通假例。又第156页下设有“頫”字声系,其下只设頫与俯通假例。“俛、頫和俯”三字原来都同义不同音,“俛”和“頫”皆有“俯”义,后来就换读作“俯”,这属于同义换读的现象。这种情况裘锡圭先生已有专门论述。[12]因此,俛与頫、俯与頫的关系不属于通假。应把上述通假字例从“免”字声系中剔除。
15.宪字声系
《会典》第180页“寒”部(上)设有“宪”字声系。“宪”字在西周金文中作。春秋时,在的基础上增加义符,成形。董莲池以为“宪”之金文乃从从目,非从害省声,即从用声[13],不确。用上古音属余母东部,“宪”字则属晓母元部,两字声韵相差甚远,不能通假。考之“害”的金文写法作形,与“宪”字之上部同形。又从上古音而言,“害”属匣母月部,与“宪”音极近,可证二者应为谐声字。“宪”字可以分析成一个从心从目,“害”省声的形声字。按《会典》体例,“宪”字声系应当纳入“害”字声系为是。
16.甘字声系
《会典》第258页“谈”部设有“甘”字声系。然其下收有“恬与栝、恬与沾、恬与铦”三个例子,皆为“恬”字通假例。《说文·心部》以为“恬”从“甛”省声。其实“舌”和“恬”的古音关系很近,“舌”是船母月部,“恬”是定母谈部。二者皆为“舌”音,“月、谈”两部关系密切。比如也是从“舌”得声的“铦”字与“月”部的“挞”字相通[14]。“恬”应是从“舌”声的形声字。故这三例应归入“舌”字声系。
17.局字声系
《会典》第339页“侯”部设有“局”字声系。《说文·口部》:“局,促也,从口在尸下复局之,一曰博所以行棊,象形”,其说不可信。刘钊先生指出:“睡虎地秦简‘局字写作,结构正是从尸从句,故‘局本是从尸从句的一个字,构型应分析成从尸从句,句亦声。从尸者,古文字尸作,下肢屈曲形,其本义与‘屈曲有关,‘局字训为‘局促,义与‘尸字像人之屈曲形正相因。从句者,《说文》‘句,曲也,故局从句,而句与局古音又相近,故亦充当声符。“局”字所从之句后来与“尸”字的一笔并划,或叫借笔,致使原形渐失。”[15]这样看来,“局”乃从“句”得声,应归入“句”字声系。
18.異字声系
《会典》第374页“之”部设有“異”字声系,其下有“冀与几”和“冀与觊”通假例。“冀”古文字里作、和形。于省吾先生指出,“《说文》据已讹的小篆释为:‘冀,北方州也,从北異声。既误为从北,又割裂独体字为形声字。”[16]“異”属余母职部,“冀”属见母微部,两字声韵相差甚远。显然,“冀”非从“異”得声。因此,应新设“冀”字声系归入“齐”部。
19.之字声系
《会典》第403页“之”部(上)设有“之”字声系。然细考“之”字声系下所列的通假字,其中有大部分实际上是从“事”字得声。例如“事与侍、事与时和事与使”等通假例。《会典》之所以会把“事”字声系纳入“之”字声系,应该是受了《说文》的影响。《说文·史部》:“事,职也,执事也。从吏,之省声。”从“事”字的古文字演变来看,“事”为“史”字的分化字。金文“事”字作、形,其上部与“屮”形相近,《说文》因此误以为从省声[17]。故应把“事”字声系从“之”字声系中独立出来。
20.弋字声系
《会典》第414页“之”部(下)设有“弋”字声系,其下有“弒与杀”通假例。所引通假例子是:《礼记·明堂位》“君臣未尝相弒也。”《释文》:“弒”本又作“杀”。“弒”属书母职部,“杀”属山母月部,二者读音幷不相近。它们在上举例子中的用法应属于同义换读现象。因此,“弒”与“杀”不应视为通假,应从“弋”字声系中剔除。
21.服字声系、报字声系
《会典》第439页“之”部(下)设有“服”字声系。乃“服从”之“服”的初文。甲骨文作、形,像手按压使人跪着,意为“臣服”,是会意字。“服”乃是一个从舟声的形声字。故“服”之基本声系应为,“服”字声系应改为字声系。又《会典》第766页幽部(下)设有“报”字声系。“报”字从幸,声。故“报”字声系也应纳入字声系为是。
22.墨字声系
《会典》第444页“文”部设有“墨”字声系。“墨”字从黑从土,黑声,黑亦表意。按《会典》声系分类原则,应把“墨”字声系改为“黑”字声系。又“墨”字声系收有黓通假字。“黓”字从黑弋声。故“黓”字应纳入“弋”字声系。
23.軎字声系
《会典》第53页“支”部设有“軎”字声系。然除了“軎”与“轊”条外,余下诸例均为“毄”字或从“毄”之字通假例。“毄”字秦汉文字作、、,从东从殳,下或加凵、口,与“軎”字无任何联系。后来,“毄”所从的东形演变成车,车+口遂与軎字形同。“軎”字声系下所列的“击”和“系”诸字,皆从“毄”得声。故《会典》在“軎”字声系内除了保留“軎”与“轊”通假条以外,其余应归于毄字声系。
24.责字声系、脊字声系
《会典》第474、575页“支”部分别设有“责”字声系与“脊”字声系。“责”在秦文字中作,其上所从与“脊”字上部的一样,都是由字演变来的。状如人之脊椎,为“脊”之初文。另外,“责”字或体作。由于朿、脊音近,“朿”上古音属清母锡部,“脊”则属精母锡部。“责、”属于声符接近的异体字。“责”是一个以“脊”之初文作为声符的形声字。故“责”字声系应与“脊”字声系相并,作“脊”字声系或脊之初文声系。
25.启字声系
《会典》第520页“齐”部设有“启”字声系。“启”实际上是“啟”字的省体。“啟”字金文写作,像手开门之形,为会意字。后来其所从又旁讹变作攴,又在其下缀加口。“启”乃是由“啟”省攴旁而成的。显然,“启”字是后起分化字。为了避免本末倒置,使读者误以为“啟”乃从启为声。《会典》应把“启”字声系改为“啟”字声系。
26.骨字声系
《会典》第524页“齐”部十三(上)设有“骨”字声系,其下有“體与履、与腓、髊与胔和骴与胔”通假例。“體”字从骨豊声;字从骨巴声;“髊”字从骨差声;“骴”字从骨此声。因此,《会典》应把这四个通假例剔除,归入其所属的韵系中:“體”字归入“豊”字声系;字归入“巴”字声系;“髊”字归入“差”字声系;“骴”字归入此字声系。
27.既字声系
《会典》第527页“齐”部(上)设有“既”字声系,其下有“既与即”通假例。《易·旅·六二》:“旅即次,怀其资。”汉帛书本“即”作“既”。陈剑先生指出,马王堆帛书中的“即”乃“既”字形近之误。[18]他还举例,马王堆帛书《缪和》中“越王勾践即已克吴”,“即”显然为“既”之误。《上博简(三)·周易》中与今本相对应的字也是既[19],可证其说。因此,应将此例从既字声系中剔除。
28.豕字声系
《会典》第554页“齐”部(中)“豕”字声系有两误。一为误把“遂”的声符当成“豕”。“遂”字从辶,声,并非从豕声。因此,《会典》应把“遂”字通假例排除于“豕”字声系,并在齐部(屋部)另设字声系统属之。二是误把“豕”与“彘”误为通假。“豕”与“彘”都表“猪”义,是近义词关系。此外,“豕”为书母之部,“彘”为定母质部,两字声韵不近,因此不能视为通假。故应该把所谓“豕”与“彘”通假例排除于“豕”字声系。
29.字声系
《会典》第575页“齐”部(下)设有字声系。为疑之初文[20]。其下有“肄”字通假字例。“疑”属疑母之部字,“肄”则属余母质部字,两字声韵相差甚远,无通假之可能。《会典》应新设“肄”字声系。
30.肥字声系、妃字声系
《会典》第600页、605页“齐”部(下)分别设有“肥”字声系与“妃”字声系。“妃”字声系中有“妃与配”和“配与肥”的通假例。“妃”属滂母微部,“肥”属并母微部,“配”属滂母物部。“微、物”属阴入对转。三字读音关系极近。显然这三个字是谐声字。它们的声符或写作已,或作巴,其实皆非。应把这些字归为同一个声系。
31.氒字声系
《会典》第621页“泰”部设有“氒”字声系。第622页收有“銛与挞”通假例。“銛”字从金舌声。“氒”字声系中所收“括、刮、适、活”等字通假例,其中的声符“舌”旁其实是“”字的变体。所以,此例应归入“舌”字声系。
32.欠字声系
《会典》第686页“歌”部设有“欠”字声系,其中收录了两例“吹”字的通假字例。“欠”属溪母谈部,显然不应该归在“歌”部。实际上“吹”是一个从口从欠的会意字,并非形声字。应把“欠”字声系改为“吹”字声系,置于“谈”部。
33.字声系
《会典》第705页有“缉”部字声系。其下所列的通假字例中皆为“执”字或从执得声之字。在古文字中,“执”字作、,表示人的双手为桎梏所执,显然是一个会意字。“执”字所从之正像桎梏之形,属于“执”字的形符,而非表音的声符。因此,这个声系应改为“执”字声系。
34.告字声系
《会典》第727页“幽”部(上)“告”字声系收入一些造字通假例。根据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有学者指出,古文字中的“造”字本从()声,而非从告。古文字的和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字。到了小篆时,“造”字所从之讹变成告。[21]“告”属清母幽部字,告属见母觉部字。二者韵部虽近,而声纽远隔。过去人们误认为“造”从告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只关注到二者的韵近,而忽略了声纽的关系。因此,应设立字声系,把从“造”的通假字例归入其中。
35.丑字声系、羞字声系
《会典》第746页“幽”部(下)分别设有“丑”字声系和“羞”字声系。“羞”字“表意初文本从又持羊,后来又改为形近的丑(篆文丑作),就成为从羊丑的形声字了”[22]。“丑”属透母幽部,“羞”属心母幽部,两字可通假。按《会典》体例,“羞”字声系应纳入“丑”字声系为是。
36.讨字声系、守字声系
《会典》第753页、754页“幽”部(下)分别设有“讨”字声系和“守”字声系。李天虹认为:“《说文》里有不少从寸,但古音与肘相近的字,如“讨、疛、纣、酎”等等,《说文》或以肘省声释之。其实这些字本来可能都是从肘声的,隶变讹为从寸”,“肘、寸二字在形体上彻底区分,很可能在从肉的肘字出现以后。”[23]据此可知,“讨、守”所从的“寸”,实际上乃是“肘”之初文。故“讨”字声系和“守”字声系应合并在一起,成“寸”(肘之初文)字声系。
37.呆字声系
《会典》第765页“幽”部(下)设有“呆”字声系。显然,这里的“呆”字非“痴呆”之“呆”,而是“保”字右半。从古文字来看,“保”字比较原始的写法是,表示一个人把孩子背在背上。因此,唐兰先生认为“保”的本义是负子于背。[24]后来,古文字中的“保”字又变作、。右部“子”旁下的一点乃是大人手臂的残笔。金文有写作,又在“子”旁左下加一饰点,小篆承之。今天隶楷中的“保”字就是从小篆中演变过来的。显然,“保”是一个会意字,不能分析成从人呆声的形声字。《说文·人部》提到“,古文保”,但于古文字从未见省作“呆”形之“保”字。故《说文》之说不可信,所以应将此条改为“保”字声系。
38.字声系
《会典》第770页“幽”部(下)设有“”字声系。其实,“”乃“穆”之省形字。董莲池先生指出,“穆”甲骨文作,西周金文作,当是一种花类植物的象形文,有枝干,花朵从上下垂,金文于花朵下加的彡可能有强调其花华美有文采之意,引申为“美好”义。字非从声,所谓乃部份由主干上割裂下来的[25]。这一看法显然很有道理。因此,“”字声系应改为“穆”字声系。
39.谷字声系
《会典》第872页“鱼”部(中)谷(去之异体)字声系中列有“谷”与“浴”通假例。去之异体或写作“谷”,与“山谷”之“谷”混作同形,如“却”或写作“却”。“谷、去”二字读音不近。显然,“谷”与“浴”通假例是误混入了“谷”(去之异体)字声系。“谷”与“浴”通假例应从谷(去之异体)字声系中剔除,归入侯部(屋部)谷(山谷之谷)字声系。
40.虎字声系
《会典》第875页“鱼”部(中)设有“虎”字声系,其中收录了“卢、虏和肤”等诸字的通假例。从读音上看,这些字的古音韵属鱼部,但声纽却属来母或并母,显然和“虎”的声纽匣母相去甚远。实际上,这些字并非从虎得声,而是从得声。于省吾先生认为字是炉字的初文[26]。《会典》应该开列字声系,将这些字归入其中。
41.若字声系
《会典》第890页“鱼”部(中)设有“若”字声系。细考发现,除了“若与鄀”“若与诺”而外,余下的通假例皆从匿声。“匿”在古文字里作,像一个人隐于在框中,乃是“隐匿”之“匿”的初文。从构形上而言,应为会意字。“若”属日母铎部,“匿”属泥母职部,可证两字声韵相差甚远。《会典》误以为“匿”从“若”声的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因此,《会典》应新设“匿”字声系。
42.庶字声系、席字声系
《会典》第894页、895页“鱼”部(中)分别设有“庶”字声系和“席”字声系。“庶”,甲骨文作,从石从火,金文作,后变作,石旁成了。“石”属禅母铎部,“庶”为书母铎部,二者音极近。可见,“石”为“庶”之声符。同样,“席”字也是从“石”声的形声字。“庶”字声系和“席”字声系应并入“石”字声系。
43.鼠字声系
《会典》第912页“鱼”部(下)设有鼫与炙通假例。“鼫”是从鼠石声的形声字。因此,《会典》应将“鼫与炙”通假例归入“石”字声系。
三、结语
我们可以把《会典》致误类型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把形声字误列为一个声系:如宫字声系、邕字声系、豐字声系、贞字声系、信字声系、奔字声系、贲字声系、宪字声系等。不在文中讨论的尚有:宴字声系当改为妟字声系、坎字声系当改为欠字声系、伊字声系应归入尹字声系、灰字声系应归入又字声系、毇字声系应归入毁字声系、类字声系应改为頪字声系、切字声系应改为七字声系、跀字声系当归入月字声系、宝字声系应改为缶字声系、道字声系应归入首字声系、雀字声系应改为小字声系、到字声系应改为刀字声系、御字声系应归入午字声系、夜字声系应纳入亦字声系、豦字声系应纳入虎字声系、如字声系纳入女字声系。
(二)把会意字误以为形声字,从而归入错误的声系。如:冀字乃独体字,误以为从異声,而归入異字声系;匿字从匚、从若,误以为从若声而归入若字声系。
(三)根据《会典》所引例句文义来判断,它有把同义词误判为通假的情况,如:用与以、诞与永、再与二、豕与彘、弗与不、勿与无、勿与毋、毋与不、女与尔和汝与尔等。
(四)把省形的表意字列为一个声系,如:夅字声系、启字声系、呆字声系、字声系。
(五)把形声字的形符误为声符,从而误入其它声系或韵部,如:黓字置于黑(误作墨)字声系、體字置于骨字声系、鼫字置于鼠字声系等。其它如把誾字置于门字声系(当从言得声,归寒部)。
(六)因字形相近或混同而致误,如:“凡”字声系之“凡”为“卂”之误;“既、即”形近互讹误作通假;由于舌、舌()旁不分而将从“舌”声的“銛”字归入氒字声系;由于谷、谷(去)不分而将从谷(山谷之谷)声的通假例谷与浴 归入谷(去之异体)字声系。另外把“壬”字声系之壬为之误,“兆”字声系下的“跳”与“騑”通假条的“騑”字,当为“駣”字之误,亦可归入此类。
另外,《会典》还将某一声系归错韵部:将“邑”字声系归在“之”部,将“龟”字声系归在“幽”部。《会典》中尚有一些问题,限于作者学力浅薄,目前还不能解决。希望笔者的这项工作会对使用《会典》一书的学者有所帮助。
注释:
[1]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页6。
[2]高亨:《古字通假会典·述例》,齐鲁书社,1989年。
[3]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96年,页466。
[4]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作家出版社,2004年,页289。
[5]季旭升:《说文新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292。
[6]董蓮池:《说文解字考正》,作家出版社,2004年,页219。
[7]林沄:《丰豐辨》,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中华书局,
1985年,页181至186。
[8]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作家出版社,2010年,页273。
[9]季旭升:《说文新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259。
[10]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载《古文字研究》第二十
辑,中华书局,2000年。
[11]刘钊:《古文字构形研究》(修订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
年,页120。
[1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页219、220。
[13]董莲池:《说文解字考正》,作家出版社,2004年,页415。
[14]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页622。
[15]刘钊:《<说文解字>匡谬》,中国许慎研究会编:《说文解字
研究》第一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16]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冀》,中华书局,1993年,页389。
[17]季旭升:《说文新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也215。
[18]陈剑:《上博竹书<周易>异文选释(六则)》,《台湾政治大
学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台北,2005年12月。
[19]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4年,页65。
[20]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页220、2283。
[21]陈剑:《释造》,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复旦
大学,2006年,页55至100。
[2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页153。
[23]李天虹:《释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中的“肘”》,《古文字
研究》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页265。
[24]唐兰:《殷墟文字記·释保》,中华书局,1981年,页56至59。
[25]董蓮池:《“穆”字的形义探索》,李圃主编:《中国文字研
究》第一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26]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页1640。
(王康玮南京大学文学院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