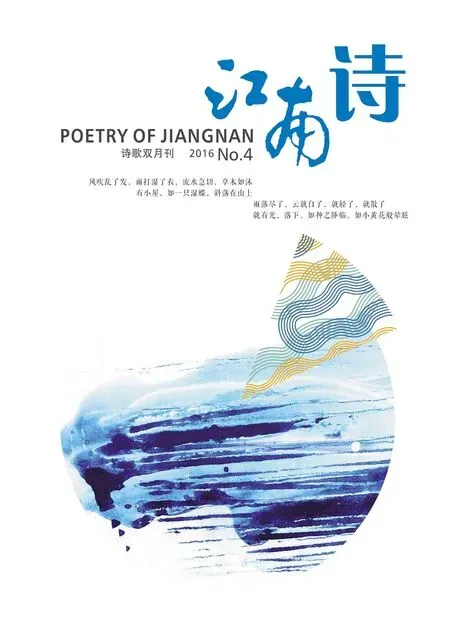无头的豫让如何复仇?
蒋蓝
我相信,世上有些事确有感应。2011年12月初,应山西省文学院之请,来太原举行散文讲座。张锐锋兄问我想到哪里走走,我告诉他,就去侠士豫让的故地赤桥村。中午在军转大厦吃过饭,文学院的司机开着一辆老迈的尼桑车来接我,《五台山》的编辑阎庆梅与我同行。
2007年我写《拆骨为刀——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侠义传奇》时,义气深重的豫让使我的写作陷于停顿:豫让是中国侠客史上第一个成功整容的刺客,他开启了历史上的咒诅之术。在先秦六大侠客中,他可能是最缺乏武功的;付出了一己的全部而未能完成复仇夙愿,又因为起点太低,他与高渐离近似,是六大侠客中唯一在无外力支撑背景下,仅凭一己之力向强势集团复仇的个案,故而显得最为悲壮;他的每一次脱胎换骨的飘浮行踪却一再暴露他的刺杀企图,使得他苦心孤诣的复仇计划毫无秘密可言——这样看来他的计谋水准似乎不足以完成天狗吞月般的大事。但,他一门心思就是要复仇,他像一个不顾一切而背离大势、顶风作案的独行者,在北风的刀刃吹拂下,他愈来愈薄,化作了贴地而飞的纸人。我还知道,具有2500多年以上历史的赤桥村,村民历代就是以造纸为业的。
太原文史学者王剑霓经考证确认,战国豫让桥确址在赤桥村。他查阅《吕氏春秋》,发现在“季冬记·序意”篇记载:“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渠,渠下豫让寐,佯为死人”欲刺襄子。引文恰好填补《史记》、《战国策》载“襄子当出,豫让伏于当过桥下”之“两当”之阙。结合实地考察,王剑霓认为囿古代帝王蓄养鸟兽之园林,赵襄子所建和所游的囿,其址在今太原市晋源区晋祠北的赤桥村。因为定襄、赵城、襄垣、顺德府等处豫让桥在当时都无建囿的条件,因此说它是豫让剌赵襄子之桥一说不能成立。
我们的汽车出太原城区一路向西南疾驰,三晋大地逐渐呈露出它的自然景致,苍茫辽阔的田畴被厚达一尺的积雪覆盖,明晃晃的太阳在赵国的天空低悬,将白雪照成了棉花和骨灰。偶尔有突然冒出来的高楼群,像一个个拒绝入境随俗的黑客,周围寸草不生,手指头粗的树苗就叫景观植被?最后树还没有长成,可能房子就成危房了。这样的小区用铁栅栏箍着,这般耸立在荒野,挺傻帽,像是在等待排空发射。谁来买这样的住宅呢?
刻意“做旧”的晋阳城占地广阔,城墙在阳光下发出暗淡的青光,它在尽力吃进热量,准备在夜晚用于反刍回忆。再往北走,连绵而来的吕梁山余脉西山,以一种“虎行似病”的慢性,将铺天的石头演绎为一脉青绿,而山顶的积雪加深了斑斓的色素,山势更像一只横卧的黑虎,将汹汹而来的平原挡在远处,不让靠近。
就在这个缓冲地带,密集的低矮房屋扇子一般摊开,那就是赤桥村。汽车顺“官道”进入村口。我看见有几十亩打围的空地,司机对我说,那里两年后就将是山西省文学院的创作基地。
村口看不到一个行人,过于密集的农家住宅关门闭户,门口堆砌的积雪用一个个的锥体反射阳光,毫无融化的迹象。因为省作协在本地选址,司机多次来过赤桥村村口一带,但没有进过村,以至走错了两次。好不容易见到一个村民,听说是来看豫让桥,他用手一指:“顺着官道走,看见最大的槐树就到了。”
赤桥村可以用几个元素来归纳综合:古槐、古渠、古桥、旧道、古作坊、古宅。这不是暗喻,而是明示了它拥有的至少2500多年的沧桑历史。
村里的水泥路并不狭窄,但沿途可以看到不少灶台一类的废弃物。司机说,此地深受“国士”义气感召,有救厄济困传统,所以清朝时期此地乞丐云集。另外一个原因是造草纸需要把原料稻草、麦秸蒸熟,村里到处都安有大铁锅,铁锅下燃大火,火下是一个高宽约各2米,深度约4米用来盛放炉渣的炉坑,俗称“锅圪斗”。一到冬季,乞丐无处安身,就钻进锅圪斗里取暖活命。
我看到几棵大槐树,树身覆有少量积雪,龙身横斜,早被寒风拔光树叶,依然俯仰自得,具有鸡皮鹤发的苍迈。赤桥村古槐有15株,千年以上者9株。估计我看到的均在千岁之上。
看到一个农妇在一个毁去围墙的小院里忙碌,她身后有一株硕大无俦的槐树峭拔于青天之下,下车询问。她说,豫让桥就在豫让槐下面!
足需五人合抱的豫让槐缠满了红布,一树从腰部分出三枝,被保护者用灰色的钢条予以固定。这是否是“三家分晋”的隐喻呢?我觉得是。树下有一个小交叉口,官道分出两翼,斜插民宅。门墙边依着一些废弃的大磨盘,还有一些有棱有角的青石和榫头。仔细一看,上面刻有花纹。阎庆梅说,那是不是豫让桥的望柱呢?老妇回头:“是的,那就是豫让桥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
老妇姓田,在赤桥村生活了六十年,她只是说,大跃进时期,豫让桥被填埋在地下。原因是水利改造,智伯渠只能走暗渠,古渠道便被铺平,残存的豫让桥便被埋入地下,因而没留下遗迹。豫让桥的一段桥头望柱石栏杆以前是保存在这个大树下的农家小院内,现在我看到的,却是扔在了路边。
豫让桥就在豫让槐的东南角几米的地下。大槐树后有一个小院,堆满了煤炭,院墙上钉着一块铁牌:“豫让桥遗址”,落款是晋源区政府。据记载,豫让桥跨晋水北河的智伯渠,南北走向,砌勾栏围护,宽9.2米,长5.2米,呈扁型,原桥为明代所建。关于“赤桥”一名由来,《山西通志》说:初名豫让桥,宋太祖凿卧虎山,血流成河,更名。另一种说法是,当年晋国六卿之一的赵毋恤战胜智瑶,在渠上架桥,方便交通并以火克水,取名赤桥。
有学者指出,从地理位置上看,豫让桥应当是由古晋阳城出西郊后的第一座桥,应当是豫让离开其“市”(晋阳城)而赵襄子出城随后不久既可到达的同一个地方。就是说,由官道与智伯渠构成的大十字结构,决定了赤桥的空间布局,交汇点就是豫让桥。
为了报答知己智伯,豫让首次潜入厕所刺杀赵襄子失败后,吞炭变声、生漆毁容的豫让以一个“新人”的陌生化身份,再次上路了。他突然倒卧在复仇中途。《吕氏春秋》说:“赵襄子游于囿中至于渠,梁下豫让寐,佯为死人”,欲刺仇敌赵襄子。“佯为死人”的豫让依然无法掩饰那凌厉的杀气。
一个人如何掩饰那自骨髓蒸腾而起的杀气?可以掩饰者,就定非侠士。
此树村里人称“豫让槐”,树高约6米,树围5.6米,是赤桥村树龄最长、树径最粗的古树,有人称之为“唐槐”,但另有资料指出,其年龄逾两千岁,我估计超过了晋祠中的古槐树树龄。站在古槐干枯的枝条下环顾,几条寂静的街道在冬阳下蛰伏,微风吹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的纸屑,参差错落的新旧房屋,静守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官道逶迤,向西边的山麓爬升,路边半堵矮墙后面掩藏着一片黯淡的琉璃,即使是浸满岁月的旧气,积雪提高了它抵御风寒的骨色,让我眩目。
从豫让古槐向两端望去,有小路曲弯穿行于民居宅院,那是智伯渠流经之地。据人探察,智伯渠今天还在。它只是被覆盖掩埋,逸出了常人的视野,因而保留了下来。村中还有一小段裸露的渠道,可以看出它的状态,与邻村一段曝于荒野田间的渠道相比,也可以感觉到蛰伏于地下的历史,因为迷路反而得以保全。安静躺在这条弯曲小路之下的智伯渠,钩稽着我的想象空间。
闻名遐迩的《晋祠志》作者刘大鹏(1857—1942)世居赤桥村,他在书里描述说:“(赤)桥西有观音庙;东向,内肖豫让像。庙前壁有刘丽中先生午阳大书‘古豫让桥石刻,旁题邑令殷峄‘豫让桥诗。桥之四周皆民居,民多资晋水造作草纸,以遂其生。”这暗示所谓的豫让祠不过是依附观音的香火而生,那么,血气喷张的豫让需要成为观音大士的“陪祀”吗?
哪里还有豫让塑像呢?我很失望。小院里有一个小土坎之上,是两间红砖平房,墙壁上钉有一块白色木牌,有挺阔的宋体和隶书:“太原市文物保护单位——赤桥观音庙”,落款是“太原市人民政府二00九年九月三十日”。刚才与我交谈的农妇见我虔诚,就打开了观音庙大门。天!里面堆满了废旧的农具、箩筐、粪勺子和一大堆脚手架,所有的光线来自靠墙左侧的一扇小窗户。
正对门的墙头,立有神龛,上边供香炉,香炉后放有黄纸糊的牌位,写有“观音老母之神位”。我看到粉墙上有漫漶的彩色壁画,从颜色鲜度而言,估计绘制的时间不会太久。
一侧身,我看见豫让了!
豫让塑像在左侧靠墙位置,泥塑,彩绘,头和右臂已经不翼而飞,脖子上仅有一根连接头颅的木桩,端坐于一方神台之上。左手向下虚按,挺胸凸肚,挽起的裤腿下是一双鼓筋暴涨的赤脚。从他挺直的身形而言,似乎成竹在胸,不过已经不像一个来自民间的刺客,而是摇身一变,成了位列仙班的神祗。也许,在民间传统的价值判断里,像豫让这样一个忠诚勇敢的人,应该享受到不一般的礼遇。但一旦礼遇,就只能让他充当观音护法的角色。虽然塑像已残,但小香炉的香灰似乎在说明,他的香火一直未断。看到我在鞠躬,农妇回家拿来了三炷香,我点燃,插入香炉。根据香炉的情形分析,肯定很久都无人上香了。
农妇对我说,这原来就是观音庙,豫让祠在偏屋,后来偏屋塌了,才把几尊神“请”到一起,一块搬进来的还有关老爷。
走出小庙,看到积雪堆满了屋顶,屋檐被压得高高翘起,我估计这危房怕不容易熬过这个冬天。我拍了几十张照片,农妇好奇滑入景框,我按动快门。她、皱纹、一地白雪和她的庙。她追着我问:“什么时候再来,请把照片给我!”我答应,一定请人送来。
站在豫让槐下面,一个电光火石的意象飞驰而至:智伯却被韩、赵、魏三家攻灭,瓜分了领地,豫让逃到山里,思念智伯的好处,他尤其怨恨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做成漆器,盛了酒浆狂饮。为此,他发誓要为智伯报仇,行刺赵襄子。
“人头做酒杯,饮尽仇椎血”的古典复仇意象,在历史上频频举杯。不但用它来做盛酒器具,而且还可以用来诅咒,制服别人。匈奴攻破月氏王之后,就用月氏王的头颅做酒器。宋理宗的光荣之头也被当做酒器。但可以说,赵襄子拿仇人智伯的脑袋做酒器,不但是意识形态仇恨学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是中土“身体政治”的急先锋。
为了知己的头颅,豫让开始了复仇。
《公羊传·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何休注:“一往一来曰推刃。”由此形成一往一来的循环报复。“推刃”不已的豫让,早已化作厉鬼,不惜用右臂割下了自己的脑袋提着夤夜而走,他要去换回那个被酒灌得酩酊大醉的知己头颅吗?
我估计,他完成了夙愿。
所以,豫让的右臂和头颅,再也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无刀也无头的豫让枯坐在此,他的左胸上长出了大片青苔。那扇距离他不到三尺的破窗户,北风呼啸,面对满屋子的废弃物,即便回来了,那头颅,如何找得到安身立命的所在?皮囊之累不但是当官不遂的古式文人的概叹,恐怕也是心怀恩义的人,难以消受恩义钝刀割肉式的慢性,只能在“引刀成一快”的决绝中实现身心两忘。
所以,在黑暗的旷野,豫让的头颅像鬼火那样一去不回。
在豫让塑像前方,有一块清同治六年由里人刘午阳所书的“古豫让桥”石碑,静静躺在黑暗的角落。我借助打火机的暗火,看见石碑的一角上,题刻着清乾隆年间时任太原令的大文人殷峄所作的《豫让桥诗》:“卧波虹影欲惊鸥,此地曾闻手戡仇。山雨往来时涨涸,岸花开落自春秋。智家鼎已三分裂,志士恩凭一剑酬。返照石栏如有字,二心臣子莫经由。”
站在槐树下,想起《吕氏春秋·序意》里,插入了一个颇有深意的人物:青荓(Píng)。
青荓是赵襄子的陪乘,在桥边,襄子感到就下命令说:“去桥下看看,好像有歹徒。”青荓到桥下一看,原来是豫让躲在角落里躺着装死。豫让见青荓来了,就呵斥说:“滚开!我还有事。”青荓忙说:“打小我就和你相好,如今你要做大事,我要是说出来,就违背了交友之道;可是你要杀害我君主,我要是不说出来,就违反了为臣之道。看样子,我只有一死了之。”说完就退开几步,挥刀自杀。青荓并不是乐意死,而是更看重为臣的节操不能丢,更痛恨为友的情谊抛弃了。青荓和豫让,可以说是为朋友情义而死。
这些情这些义,可以烧开男人们的血,却很难让我们的身形在厄运变故中挺直,哪怕就是再坚持几分钟。但随着阅历增加,血液被世故与酒色所冲淡,到了永远无法蒸腾的心境,世故者说这就是古井不波境界,知识精英会嘲笑这样的愚行,他们骈四骊六地谈论着纸上的自由与幸福,珍爱生命最重要,在这个盛产纸张的村落,我绝不相信这样的自欺之谈。世故与学识很多时候就像堆积在豫让祠的积雪,除了压垮房屋,毫无用处。想到这里,我就很冷了。
出赤桥村,夕阳像盛满血的塑料口袋悬在最高的槐树上。偶尔见几只乌鸦精怪的身影,几上几下,口袋就破了,夕光恍如智伯渠的水,慢慢注满了炊烟四起的村庄。
北宋胡元任的《苕溪渔隐丛话》里,收有一个酒令:
“令”:鉏麑触槐,死作木边之鬼;
“答”: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
我去年在写作侠义文化专著《复仇之书》时写过鉏麑,熟悉他的生平,这是一个春秋时的晋国力士。喜好仙鹤的晋灵公恼怒于大臣赵盾多次进谏,派鉏麑行刺赵盾。他深夜遁入赵府躲在槐树上,见赵盾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忍下手,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可以说,鉏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自杀来中止行刺、为正义而殉身的刺客。把这样的人与事用于划拳的酒令,他们可能是木边之鬼,但绝非山下之灰。这酒,男人们喝得就有豪气了吗?这些人即使往血管里添加火药,却从来不会为情义引爆自己,哪怕是走火一次,也是百年难遇。
所以说,酒,是水也。
鉏麑碰死在槐树上,而赤桥村至今能让我目睹旧迹的,依然是槐树。套用鲁夫子的箴言,“一株是槐树,还有一株也是槐树”。人总会死的,连石头也在风化和剥蚀,但槐树以纵贯三晋大地的深犁,低尺度地举起了一蓬黑血。读唐朝诗人胡曾《咏史诗·豫让桥》,中让我不禁回想起那从豫让桥突然飞起的杀气:
豫让酬恩岁已深,
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桥上行人过,
谁有当时国士心?
白雪之下,那个自刎的复仇者已经不能说话。再没有比一心等待着失败的复仇者,更让时间绝望的了。那足可以使时间失去耐心的豫让,枯坐,无头,浑身扑满天光的尘埃,他的右臂提着自己的头颅在历史的背光处觊觎,完成他的诅咒。他剩下的身体,毫无牵挂,等待庙宇垮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