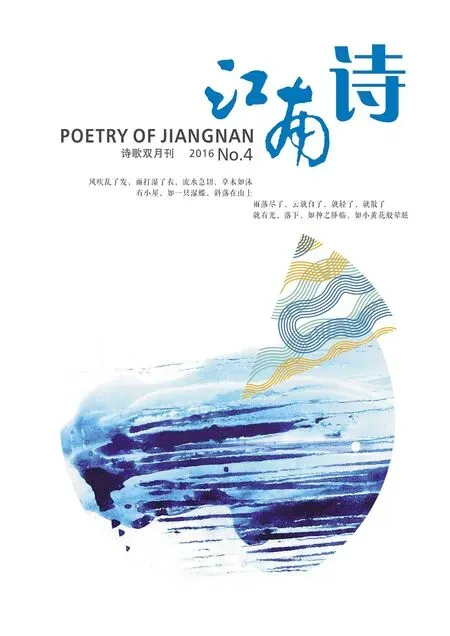悲戚面容下的灵魂虚肿症
梁雪波
不知不觉中,海子离开人世已经二十多个年头了。这位天才诗人生前籍籍无名,在贫困和孤独中写作,渴望被世人接受而不可得。如今他的生和死已经被神化,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的祭日也已成为一个盛大的诗的节日,这是他活着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今天翻开海子的诗,我惊异于那些抒情短章在技巧上的简单,但却有着“刀劈斧砍般”的力量。那些质感的语象被反复吟唱,不断擦亮,成为生命本身的呼吸放射。海子在写作中吸收了民歌的元素,句式错落复沓,因此具有易于朗诵和歌唱的音乐特征。在他的诗中充满了个人行动性的语汇,例如:劈、砍、埋、抱、走、打、飞行、摔碎、燃烧、撕裂等等,并一再将这种行动推进到极端,显示了意志的决断。在关于荷尔德林的随笔中他总结道:诗歌不是一种修辞练习,而是一场烈火。他自觉地放弃了专注于修辞技巧的写作方向,将词语倒入血与肉铸就的灼热之鼎,用生命燃烧诗篇,这种狂飙突进的写作激情推动着他的生命投向诗歌的火焰,而燃烧的生命更加剧着诗歌辉煌的吞噬,并最终导致他在25岁时的轰然爆炸。我相信即使没有现实的刺激等偶然因素,海子也会提着诗篇和头颅走进死亡,这是剧烈燃烧的宿命,无法阻挡。以写作燃烧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子无疑是一位“身心合一”的诗人。
因为海子的死,每到春天,一个本应莺莺燕燕的日子就渗出了一种苦味的汁液。而海子又是一个特别敏感于季节轮转的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有大量关于春天、土地、村庄、河流、桃花的诗歌。这些诗篇对应着诗人在精神高压下的内心景象,黑暗和幽深的被人们过滤掉,而那些明亮色彩的词句正好适合装点每年一度的诗歌盛典,尽管这场盛典因具有缅怀性质而不得不带着一丝感伤。而海子生前的贫困和传奇般的死,他明亮而忧伤的抒情气质恰好满足了人们多重的心理需要。
每年3月26日,一个生前被时代遗弃的诗人被人们呼唤而出,但已不是“低低的怒吼”,也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精神的“复活”,它更像是一次表演者和观众的默契合作,其中也不乏一些现实利益的驱动。当诗歌精神衰微、诗歌边缘化的今天,纪念海子成为提醒人们现代诗的存在以及缅怀一种古典精神的仪式。虔诚的人们涌向水泄不通的礼堂,聆听朗朗的颂诗声,或者风尘仆仆地从四面八方赶往诗人的家乡,在那矮小的坟茔前,他们声音颤抖,表情悲戚,忆及诗人短暂的一生,很多人流下了眼泪。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个日子里唤起一种内心的感动,以表明自己是多么地热爱海子、热爱诗歌。同时这种自我感动还要求着一种群体性的表现,如通过集会、朗诵、表演等形式来共同分享彼此的感动与感伤,“因为意识到与别人一道,感伤变得越发加倍,滔滔不绝的汹涌感伤最终上升到了崇高的地步,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崇高”,甚至在这种感伤的氛围中容不得别人不感伤。这正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Kitsch”,一种廉价的精神替代,一种“灵魂虚肿症”。
事实上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深入地阅读海子,而能够与之对话又需要具备怎样的灵魂质量?人们害怕的是置身于时尚潮流之外。对于海子,有些人的阅读仅止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有些人沉醉于海子的死亡神话,还有人悲愤于这个时代的物质化并煞有介事地为诗歌宣读了悼词。他们有所不知,海子并不是诗歌的终结者,诗歌也不会因为谁而停止脚步,它一直在强劲发展。作为诗歌链环中的一个,海子的价值和意义毋庸置疑,但是在纪念海子、凸显海子诗歌价值的同时,也在形成新的遮蔽。这种遮蔽,既有对其他已逝诗人的冷淡和遗忘,更有对现在仍然坚持写作的诗人的无知和漠视。对于前者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骆一禾、戈麦、昌耀、胡宽、余地、方向,以至更早的死于文革中的林昭等等。至于当下诗人的尴尬处境,除了生存上的压力,再看看如今诗集出版之难就可知一二了,据我所知,除了海子、顾城、席慕蓉、徐志摩等少数人的诗集尚有较好的销量以外,其它诗人的诗集几乎没有任何市场,是注定赔本的产物,各出版社编辑因而将诗集称为“出版毒药”。诗人已被以利益生产为主导的市场无情地淘汰了。困窘的诗人们于是羞于以诗人称道,大众于是以为诗人已是一种接近绝迹了的物种。于是,这场发生在春天的假诗歌之名的集体纪念活动,更像是一次加深遗忘的仪式。纪念就是为了更快地遗忘。我们年年纪念鲁迅,数万名专家学者吃鲁迅,而鲁迅在哪里?我们纪念海子,而诗人的独立、高拔、不畏时代渊暗的精神在哪里?诗人的赤子之心在哪里?人本与文本的同一共振在哪里?在社会日益世俗化的今天,曾经一文不名的诗人海子,已经成为文青和小资们嘴里一块嚼来嚼去的文化口香糖,这正是这个时代奇特的文化景观。
这大概就是诗歌的命运,也是海子的命运,尽管身在天国的他已无法左右人们的误读,但他期待的诗歌的春天并没有到来。事实上,对海子所跃入的精神绝境,我们缺少面对的勇气,对他所忧思和追怀的文化母题,我们已失去了探究的兴致。海子所深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认为,要改变世界的黑夜状况,必须回溯到诗歌精神的源头,必须穿过平庸而悲凉的时代牧场,将一个时代的转折植入文本之中,并进行神学式的改写。他指出“一个悲剧性时代的可怕的闲适”,其悲剧性在于,一个闲适的时代被催逼成一个撕裂的时代。随着神性和人的自我的双重失落,神降为了“自然之强力”,把人从内在生命的核心撕扯到死亡之异域。而这样的“撕裂”、“撕扯”,在我们这个矛盾重重的时代,已被敏识者以及普罗大众切身地感受到了,但我们尚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我们尚没有在一个破碎的时代对神性葆有坚贞,对遭逢的苦楚葆有忍耐和“改写”的欢欣,这正是一个贫乏时代的真实图景。
对海子这样一位新诗史上极为重要的诗人,我们虽然年年纪念,但至今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还原,而在“海子神话”背后又有多少持守、忧思,多少“在幽暗中的努力”是被遮蔽的?好在真正的诗人并不在意这些,他们依然前行,诗歌依然在路上——
“永远是这样
风后面是风
天空上面是天空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