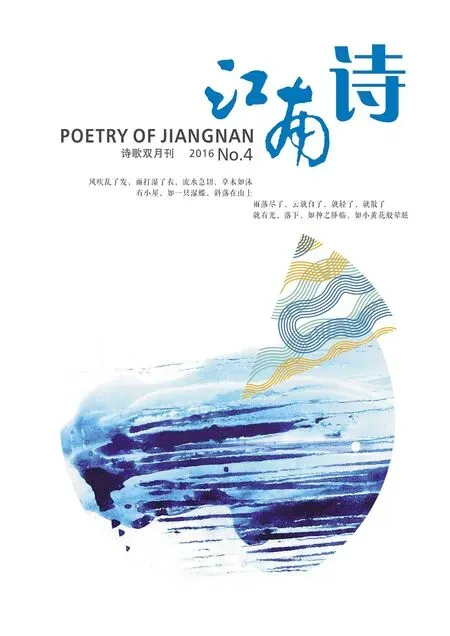“我们在世俗的旷野里丧生”
张猛
翻开俄罗斯作家、诗人丹尼尔·哈尔姆斯(1905—1942)的生平履历表,我们会很自然地把他与 “非主流”联系到一起:他1924年开始写作,经常在彼得堡的各种场合朗读自己的诗歌,却鲜为人知。1926-1927年间,他和友人组织过“契纳利”、“左翼”、“左翼古典主义者研究所”等几个文学团体,影响甚微。1928年1月24日,他参加“真实艺术协会”(ОБЭРИУ)组织的文学晚会并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第二天他的剧作《伊丽莎白·巴姆》遭到《红色报》的炮轰,评论者称该剧“恬不知耻的直白,意义晦涩,无人能解”。20年代末他开始投入儿童文学创作,儿童诗歌作品以其滑稽可笑、妙趣横生的口头创作风格受到读者喜爱,而根据他的同时代人回忆,他对儿童充满了厌恶,还曾经在日记中策划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消灭掉儿童和老人。1931年和1941年,他因为作品“反对苏联政权”和“宣传失败主义”而两次被捕,虽然数次假装精神病,也未能幸免于难。[1]这样的文风和个性,在盛产严肃文学的俄罗斯不能不算是个“异类”。
丹尼尔·哈尔姆斯主要的创作形式为诗歌、微型小说和微型室内剧。尽管有学者指出,他的创作沿着果戈理的传统,发展了其中的荒诞、狂欢化和笑的艺术[2];但总体来说,他所追求的文学样式,以及他在作品中以讽刺幽默、轻松随意的笔触勾画的形象和场景,他指认的死亡与肉欲、崇高与庸俗、真实与谬误,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苏联文学极不相称。因此,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他又被称作“俄罗斯的欧洲人”。
一般认为,20世纪兴起于欧洲国家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于二战以后,而丹尼尔·哈尔姆斯主要的创作时间是20世纪的20、30年代,从时间上似乎没有可能将两者联系起来。但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场波及文学、艺术、哲学、建筑、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其发端并不能进行确切地定位。英国文论家凯文·奥顿奈尔也指出,“后现代主义不应被看成一个界限明晰的历史运动,而应被看成一种可能出现在任何时代的思想观。”[3]另有资料考证,以哈尔姆斯为代表的“真实艺术协会”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提供了经验。[4]据此,我们考察丹尼尔·哈尔姆斯的创作(本文主要以诗歌文本为例),可以参照后现代理论的相关研究,以期揭示“真实艺术协会”的作品内涵,探寻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
重复/无意义
在丹尼尔·哈尔姆斯从事创作活动的早期,曾经深受未来主义诗人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等的“超理性诗学”(заумь)的影响。他坚信,语言除了具有能指功能以外,还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他模仿赫列勃尼科夫的“星球语言”创作诗歌,制造玄奥难懂的物象的非逻辑化排列。譬如这首《做客》就堆叠了毫不相关的客体,像是语言在稿纸上横冲直撞,造成了“非此非彼”的效果:
老鼠邀请我到一个新房子的
茶碗里做客。
我很久都没办法进入房子,
费了很大劲总算钻了进去。
现在您对我说: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没有房子也没有茶,
什么东西都没有!
按照俄语语法的通常规律,“新房子的茶碗”是十分牵强的搭配,而诗歌末尾揭示“什么东西都没有”更是愚弄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文学家要为读者构建一个完整世界”的契约在这里失去了效力,哈尔姆斯的诗歌是让普通读者失望的文本,它是对更高智力的挑战。无意义的诗歌文本从惯常文学逻辑来分析,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无意义恰恰是对“意义”本身的反叛,“这种无意义的目标是否定特殊的期待,因此揭示作为它的隐蔽的背景和它的不定的效果的先决条件的艺术机制。”[5]无意义不再是“没有意义”,而是从对立的角度寻求抗争的意义。
如果说语义上的逻辑不通会使读者费解,那么无节制的重复更加剧了阅读的疲劳。哈尔姆斯似乎努力地想使自己的诗歌充当无聊和空洞的载体。这里的重复不再是为了加强语气,不再是为了铺陈声势,而更像是没话找话,将诗歌文本繁殖成碎碎絮语,如同梦呓。
曾经有一个木工[6]
但他是个干瘦的木工
抹浆糊的木工
他做椅子和桌子
用锤子做桌子
用榛树做桌子
大家都叫他伊万
他的父亲也叫伊万
所以大家也叫他伊万
他有过一个妻子
不是妈咪,而是妻子
不是妈咪而是妻子
她现在叫什么
我现在也记不清了
现——在——忘掉了
以上节选于哈尔姆斯早期创作的一首诗歌,幽默中略带讽刺,但是词语所传达的信息量寥寥。该诗的名字也颇令人头疼——《关于伊万·伊万诺维奇的请求和后来发生的事》,题目几乎已经涵盖了诗歌的主要内容。伊万是俄罗斯最为常见的名字,再加上他的父亲也为伊万,这个符号显得更加平庸。他的职业是木工,接着诗人列举了他具体的工作:“他做椅子和桌子,用锤子做桌子,用榛树做桌子。”这样的画蛇添足似乎是多余的累赘,但是恰恰因为这种反复,一个干瘦无力、平庸乏味的丈夫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为后来伊万向妻子求爱遭到拒绝埋下伏笔。按照后现代理论理解,“重复是任何真实性、统一性或独特性结构中固有的,重复通常被看做用来建构同一性。”[7]也许我们可以说,哈尔姆斯在一遍遍的复制中制造了一个景观——这是疏离于现实生活细枝末节中的片断的一次集中展览,读者从这种展览中窥见了隐藏在崇高意义里的琐屑和寡味,他们会惊叹真实的生活就是诸多思想匮乏、旨趣低廉的元素的合集,他们会从单调的重复里发现平庸生活的真实。
游戏/戏仿
丹尼尔·哈尔姆斯在生活里是一个善于搞怪的人。他的装束总是能在众人眼里脱颖而出:双排扣坎肩,高尔夫球裤,嘴里还叼着烟袋。他喜欢在别人面前变戏法,有的时候朋友们还会发现他坐在树干上思考。作家生活上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反映到诗歌里,有一种神奇的魔法效果。游戏无处不在,轻松和诙谐消解了严肃的结构与主题,仿佛是一种嘲弄。例如这首简短却意蕴丰富的诗歌:
所有所有所有的树木都是“必夫”
所有所有所有的石头都是“罢夫”
整个整个整个自然就是“布夫”。
所有所有所有的姑娘都是“必夫”
所有所有所有的男人都是“罢夫”
整个整个整个的婚姻就是“布夫”。
所有所有所有的斯拉夫人都是“必夫”
所有所有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罢夫”
整个整个整个的俄罗斯就是“布夫”。
该诗中的“必夫”、“罢夫”和“布夫”是作者杜撰的并没有实际意义的词汇(пиф, паф, пуф),目的是为了造成诗句末尾的押韵和对称,因为没有对应的外语词汇而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哈尔姆斯玩弄语言游戏,用三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词来代替概念的对等,似乎是为了表现大自然、婚姻和整个俄罗斯都是虚无的符号,没有实质上的所指。然而,树木、姑娘与斯拉夫人作为“必夫”,石头、男人和犹太人作为“罢夫”,中间仿佛又暗含着联系。这种相对意义上的联系和绝对意义上的孤立折射出哈尔姆斯亦庄亦谐的游戏规则。哈尔姆斯对于词语的结构和发音很感兴趣,他经常“漫不经心的”创造新的词汇,或者是将日常熟悉的单词更改个别字母或颠倒组合的顺序,又或是特意强调某个字母(加黑、大写),在单词上标注正确或错误的重音[8]。阅读哈尔姆斯的诗歌,仿佛在穿越布满埋伏的雷区,读者需要小心翼翼,不然就会因为“似曾相识”而犯错,落入世俗的窠臼。
除了文字游戏,另一种文本中的游戏表现在他对于经典作品中的桥段以及基本形成定论的文化名人的言行进行戏仿。《两个黑人女士的梦》(1936)就把俄罗斯文学巨匠、《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列夫·托尔斯泰进行了戏谑式的描写。托尔斯泰走进了黑人女士的卧室,“脱掉了大衣,又脱掉了套鞋和靴子。”这与托尔斯泰在小说和评论中呼唤的道德与善显然是大相径庭,传统的思想探索者形象在哈尔姆斯那里坍塌了,“托尔斯泰倒了下去。多么可耻!整个俄罗斯文学都在尿壶里。”不仅托尔斯泰,“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也经常遭到他的奚落。这些在传统观念里的神圣形象经过他的解构,立刻变得一文不名,甚至成了下流龌龊的伪君子。这一点可以见到后现代文本的迹象,因为“在后现代的文本中,一切都遭到戏仿,由里到外的反转,贬低——包括文本建构的自身规则,游戏规则本身,最终一切丧失了意义,变得相对化。”[9]哈尔姆斯通过玩世不恭的游戏和戏仿,解构了符号被赋予的固定所指,也使自己站到了传统文学的对立面。
身体/欲望
“和精神相比,肉体是速朽的、虚荣的、哗众取宠的。”这是主流的价值观念对于存在与虚无的界定,其中的褒贬抑扬不言自明。在以往的文学实践中,重灵魂、轻肉体一直是作家信守的准则。而尼采哲学重新定位身体,认为信仰实在的身体比信仰虚幻的精神更具有根本意义。20世纪的法国新尼采主义发展了这一观点,用“身体和动物性取代形而上学理论”,上升为人的主体[10]。阅读哈尔姆斯的诗歌作品也能够发现,他对于“身体”,尤其是对于人的动物性身体兴趣盎然。
我已很久没有伏案写作
无力的我疲软松弛
笔杆从手中滑落
妻子骑坐在我身上
我一把推开稿纸
亲吻自己的妻子
在我面前挺立的一团
保持着静默。
我吻着妻子的侧背
脖子,乳房以及下腹
径直在两腿之间嘬动嘴唇
那里爱液流淌
以上是《妻子》一诗的开头部分,后文还有更多对于性爱场面无所避讳的描写。哈尔姆斯这里所谓的“笔杆滑落”、“疲软松弛”都暗示了“性的衰竭”,无处下笔其实是生命力倦怠的体现。但是妻子的爱欲重新充盈了生命力的表征与内涵,“性”被作者提高到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在这首诗里哈尔姆斯巧妙地运用了两处对比:妻子与肉欲,写作与做爱。动物的欲望满足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异性是最主要的一种。欲望书写有违恪守节制的传统伦理,但是发生性爱关系的又是自己的“妻子”,而不是巴塔耶所强调的作为男人色情对象的“妓女”[11]。这样囿于规范下的暴露给诗歌赋予了巨大的张力;写作是精神演说,而做爱是肉体斗争。面对精神和肉体,“我一把推开稿纸”,选择了人性的动物层面。或许作者意欲指出,肉体和精神相比,更容易满足和实现。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身体上的满足会激发精神上的创造,是写作的前提。因为在诗歌结尾,从性爱中获得极大快感的作家摊开纸笔,高声叫道:“就让字母和字母组合吧/拽一根绳子/把各种念头缠织!”
另一首诗歌《变形航空》(1927)同样肯定了肉体欲望作为存在方式的亮点。诗中的少女因为和飞行员的肉体接触而体验到飞行一般的快乐,“斧头”作为男性生殖器的隐喻既有快意的内涵,也有死亡的指向——“做爱”与“飞行”是告别这个庸俗地球的两种方式。“飞离地球的太空体验是作为具有正面意义的奇迹出现的”[12],而当玛德琳和飞行员到了暮年,青春不再,没有性能力,也就丧失了体验摆脱俗世的“超能力”。“飞行员在路途上变老。/挥了挥手——飞不动了/伸了伸腿——走不动了/稍稍竖了一下,立刻疲软倒下了/后来时光流逝却不会腐烂/可怜的玛德琳惆怅终日/在火堆旁编着鞭子/驱赶着偶然而至的梦想。”肉体作为“奇迹”的向导,在哈尔姆斯诗歌中是不容忽视的存在。诗人对于“奇迹”有浓厚的兴趣,为此他曾经潜心研究玄学,还吸食大麻记录自己的幻象。而关于性爱愉悦感与“升天”的联系,在《诱惑》、《窗户》等诗歌中都有体现。就连他自己的日记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字句出现:“我想让你为我口交,爱你。”(1927年4月)在他那里,肉体有一种不受伦理桎梏的本能,能够冲破世俗的藩篱与奇迹相遇。
遗忘/消失
记忆是时间的仓库,方位是空间的坐标。时间和空间的确立,一直是理解文字作品的必要条件。传统文学作品如小说凸显“时间”、“地点”和“人物”,而后现代作家则极力模糊这些因素。在哈尔姆斯的诗歌中出现的“遗忘”和“消失”的主题,恰恰是这一努力的先声。哈尔姆斯的许多文本都不是在建构一张清晰的面孔,一副明朗的图案,相反,棱角和层次由于一遍遍的打磨失去了质感,像透过毛玻璃观察到的景象。
哈尔姆斯经常在自己的日记中抱怨找不到写作的素材,因为没能抓住瞬间闪过的灵感而懊恼。他也在诗歌里讨论写作,“不止一次地描写想写又写不出东西的状态”,这有点儿类似于“元叙述”,是“关于写作”的写作。
我久久注视着苍翠的树木,
宁静充满了我的心。
仍旧像以往一样,没有大的,独立的想法
又是那些碎片,断章和琐屑。(1937)
把“遗忘”作为写作的源头,“破坏了言语的的流畅,阻碍了它的表达,同时它急剧地转换了话语生成的情境。”[13]这就打破了遵循一定叙事结构的写作模式,使文本变得无章可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结构主义的挑战。哈尔姆斯的“遗忘”更多地体现在他的微小说中。例如在《坠落的砖头》中,一个行走在路上的人因为突然掉落下来的砖头,忘记了自己去商店买什么;接着,第二块砖头砸中了他,他忘记了要去哪里;第三块砖头使他忘记了来自何处;第四块砖头让他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姓名……这种充满荒诞色彩的“遗忘”交织着悲喜剧的情感,探讨的却是严肃的存在意义的问题。
“遗忘”中断了时间,而“消失”则抹去了空间,使人的存在变得摇摇晃晃,没有了确定和均一的感受。下面的这首表现“消失”主题的诗歌正印证了这样的感受。
彼得罗夫有一天走着去森林。
他走啊走,突然消失了。
于是柏格森说
这莫非是梦?不,不是梦。
他望了望,瞥见护城河
而护城河里坐着彼得罗夫。
于是柏格森朝那儿爬去
爬着爬着突然消失了
彼得罗夫满脸惊讶:
我的身体肯定出了毛病。
我亲眼看到柏格森的消失。
这莫非是梦?不,不是梦
哈尔姆斯在诗中略带戏谑地描写柏格森亲眼看到彼得罗夫的消失,这种突然的中断是对柏格森提出的“时间是动态的流动,呈现出经常的和永恒增长的量变”学说的否定。诗人在这里想要表明:时间流动并不是持续的,偶尔的断流在生活中是可以出现的。“消失”是哈尔姆斯追求离奇荒诞情节的惯用手段,这或许也和他孜孜以求的“奇迹”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不确定性/怀疑
对绝对精神和普遍真理的怀疑是后现代批判的一个主要方向。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所有的道德律令和科技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把人推向分化的两极。“在文化接管了生物本能对人类的控制权,并完成了人类身体和心智的进化的同时,语言区分和决定着社会表现行为的主体。然而,这一过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又不断地在文化的多样性和产生新的社会实践的自由中重申自己的权力。”[14]哈尔姆斯诗歌中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对人存在本质的追问上,例如这首写于1929年的诗歌:
我从哪里来?
为什么我站在这儿?
我看到了什么?
我这是在哪儿?
呃,请允许我掰着手指头
把所有的东西数一遍吧
——(他掰着手指数起来:)
凳子,小桌子,大桶,
提桶,小调车,炉子,
扫帚,箱子,衬衫,
球,打铁车间,小甲虫
带绳套的门,
带绳套的把手,
放在手帕上的四把小刷子
天花板上的八个小按钮。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在我们一生中的某些时刻,谁都无法避免偶尔陷入精神上的困境,面临这样的质问。一旦怀疑深入下去,业已形成的理性包装就会遭到一层层盘剥,我们会痛苦地发现,任何绝对性的描述和定义都不能尽善尽美地给予解答。诗中的“我”同样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列举身边的可见实物。在作者看来,这些人工创造的物件和自然界的生物就证明了人的存在,我们的“生产”反映了我们的历史和现在。由产品来确定生产者,这种认识上的倒置也反映了生产者本身的不确定。我们自己不能够确定自我,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而是要靠外在的事物来证明。而没有生命的外物无法表述创造者的非物化特征,因此我们的存在也变得不确定了,我们的形象依附于我们生产出的物的形象。从这些看似确切的列举中不难体会到哈尔姆斯的痛苦,他所理解的自我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淖。
对存在的确定性的怀疑时常打乱了哈尔姆斯的写作路径,他的同一篇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姓名有时候会出现更改、变形,似乎叙述的对象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容器中的液体。他还描述过如何给男人和女人寻找配偶:所有17到35岁的应征者脱光衣服在大厅里走动,脖子上挂着写有自己名字和地址的牌子,以便于有意者致函求爱。这里的“牌子”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隐喻:任何人都有可能交换牌子,成为另一个人。因此,词语所赋予人的确定意义消失了,“意义只存在于语言中……我们创造了话语,也因此同世界建立了一种随机的联系。我们将某种规则强加给世界,又用这种规则来构建世界。”[15]哈尔姆斯为我们描述的是一个充满了相对意义的世界,规律的必然性被偶然事件所打破,在他那里,变化才是常态。
结语
丹尼尔·哈尔姆斯生活在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和成熟的年代,他的作品由于受到未来主义的影响,具有先锋派诗人的诸多特点;也有俄罗斯评论家指出,哈尔姆斯是俄罗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 “他的诗学将无法结合的成分结合起来,倒置世界的外观,这都是超现实主义的特点。”[16]在他的超现实写作中,正透露出后现代文学的某些特征:他写作非逻辑化的诗歌,运用无意义的重复抵制合乎规则的意义表达;他无视语言的规则,用文字游戏调侃正统文学的庄重;他袒露人的生理欲望和肉体崇拜,将身体置于绝对精神之上;他描写人的思想空虚和失语症,以“消失”和“遗忘”的主题向旧的时空观挑战;他质疑存在的意义,表现人和世界的随机性联系。
从先锋文学和乌托邦的关系角度来看,丹尼尔·哈尔姆斯和苏联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理念上也有巨大的差异。他以自己的创作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和权力的神话,像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一样,“不再像大多数苏联作家那样执著于表现鲜明的政治——历史——社会观念,而是将反乌托邦精神融入自身的艺术形式探索中,从而在文化立场的高度而不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高度实现了对于国家乌托邦主义的反动,其作品中透出的怀疑主义与对荒诞的冷峻感克服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本的单纯的理性主义激情。”[17]
“我们在世俗的旷野里丧生”,在丹尼尔·哈尔姆斯看来,世俗生活的种种高尚与伟岸,道德与伦理,甚至是严肃的表情、不苟的态度都构成了存在的枷锁,规训了人最本真的天性。因此,他不屈不挠地同业已形成的规则作斗争,努力想要逃离这个理性构筑的世界。1939年,由于害怕被派往前线参加战争,他费尽心思假装精神病人;1941年,他再次被捕,又一次在半理智、半疯癫的状态中被送入医院。后来诗人的生存状态已不得而知,直到1942年2月2日,在监狱医院的病人档案中提到他的死亡。这一次,哈尔姆斯就像他自己诗歌中描述的那样,一个人离开了家,和这个世界做了永远的告别——
他总是直直地往前走
还总是向前眺望。
不睡,不喝,
不喝,不睡,
不睡,不喝,不吃。
直到有一天在霞光中
他走进了幽暗的森林。
从那一刻,
从那一刻,
从那一刻他消失不见。
[1]:Кобринский А. Даниил Хармс. М.: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9. С.490-497.
[2]:Жан-Филипп Жаккар. Даниил Хармс и конец русского авангарда. М.: МСМХСУ, 1995. С.187.
[3]:(英) 凯文·奥顿奈尔:《黄昏后的契机:后现代主义》【M】,王萍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页。
[4]:Маньковская И.Б. Эстетика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а. М.: АЛЕТЕЙ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С.13.
[5]:(英)理查德·墨菲:《先锋派散论: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和后现代性问题》【M】,朱进东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页。
[6]: 原文为беренда,是作者杜撰,与之相近的词是барюлька,意为木雕玩具。译者注。
[7]: (美)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M】,章燕、李自修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414页。
[8]:Валерий Сажин. Мир Даниила Хармса./Даниил Хармс: Мал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ЗБУ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0. С.8.
[9]:Липовецкий М.Н. Русски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М.: Уральский гос. пед. ун-т.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7. С.21.
[10]:张之沧:后现代身体论【J】,江海学刊,2006(2),27页。
[11]:巴塔耶.:《色情史》【M】,刘晖译。北京:上午印书馆,2003年,117-124页。
[12]:Валерий Сажин. Мир Даниила Хармса./Даниил Хармс: Мал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ЗБУК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0. С.11.
[13]:Ямпольский М. Беспамятство как исток(Читая Хармса).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8. С.82.
[14]:(美)维克多·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M】,章燕、李自修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235页。
[15]: (英) 凯文·奥顿奈尔.《黄昏后的契机:后现代主义》【M】,王萍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7页。
[16]:Руднев В.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культуры XX века. М.: АГРАФ, 2003. С.299.
[17]:赵杨:《颠覆与重构: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反乌托邦性》【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