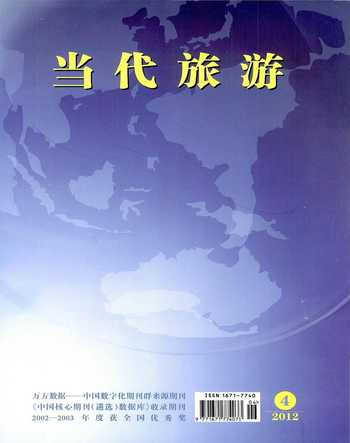黄宗智法律史研究范式中“第三领域”的学术贡献
马雁
摘要:第三领域是黄宗智理论模型中的逻辑进路和材料组织的肌理与脉络,是一个国家法庭与民间调解交互作用的空间。在处理民事纠纷方面,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实现部分制度化,构成了司法体系中第三领域的主要内容。从主题价值和比较方法论的角度,可将第三领域总结为新文化史的范式特征,并具有前瞻意义和独特的创新价值。
关键词:法律史;第三领域;范式;学术贡献
黄宗智先生所提倡的结合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利用诉讼档案来研究清代以来的法律制度的进路,是享誉史学界的法国年鉴学派开辟的总体史研究方式的一个体现。总体史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生活,进行总体史研究,必须打破所有学科和领域的严格界限和分离的状态,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学科的专业化趋势,其实是人为地制造研究的封闭格局,形成一种互不往来的闭塞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宗智先生的著作及其试图综合社会史、文化史和制度史的努力,不仅构成某种智识上的挑战,更获得了某种智识之外的意义,因此,黄先生的著作似乎可以称为一种“总体性”的法史学研究成果。
一、主题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黄宗智先生充分利用了《满铁惯调》村级民事纠纷的实地调查材料、重建了这些材料中628件民事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阐述了民间调解作为纠纷处理非正式系统的构成、作用和实际运行,认为清代民事审判并非州县长官的“教谕式的调解”,而是根据法律频繁并且有规则地处理民事纠纷。628件案件中,126件是告诉后由庭外民间调解处理的,264件记录不完整的案件中,应有半数左右属未经堂审即得以调解的,因此。通过半正式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达到258件,这些案件的处理方式,即为清代纠纷处理中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第三领域”。
从对诉讼档案的量化分析,不仅体现对个案处理细致入理的观察,也以定量研究的方法,提出了普遍性的问题。如县官是不是偏向道德训诫而非法律条文、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他是否更像一个调停者而不像是一个法官?如何理解诉讼档案与传统观念间的差距?从区分清代民事调判制度的形式、诉讼的规模、民事诉讼费用、“衙蠹”及当事人的抉择与策略分析等事实角度,揭示了不同社会背景与结构下的民事诉讼形式——小农社会背景下的宝坻、巴县形式,复杂社会结构下的淡水、新竹形式,并将之视为由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的历史的纵向变化。
黄先生也从阐释学的角度,提出清代民事诉讼实际并非是传统观念中设想的走极端,比如无讼与滥讼、清官与衙蠹、良民与讼棍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认定模式,而是从场境和具体实践的角度,证实了律文正史与法律运作现实的差异和背离,指出了州县官们的活动中德治文化与实用文化的双重影响,即秉持“实用道德主义”原则处理案件的真实动机。将清代法律界定为实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性结合,并将之放在“世袭君主官僚制”的政治制度背景下理解,认为清代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可以看做是“世袭君主——实体的”表达和“官僚一理性的”实践的一个结合,德治主义和实用主义纠结在清律、县官和地方政府的实践中,权利在理论上被否定但在实践中得到保护。
黄宗智的理论创见是提出了一个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清代纠纷处理的“第三领域”。在黄宗智的解说中,第三领域内,纠纷是在当事人及有关调解人员对县官批词中难得见到官方律例的表达。这涉及到黄先生提出的一个对“法律”概念解释的问题,即采用规范法学意义上的界定,认为规则的法律只存在于大清律例中,在黄宗智的第二领域(民间调解)与第三领域中,出现的裁判依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及其组织体系,而是为一定群体所共享、共守的一套规则知识和观念组成。“第三领域”运行的前提是存在两套知识系统,官僚阶层共享的关于儒家经典及官方表达(律例)的知识,民间调解中的“地方性知识”。“第三领域”是上述两种知识系统相互冲突、平衡、妥协、吸收的空间,或者是两者关系作用的一个结果或者构成。
《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更能够充分体现黄先生从经济史、社会史到法律制度研究的学术旨趣转向。因为“法律制度的研究结合了社会史与文化史。过去,社会经济史和文化史学者多分道扬镳,互不过问。但在法律领域中,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这种转向的主题揭示意义,还在于“法律史促使我们不仅对待行动还要对待表象,不仅要对待现实还要对待理想。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这使法律制度的研究获得了跨学科的意义,并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问题发生关联,对于改变“幼稚的法学”的尴尬局面,不无裨益。
作者运用了一些地方诉讼档案,除了前面提及的四川巴县档案、河北宝坻县档案、台湾淡水分府和新竹县档案以外,还包括一些民国时期的诉讼档案。这里,也揭示了法律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对于史料的整理与系统化,以及新史料的发掘与使用,是否仅仅停留在论据层面就达到了学术上的创新。我认为,史料的运用和整理在达到“充分化”的程度时,它的学术贡献才是独具价值的。这不仅依赖于对史料的系统化工作,更依赖对于这些史料的阐释并挖掘其中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其他史料相互佐证,贡献于“总体事实”和理论构建。诉讼档案不仅在史料的使用上较少,它“同时包含有关表述和有关行动的证据,意识与行为的分别研究不可能像诉讼案件的研究那样显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这里存在一个学术研究在保持自身独立品格的同时,与何依存、为何服务的问题。该著作偏向讨论中国法律历史中的现代性的方面。黄宗智关心的始终是清代法秩序与中华民国法秩序,以至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以后的现代中国法秩序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从近百年的法律实践来看,可以看出现代中国法律已经初步成形,既有明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也有实用的认识方法,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二、比较方法意义上的“第三领域”范式
笔者的理解是,将两本书相互渗透,全面理解作者的系统思路和理论构设框架,体会贯穿其中的论证线索,获得一种无偏颇的认识。同时,这种安排也暗含了方法论上的提示,由于民国法律制度和现代法律制度在性质和实践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通过对于民国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对比,可以间接得出关于清代法律制度和实践的看法。法律史中以今析古的比较研究方法,昭然若示。所阐述的清代法律和习俗有关民事的概念结构和逻辑、案件记录中透露出的清代司法实践、20世纪立法者对法律中现代概念的追寻、国民党法院如何于立法者的意图与当时的社会风俗之间斡旋。体现历史变迁的动力和型式的内容连贯一致的学术史命感。
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结构分析模式影响下,屏蔽了关于变化与连续的过程中多侧面的相互作用。黄先生将比较的原则和方法贯穿于三个层面:即成文法、民间习俗及司法实践。认为对于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确切比较不能仅以成文法为基础,因为那样会夸大实际的变化;清代与国民党法律不同的指导意识形态与社会取向的确重要,但它们的不同也可能掩盖了习俗的基本延续及法典的实用条例与法庭的实际行为对习俗所作的重要让步。通过以上三个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考察,才有可能了解自清代至于民国间民事法律制度的变化与连续。
贯穿于《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的主线是表达和实践的比较,《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的主题则涉及到清代、民国以及过渡时期的关于法典、习俗和司法实践三个层面的比较,比较的难度愈发增大。黄宗智先生秉持超越价值评判进行比较的学术自醒。在第三领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中,阐明了超出现代主义假设看问题的学术理路,目的在于阐明两者经过明言以及未经明言的合理性,没有认为此优于彼。通过把每一方都当作另一方的澄清性陪衬而把两者概念化和相对化。从这点上看,这种研究的精神和旨趣接近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要求,具有新文化史的范式特征。
三、研究所得到的启示
(一)法律史研究中的立场以及方法论问题需要获得应有的重视。
在保持自身的独立研究品格的同时,也需要对研究场境中的“总体事实”做全面深入观察,并有助于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理论体系的发展。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客观主义与文化分析主义可以获得结合,并相互应证。
无论是“实践逻辑”还是“现代传统”,都促使研究关注社会事实,既不将事实化约为“表象”,也不忽略理论提炼,在认识问题复杂性的同时,致力于理论发展的努力。科学对待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的关系问题。
(三)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很重要。
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在学术传承和学术创新方面的价值,更甚于一些具体的论断。法律史研究中,常遇到材料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缺欠其实更多是缺乏问题意识的结果。历史材料本身是沉默无语的,如果缺乏问题意识,再勤奋的努力也可能局限在零散的整理工作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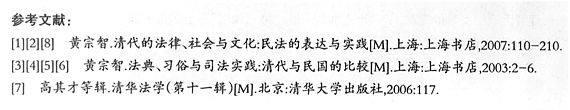
——简评《中国法治的范式研究:沟通主义法范式及其实现》(郭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