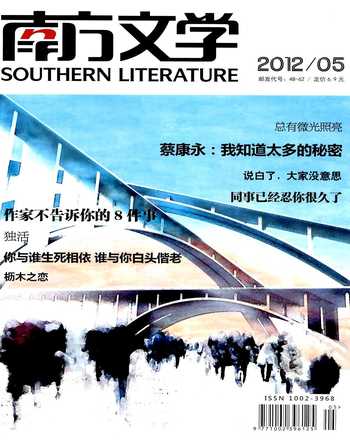救命天台
兰若水
小区五百米外重重叠叠的房子,正是这个城里有名的城中村。
护栏上坐着一个人
深夜,阿炎上了天台。八层楼高的旧式小区,每层楼梯间的灯倒都亮着,他弓着身子钻过通往天台的锈迹斑斑的铁门破洞。凛冽的风迎面吹来,他精神一爽。往前跨一步,他看见天台齐肩高的水泥护栏上坐了一个人。
这情况有点意外。阿炎皱眉思量半晌才走过去,走近了发现是个男人。那人仿佛没有听到脚步声,一动不动。阿炎手撑着水泥护栏的边缘,想跳上去,但失败了。他碰碰那人的手:“搭把手,我也上来坐会儿。”
那人迟钝地回过头来,暗淡的路灯在他的眼睛里反射着光,令阿炎觉得怪异。他的声音低哑冰冷:“上来干什么?”阿炎长呼一口气:“看夜景!”凑近了看,阿炎辨出了那人也就三十出头。彼此凝视了好一会儿,半晌,那人回过头,不愿意拉他上去。
风仍然凛冽,打着那人的衣衫,啪啪作响。阿炎闻到他身上的烟味,自己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坐在他旁边,从口袋中摸出一支烟,递了过去。那人一愣,慢腾腾地接过烟。风大,两个人头抵头凑在一起点火,半天才点着了烟。各自只抽一口,就都夹在手指中忘了接着抽,风吹来,两个烟头明明灭灭,鬼火似的。
不知过了多久,阿炎方才问:“遇到了什么事?”
那人的声音在风中浮浮沉沉:“多啦。”
阿炎语调轻快:“反正无事,讲几件来听听。”
那人道:“无非是那些事,猜都猜得到。”
阿炎淡淡地说:“赌得一分不剩?”他们这个年纪的男人,人生最失败不过是没钱。没钱,便什么也没有;有了钱,便什么都有,女人、房子、车子。
“不是赌,是被女人骗。骗了我的情不算,还骗了我的钱。”
原来是人财两空。阿炎哧的一声:“这算啥?你还年轻,好好工作挣钱呗。”
那人的声音没有起伏:“公司也破产了。”
确实算得上一个男人最悲惨的境地了:爱情、金钱、事业在一夕之间全没了。阿炎说:“好歹你还有健康的身体和大把的时间,还有父母。从头来过就好。”
那人将烟头扔出去,被风一吹,不知飘向何处。他闷闷地说:“对,就是还有父母……”潜台词没说出来,但阿炎自是懂得。
父母……阿炎想起了自己三年不见的父母,心下一阵难过,又递给那人一根烟。两只烟重又亮起来,在天台上明明灭灭。
这个人命真好
这老式小区,与城市繁华有关的,不过是近处的路灯与远远的车嚣,却将小区衬得更寂静。这时飘来一阵桂花香,阿炎几欲要沉底的心被这香气回暖。他问:“一个30岁的男人,读书成绩优秀,家境也不错,本科毕业一年后,找不到工作又复习考研,考了三年才考上。没交过女朋友,没有挣过钱,现在硕士毕业两年了,还没找到工作,得靠父母养着。他与你,哪个更失败?”
那人激动起来:“这个人命真好!父母能供得起他上学,就算暂时不工作也没问题吧?而且,硕士去哪里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哪像我这种初中没毕业就出来靠体力挣钱的人,很辛苦才能挣到一点钱,开起来一间公司,却被一个女人骗走了。”
阿炎摇头:“好工作?这年头都是靠关系。考公务员,得有关系;进大学教书,人家说要博士学位,其实也是要关系。第一,父母供他读书花费太多,现在真没钱再为他走关系;第二,他不想花那个钱。他觉得凭着自己的能力与知识,本能胜任某份工作,现在却还得掏钱去走关系买那份工作,这是整个社会的耻辱。他耻于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那人费力地理解了阿炎的话后,十分不屑:“机关、大学去不了,可以去企业。现在企业不是招不到人才么?为什么一定要将眼光盯死在机关、大学呢?”阿炎扯了扯嘴:“他学的是哲学专业,只有机关或大学里需要这种专业。”
那人想了想:“也不一定要专业对口。硕士除了专业外,肯定还有别的长处。英语比一般人要好吧?文笔比一般人要好吧,说不定口才也比别人好,反正他有很多选择。我是初中没毕业就出来了,只能干流水线和工地的活,我也没觉得苦。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些日子,让我学会了看人,学会了与人打交道,后来才开得起那间公司。”
那人生出谈兴,讲起自己的故事来。
陌生人的故事
我老家在广东韶关乡下,父母生了三个姐姐,那时候的计划生育政策抓得严,父亲带着母亲,在外面东躲西藏地做点小生意,就为了生下一个儿子。有了我后回到家,被罚得家徒四壁。姐姐都早早外出打工,就为了供我读书。可我不争气,整天捣蛋,初二时将班主任老师的单车偷出去卖了,拿着钱去城里玩,就那样被开除了。
我早就想来深圳这个大城市了,巴不得不读书。如愿来到深圳,一看,才知道姐姐们的钱挣得那么不容易。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两个姐姐,每天都要加班五六个小时,人瘦得走路都像在飘,在超市里做营业员的三姐,站得腿都肿了,还时常被主管骂……有一天,二姐因为连续加班而晕倒在车间里。
那样的见闻让我迅速地长大了。刚满十六岁的我,在二姐所在的工厂干起了搬运工。第一天下班后,我觉得整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姐姐租的房子在八楼,下班后,我手脚并用才爬上去。
几个姐姐看见我红肿的手、淤青的腰,心疼得直掉泪,争着为我倒水、端饭和按摩。我们姐弟四人租了一个十平米不到的小房间,没有窗,白天也要开灯。姐姐们在那里一过就是好多年。我心里发誓,一定要有出息,要赚很多钱,让姐姐们住上有阳光有风的大房子。
我拼命工作,拼命攒钱,拼命去讨好人。后来我终于开起了一间公司,确实也赚了点钱。可是,那钱却全让前妻拿着,连我二姐夫生了病,她都不肯拿点钱出来救命。
姐姐们当然怨,不是怨我,而是怨我怕老婆。没几天,我人财两空时,姐姐们的怨变成了担心。她们担心我做傻事,天天宽我心,给我做好吃的,让我住在她们家,背着姐夫给我钱,让我外出走走散下心。你说,我还活着干什么?有钱的时候姐姐们讨不到半点好,没了钱又得拖累她们……
那人说到这里有点哽咽,声音已经嘶了。
“你有几个好姐姐呀。”阿炎说这话时,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他是家中独子,从未尝过姐弟情,他能体会的亲情,只来自父母。父母……阿炎鼻子酸了,下意识地挺了挺腰,可身子一晃,忽然失去平衡,差点就朝下面一倒。那人一把抓住他的肩,说:“小心!”
阿炎稳了稳心神,说:“我讲讲刚才那个硕士的故事吧。”
哲学硕士的故事
不甘同流合污的哲学硕士,曾打算要用自杀来痛斥这个世道的不公平,唤醒这个世界的良知。但最终他选择了勇敢地活下去。
他利用自己的特长美术,去了一家超市做美工。同事大多来自城市底层或者乡村,顾客却是各色人等都有:有穿着睡衣蓬头垢面的太太在快打烊时来买特价面包,第二天却又看见她衣着高雅体面地来选购高档日用品;有农民工在快打烊时买一盒冷了的半价盒饭;街边的乞丐拿着百元大钞买不便宜的酒和熟食……
他忽然明白,其实这营营役役的人间,是哲学最好的研究对象。
他潜下心来,一边工作,一边继续研读先贤著作。不久开始在报纸网络上发表一些自己独有的思想见解。
五年过去,他的第一本哲学专著出版,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向人们阐述了哲学最深奥的思想。在这个信仰极度缺失的时代,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指引。于是,这本书成了畅销书……
那人听得认真,哲学的话题对他来说也许还是深奥了些,但“畅销书”的意思没有人不懂:“就是说,赚了很多钱。”阿炎点头:“赚了钱。”那人又问:“那有没有人请他去机关和大学工作?”阿炎摇头:“没有,他也不想去机关和大学工作了,他觉得,自己最合适的就是呆在有各色人等的地方,去观察,去思考。”
那人长叹一口气:“可惜了,中国的大学里不正是缺这样的老师吗。”忽又问:“是什么事情让硕士改变了自杀的念头?”
阿炎瞄他一眼,道:“父母,他想到了父母。”
本来,他是要在今晚行动的
那人沉思半晌,拍拍阿炎:“几点了?”
“不知,我没带手机,也没戴表。”阿炎摊摊手。
那人微笑,是今晚第一次微笑,那微笑点亮了阿炎的眼睛,他说:“我也没带。但估摸着很晚了,该回了。”
阿炎还是不放心:“你回哪去?”
“我姐姐就在那里租房住。”那人指了指小区五百米外重重叠叠的房子,正是这个城里有名的城中村。那里的房租很便宜,是这个城市外来人口的首选居住点。
只是城中村的房子,房东怕出事,总是锁住了天台的门。而这个小区,管理一向松懈,他应该是熟悉了这边的情况,于是趁黑来到了这个天台。
两个人相互扶持着,从水泥护栏上跳进天台。
阿炎与那人一起下楼,走到小区门口,那人回身,说:“谢了,兄弟。今晚不是你的话,我就跳了下去。”
阿炎一时语塞,只好拍拍他的肩,语意含糊:“彼此彼此!”
看着他走向了城中村,阿炎回过身来,对睡眼朦胧的保安说,天台的铁门已经破了一个洞,应该快点补好。保安一边听,一边辨认着阿炎是否是小区里的住户。
那人的身影走远了,阿炎也慢慢走进了城中村的小巷。经过路边的一个垃圾桶时,他将口袋里几件普通人不认识的专业工具统统扔了进去——就在上个星期,他还一直在那个小区蹲点,自从发现了天台门上有个破洞之后,他本来已经打算好,今晚,趁着夜深人静,小区居民都已入睡后,他就开始行动,先从破洞钻进去,然后从天台顺着水管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