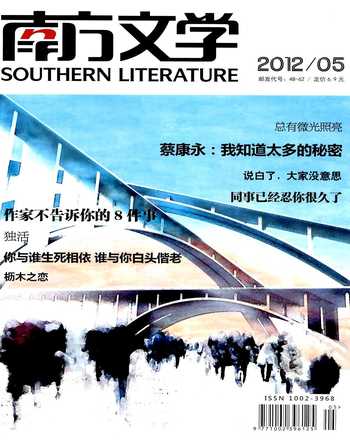上帝在云端
2012-04-29 00:44关曦明
南方文学 2012年5期
有时候,迁徙是一件简单的事。
两小时零十分的空中路,便足以改变一段人生的下半场。
但有时候,完成一次迁徙需要十三年,甚至更漫长的时间。
发型师阿剑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家。他顶着一颗蘑菇云状的陈奕迅头,在镜子里语重心长教导我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啊,人一生不是经常能有这样的机会……
是是,我叩头如捣蒜。
然后就是两小时零十分的行程。昏睡中醒来,飞机已在跑道滑行,这时我听到我的左、右、后三方依次传来三位老阿姨压低的间谍嗓音:“喂?已经降落了,但还没停稳当,不能多说,挂了哈……”
禁不住破口大笑。
这个城市的居民安逸到让人无语。
出太阳了,全城人民晒太阳,在街边摆张桌子,喝茶,搓麻。
春天来了,全城人民看花花,能把出城的路口堵得蜜蜂都飞不过车海。
清明到了,全城人民祭祖宗,不过你不用揪心,那场景能热闹到让你忘记什么叫凄凉。
这个城市的人民热爱围观。
这个城市的人民喜欢一窝蜂。
几乎每个红灯路口都有人横穿马路。
到处在修地铁,街市上卤肉摊子旁边尘土飞扬。
穿绣花鞋买菜的女人毫不费力就飙出一串粗口。
真开心。
但也有一些不和谐景象,比方说,如此春光明媚、微风吹拂的周末我仍在赶稿,面对电脑,日做夜做。我的亲友们就万分不解,他们认为我是个不热爱生活的人,是个极其可悲的可怜虫。
好吧,可怜虫写完最后几句,就出去吃饭晒太阳。
啰嗦一句,我喜欢这个城市里有很老的老人在街边拄着拐杖慢慢走。
再啰嗦一句,我喜欢这个城市的小朋友脸颊都挂着两团健康的桃红。
哲学家阿剑说得对,这是一次转折。
飞机在云端,浮云骤雨远飞。
上帝在云端,早已铺排好流年。
关曦明
2012年3月
猜你喜欢
作文小学中年级(2024年2期)2024-03-02
娃娃乐园·综合智能(2022年10期)2022-10-18
扬子江(2018年5期)2018-09-26
空中之家(2018年1期)2018-01-31
Coco薇(2017年11期)2018-01-03
商周刊(2017年8期)2017-08-22
米娜·女性大世界(2016年9期)2016-12-02
空中之家(2016年1期)2016-05-17
中国新农村月刊(2015年10期)2015-05-30
爆笑show(2015年1期)2015-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