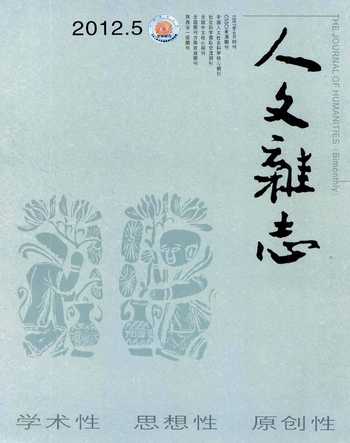中西方社会资本的再比较
何君安
内容提要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网络当中所蕴含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合作态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化解集体行动困境,对公共事务治理绩效具有根本性制约作用。中西方社会资本形式有很大不同。论文对中西方文明不同的价值偏好、社会总体结构状况、个体的自我定位、幸福观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对中西方的社会资本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对其类型进行了重新归纳。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文明特征 信任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78-04おおお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在关注的一种理论。美国华裔社会学者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为者在行动中能够获得和使用的、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根植于“一个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人们能够相互了解和认可的持续的网络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团体的成员关系之中”;①罗伯特· 帕特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②所以,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由于社会网络中的信任、规范使其成员可以获取的资源。请注意,“这里的社会网络不一定非要采取正式的组织形式,如果一个社会里的人们愿意信任其他人,包括陌生人,这个社会里的人实际上也构成了一个无形的、巨大的社会网络;人们可以利用由这种互信产生的资源。”③
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问题的研究,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对中西方的社会资本进行比较。学者们一般认为,首先,从信任模式上讲,西方社会是普遍主义信任,而中国是特殊主义信任。在中国社会里,血缘关系的有无、远近对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影响很大,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局”。
其次,就蕴含和培育信任的社会网络来讲,西方社会的网络结构以水平型为主,是平等的成员基于共同需要自愿联合而成,具有类型多种多样、是建构的而非继承的、成员身份平等、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决策、成员自觉履行责任、网络功能比较具体等特征。而在中国,最为根深蒂固、渗透性最强的网络是家族型、关系型网络,具有类型的单一性、内部结构的非平等性、成员身份的依附性和先赋性、较强的内聚性、边界的封闭性、功能的全能性等特征,难以培养起人们超越家族、熟人层面的普遍互信态度。
就社会资本的另一要素——规范来说,在西方水平型社会网络当中,规范是明确的,注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是为特定目的制定的,可以修改和变化。其基本内容是互助、合作、互惠,具有对所有成员的普遍约束力。而在家族及其衍生形态的网络当中,协调人们行为的规范是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复杂“人情”。它不是建构的,而是继承的,具有模糊性、灵活性、适应性、伸缩性、变通性。
以上关于中西方社会资本的比较,从微观层面描述了中西方信任方式、交往规则、网络结构的不同,有一定依据和说服力。但是,根据上述论断,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基本是“以邻为壑”的关系、没有多少信任可言,那么,中华文明作为最好地保持了自己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文明形态,其超越家族——熟人层面的集体行动是如何达成的?它超强的内聚力、生命力又来自何处? 完全依靠王朝政府的整合显然不能说明这一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某种共同认可的“集体意志”,王朝政府的整合成本将非常高昂。
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和生命力之所在,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与人为善、爱好和平、包容大度、顾全大局、知恩图报、自我牺牲、重义轻利等一系列美德和强烈的凝聚力、向心力、民族认同感。毫无疑问,这些美德也是我们民族的社会资本。帕特南认为,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都是“道德资源”,[意]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最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华民族当然应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
此外,目前学术界所进行的社会资本比较研究,都是在“隔离”了不同文明形态的总体特征后就社会网络、人际信任态度、交往规范等微观层面进行的,而实际上这些微观层面的结构、态度不可能不受到其所处文明的宏观总体特征的影响。而如果对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不只局限在微观层面,而是扩展到东西方文明的价值旨趣、社会总体结合方式、对个人自我的定位、幸福观等方面,就会发现还存在更多区别。
第一,从中西文化的价值旨趣看,儒家文明偏好的价值是“善”,西方文明追求的最大价值是“真。”儒家是“以善统真”,西方文明是“以真统善”。在以“善”为最大价值的情况下,儒家相信人性本善,主张人人都应该也能够发挥其善性,通过外在教化和内在反省,做到明礼诚信、仁爱忠恕。在其影响下,中国普通老百姓大多宁愿持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态度,相信良心的自我规约作用,愿意奉行和平主义。这无疑有助于增强信任、促进合作,至少为信任、合作提供了较好的氛围。
而西方文化在追求“真”的情况下,常常对人性持怀疑批判的态度,将人视为需要防范、克服的对象。由于对人性的怀疑态度,必然使世间由人所从事的各种活动都具有潜在的恶性、不足以成为可以从根本上信赖的力量,最后只剩下孤单的个人权利——事物是否可信完全交由个人判断。从这种意义上讲,西方的民主、法治乃是建立在怀疑、防范而非信任的基础上。而由于怀疑所产生的宗教战争、阶级阶层种族偏见、党派纷争又在多大程度上抬高而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制造而不是消解了集体困境呢?就在本文写作的时候,新闻报道美国众议员吉弗兹遭枪击案,死亡6人。据专家分析,尽管美国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枪击,但禁止枪支的法案在美国一直难以通过,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人性恶、必须依靠持有枪支进行自我防范、保护自身安全。
第二,从中西方社会的结合方式看,中国是整体主义社会,西方是联合主义社会。所谓整体主义,指以整体为部分及个体之价值源泉,部分或个体没有自身独立的意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虽然家族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但面对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任何家族,甚至包括皇族,都没有独立的意义,皇族成员面对皇帝同样是臣民。这也是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一个阶级社会的根据之一。参考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3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只能称之为整体主义的社会,而不能称之为家族主义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在秦之后也有封建,即依靠家族进行统治,但大多数时期内都是皇帝及其官僚的统治而不是皇族、宗族的统治。家族统治恰恰是西方封建社会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不形成对国家、民族的较高认同感和向心力、内聚性,以及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善恶标准。强烈的落叶归根意识、爱国主义情操和虽然简单、但却一致的善恶和是非标准就是证明,而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特殊主义信任的不足。也因此,近代以来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常常面临的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表现得就不是特别严重。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危机不是认同危机,而是由于中央政府效能下降而产生的整合危机。
另一方面,在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重在解决个人与群体的纵向关系,养成了人们较强的义务观念,将个人承担对群体的义务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就公共事务的治理而言,中国社会也不取人人参与、互相合作的方式,而是要求每个人遵守社会的集体法则、承担自己的义务,只要每个人都能按照大家共同认可的规范行事,社会自然就会得到良好的治理。
与中国相对,西方是联合主义的社会。所谓联合主义,指个体(部分)不仅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而且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整体只不过是独立个体之间的联合,服务于个体。联合主义以普遍互信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纽带,以平等、自由、参与、合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基本原则,以辩论、投票为达成集体决策的基本方法,培养了人们的公共精神、锻炼了人们的合作能力,但是,也使西方社会始终面临个体与整体、权利与权力、少数与多数、自由与法治的冲突,发展到极端,甚至否认公共利益、共同福利的存在,认为人们从根本上不可能就公共事务达成共识、只能寻求有限的妥协。[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2页。更有甚者,将一切社会建制都视为压迫自由的潜在力量,因而不时出现无政府和反社会的思想倾向和行动。
第三,从对个体自我的认识来看,中国文化当中,“我”是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可以扩张、伸缩的概念;而西方文化当中,“我”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与他人在精神、情感上互相包容,一个“我”的概念,可以扩展到家庭、家族、地方、国家、天下乃至自然万物。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宋人慈照禅师云:“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关学大师张载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都说明了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与他人的相通性、相融性。而且,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及万物都是天地之所生、一气之化育, 因此,“人的尊严的观念是遍及于一切人的。”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25页。“途之人可以为禹”,“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都是教育人们要尊重任何一个人。总之,中国文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也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做到“并育而不相害。”
再看西方文化当中的自我概念。由于西方文化采取天人相分、外在超越的致思路径,人自身也被对象化、客体化,个人自由便在于超越外在世界,“自我必须斩断与外在世界相维系的枷锁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④在此情况下,人与人的共处只能依赖内心对“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则”的信念。但这种“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则”无论是上帝的启示还是理性的发现,都必然是外在于每一个具体个人的“冰冷的理性”(尼采),无法契合具体个人的精神与心灵。文德尔班说,自从苏格拉底之后,希腊人便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每个人内心里都有自认为是必然的、能防御别人的个人意见和目的,除非这些个人的意见和目的之外还存在任何本身正确而真实的东西。”[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第97页。而外在于人的“本身正确而真实的东西”之是否存在及与个人相比孰重孰轻、孰高孰低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总之,在西方文化中,“自我”与他人能否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始终是有争议的。就像维特根斯坦的疑问,“如果我信任他,我的心智能进入他的思想中吗?”L.Wittgenstein, 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115-116,104.因此,西方社会里人与人的互信即使程度再高,也难以解决“人的孤独”的问题。西方文化中也有强调人与人应该互相理解的思想,苏格拉底“采用对话的方式便是表示只有在主体相互问答之间才能发现关于人的真理,人不能客体化而变成认知的对象,但这在西方文化中不占主流”(余英时:《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诠释》第24页)。
第四,从中西方的幸福观来看,西方人的幸福观是实在的,指人所面临的障碍得以克服、目标得以实现和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自我价值与意义;而中国人的幸福观具有外在性,比较看重社会的评价。中国文化走的是内在超越的道路,个人应该超越自己、获得社会的认可。因此,我们从小就训练儿童遵守社会的集体行动规则,做“对自己有好处又不妨碍邻居”的事情。这种对自我超越的追求,往往伴随着物质上的清贫,但却可以获得心灵的安宁。[法]若泽·弗雷什:《中国不笑,世界会哭》,王忠菊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第35页。“脚在尘世,头在苍山云端”,“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一个人”,既反映了中国人重视心灵慰藉的幸福观和追求“做人境界”的人生价值旨归,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为何如此偏爱社会的和谐而非个人的自由。
而在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中,幸福只能是对人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探究、解决,对妨碍实现人的目标的外在障碍予以克服,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人的力量、价值与意义。在西方文化中,无论是将幸福归结为美德、理性、快乐、知足、信仰、自由、功利、权力、创造、探求真理等等,都是外在超越幸福观的反映。它在鼓励人奋进的同时,也容易将他人异化为自我的对象物,使人与人之间面临根本性的紧张。
总之,中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各有其内在的精神,保持着自身微妙的内在平衡。要对东西方的信任、规范、合作网络等社会资本进行比较,就不能不将其放到各自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是特殊主义信任、西方是普遍主义信任,更不能轻易断定西方社会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
最后,基于前文的分析,可以对中西方的社会资本类型进行进一步的总结。
1.情感取向的社会资本与理性取向的社会资本。所谓情感取向的社会资本,是指以情感作为建构社会资本的主要纽带,在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中,比较看重情感因素,各种利益的考量、理性的权衡,必须以巩固和增进情感、至少是不损害情感为原则,或者是在情感的面纱下进行。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礼物经济就是此种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关于礼物经济是情感化社会之“遗存”的论述,请参考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凤凰出版集团,2004年。在此情况下,权利义务界定明确的规范成为对信任和社会网络的伤害。它倾向于将理性化的角色关系转变为非正式的情感联系,或者是以情感来中和角色关系。它常常贬低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等正式规则的作用,期望通过培养共同情感使社会事务得到良好管理,致力于建立一个人情化的社会。它更容易加深人们对社会网络和国家整体的心理依恋,塑造人们较强的心理归属感、依赖感。而西方社会的社会资本具有较多理性取向,以现实目标的实现作为各项社会建构的目的。相比情感取向的社会资本,更与法治的精神相通。
2.文化凝聚型的社会资本与规则约束型的社会资本。文化凝聚型的社会资本是指以共同文化作为内在的凝聚力,将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渗透在所有的社会网络中,成为社会网络建立与行动的共同原则。在此情况下,所有社会网络具有某种“相似性”,价值取向相近、内在规范相似、网络功能相同,社会资本具有更多继承性、持久性。而西方是规则约束型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具有更多差异:价值取向的差异、网络类型的差异、结合紧密程度的差异、功能的差异、规则的差异等等。它以人们的需要作为内在规范的依据,更容易变动和更新。
3.向心型社会资本与分立型社会资本。中华传统文明的特性使我们的社会网络常常围绕某一中心而形成、具有向心的特征。国家有皇帝、政府,家族有族长,社会网络也往往有一个核心人物,主导着话语权。人们对这一核心人物具有较高的期待和信任,习惯于将公共事务委托给他来管理,常常赋予他较大的自主权,而他也对网络的维持负有最大的责任。就所有的社会网络来说,又趋向于政府,以其为核心分布开来。正式的政府组织对社会网络和非正式习俗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而在西方社会,各种社会网络之间是分立的,内部是平等的,即使是代表整个社会的政府,也并不比其他社会组织高尚多少。オ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心 远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课题“社会资本培育与有效政府建设”(项目号:09JK212)的阶段性成果。
①③ 转引自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第120、121页。
② [意]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