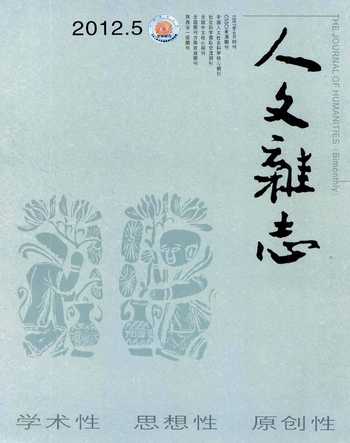新感觉派的“欲望叙事”与存在主义的“艺术生理学”
杨经建 周舟
内容提要 新感觉派小说的“欲望叙事”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言说方式,即,新感觉派从幻象般的感觉中开掘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焦虑与存在状态,以自己独特的欲望叙述与存在主义的“艺术生理学”实现了对接。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尼采的权利意志是“欲望哲学”或“艺术生理学”的思想根基,它们从生命存在的本质、人和世界的关系来认识与理解身体、欲望和艺术的本质,试图以此创造新的思维和生命形式及其可能性。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同存在主义的“欲望哲学”并将自己的生命化作一个“存在”的问号,通过这个问号重新探询欲望诉求的可能性。而从王国维到新感觉派则显示了非理性主义欲望叙事在现代中国演变的轨迹,如果说在五四文学的欲望叙事中“欲望”和“启蒙理性”共生,那么新感觉派以“感觉”的方式通过对欲望话语的伦理改写,思考人在“欲望”层面上作为生命存在“主体”的自觉是否可能,从而凸显了欲望对“文化”——存在主义叙事的意义。
关键词 新感觉派 欲望叙事 艺术生理学 欲望哲学 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082-06おお
一
生命被叙述为非理性的存在,个体在寻求欲望的满足中确认自身存在的价值,这是存在主义(文学)对于欲望的言说,也是新感觉派小说的“欲望叙事”的表达。情况往往是,面对着作为历史与现实“缝隙”间的一块“飞地”的“上海”,充满着感觉化的都市物欲景观构成了新感觉派小说中独特的审美意象核心。所谓“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①即如在穆时英的《PIERROT》中,都市大街上盛满了人们的欲望和表情:“街有着无数都市的风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的醉眼,美容院里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法眼,电影院的奸猾的三角眼,饭店的朦胧的睡眼”。所有这些撩拨和怂恿着都市人的感官世界,挑弄并诱发出人们心底的欲望,进而营构出有关欲望的都市叙事文本。不仅如此,穆时英在小说中不停地转换感官的角度去摄取并表现纷繁变化、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以及现代都市人种种颓废、迷乱乃至病态的心理。以至于穆氏笔下那些迷茫紊乱、无所适从的主人公,犹如本雅明所指的波德莱尔笔下的“浪荡子”,往往闲逛于街头和流连于舞场,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要干什么,在没有背景也无所谓前景的现代都市空间游荡。“他们的愉悦与厌倦都是物质和欲望的符码。”②
就“欲望这个话语概念本身而言,它是生命生存和延续的必要条件,是生命的本质属性。“首先,它是对生命的肯定。没有欲望就没有生命,没有人的欲望就没有人的生命;没有了人的生命,世上的一切都将失去对人而言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如此,欲望还与创造力、活力紧密相连。欲望寻求满足的过程,就是创造力产生的过程。”②程文超等:《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51页。问题恰恰在于,人类文明的创造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自身欲望,并使这种欲望满足的过程纳入可控性和渐进性。或许可以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象征性事件:作为区别于动物的人类之觉醒,正是从自觉地满足自然欲望开始;至于那条蛇何尝不是人之欲望的隐喻或外化,在《圣经》中它无异于撒旦,在《浮士德》中又化身于靡菲斯特,而在波特莱特的《恶之花》中便成为人自身。由此观之,与其说是上帝把人逐出了伊甸园,不如说是生命个体对欲望的追求促成了人的觉醒。在此意义上,欲望的存在是人的故事的开端,也是人类文明的前提。而对于“欲望”,文化哲学的要义就是进行一种欲望“如何”获得满足的叙述,并从这“如何”的叙述过程中构建一套有关“欲望”的价值、一种有关“欲望”的意义。“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来自西方,所谓‘欲望更是西方文化中的老话题。舍勒(M﹒Scheler)指称“现代性即是‘本能造反逻各斯,这其实说的是反抗现代性,‘本能即‘欲望,‘逻各斯即‘理性。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一直包含着反抗现代性的历史,也即是‘欲望反抗‘理性的历史。”②
毋庸赘言,“在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小说中,存在着一个欲望对象的象征系统,这个系统很庞杂,……这几乎是一个可以无限开列下去的象征清单,到后来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一切所构成的大都会本身,就是欲望的巨大的化身、表征和符号。”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35-136页。正如穆时英的《黑牡丹》中的那些红男绿女们都“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实际上,穆时英笔下所呈现的人“类”大多是现代都市的摩登男女,属于“Jazz,机械,速度,都市文化,美国味,时代美的产物集合体”(《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人生的莫测和生活的压抑,都市的浮华和时光的易逝,生命的空幻和存在的未明,都使这些都市客明确了“此刻”与“瞬间”的重要意义。消费主义的感观刺激常常成为他们确证生命存在的唯一方式。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更是让两个希求欲望满足的男女失去了对时间的感觉,表征了欲望沉沦中人的自我的失却;在此,所谓欲望叙事让主体人的自持在欲望的撞击下,变得破碎和模糊。在施蛰存的《鸠摩罗什》中,一代宗师本能欲望与道产生激烈冲突,最终象征人的生命力的本能欲望战胜了宗教对人性的扭曲与压抑。施蛰存的小说善于写古代的高僧、名将、英雄、美人等,实际上是以他们为载体表现现代都市人的复杂的心理体验和人生况味。新感觉派小说家就是从幻象般的感觉中开掘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和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对这“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上海的狐步舞》)充满了无法释怀的心理欲求。
二
随着欲望话语合法性的确立,“欲望”被剥离了历史和道德价值的框架且作为人性最基本的形态赋予了自足性。新感觉派作家小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非理性主义的欲望叙述推向了高潮,“在这个欲望的时代,在这个强大的欲望逻辑的笼罩下,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已然堕落,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已然过时,补天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已然无力。”张光芒:《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所谓的“欲望叙事”成为新感觉派小说的重要叙事方式。
如果将欲望叙事扩展到文化哲学层面,相对而言,存在主义先行者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堪称现代西方哲学中最为典型的欲望叙事。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作为表象而存在的。而作为其基础的不是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更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或“绝对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盲目的、永动不息的、永不疲惫的欲望冲动。这种欲望冲动是一种求生存的欲望冲动,叔本华将之称为生存意志。因为叔本华发现,康德把人叙述为理性的人是不对的。他认为人不仅有理性,而且有欲望与情感,即意志。而且,人最本质的东西是意志或意欲(Will)。由此观之,叔本华的意志或意欲(Will)并不限于贪嗔痴之类,一切生命力量都可以说是一种“欲望”,奋进的欲望、感激的欲望、利他的欲望……。这样,人的自我欲望就不仅是痛苦的来源,而成为了实现/超越自我,成为尼采式超人的必然途径。因此,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意志或意欲(Will)的一个表象。意志总是冲动的,所以它在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形式就是“欲望”。叔本华的逻辑是:人具有欲望,这是生命的本性。有欲望,就证明想去得到一些现在还没有的东西。所以,欲望说明缺乏,缺乏则意味着痛苦。这种痛苦是生命存在应该承受的。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你会痛苦;如果欲望得到了满足,你又会无聊,还是痛苦;在欲望得到满足后又会有新的欲望产生,而新的欲望意味着新的痛苦。生命意志是无限的,而个体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意志在个体生命身上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一发现对叔本华来说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难题:发现人的本质是欲望之后怎么办?怎么安顿人心与社会秩序?叔本华令人意想不到的走向了“禁欲”。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从传统文化的迷雾中敞亮欲望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而禁欲却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从肯定生命意志开始,以否定生命意志结束,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里似乎包含着佛教的言说。叔本华确实受了印度宗教的影响,但他认为这决只不是宗教的问题,对于意志的内在矛盾及其本质上的虚无性,教徒和哲学家都应该去认识。质言之,叔本华的欲望叙事不仅是对启蒙理性的有力颠覆,而且是对西方的整个理性主义传统的无情打击。因为尽管他走向了禁欲,但他毕竟是从与传统理性主义不同的另外一个路向上,即从生命角度去叙述人、人的欲望。
而中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精神对话就是从“欲望”着眼的。王国维在接触叔本华之前已深深体验到人生的辛劳与失望,茫昧于生命意义的晦暗不彰。叔本华关于生活、欲望与痛苦三者合一的悲观主义证实了、强化了王国维原已拥有的悲观情怀。“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方面,无往则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王国维:《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生活的本质是欲望,欲望的后果只能是痛苦,这既是叔本华的推论也是王国维的体验。王国维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欲”,追求欲望必然会带来痛苦,“欲”偿之不足,是苦痛;如愿以偿,是倦厌,也是一种苦痛;要追求“快乐”的努力,是苦痛;“快乐”以后又回复“快乐”,又是苦痛,而这种苦痛,随着文化愈进,知识弥广,苦痛更深,结论只能是世界是地狱,生活是无穷的苦痛。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所以说王国维的欲望言说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意味。而王国维之所以像叔本华那样将“生命—欲望—痛苦”视为“人生之问题”的核心,正是忧虑于个体生命存在本身被遮蔽使得“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③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7、9页。或者说,是源于对个体生命困惑的“忧生”:个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在他看来,“欲望”成为与生俱来的本体意味着人之存在的根源不在“忧世”而在“忧生”,因而,它思考的不是社会的缺陷而是生命本身的缺陷。对于个体性自我存在的拒绝曾经使得中国文化长期滞留于“我们的世界”,并导致知足常乐的人生体验,甚至以取消向生命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困惑。但是王国维的文化思考却并非如此,它是对于个体性自我存在的见证,是从悲观主义、痛苦、罪恶的角度看世界,也是通过向生命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困惑。哲学由此也就进入了“我的世界”——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并且力求为“我的世界”立法。既然生命的真实是个体,那么审美活动无疑就大有用武之地。或许审美活动本来就应该是个体的对应形式,只是在理性主义的重压下它才不得不扭曲自己的本性去与理性主义为伍。一旦生命回归个体,审美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回归本性,成为生命个体的通道:隐匿的存在从中敞亮而出,不在场因之呈现而出。于是王国维的文化思考延伸到“生命—欲望—苦痛—解脱或慰藉”的美学境地,即艺术慰藉或解脱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③个体生命活动只有通过审美活动才能够得到显现、敞开,审美活动只有作为个体生命活动的对应才有意义。而固守着生命的感悟,洞察了人生悲剧,生命的痛苦、凄美、沉郁、悲欢才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思想的世界。王国维之所以最终以生命为代价来确证和索取“此在”的意义——解决存在之困惑,是因为他的选择自杀并非通常所说的最终走向叔本华的以死“解脱论”和对悲观主义的归宿,而是萨特的选择的自由或海德格尔的自我的筹划——实现了一种纯粹的“此在”方式:“Heidegger认为最能体现独一无二的个体存在是他(她)的前行到死亡中去。因为只有在这个此在中才能体认到存在,……只有前行到死之中取得此在才能体认到真正的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存在。”“依据Heidegger……,领会着死亡而生存,并不只是意识到自己有限时间性的存在,也不只是‘真我自觉选择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它是站在前行到死亡中的基点上去决断客观性的明天。”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92-93页。可见,王氏将自己的生命化作一个“存在”的问号,并且通过对这个问号的解读来重新探询欲望诉求的可能性。有理由相信,从王国维的哲学到新感觉派小说,显示了非理性主义的欲望叙事在现代中国演变的某种轨迹。
从叔本华出发又超出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有史以来的最为确切的欲望叙事,乃至可以说,在现代西方思想界最“纵欲“的还是尼采。众所周知,“身体”是尼采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尼采大张旗鼓地为身体疾呼,肯定肉体生命及对生命本能的张扬。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人强健而乐天。他们绝无顾忌地坦身露体,在别人嘲笑自己以前先行自嘲。因为他们要在被人掌握前先走一步,摧毁已成的自己。这才是欲望逻辑的真谛。针对叔本华的禁欲主义,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禁欲主义理想意味着什么?》中宣称 “宁可让人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与叔本华的“禁欲”诉求不同,尼采所要求的是无限扩张个体的意志力,企求原始快感的横流旁溢。由此推演下去,是个体生命意志的疯狂和残酷,是绝对的粗暴和毁灭。只有艺术才是意志和生命力的最高显现,它必须摆脱道德的约束,或者是嘲讽它们。而且,艺术家比自古以来的所有哲学家都更正确,因为他们没有离开生命循之而进的总轨道,他们热爱“尘世”的事物,爱他们的感官。尼采几乎是把艺术、审美状态与生命力意志同一化了。只有审美的状态才具有丰富的传达手段,同时对刺激和信息具有高度的感受性。它是生物之间进行交流和传递的顶峰,是语言之源。尼采于是大肆宣扬审美状态的残酷性、疯狂性,认为在审美状态中人们置光彩和丰盈于事物,赋予诗意,直到它们反映出生命意志的丰富和生之逸乐。性冲动、醉、残酷是生命意志的基本状态和主要因素,它们都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庆之欢乐。尼采的欲望叙事旨在为意志及其欲望卸下千年的重负,重寻狂欢的酒神。由是,作为生命本能的欲望不仅开启了人们对于身体的关注,更开启了审视艺术与美的新通道。而身体、欲望、艺术的共舞又将人类的生命意志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尼采力图从生命存在的本质、人和世界的关系来认识与理解身体、欲望和艺术的本质与价值。如果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一种生命原欲的升华论,那么,尼采所做的就是生命原欲的还原论。尼采明确地断定,艺术是一种生物机能,它是生活的最强大的动力。美属于有用、有益、提高生命等生物学价值的一般范畴之列,它很久以来就提示着、联系着有用事物和有用状态的种种刺激给人们以美感,即权力感增长的感觉。参阅刘小枫:《诗化哲学——德国浪漫美学传统》,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36页。
法国当代哲学家、新尼采主义者德勒兹正是通过激活尼采而引发了对欲望哲学的热情。德勒兹以“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性的”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将“欲望”界定为构成主体或社会存在的一种基本实体,其“欲望”概念是对尼采“权力意志”的直接发展——将“权力意志”的要素定义为“激情”(affectivité)、“感性”(sensibilité)和“感官”(sensation)。德勒兹认为,被传统的心身二元论哲学所割裂的身体、身体感觉或感性经验不但构成一切语言或命题的基本话语内涵,更是考量、审度一切事物的主要尺度,它在其本质上是“一种无形的、复杂的和不可还原的实体。它虽位于事物的表面,却是陈述中所附着或存在的一种纯粹事件。”④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9、22.因此,感觉一方面通过陈述进行表达,另一方面也可以指谓事态属性。“它就是陈述和事物之间的界限。”④依德勒兹所见,“欲望的唯一客观性就是流动”,亦即柏格森所说的“生命之流”、“内在绵延”及其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创造性。而人类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命存在的自由,除了创造和运用一种更为平衡的技术之外,还要用欲望、意志、想像、激情来改变生活与世界。“因为欲望和无意识要比需要、利益以及物质生产更为重要。”德勒兹反对“那些过滥的、阻碍着无意识之流的各种机制、话语、制度、专家和权威”;在认知和实践领域主张一种“非固定的、解辖域化的、游牧式的运动”;认为“它出现于生产性欲望的微观生理(microphysical)平面上。”[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很明显,德勒兹像尼采那样将身体、力量、欲望、意志和激情等要素置于生命存在论的再现图式上;在这样的存在论图式中,人的欲望得到真正的解放、生命激情自由流淌,一种反俄狄浦斯的主体得以形成,“这样一种主体,即其欲望自由奔流的主体,将会形成一种爆炸性的和革命性的力量。”[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质言之,德勒兹摒弃西方传统的原子论形而上学以及静态存在哲学,从而以关于自然力量和生物力量的理论为认知前提,对既往的所有价值都进行重新评估,试图创造新的思维和生命形式及其可能性。参阅张之沧:《论德勒兹的非理性认知论》,《江海学刊》2009年第1期。
三
“新感觉派的叙述特色之一,便是探讨都市与人的关系,以及欲望在现代物质文明冲击下的发展路向。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小说,善于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从不同侧面透视欲望在都市社会中的表现形态。”程文超等:《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尽管施蛰存在新感觉派创作中有其独特之处,但欲望叙事却殊途同归,比如《梅雨之夕》以丰富的心理细节表现了一个男人与一个路过的女子雨中不期而遇时所体验到的心理欲望,这颇似戴望舒的《雨巷》;而且两者都是以陌生女子的“消失”作结的。然而不同于《雨巷》所呈现的极富古典意境的幽深小巷的潇潇春雨,《梅雨之夕》中强调的是“淫雨”中的相遇,正是从“淫雨”的双关语义中叙述者透露了人物内心的情欲像雨一样流溢,当这样的情欲呈示为流动形式——意识流般表现时,人的欲望更是难以遏制。
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一种文本,它通过将女性表现为文本来讲述关于男性欲望的故事。”转引自张英进:《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97年第3期。如果说现代都市的物质空间所展示的是欲望化的“都市风景线”,那么都市女性则是“都市风景线”的象征符号——新感觉派小说欲望叙事的最典型的表征就是那些摩登女性,李欧梵曾将新感觉派小说中的都市摩登女郎称之为“性感尤物”,这些张扬着肉感穿梭于各个暧昧空间对男性产生致命诱惑的“尤物”的躯体最能体现都市的欲望化特质:“这种女人是超现实的,是男人——特别是像刘呐鸥那种洋化的都市男人——心目中的一个幻象。”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18页。国内学者乔以钢先生则将这样的小说样态称为“尤物叙事”,在“尤物叙事”文本中,男性人物一方面将“尤物”等同于“物(欲)”用以检验自身存在,结果却是被“物(欲)”所异化,丧失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乔以钢等:《论新感觉派文本的“尤物叙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的确,在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中,那些风采独异的摩登女郎无异于“近代都会的所产”(《风景》),刘呐鸥笔下的女性均属欲望化的尤物,成为男性直接感受都市和消费人生的对象。她们不但甘于把自己的身体置换为商品以换取生活所需,而且在“游戏”中还常常处于主动位置支配和嘲弄着自以为是的猎艳者。李欧梵因此认为刘呐鸥的作品里型构了“以‘现代尤物为代表的都市辞藻系列”,而且是“中国第一个建立这个意象的现代作家。”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施蛰存的《特吕姑娘》中的秦贞娥是永新百货公司的香妆品部的服务员,为了尽可能地推销商品而谋取高薪酬的她不知不觉中成为了Missde Luxe(英法语:奢侈小姐),皆因她常常劝导顾客(大多是男性顾客)购买贵重物品而上了流行小报,以致被人们无聊乃至不无色情地地品评她的姿态和容貌——其本身就成为被“欲望”消费的商品。在穆时英的小说中,那些摩登女郎的外形特征和精神气质一般都没有了东方女性含蓄内敛、温柔贤静的特点,更多的彰显出诸如性感妖娆、锋芒毕露、张扬放纵的西方女性的风情特征。比如,摩登女郎们或是有着“蛇的身子,猫的脑袋”和“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或是显露出“希腊式的鼻子”,“嘉宝型的眉”,“红腻的嘴唇”和“天鹅绒那么温柔的黑眼珠子”(《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丰腴的胴体和褐色的肌肤”(《红色的女猎神》)。至于《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里的蓉子则习惯于把男人视为“消遣品”,无聊时当作“辛辣的刺激物”,高兴时当作“朱古力糖似的含着”,厌烦时就成了被她“排泄出来的朱古力糖渣”。摩登女郎们即使有“辽远的恋情和辽远的愁思和蔚蓝的心脏”,“也只是一种为了生活获得方便的商标”(《PIERROT》)。
《CRAVEN“A”》更是一个在男性视角下完成的欲望叙事的典范文本——女性始终无法挣脱被欲望化和符码化的命运。作品透过“我”在舞场的一角偷窥一位抽着CRAVEN“A”香烟的女性,在一种近似意淫的心理体验中,奇特地以国家地图来隐喻、描绘女性身体——沿着地图从北到南、从上到下地描述着女性的躯体部位, “作者用‘黑松林隐喻头发,用‘火山隐喻嘴,用‘小山隐喻乳房,用‘海堤隐喻双腿,用‘汽船入港隐喻男女交合。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那段关于‘大都市夜景的描绘,分明喻隐着30年代作为殖民入侵地和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城市形象。由此,地图、女体和城市在文本中达成了同构性的共谋,都指向了潜文本的欲望。”李洪华:《现代都市的“颓废”书写——穆时英小说创作新论》,《南昌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不言而喻,其中富有隐喻色彩和色情意味的书写明显地带有性幻想的特征——女性在此被欲望话语“编码”进入新感觉派的叙述与想象中。这意味着,她们对于新感觉派作家的意义在于建构感觉,通过这种感觉来展现现代都市人生命的躁动和存在的焦虑。
不言而喻,新感觉派小说一方面放弃了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传统职责,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欲望并不简单地就是对‘理性的反抗。五四时期启蒙理性催生的‘个性张扬往往是‘欲望的张扬。现代文学中的‘欲望叙事所要逃避或反抗的,其实是文学中趋向整体主义历史理性的启蒙理性以及整体主义历史理性本身。”③程文超等:《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1、162页。有不少研究者论及新感觉派小说的“欲望”叙述时,指出其只是表现出一种创作姿态,它本身并不具有建构性,建构性的事业仍然需要“理性”来成就。如果说,五四文学以郁达夫为代表的文学的“欲望”反抗指向了传统儒家伦理,即,文学中的“欲望”和“启蒙理性”共生,抨击封建礼教专制和现实压抑;那么,新感觉派小说的欲望叙事逐渐游离五四“启蒙理性”和“整体主义历史理性”,作家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叙述策略:以“感觉”的方式通过对欲望话语的伦理改写。无论是施蛰存旨在以性爱动机去消解历史对象的光环,还是刘呐鸥、穆时英以人的生物性来注释人的生命形式,现代人的生存真相和存在本相在他们看来都毫无神圣感而是关乎“财色”根性。当欲望的文化价值被如此重估,或者说,欲望叙事不再囿于神、理性、道德规范等的范围内而是展开其另外一面——“负面”的“欲求”内涵,原欲被看作是生命的本质力量,也许它在主观上并没有直接关涉存在本体论问题,但在客观上它所践履的是“本能造反逻各斯”的路径:思考人在“欲望”的层面上作为生命存在“主体”的自觉是否可能,也就是以“欲望主体”颠覆或取代“认识主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欲望对“文化”——存在主义叙事的意义。
在这样的价值前提下,新感觉派小说或者说文学建构首先必须面对欲望,然后才能去寻找有创造性的文化表述。所谓“感性的生活—欲望的转移或释放—价值理念的崩溃—精神的幻灭,成为新感觉派小说触目惊心的现象,传达出那个时代特有的‘危机意识。”③换言之,文学的“欲望”表达无疑是对“整体主义历史理性”的疏离和反思,它是为了期待一种建构,而不是意在沉沦。随之而来的不是欲望叙事的枯竭,而是欲望之于文化生产性、创造性力量。オ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重点课题“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论”(项目号:10112462);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重点课题“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略”(项目号:10A084)。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55页。
② 包亚明等:《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浅析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评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