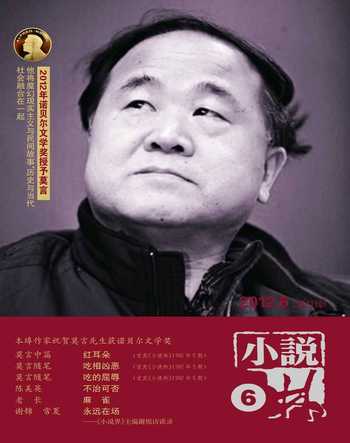思想寓于形象
陈美英
写完这篇医疗题材小说,我如释重负,算是对一段医疗生涯的总结,无论行医,还是就医。我一向拒绝现实主义,但这篇小说我还是以医疗真相不厌其烦地呈现人物生存现实,虽然我根本上要表达的,是对于实现人的主体性的探寻。
卓著是我首先想表现的人物。作为一个复杂的医生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原型。哲学家般冷静,文学家般情感丰富,她在有父母却缺乏爱的自卑感中活命,最终没能抵挡住自我否定,选择了简单终结生存困难的道路。她一定是劝病人治病的,医生怎么能给病人说放弃生命的话,在这个活命至上的国度。如此说来,治与不治,是关于是否去死的问题,病人看似有主动选择权,其实是没有的。卓著看似患了抑郁症,其实是哲学家在人群中抽离出来,在对自身生命权的否定中辩证思考生命价值的问题。也许她由此深谙一门死亡艺术古雅的气派,像远古的智者以自身实践死亡的神圣性。没有爱的成长过程对于个体来说是不幸的,吕执拗是客观地被抛弃的孤儿,但他却有孤儿院里的爱。他多少还有点童年可追忆,所谓有家可归。吕执拗最终毅然前行在演员职业和自我实现的道路上。我以演员身份确定病人角色,将其天才与命运的坎坷结合,由他的生命河流方向自行决定故事发展。他的打官司、最后住进剧组,都是要得到真理和人群中的存在感。他是有相当自我意识的。相对来说,卓著的自我意识较弱,除了主动给吕执拗治病,少有作为。生存就是行动,但行动的根本是要有目的、有意义,因此还得牢持心中正见。如何获得正见?只有一次次在生活中被激流冲击,并获得个性价值思考。
传染病的防治乱象相当严重,但并不为人所知,就连作为医疗行业的人,也受其害。卓著科室在收治病人上以经济利益为原则,导致传染病传播,导致医务人员感染,这种现象并非少见。这样的乱象与人物自身从小到大、到因医事相遇所致的相互无力承担,都是荒谬世界的真相。我故意淡化卓著作为医生形象出场,而是作为吕执拗遇上的朋友身份,让他们灵魂映照。卓著是否真的自杀,也只能是猜测。她留下的物件,也许是巧合,是象征。对于一个与医疗体制形成反讽的医生形象,她的消失充满寓意。关于医患关系,素来是争议性话题,人们普遍认为是冲突剧烈的。这篇小说却以温情展现,这也并非不合理。孑然一身的无助感、对生命本真意义的追求,使他们异于常人。那些生活过的并不自愿的时间,对于生命来说是过于沉重和浪费了。我赋予人物如此艰难的个体存在感的找寻任务,就像在黑夜里泅渡。我抛弃传统叙事的紧张感,试图在人物的生活流中寻找分岔,让人物自身命运的可能性由此展开,这样做是想呈现复杂的生活现实,也体现现在时态个体心灵的危机感。我一向在以往的小说中任由人物自己旅行,人物都进入梦幻场景,他们与世界的遭遇往往不是我事先能充分决定的。这篇小说的梦幻色彩却较淡,与周遭相遇时,他们得到的是生硬的物体感,无论在大环境还是小场景中。我让这篇小说呈现更多的是心灵的相似性和现实的逼仄性,但思想的整理还是寓于其中。治与不治,活与不活,这是关于生死的问题。吕执拗因为具有主体性,所以选择治。卓著因为无力爱,选择了不治。她更多的是诀别于心死。
思想寓于形象中,人物无力动弹了,因为世界在他们的感知中很少有想象力发生。卓著的童年是欲哭无泪的冤屈,是被歧视为女孩的传统恨女社会造成的。孤儿情结导致的自卑感,是外人无法真正理解的。这也是我赋予卓著这个人物最大同情心和命运挣扎的出发点。她和吕执拗说了不少话,总算把她的一生交代了个大概。她和吕执拗之间有些生活浪花扑打,但她的压抑使它们平淡得如同白大褂一般。我让这个医生和病人互相心疼,不是恋人,却是大爱。就是想说明,其实一点点理解和同情,在弃儿般特殊人群中,也是凭机缘才得的。我淡化了故事冲突,让现实生活自然地表现自己,是我在修改这篇小说的艰难过程中发现的。中篇小说要实现我喜欢的诗化意境,还是很难的。我在这篇小说中部分做到了。我因此略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