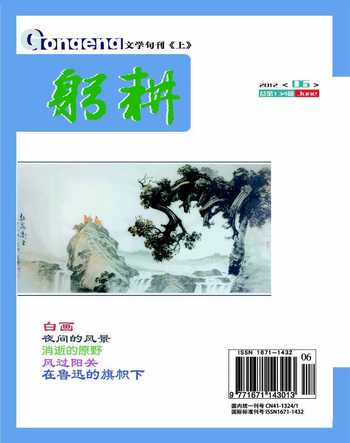小说四题
王振东
上坟
翠花打小没了爹,是娘屎一把尿一把地把她和哥拉扯大,为哥娶了媳妇,为她嫁了人。娘本该享享福了,可嫂子爱梅太懒,家务活全落在娘一人身上。娘本来身体就不好,一天下来,身子骨累得像散了架一样。翠花疼娘,经常回去帮娘洗洗涮涮,心想自己要是有孙悟空的分身术,分一个自己帮娘该多好啊!
正月十六那天,娘没缘由地一头栽倒在地,永远地走了。翠花想到娘一生的不易,哭昏过去……送走娘,她整整睡了三天,做了许多梦,每次都梦到娘还活着,可等梦醒了,才感到娘确确实实地不在了,泪就像小河里的水一样哗哗流淌。
日子在煎熬中到了清明节,翠花想回去给娘上坟,可一想到那个该死的风俗,又犹豫了。在黄土洼,每年的大年初一、清明节、十月一日和父母去世周年那天,有给去世父母上坟的风俗,烧些纸钱,燃挂鞭炮,寄托对逝去亲人的哀思。但已出嫁的闺女,却只能在父母周年那天才能上坟,如果在大年初一、清明节和十月一日这三天回娘家上坟,据说会给娘家带来灾祸。翠花那年考上了大学,家里供不起,只好嫁了人。对于这个风俗,她这个差点儿踏入大学校门的农村女人也是半信半疑。她和丈夫商量,丈夫劝道,宁可信其对,不能信其错,咱可甭坏了祖先传下的规矩。她只好怏怏作罢。
十月一日这天,翠花还想回去给娘上坟。她给丈夫一说,丈夫还是摇头反对,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娘,可娘毕竟不在了,说句不中听的话,为了给死人烧纸,真给哥家带来灾祸,你会后悔一辈子的。翠花想了想,只好打消上坟的念头。
大年初一到了,翠花没再想给娘上坟的事,因为距娘去世一周年只剩半个月时间,那天她可以理直气壮地给娘上坟,给娘烧好多好多纸钱。
距娘周年越来越近,翠花简直有些迫不及待了,提前几天买回了供品、纸钱和鞭炮。谁知正月十六那天早上,丈夫下红薯窖拾红薯时,缺氧的红薯窖一下子把丈夫熏倒了,在医院住了三天才痊愈出院。这个周年翠花自然没给娘上成坟。
日子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咣当咣当走过了一年,娘的周年又到了。可老天仿佛捉弄翠花似的,那天她公爹去世了。可怜翠花空有一片孝心,又没能给娘上成坟。
两次都没能成行,这让翠花为娘上坟的愿望更加强烈。给公爹守完孝,距清明节也不远了。翠花想,啥风俗啊?那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种禁忌,我就不信上回坟真能给娘家带来灾祸!
清明节那天,翠花悄无声息地来到娘坟上,烧了纸钱,燃了鞭炮,然后虔诚地跪在娘的坟前磕了四个响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泪像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
翠花给娘上坟的事,像风一样很快传到了爱梅耳朵里。她气呼呼地跑到坟上,大声质问翠花,在咱黄土洼,我还没见过一个出了嫁的闺女像你这样回来上坟的。你嫌俺家穷的轻?!
翠花赔着笑,嫂子,我巴不得你和我哥过得比城里人还好哩!
爱梅撇着嘴,既然这样想,你为啥还回来上坟?难道忘了咱家乡的风俗?
翠花哽咽了,娘在世时为我们吃尽了苦,她死了两年多,我连张纸儿都没能为她烧,我心里有愧啊!
你心里有愧,就该让我们过不好?
嫂子,现在都啥年代了,咱该对那个风俗的对错有个分辨了。
分辨个啥?人老几辈都是这样做的。你甭不信,我家要是出了啥不好事,到时候再给你算账……
可一个月过去了,爱梅家里鸡鸣狗吠,六畜兴旺,并没有发生啥不好的事,倒是喂的一头母牛下了双胞胎牛犊。这可是件大喜事,爱梅高兴,就演了一场电影。
俩月过去了,爱梅家里炊烟袅袅,一派祥和,还没有发生啥不好的事,倒是种的十亩麦子获得了好收成,每亩合一千二百斤。爱梅高兴,就给丈夫买了一瓶酒。
又过了俩月,爱梅家里莺歌燕舞,欢声笑语,仍没有发生啥不好的事,倒是儿子小涛被省里的一所大学录取了。爱梅这次更高兴,请了县里的剧团,美美地唱了三天。
接二连三的好事让爱梅也对那个古老的风俗产生了怀疑——如果是对的,那咋没在我家应验?她感到真的对不住翠花了。
小涛上大学走的前夕,翠花回娘家给小涛送学费。爱梅说,翠花,都怪嫂子不好,让你受委曲了。翠花说,嫂子,不怪你,要怪只能怪封建迷信。我想了多天,老祖宗传下来的风俗,教人向善的得遵循,迷信害人的得摒弃,就像锄草一样,把庄稼留住,把野草锄掉,你说对不对?
黑叔
黑叔已走了三十多年了,尽管村里人一直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可在每年黑叔的祭日那天,村里人照样会三五成群地去他的坟上烧些纸钱,祈祷他在“那边”过得幸福。
我六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个逃荒的汉子。他长得又瘦又矮,一双不大的眼睛白多黑少,一只鼻子又大又扁,与眼睛极不协调。他最突出的特点是黑,黑得就像刚升井的挖煤工人。后来,他就落户到了我们黄土洼,在生产队的机井房里安了家。因为他特黑,村里人都叫他老黑,我们这一辈儿的人都叫他黑叔。
黑叔很勤快,很随和,东家垒房,西家砌灶,只要主人一叫,他立马就到,吃饭时,主人就留他吃顿便饭。那年月柴火特缺,每年家家户户都要到二十多里外的山上去拾。黑叔就每天到山上拾“跑挑”,然后分给村民。
黑叔是个戏迷,十里八村起戏了,他就领着我们这些娃崽去看,但他并不真正懂戏。除了记住几个戏名,哼些唱段,其余的多半是糊里糊涂。农闲时,黑叔每年都要张罗着为村里唱台戏。大队没有节余,又没有人愿管这闲事,人心哪有恁齐?黑叔便舍着脸面挨家挨户按人收钱,收齐了,选个日子呼喝了村里的牛车,把戏班子拉来,搭个土台子唱上几天。黑叔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可他乐意。
村东头田叔远在百里外的县化肥厂工作,田婶一人在家拉扯五个孩子,还要种自留地,把田婶的脊梁都累弯了。黑叔看到田婶忙了家里忙地里,就主动帮她运粪、锄草。田婶过意不去,时不时帮黑叔浆洗、缝补一下衣裳。一次,黑叔帮田婶收玉米时,不小心把裤子扯了个口子,田婶看这条补丁摞补丁的裤子实在无法再补了,便到代销点扯了几尺蓝洋布,为黑叔缝了一条裤子。田婶怕白天给黑叔送去让外人看见说闲话,便在晚上送了过去。当田婶走出黑叔住的机井房时,刚好碰到本村一个想占田婶便宜而没占到的“二流子”,第二天,风言风语便像瘟疫一样在村里传开了。不久,这话传到了田叔的耳朵里,便喊上小舅子,把黑叔痛打了一顿。黑叔没做任何反抗和辩解。后来,他对人们说:“这种事只会越描越黑,我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中。”
因了黑叔的貌相,他一直没有对上亲。后来,家乡闹灾荒,与黑叔相依为命的老娘饿死了,他便只身逃荒到了我们村。也该黑叔有艳福。一天,一个人贩子给黑叔领来一个媳妇,二十几岁,长得水灵灵的,黑叔虽然嘴上说着那岁数、相貌不般配,可手上还是把攒了多年的四百块钱给了人贩子。晚上入洞房时,黑叔盘腿坐在床上,嘴里哼着豫剧《抬花轿》,脸上泛着黑红的光。可该宽衣解带时,姑娘死活不肯。黑叔也生了气,大声对姑娘说:“你可是我花四百块钱买来的呀!”姑娘扑通跪在黑叔面前:“大伯,你行行好放俺走吧,俺家里有男人,还有个两岁的孩子。人贩子骗你的钱,日后俺一定还你。”黑叔毕竟还是个没碰过女人的人,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姑娘俊俏的脸蛋、丰满的胸脯,喉结不停地上下滚动。少顷,黑叔猛地趷蹴在地上,对地重重地擂了一拳,长叹一声,双手插进头发中。好半天,黑叔站起来,走到姑娘面前,平静地说:“你走吧。”姑娘迟疑了一下,慢慢朝门口挪动着脚步。“回来!”黑叔猛地大喝一声,“这黑灯瞎火的,这会儿往哪儿走?明儿个我送你。”黑叔让姑娘插上门栓,睡在自己的床上,他却在门外蹲了一夜。第二天,黑叔把姑娘送到汽车站,临走,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三十块钱给姑娘做盘缠。那姑娘走后,黑叔把半斤老白干全倒入肚里,呜呜咽咽哭了一晌……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黑叔依然爱为村里张罗着唱戏,可每逢唱到《光棍哭妻》,他那青白的眼,总要湿润几回,他又想起了那个姑娘。
就在那一年,村里唯一的土井淤了泥,一桶下去只打少半桶泥水。村里决定淘井,可谁也不敢下,井深不说,井壁还噼哩叭啦往下掉泥。黑叔不怕。他甩掉打着补丁的汗衫,只穿件大裤头,一拍肋骨突出的胸脯:“我老黑下。你们都有家有口,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怕啥!把辘辘绳给我拴上……”便下到七丈多深的土井。
土井淘出了水,却要了黑叔的性命。那年,他才四十二岁。本来黑叔把井底的活收拾得很干净,铲完最后一铲泥挂好带泥的水桶,擦把汗低头收拾工具准备上井,不想绳索断了,绞到井口的泥水桶一下子掉了下来,正中黑叔的后脑勺,可惜黑叔没喝上一口土井水便去了。
那夜很静,天上挂着一轮清白月,像是黑叔的眼。
村里为黑叔办了有史以来最体面的葬礼。全村人组成的送葬队伍缓缓从井旁经过,将黑叔葬在了距水井三丈来远的地方,又在墓边树起一块石碑,上边端端正正地刻着四个字:好人老黑!
走闺女
三婶,你这是去哪儿?走闺女呗!走闺女是黄土洼人的说法,意即去闺女家。这不,三婶和三叔因琐事拌了几句嘴,三婶一气之下就去了闺女家。
这天下午,三婶让三叔在家喂牛,自己去麦田套种苞谷。种完一垄,三婶的口就干渴起来。这时,刚好结实回家,就让结实给三叔捎个话,让三叔给她送壶水。三叔给牛拌上草,正准备去送水,不巧村里的有福来串门,两人就闲扯起来……等有福走了,三叔却把送水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三婶左等右等不见三叔,便回到家,见三叔正坐在院里吸烟哩。三婶气得大声吵嚷,我在地里顶着日头干活儿,你连壶水都不给送,你就这样对我?
三叔这才想起忘了送水,就把有福来串门的事说了。
三婶哪里听得进去,忘了?你心里分明没我!说着,泪就落了下来。
三叔见三婶胡搅蛮缠,也生气了,你甭上纲上线,没送水就心里没你了?
三婶说,就是,看看人家的男人,待自家女人多好。看看你是咋对我的!
三叔赌气说,我不好,人家好,你去找好的呀!
三婶也赌气说,你当我找不着?离了你那夜壶照样尿尿。我这就去找!
三叔揶揄道,去吧,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好好疼你。
三婶真的收拾了一个小包袱,抬脚出了门。三叔也不拦挡,看着女人的背影笑。
三叔三婶在一个锅里耍稀稠已经二十多年了,就这点儿小事,要是有人说说劝劝,也不会到这一步。可后半响邻居们都下地了,儿子和他们分家另过又住得远,所以二人吵架也没人听见。三婶气呼呼地出了村,心里骂道,死老头子,你一个人在家好好过吧!
三叔孤雁似地坐在院子里,清静了一会儿,背着手去了田里。他看着滚滚的麦浪,闻着浓浓的麦香,使劲儿吸溜了一下鼻子,麦香便像小河流水一样在体内潆绕,整个毛孔都舒展开来。他又连着吸溜了几下,刚才的郁闷慢慢消散,心情顿时舒畅起来,心里对三婶说,你走了我倒清静,我倒自在,可没人跟我吵架了。
三叔来到自家田头,贪婪地吸溜了几下鼻子,就下田里薅草。薅累了,就坐在田头吸烟。等日头快落下时,背起草往家走,心说,今儿后晌既散了心,又薅了草,真是一工二得,两全其美呀!到了家,忽然觉得饿了。三叔从未做过饭,去儿子家吃吧,儿子儿媳问起他娘来,咋说?干脆自己学做吧。他娘擀面条时,自己也见过。三叔开始和面。一和,稀了。放面再和,又干了。再兑水,又稀了……这样来回放了几次,最后也没和好,倒把三叔弄出一身汗。三叔气急,抓起面块扔到猪食槽里,和衣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的三叔睡不着,心想,这女人不在家,看来还真不中哩!得把他娘叫回来。她八成是走闺女家了。找个啥理由呢?他想呀想呀,忽然有了主意。
第二天早上,他让一个小孩去叫儿子,就说他病了。儿子慌忙赶过来,见爹躺在床上,问爹咋啦。三叔说,头疼。那我去请医生。不用。我娘呢?你娘去你姐家了。爹,你是不是想我娘了?谁说我想她了?她走十年我也不想!儿子一听,知道爹是啥病了。
在闺女家,三婶刚来时欢声笑语,能吃能睡,第二天就两眼呆滞,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帮闺女剥花生时,老出错——剥了一手窝花生,把花生米放在了花生壳上,却把花生壳放进了盛花生米的篮子里。闺女问,咋啦,娘?三婶没回闺女的话,问,闺女,我来几天了?闺女说,两天了。三婶说,我咋觉得有两年了。闺女摸了摸娘的额头,娘,你不发烧呀,咋说起胡话来了?!三婶说,我右眼光跳,老话不是说“左眼跳财,右眼跳捱”吗?我咋觉得家里有事。闺女说,娘,爹身子骨棒棒的,麦子也没熟,家里能有啥事?三婶说,不在家,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闺女说,娘,你是不是想爹了?三婶脸一红,想他?一百年不见他我也不想!闺女说,不想就在这儿住呗……晚上,娘躺在床上睡不着,翻来翻去像烙烧饼。
第二天早上,娘烧火,闺女做饭。忽然,电话响了。三婶“腾”的站起来,一溜小跑去接电话。电话是儿子打来的。儿子说,娘,我爹病了,你赶紧回来吧。你爹要紧不要紧?三婶声音直打颤。反正不吃不喝,光睡觉。三婶一听,饭也不吃了,背起小包袱就走。闺女也紧跟着娘回了家。
三婶赶到家,跑到床前,拉着三叔的手说,他爹,咋样?
三叔说,不碍事,然后话中有话地对闺女说,你回吧,女婿也离不开你!
三婶送走闺女,又回到床前,俯身用额头贴三叔的额头,试试爹发不发烧。三叔趁势抱住三婶。三婶挣脱三叔,死老头子,你到底啥病?快把人吓死了。三叔得意地指指胸口,心病。三婶猛醒过来,双手捶着三叔的胸脯,都多大年纪了,还没个正经……
石秘书
这是爷爷讲的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时,村里家家都缺吃的,时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全村人都盼着赶紧麦罢,以便分那每人几十斤的麦子。
麦口间,公社派石秘书来我们黄土洼“蹲点”。石秘书来村后就住在我家,因为我爷爷是贫协主席。石秘书吃的是派饭,一家吃一天,轮着吃。尽管主人们都竭尽全力招待,可碗里还是稀汤寡水,缺盐少油,偶尔桌上有点“内容”,那一定是好客的主人费尽心思东拼西凑来的。
转眼间麦子熟了,全村男女劳力起早摸黑抢收麦子,总算把麦子弄到场里了。这天后晌,生产队长奎叔用商量的口气对石秘书说,石秘书,今儿个队里要在“南天边”栽麦茬红薯,我怕保证不了质量,你能不能带一下工?石秘书说,没问题。“南天边”是我们队最远的一块地,距村子三里多远。干到半晌,一个大队干部找到石秘书,说有急事取件东西,请他回去一趟。石秘书只好回村。
办完事,石秘书返回“南天边”时,顺便到场里看看。忽然,老会计德成喊石秘书。德成说,我正做本季的粮食产量账,你过去看看吧。石秘书心头一热,心说老会计怪实在哩。很多队里的会计都在粮食账上做手脚,以求少向上报点儿,群众能多分点儿。老会计叫看账,说明他没做假。石秘书心里高兴着,嘴上却淡淡地说,老会计还跟我客气什么,你做账,我还能不放心?德成坚持说,还是看看吧,你也好提提意见。老会计越让看账,石秘书就越说不看了。见石秘书真不看账,德成关心地说,石秘书,别去场里了,那里又热又脏,再说也快收工了。石秘书说,没事。德成见石秘书非去不可,只好作罢。
石秘书没走多远,后边又有人喊。他回头一看,是副队长栓付。栓付说,石秘书这是去哪儿?
去场里看看。
甭去了,到我家坐会儿,今儿黑在我家喝汤。
不去了,饭在保才家吃。
有好吃的,你不去可要后悔的。
不后悔,好吃的留给嫂子吧。石秘书说着又要走。
栓付一步跨到石秘书前边,你不去真会后悔的,你嫂子从她娘家拿回来几个鸡蛋。
石秘书笑道,真的?
栓付心里一喜,我还能诓你?
石秘书说,那好,鸡蛋留着让孩子吃吧。
栓付还想说什么,可石秘书已经走了。
拐过一个弯儿,石秘书就看见奎叔正领着几个壮劳力扬麦子。
扬麦子是个技术活儿。用木掀铲一锨麦子,往上一扬,麦子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下来,麦子和糠就分开了。扬场需要风,风不能大,也不能小。风大,就把麦子刮跑了;风小,糠扬不出去,麦子就混到糠里了。石秘书看看天,没有一丝风。这怎么扬?他想。
来到场里,石秘书觉得场上的气氛有些异样,也没在意。他扒拉了一下麦糠,发现有大量的麦子混在里面。那时农村的粮食大部分要交公粮,留给农民自己的却很少。为少交多分,很多地方就将好麦充秕麦分掉。石秘书想,怪不得队长让他带工栽红薯,老会计和副队长又千方百计阻拦他进场,原来是准备私分麦子哩。石秘书“噌”地站起来,大声叫奎叔过去。奎叔战战兢兢地来到石秘书跟前。
石秘书正准备把奎叔好好教训一顿,再交公社处理。倏地,他想到自己驻队以来,村里人对他的好。又想到农民要吃点自己种的粮食,竟然这么难!心里便“格登”一下,心说我差点办个昏事,眼睛就有点儿潮。他丢下手中的麦子,假装迷了眼,用手揉揉,然后对奎叔说,我去“南天边”路过这里,看看活儿干完没有。别的没事,快干活儿吧。
按以往的做法,麦子扬完后,好麦入仓,秕麦当场分掉。可这回奎叔没敢分。晚上,石秘书了解到秕麦还没分,便问奎叔。奎叔怯怯地看着石秘书,嗫嚅道,还……分?石秘书说,为啥不分,秕麦不分留着干什么?今晚我要到别的村转一下,你们辛苦点儿,加班分了。
一天吃晚饭时,石秘书忽然觉得饭菜“丰盛”了,有豆腐,有油馍,还有鸡蛋。细想,好像这几天家家都是这样。石秘书很纳闷,回到我家便问爷爷。开始爷爷不说,怎奈石秘书非逼他说,不得已才说出实情:大伙儿都说你是好人,就私下商量,变着法子给你改善生活。可大伙儿家底有限,有心无力,队里决定给管饭户每天补一块钱。
石秘书一听,把奎叔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你这队长是咋当的?你已经犯了一次错误,难道还要再犯一次?赶快取消补助,取消“特殊餐”,否则我撤你的职。
石秘书在我们村驻队结束时,全体村民都去送行,他们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石秘书变成一个黑点儿消失在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