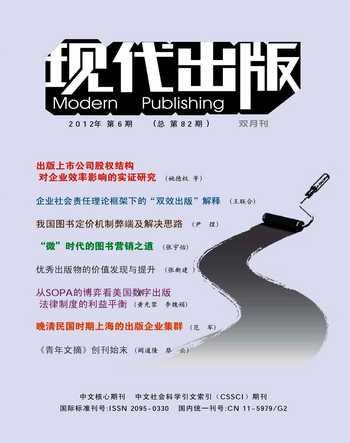论出版者权与邻接权的本质区别及其保護
金雷宇
摘要:我国《著作权法》将出版者的权利与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等惯例称为“邻接权”的权利规定在一起,并单独作为一章,统称为“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这种少见的立法安排多年来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同时使得学界对于邻接权的表述产生了一些歧义。本文分析了出版者权与邻接权的本质区别,认为无论是专有出版权还是版式设计权,都与一般意义上的邻接权有着较大的差异,应该明确予以区分以利于更好地保護。
关键词:出版者权;版式设计;邻接权;出版业
首先必须说明,出版者权(出版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在现行《著作权法》中依然是被整体纳入“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框架之内的。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出版者权的核心内容“专有出版权”与“版式设计专有权”都是“邻接权”。尽管《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特别说明出版者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是指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但是从国际惯例来看,所谓“相关权”一般是没有图书出版者的权利的,因此混淆还是不可避免。
一、专有出版权与邻接权的显著差异
在国际上,邻接权一般仅指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因传播作品而产生的权利。就其传播的功能来说,出版活动与上述三项活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国1991年的《著作权法》,授予图书出版者不超过十年的专有出版权,并将其与表演、录音录像、广播电视播放并列为一章。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以限制著作权人的权利为代价,使出版者有法定权利通过合同形式从著作权人手中获得出版权。在当时的立法框架下,出版者享有的包括“专有出版权”在内的一切权利,均属于“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意即“邻接权”。但是,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出版指的是“复制”加“发行”,而这两种权利明显是属于著作权人的,假设真有一种“出版权”的话,也理所应当要由著作权人享有。在2001年颁布的现行《著作权法》中,出版者是否享有专有出版权须由著作权人同其在出版合同中约定;同时明确了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杂志的版式设计享有专有使用权。这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出版者权与邻接权之间以往过于明显的逻辑冲突,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
根据前述隐含的逻辑,出版作品的权利本质上是由作者的著作权衍生出来的,其性质仍然是著作权,并不是“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这里涉及对邻接权的不同理解。有不少教材,认为邻接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邻接权,通常包括表演者权、音像制作者权及广播组织权三类;广义的邻接权,是把一切传播作品的媒介所享有的专有权一律纳入其中,其基本内容除以上三项外,还包括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报刊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客观事实其实是先有《著作权法》的模糊规定,而后才有这种“广义邻接权”的观点,因此这是循环论证,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出版者权是不是邻接权,从内容的权重来衡量,主要看“专有出版权”是不是邻接权。因为出版者权的主体就是专有出版权,而其他的如“投稿选登权”“再版权”等,完全可以与“专有出版权”一并解决。但是,根据前述理由,“专有出版权”所包含的种种权利,均由著作权人让渡而来,其来源是著作权而非“相关权”,其获得方式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双方作出的一种合约安排。因此,将出版权归人邻接权,等于是将作品出版的权利直接界定给出版者,于法理不符;而如果承认“复制”和“发行”是著作权人的权利,却又将它们置于邻接权下,则与邻接权的定义明显冲突。
由于我国出版业长期以来在传播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因此一开始特别强调对出版者利益的保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2001年修订后的《著作权法》中,“专有出版权”事实上已经被置于合约经济的框架之下,这是务实的方向,体现了立法者循序渐进理顺这一关系的意图。应该看到,尽管目前各说纷纭,但学术界对于“专有出版权”的性质界定还是比较一致的,即它不属于邻接权的范畴。《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也对此进行了解释。只不过在具体的立法体例上,这一权利尚没有跳出邻接权的范围,因此争议依旧。2012年出台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终于将“专有出版权”移至“权利的行使”一章,是对这个问题的及时反应,同时也印证了之前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对于“版式设计专有权”,学界一般认为应该是邻接权,理由是它和“其他”邻接权一样,是为了传播作品而产生的权利,因此这两者应该区分开来,“版式设计专有权”应该列入邻接权。然而正是这一点,笔者持有不同的看法。
二、版式设计专有权与邻接权的本质区别
从历史上看,以法律形式规定邻接权保護,最早见于奥地利1936年的著作权法。1961年的《保護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与广播组织国际公约》(简称《罗马公约》)开启了在国际间保護邻接权的历史。所谓邻接权(neighboringright),是指与著作权相邻近的权利或者相关联的权利。它是在传播作品中产生并来自作品的权利,是作品传播者对其传播作品过程中所作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权利。作品创作出来后,需在公众中传播,传播者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要有创造性劳动和经济投入,这种劳动与经济投入应受到法律保護。但是,这并不是说,只要是与传播作品有关的劳动或者经济性投入,都一定会成为邻接权的来源。“版式设计专有权”是否符合邻接权的特征,则要从多方面来看。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版式”是指“版面的格式”。换句话说,“版式设计”是对印刷品等的版面格式的设计,包括对版心、排式、用字、行距、标点等版面布局因素的安排。必须指出,这个定义是非常狭窄的,很可能使“版式设计”失去现实意义。因为这是把“版式设计”的功能仅仅理解为格式的美化与修饰。在一本书的尺寸里,对于文字格式的安排方式是极其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使得任何一种格式都难以产生足够的创造性劳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aker诉Selden一案中提出过一种“融合理论”,当某一思想只有唯一的或为数极少的表达方式时,则表达与思想融合为一,该表达不受保護。因此对于“版式”的理解,应该包括图文的组合形式,甚至色彩的运用等等。只有这种综合性的“设计”才有可能具有独创性,才称得上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这种劳动的投入正是许多人认为“版式设计”应该属于邻接权的重要理由。但是这种劳动是不是邻接权所指的涵盖传播过程的劳动投入呢?“版式设计”与邻接权的“传播活动”有何区别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会使“版式设计专有权”与邻接权的内在区别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来。
首先,邻接权的“传播活动”的客体是什么?比如表演,其客体自然是作品;录音录像的客体是音像制品;而“版式设计”的客体从语言逻辑看,显然应该是“版式”而不是作品。可见,邻接权是涵盖整个传播活动(包含作品)的权利,而“版式设计”不涵盖作品,仅仅是作品传播过程(出版活动)中一个微小的部分。
其次,邻接权的劳动或经济投入(其实劳动投入就是经济投入,因为劳动是有价格的),是附着于作品之上的。也即是说,这种投入的形式,如果没有作品的被传播,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但是版式设计却并不相同,版式设计的种种结果,就算没有具体的作品内容,比如换成无意义的文字填充,其图文结构的视觉元素依然可以显现出来。邻接权不可能脱离传播对象被单独地显示,而“版式设计权”却有可能,只要将“版式”固定下来成为形式,本身就有可能以视觉作品的特征取得著作权。即便不易固定成作品,它也至少可以通过“相似性”来判断区别,在视觉上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虽然邻接权所指的传播活动和版式设计活动都是一种“抽象的活动”,但是,前者的活动一旦作品内容被抽走就立刻空洞无物,它不能被物质性地识别出来,而后者的活动结果却是具体可感的。因此,邻接权所指的传播活动,除了依靠控制作品内容外,没有可能用其他的方式获得回报;而版式设计活动却可以通过“版式”这个具体的物质表现形式而获得回报。
再次,邻接权的形成有一个逻辑一致的隐含着的链条。比如从作品到表演,没有作品的授权,就没有表演者权;从表演到录音录像,没有表演者授权,就没有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从录音录像到广播,没有录音录像制作者授权,就没有广播组织权。也就是说,邻接权是产生于作品的一种有上下串联关系的权利。它的使用要从作品开始,并层层授权,没有上一层的许可就没有下一层的权利。但是版式具有独立的特性,它并不需要著作权人的授权就能够通过出版者自己的工作而形成。同时,被出版的作品是否受到著作权保護也并不影响版式设计权的成立。它是一种平行于著作权的权利,有了它,作品或许可以得以更好地传播;没有它,作品依然可以通过“不具有版式设计专有权”的版式而得以传播。简单地说,具有产权形态的“版式设计”并不是作品传播所必须的流程和环节。
举一个例子,让我们可以换个角度使上述问题看得更清楚。假设有一个出版者出版了一部作品,其文字内容与图案内容均与另一个出版者的出版物毫无关联,但是两部作品的版式设计却一模一样。这里顺便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因作品内容不同而判断前者没有侵犯后者的版式设计专有权。如果版式设计权必须依赖于作品内容,那这个权利事实上意义不大,因为它只能阻止那些同时或者事后取得同一作品出版权的其他出版者无偿地使用它,这不符合《著作权法》的本意。因此,要使版式设计有现实意义,就必须使其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作品内容而可以独立存在。言归正传,在这个例子里,倘若前一个出版者侵犯了后者的版式设计专有权,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认定侵权的性质呢?如果说这是侵犯了后者的邻接权,那么其“邻接”的作品在哪里?因为没有作品,邻接权不能凭空产生;如果说这是侵犯了某种“版式”,则这个侵权与邻接权何干?
可见,“版式设计专有权”虽然看似与传统意义上的邻接权很相像,但其实质却存在很大的区别。从邻接权产生的根源来看,所谓“创造性的传播活动”也并非是其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否则的话,传播作品的主体很多,为什么只有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和广播电视组织获得邻接权呢。主要是因为上述群体掌握有一般人难以拥有的传播手段和资源,尤其是广播电视组织;同时也是因为它们的投人之巨大也不是一般的传播者可以企及的,这种巨大的投入所带来的传播手段的变革,对于优秀作品的广泛传播意义重大。就这一点来看,版式设计的投入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微小的,没有足够理由将其与邻接权相提并论。当然,传播科技日新月异,邻接权又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版式设计权绝对不能作为邻接权的一种形式而存在,未免太过武断。只不过,版式的独创性与经济投入相对较小,出于不影响出版业良性竞争的考虑,著作权法对其的保護也不可能过高。更重要的是,上文已经提及,出版者对版式设计的权利,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保護。
既然出版者权的内容均不属于邻接权的范畴,那么究竟如何保護出版者的权益呢?
目前对于出版者权益的“邻接权”保護,主要集中在《著作权法》的第四章第一节,即“出版、表演、录音录像、播放”中的“图书、报刊的出版”。先且不论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完全可以不设置在第四章,依然可以设置在《著作权法》之内。就算完全没有这一节,出版者的权益也可以通过《著作权法》的其他规定以及《合同法》得到基本的保障。当然,能够在《著作权法》中对出版者的权益进行更为完备的表述,对于出版业的发展总是好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版权形象的完整性表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版式设计专有权”不适合在出版合同内进行保護。因为对于出版者来说,订立出版合同是为了约束著作权人,而“版式设计专有权”并非来自著作权人,合同约束不了。这也是不少人将“版式设计专有权”干脆视为邻接权的部分原因,因为如果不这样,似乎这一权利就无法保護了。
然而依据前述的理由,“版式设计专有权”可以成为独立的权利。如果说版式设计的功能仅限于对版面的美化和修饰,那么此种“劳动”与编辑的劳动有何区别?而图书编辑是既没有著作权,也没有邻接权的。因此,版式设计绝非美化与修饰那么简单,而是应当被视为一种视觉艺术。它不仅是“单纯的文字表现方式”,更是一种“夹杂了视觉要素的表现方式”。在美国的版权体系中,没有对于版式的特别规定。其第101条规定了“实用物品的设计,如果有可以同该物品的实用方面区别开来单独存在的绘画、刻印或雕塑特征,在这个范围内,该设计应视为绘画、刻印或雕塑作品”。具体到我国,笔者认为“版式”最接近《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四项之美术作品,或者第七项之示意图等图形作品(与装帧设计也具有相似之处),依据《著作权法》是可以获得保護的。更何况,“版式设计”还可以直接放在“出版者的权益”下,置于《著作权法》的其他章节予以特别保護。一种原本有可能获得直接保護的权利,如果置于间接权利下,岂不是舍近求远!
四、结语
作为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出版者自身的权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其权益的进一步研究,也有助于权益的保護。“出版者权”所涵盖的权利非常广泛,然而大部分内容都可以运用合约的方式予以恰当的保護。对于其中的特殊权益,比如“版式设计”、“装帧设计”等,则不应仅仅着眼于某种模糊的、不易界定的以及效益低微的权利,而是应该深入挖掘其在著作权意义上,以及在其他知识产权比如专利上的价值,以尽可能地扩大自身的权利基础。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