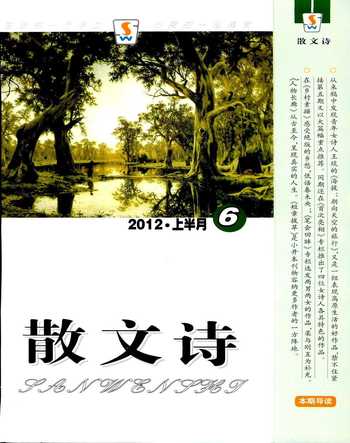杂色空间
云珍
我们始终没有顾得上搜寻南山
不是东篱。一朵菊花极不情愿地半开。
我用目光一瞥一瞥地削去,就看见金黄色的香气丝丝缕缕。天气有些昏沉,薄薄的烟霭罩着城市。匆匆的脚步在雾障里滑动,它们没有看见菊花。当然,菊花也没有必要为之盛开。
落叶驮着尘粒死蝴蝶样僵硬地飘,空气里多了一种腐败。
菊花似乎也在用光芒解剖我的身体。
我们始终没有顾得上搜寻南山。
南山在楼房之外……
谁于风景里伫望刹那间盛开的窑洞
若有所思,抑或怅然若失?
——这僧!
孤寂的灯苗忽明忽暗,敲窗的冷雨于夜半点点滴滴地拷问灵魂。一尾云影在远山架起的夕阳上蒸煮,出逃的木鱼已远离湿淋淋的梵音。
谁于风景里伫望刹那间盛开的窑洞?
大山是一副剔净了血肉的骨架
如果不是盯得太久,山羊不会有石头的硬度,石头也不会长出山羊的胡须。
高原三月,大山是一副剔净了血肉的骨架。山雀的啼鸣东一滴西一滴地滴着。盛开在骨头上的磷火,为干枯的眺望镀了一层水色。牧羊人随山雀的翅膀剪上剪下,大山始终缝不拢寂寞。
当石头不再长出胡须,变得柔软并且发出咩——咩——的哭喊,牧羊人操起牧鞭抽打,落日咯出的鲜血如四月的桃花。
牧羊人的梦鲜嫩水灵如发芽的小草,乡村的夜晚得以生津止渴……
有人在春天里行走
有人在春天里行走。黑瘦的身影楔人青青的远山。
阳光咔嚓嚓地铰着,看见或浑然不觉无关宏旨。吆着的牝马在半道上产驹儿,不能承受之重令弯弯的山道高高翘起。还有急于学飞的鸟鸣再不播发就要发霉了。
一只云朵走丢了,咩咩的风是带头顶架的那只。它须不停地停下,取出一直拱来拱去的种子,撒下新一茬光芒。
黑瘦的身影被零零碎碎地分割、播落……不管怎样都必须忘记
小小爆竹微弱的火焰,没入夜倒悬的湖蓝。
——逝者的往事如炸碎的纸屑,落入融雪般的记忆……
潮湿的南风走街窜巷。吹鼓手的唢呐朝向四个方向吹,丧事红火也好寡淡也罢,无非村人啧啧的妒羡或者指指戳戳,于逝者无关。送葬的队伍聚了又散了,新的一伙南风站在四月的脊梁上高呼:种谷……
鸟鸣串起被花香染过的露滴挂在小村的颈项上,土眉土眼的小村散发珠光宝气。
鸡叫九遍,风尘仆仆的太阳穿窗而入,有人挎着老犁,走向更深广的田野。
不管怎样都必须忘记。
匍匐的农事等待一一扶起。
那是自身的一种精彩
默然与敷衍一样惨败。
灼痛了的矜持吐出痉挛的烟圈无奈地寻找却无逃离的缝隙,不是不可以破门而去,是之后那些目光的剿杀无异于自重兵中突围。
有人在月色堆砌的山冈上啜露饮风并侧耳谛听,所有的星星都在唱歌,就像生命打开。孤傲的流星划了一条长长的弧线,溅起的水花是喜悦的一笑还是一声轻叹?
无论如何,那是自身的一种精彩。
我的想象战战兢兢
不能断定一株被伐倒的稗草与我的距离是不是等于我之于一颗灵魂的快乐、挣扎和战栗的抵达。
六月的阳光渗于地下。水勾兑了冷冷的月色。照亮稗草的起舞和玉立的叛逆。她的触须深潜、探寻,更多的力量与火焰指向愈加艳丽自己的花朵。
我的想象战战兢兢,躲藏于一柄锄头的追杀。阳光里吱啦啦冒烟的尸体,一个个乳白色的“?”写于湛蓝。有风急速地吹过……
没有人看见我被六月的风雪呛出的眼泪
我在绿浪里凫游,一个猛子扎入了白茫茫的冬天。
怎么看,都好像正在经历一场大雪,高低错落的土屋还没有被盖住,那是因为它们还紧抱着温暖。而这是六月呀,一个汉子在阳光咕嘟嘟冒泡、打旋儿的地方蹲下又站起,他是在一瓢一瓢地往桶里舀水。一只鹰邀来几朵灰黑的云,它们都在极力地伸展翅膀,扩大这块土地收获的理想。他担水走路的姿势很耐看,就像城里扭秧歌的女人!担子拽着大地起伏,像远山的呼吸。我听见咯吱吱的声响,却不能断定是发自他的骨节还是他咬紧牙关的一次次隐忍。他走在盐碱滩的边缘上停下,我看见有水自铁桶里倒出,那边就有了星星点点的绿意。一股潮湿的风吹过,吹起一些盐碱的碎沫,如雪,蓝色的天空很快就变成了麻脸,很恐怖,很迷乱。
我又开始扎猛子,值得安慰的是我撞着了一墩红柳,我抓住它,它很干枯,仿佛全身的水分都用在了自身那些粉红色的小花上。
黑蝴蝶终于一朵朵地飞来,太阳那只毒蜘蛛缓缓离去后星星开始发芽,我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没有人看见我被六月的风雪呛出的眼泪。
一只山羊站在溪边的青石上涮洗胡须
谁能一时辨清在一起飘移的,哪是石头哪是山羊哪是灰色的云絮?
那么柔韧、苍劲,仿佛峭岩缝里冒出的枝杈,高举着露滴、花蕾、蹄迹以及快乐或者忧伤。
这是浸泡在葡萄酒里的黄昏,滴沥的鸟鸣爽口,虫吟不再进溅吱啦啦的火星,咩咩的吼喊仿佛花蕾爆开,露滴滴碎,蹄迹拔节……
空空的山谷彩色的溪流涓涓。
一只山羊站在溪边的青石上涮洗胡须,山下的炊烟因之而生动、蜿蜒……
不知不觉我被它们绕去
我看见。薄薄的绿色草香和乳雾沿着山壁缓缓飘过。小草吸饱了母乳,不哭不闹。一个妇女半跪在一头牛的胯下,一下一下地捋着明亮亮的乳。当草香和乳雾擦过那匹马,擦过那粘贴于青青山壁的枣红色剪影,我疑惑那就是一团火正在冶炼石头。一只百灵鸟吱溜溜叫着掠过,火苗跳了一下又往前蹿了一下,接着,它急速地烧去,朝着草香和乳雾升起的方向。那个妇女已开始收拾奶桶,她的旁边站过来一位汉子,汉子扬了扬手中的马鞭。所有的,一时都成为了线条,纵纵横横地纠结,那鸟,那火焰,那山石,那汉子或女人以及草香和乳雾……
一对彩色的蝶翅围着我,上下左右地裁剪。不知不觉我被它们绕去,但我确实不能猜想有我参与编织或被编织的将是怎样的一个草原。千年后被返顾的我们是什么样的鱼群
破损的陶罐闪烁粗糙的光辉。
那时,她是吸饱了母乳或踡曲于羊水中的婴孩,紧抱清纯,同时被更大的清纯抱紧。可能始于泥土母性的暴动,雄性的火直抵子宫……
鱼卵撒开,一尾雌鱼高举浩浩之水,倾倒的光辉灼亮洞窟洇湿荒原,流作长江、黄河,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
敲去一块骨头的母亲,已褪色的骨头碴子,血脉点点,丝缕如水,哪一丝是盛唐的“贞观”,是凄迷的“甲午”?哪一缕是止息的西罗马。是依然洇染的文艺复兴?
心绪叮咚,目光耸作一角琉璃的补丁,盛满清纯。千年后被返顾的我们是什么样的鱼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