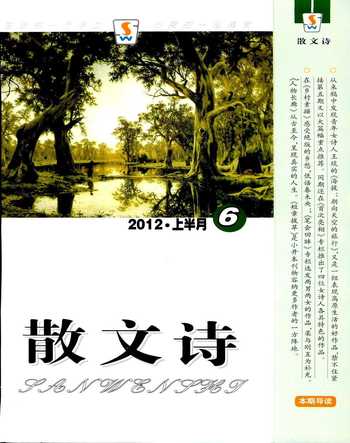春未央
姜桦
傍晚
四月之夜草木新鲜。
露水微凉,通往滩涂的小路上,风轻轻吹动。吹着路边那密密匝匝的野蔷薇。一朵朵红色、粉色的花朵摇摇欲坠。那软泥一般的花朵,真担心它们会倾倒流泻下来。
还有那一棵棵的树。路边的树,除了杨树槐树,那些水杉和银杏树,开始时觉得它们连一片叶子都没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就像孑然独立的我。然而,仅仅只是片刻,像是有无数人一起安上去的,无数的叶子在瞬间布满了枝头。
鸟群栖落,星辰带动我的目光。越来越近的夜晚,我在等谁?
归鸟、星辰和风,此刻,你又躲藏在哪一朵花的背后?
川田暮晚
流水丰沛的季节,黄河边那大片的绿树是流水硬贴上去的。
夕阳。麦地。高高的杨树林。没有谁能够说准那湍急流水的深度,更没有人能够说准那一刻的风向。
波浪和树叶漂流在河水里,钓者的钓竿笔直地伸向水面。浮标颤抖。那小小的铅坠穿过湍急的水流,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下去。只是,恐怕连它自己都不知道,最后,它是否沉到了河流的底部,沉到了流水的内心?
但是,那个钓者在内心里说准了。还有那顺着水流生长的庄稼。草木熏香,那停留在川田上的玉米、花生、大豆、山芋,它们知道,一定是河坡上的那些草汁染绿了奔腾不息的流水。染绿了天边的夕阳和残照。
童年。少年。几十年,我的衣胞埋藏在你故乡的土地。告诉我,到底是谁,赐给这土地那样的一份安静?
而我,是否也仅仅就是为了做一回留在你画幅上的那个钓者?
海边花田
芦苇的侧翼是连绵的缓坡。爬上海堤,我才知道,海边的野菊花原来是这样盛开的。
滩涂生长着无边的芦苇。十月末,秋风乍起,芦花初放,无数的野鸟从滩涂上飞起来,那芦苇花的涌浪一波一波,直接就要掀到海里去。但是,它们突然又会急急地停下来——它们是遭遇到了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野菊花。
恣意,放纵,挥霍,金黄素白的野菊花,海堤之下的任何一处,只要你能够想到的地方,没有一处没有它们的身影。它们开得那么充分,想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许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海边的芦苇花开得有些放不开。开始,我还一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可是今天,当我走上海堤,将车窗摇下、打开,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视角,我发现,正是那沿着海堤盛开的野菊花,它们的恣意、野性,无拘无束,使得大地上的花朵失去了开放的勇气和力气。而那海边的芦花,大概也因此呈现出了这样的一种姿态。
深秋的沿海滩涂,你是否见到过那遍地开放的野菊花?大片大片雪原起伏的烂漫野花,那一种气息,惟有那叫做“芬芳”的词方能够形容。
夜阑珊
今夜,月亮挂在天上。
一轮月亮。一轮橘黄颜色的月亮,硕然,庞大,却有那么一些冷。
湖边如此安静。甚至能够听见游鱼喝水花朵交媾的声音。湖滨小路,蜿蜒,平坦,如一片波浪在起伏。路边上低矮的灯,它们的光洒在草地上。在这四月春深的季节,那些草不明亮反而格外黯淡下来。
春夜湖畔的灯光,我知道它们一定是忍着的,就像我此刻的心绪,如果不是有一双手按捺着,它一定会流到脚下的湖水里去。脚步轻轻,生怕踩痛心弦,牵着风一如牵着你,今夜,风无声,而我们彼此的心里有千年的波涛在回旋、起伏。
神啊!我,就这样遇见了你!
春夜阑珊。阑珊,还有我的心。你是真实的
恍惚。抑或。世界仅仅就是人们常说的“可能”与“不可能”?
但你是真实的。这个早晨,黄昏,沉重的夜,都是真实的。从现实的世界到独我一人的梦乡,那满枝的梨花桃花杏花苹果花,你馥郁的香气,真实地存在于我无边的梦境和遐想里。
在春天的第一场梦里,我来到大海的身边。小小芦苇和大叶米草,春天里新生的青青草木。黄昏后,月亮底下,按住那星辰闪亮的门铃,夜晚的风和光里,我知道你对着哪一扇窗口。
我就坐在你的身边,你的窗前。
一颗心,一颗留在海边的卵石。
夜晚宿命的灯盏和光芒,我是否已经忘记曾经经历的沧海桑田?
不可分
世间万物,是否只有远离了才算是永恒?我只知道,那靠在一起的波浪,如此密不可分。
春神
以速写山水的笔墨,我写下:春神!
啊春天,多么好!一条小溪从滩涂上流过,岸边,那些鹅黄淡紫的花,神在唱着欢快的歌。
过去的日子,我听过多少这样的歌啊,为什么只有这一次,觉得似有水珠抖落在心里?
像一朵花引领着风的方向,这冬天里走来的春神,她一直在我的心里挪动着她的小胳膊小腿儿,玩耍,嬉闹。已经是后半夜却依旧睡意全无。我真的不知“今夕何夕”了吗?
春天春天,这么好的田野;春天春天,这么好的流水;春天春天,这么好的绿树和花!
今天,我必须也只能这样,从改变对你的称呼开始,开始我的生活。
油菜花。蚕豆花。大片的水杉林栗树林银杏林。还有芦苇丛生几近搁浅的河流。白天的景物恍若油画。春天!阔大的穿衣镜里,你明亮健康的身影让我留恋。
一个灵魂被另一个灵魂所引领,一千遍一万遍地如此急切地唤着你的小名,我知道,你早已走在了我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