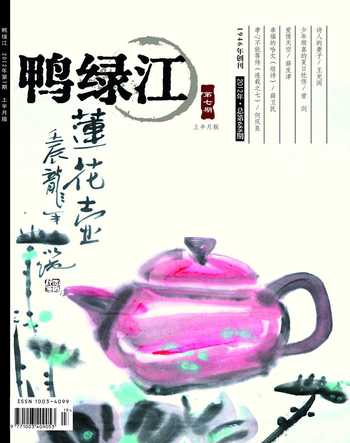少年顺喜的夏日忧伤
曾剑,湖北红安人,1972年10月出生,1990年入伍。先后在《青春》《长城》《山花》《作品》《十月》《鸭绿江》《解放军文艺》《青年文学》《西北军事文学》《西南军事文学》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多篇小说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曾获军旅优秀作品短篇小说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短篇小说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二等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作品》全国军旅短篇小说征文奖、《鸭绿江》文学奖等多种军内外文学奖项。曾就读于辽宁文学院新锐作家班、解放军艺术学院青年作家班、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
顺喜骂碗老不死的,因为它是祖上传下来的。据说是爷爷的爷爷,在衙门里当厨子时,给爷爷的奶奶偷送东西吃,才流落到民间的。碗不大,顺喜会使唤筷子那天,就用它盛饭。碗很厚,白滑滑的瓷壁上,一朵凸起的蓝花鲜亮地盛开着。那白瓷碗就成了一片洁白的天空,那朵美丽的花,就是一副蓝色的降落伞。顺喜好几次在梦里乘着这个降落伞,飘到衙门里,吃爷爷的爷爷给他做的衙门饭。
如今,一切都变了。倘是以前,父亲母亲吵闹,爸凶,娘就会歇下来;娘的声音高上去,爸就会变成哑巴。爸最怕娘哭,娘一哭,他就会停下吼叫,或者干脆走到后山林子里,等娘的气消下去,他再回来。但现在,娘的泪仿佛变成了一滴滴油,只会把爸的火气浇得更旺。当娘的眼泪像阴雨天屋檐下的雨滴,一滴快似一滴时,爸抓起桌上的一个盘子,狠狠地砸在那被眼泪浸湿的地上。顺喜看见一地的白光,向四壁飞溅。
娘不示弱,一甩手,香案上的橱柜里,便噼哩叭啦,像过年时的鞭炮,响成一片。瓶瓶罐罐东倒西歪,晶黄的菜子油流出来,橱柜里便像是爬出了一条黄亮亮的蛇。顺喜看着,感到肚子里有一股灼人的气体,也似蛇一般蜿蜓而行,顺着胸腔上窜。
碎响声消失了。橱柜上残存的玻璃冰山一样挺立着,顺喜觉得那山尖尖就戳在他的心窝上,一阵隐痛,由内到外浸漫开来。
“别吵了!”顺喜终于无法忍受。他学着他们的样子,抓起桌上的白瓷蓝花碗,狠狠地往墙上砸去。但他没听见脆响。那碗在土墙上,成了沉闷的哑炮,最后扣在地上,夯实的一声,硬是没碎。
顺喜冲碗底跺一脚,骂一声:“老不死的,你不碎我也不用你。”
顺喜对碗的咒骂,并没引起父母的注意。爸依然叉着腰,娘的头发都散开了。两人喘着粗气。顺喜受了冷落,他们竟这样无视他的存在。顺喜弯腰,捡起蓝花碗,冲父母喊:“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这个碗吃饭了!”然后,他夺门而出。
门前是口大水塘,水清洌清洌的。塘坝上,合抱垂柳,将它的枝叶秀发般垂下来。知了的叫声,从枝叶间钻出。现在,知了的叫声早停息了。它们知道,它们唱不过顺喜的娘。顺喜的娘年轻时,曾在乡演出队唱过楚剧。尽管那时楚剧已在衰落,被乡下人称为丑剧,但顺喜娘唱得认真、动情,高兴时,露出一嘴白玉似的牙;悲伤处,泪在她胭脂脸上溪水般流淌。据说很多人并不是为了看楚剧,而是看顺喜娘到场的。看她笑,看她哭。
顺喜将碗扔进水塘,这下总算听到了清脆的声响。水花溅起,又雨点般落下去。蓝花碗在水里晃晃悠悠,像一只被撞毁的船,慢慢地沉入水底。蓝花碗彻底消失的那一刻,顺喜感到眼前一空,心中的那条热辣辣的蛇就窜到了头顶。
找春花去!顺喜对自己说。不是她,父母就不会这么厉害地吵。找到她,狠狠扇她几个耳光,让她的两个嘴皮子变成发面饼,看她的嘴还欠不欠。
顺喜爸是小学的民办教师。那天,他们观音寨小学开完总结大会,就宣布放暑假。顺喜蹦跳着上了爸的办公室,他想让爸骑自行车驮他,但他的愿望落了空。爸对他说:“天还早,你先回去吧,我这儿还有点事。”爸的语气很轻,声音却是颤抖的,好像有些激动。顺喜盯着爸的眼看,想猜测爸的心事。爸的目光躲闪开来。顺喜想,还挺神秘呢,就知趣地抄小道回了家。
顺喜回家时,瓦屋顶上的烟柱子在夕阳里清晰可见。顺喜喜欢黄昏的烟柱子,烟柱子一升起,他就知道娘在给他和爸准备夜饭,心里就暖烘烘的。
天还很亮。顺喜懂事地走进屋,把菜篮子拎出来,帮娘摘菜,洗菜。然后,他就坐在灶堂前,往里添柴火。火焰像条又大又软的红舌头,舔着锅底,也舔着他进进出出的手。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像锅上的水汽,热腾腾地将他包裹。
然而,这种幸福,被春花的一句话击得粉碎。春花冲进来,对顺喜说:“顺喜哥,我看见你爸和小杨老师在一起,他们坐在紫竹林的桃花塔下。”
小杨老师是城里师范学院的学生,就要毕业了,毕业前的半年实习,她申请到顺喜他们观音寨小学来支教。
顺喜猛吸一口凉气。他看见娘的嘴半张着,脸刷地一下苍白了。锅铲在锅的上方,硬是没往下落。娘像只木偶似的定在了那里。
顺喜冲春花喊:“你瞎说个鬼!”
春花说:“真的,我想和你一起回来,就上你爸的办公室找你,没找着,也没看见你爸。看大门的王伯说,你爸去了紫竹林。我想,你肯定跟你爸在一起,就到紫竹林找,看见你爸和小杨老师坐在桃花塔下,就是没有你。”
屋子一下子静了。许久,顺喜听娘说了一声:“紫竹林,桃花塔,多美,他们莫不是正在那里演一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顺喜和春花不懂《梁山伯与祝英台》,更不知道桃花塔的故事,不知道那是桃花乡版的《梁祝》。许多年前,一个富人家的女儿桃花,爱上了一个穷书生紫竹。两人花前月下,私定终生。可桃花的爹嫌贫爱富,把女儿另许他人,并将紫竹痛打一顿。紫竹内火攻心,又得了伤寒,不久死去了。桃花闻讯,拿了根布带,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桃树上。悔恨莫及的桃花爹,在桃树旁修了一座坟,将两人合埋一处。又在坟上修了塔,名为桃花塔。塔全部用石头建成,塔门上雕着门神,塔有九层,每层九个小石门,雕着九九八十一个妖魔鬼怪,守护着紫竹和桃花,不让人打扰他们的美满生活。那年的桃花开得格外艳。桃树旁,钻出一株紫竹。后来,紫竹成林……
顺喜和春花,不懂大人们讲的爱情故事,只知道塔下埋着一男一女两个死人。顺喜胆小,人多的时候,才敢到紫竹林里去看桃花塔。春花也不知怎的,竟敢上竹林里去寻他。
屋子里短暂的寂静之后,顺喜听见锅铲声再次响起,而且一下高过一下。最后,他听见嘎的一声,锅下的那条大红舌头就分裂成无数条,向四周炸开。伴着滋滋的响声,灶堂里的烟一团团往外涌,一股焦蚀的异味充塞鼻孔。娘把锅炒漏了,汤水流出来。顺喜被包裹在浓烟和灶尘之中,他急忙往外撤火。
娘把锅铲往锅里一扔,锅铲直接掉到灶堂里。顺喜愣在那里,呆望眼前的一切。娘抓起他的手。他被娘死死地拽着,上了宽宽的土道。
娘的那条大麻花辫子散开了,在奔走的风中,马鬃一样飘动。顺喜惊讶娘哪来这么大的力气,跑起来像一匹马。顺喜感到自己成了一只风筝,胳膊被娘紧一下松一下地拽着,最后几乎飞了起来。
但春花的话并没得到证实。在快到学校的那个涵洞口,顺喜看见了爸。他并没骑车,而是很悠闲地散着步。爸的脸在夕阳最后一道霞光里,掠过一道潮红。他似乎在沉思,或是在回忆某种愉快的往事,以至顺喜和娘走到他身边,他竟然没看见。或许看见了,却把他们当成了普通的过路人。
娘继续往前跑。顺喜以为娘没看见爸,翘起脖子刚想喊,娘使劲拽了一下他的手,爸的身影便在他眼前一闪而过。
娘拽着顺喜,到了学校,也没停下来。过了学校,往东是紫竹林。紫竹林里照不进夕阳,阴沉幽暗。顺喜只觉头皮发紧,又不敢挣脱开娘的手。他跟着娘,踏上长满青苔的石板路。顺喜不明白,爸走了,娘为什么还要把他带到这儿来,又要把他带到哪儿去,直到他们在林子中央的桃花塔下,看见了小杨老师的背影。小杨老师穿着红色的薄纱衣,草绿色军裤,站在塔下,迎着晚风,像一朵荷叶上怒放的莲花,也像一团正燃烧着的火焰,在风里雾里摇摆着。
听见脚步声,小杨老师慢慢地转过细长的脖子,当她看清是顺喜和顺喜娘时,脸上陡地飞来两朵云霞。顺喜看见她那两朵云霞里,有着鲜桃一样细密的白绒毛。
“小杨老师,天晚了,你咋还在这里坐着?你不怕吗?这塔里可埋着死人。”顺喜娘说。小杨老师脸上的红云倏地不见了,脸苍白如纸。
“小杨老师,你可能还没听说这塔里的两个人是怎么死的吧?”顺喜娘说。娘一口一个“死”字,顺喜的脊背直冒冷汗。
小杨老师说:“听说了,刚才陈老师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很感人。”小杨老师的声音颤抖着,也不知是害怕塔里的人,还是害怕顺喜娘。
“这么晚还不回学校。不怕死人,活人也不怕吗?这紫竹林里说不定有坏人哩,你长得又像一朵花。”
顺喜看见小杨老师的头低了下去。她双手掩面,顺着石板路,向着学校小跑。那团跳跃着的火焰,便在顺喜眼前消失了。
顺喜和娘回到家时,爸不见了。邻居说,陈老师留了话,说是上学生家走访去了,得很晚才回来,让顺喜和他娘别等他。
“都放暑假了,走访个屁!”娘说了句粗话,把气撒向了邻居。顺喜清楚,爸是在逃避一场战争。
但战争还是在午夜爆发了。其时,顺喜正在做一个梦。他在梦中惊醒时,耳旁响起从上屋传来的争吵声。
爸说:“小杨老师明天就要回城里过暑假了,有些事交代一下。”
娘说:“什么事要跑到桃花塔下去交待。”
爸说:“孤男寡女,在办公室里,你还不是要说?”
娘说:“怕我说,还不是有鬼?人家小杨老师可是说你给他讲桃花塔的故事了。”
爸无语。
“那下面压着的,可是一对殉情的恋人,自从那个小妖精来了,你下午上完课,总是磨磨蹭蹭,不爱回这个家。你们跑到死人塔前,莫非也要演一段风流韵事!”娘的声音大起来。
“莫名其妙!”顺喜爸说。
“岂有此理!”顺喜爸又说。
“母狗不掉腚,公狗不跳背!”是娘的声音。
顺喜没听太清,似乎也听不懂,他坐起来。只听爸和娘的屋里,传来重物落在地上的声音,爸说:“人家是来实习的,还是个学生,你莫要太过分!”爸的话音一落,顺喜的房门吱呀一声开了,顺喜看见一片人体状的白云飘了进来。顺喜吓得直喊“爸”,那白云竟应了一声:“喊什么喊?”顺喜这才发现,飘进来的是爸,他竟然一丝不挂。爸的裸体散发着朦胧的光。顺喜像中秋之夜赏月那样盯着爸。爸训斥道:“小崽子,闭上眼睡觉。”爸说着,扯了一条床单,裹在身上,把顺喜往里一推,自己就躺下了。
顺喜闭上眼,但爸的裸体并未在他眼前消失。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毫无遮拦地看爸,但在窗外射进来的月光里,顺喜非但没看清爸,反到平添了些许神秘。
顺喜娘把赤裸的爸赶到顺喜房里的第二天清晨,一湾人集聚在顺喜家门口的那棵大槐树下。那儿有一口铁锅,锅是没底的。瘸腿的麻球一瘸一拐,来到树下,说:“这锅不是炒漏的,这是砸的。”他的话得到顺喜隔壁家那个女人目光的肯定,瘸腿的麻球面露得意之色,一瘸一拐,扭着他那半月形的屁股,走了。
那天,太阳落山时,村里响起了一首儿歌:金枝嫂啊满堂哥呀,白天吵架夜里摸啊,摸错地方就砸锅啊……
顺喜娘听了,脸色煞白。麻球眼看就七十岁的人了,一辈子没娶女人,就指望着编这些酸溜溜的歌过嘴瘾,勉强活着。总不能不让他活吧。
顺喜娘拿麻球没办法,就把气撒在手中的物件上。她扫地会扬起一屋灰尘,喂猪会用搅食棒把猪打得嗷嗷直叫,喂鸡把鸡撵得像鸟一样飞上天。爸有时也会突然扔出去一件东西,比如娘捣衣的棒捶,娘的搓衣板,以示对娘的抗议和警告。
都是春花惹的祸!顺喜认为还是应该去找春花,狠狠地揍她一顿。春花有时像个男孩子,顺喜文弱,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打得过她。顺喜想,实在打不过,就抓她的辫子。他是男孩,没辫子给她抓,这样,他就能打赢她。
春花一家三口人,在一块水田里,干着不同的活。春花爹骑在秧马上扯秧苗,浣秧泥,用干稻草把秧苗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的。他嘴里叼支烟,烟头在阳光下一闪一闪。春花穿着红色短袖布衫,腿浸在泥里,身子显得更娇小。她把爹扯的秧苗摞在一只秧马上,肩着秧马前的绳子,像动画片里的纤夫。她把秧苗卸在田头另一端娘的身后。春花娘捡起秧把,拆开,左手握秧苗,拇指食指将秧苗分出一小绺来,右手掐住这一绺秧苗的根,往稀泥里插。春花的娘插得真快,只见她胳膊动,却看不见她的手。她的手像是长在了泥里,面前一会儿就有了一片片的绿,让人怀疑她是吹了一口仙气,那些秧苗就自己立在那稀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