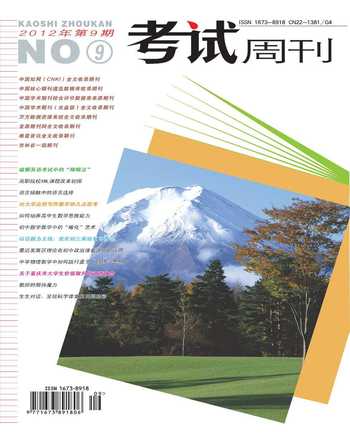《还乡》的神话原型解读
汪明珠
摘要: 哈代在小说《还乡》中大量运用了神话原型,暗示人物的命运发展。本文通过神话原型视角,对《还乡》进行重新解读,重新揭示和发现哈代作品中的深层次意义,使这部经典文学作品焕发出熠熠的时代光芒。
关键词: 小说《还乡》神话原型深层意义
1.引言
《还乡》是哈代第一部重要的悲剧小说,也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性格与环境小说”。小说以哈代的故乡多塞特郡和附近的农村地区为背景,描绘了英国西南部的风土人情,再现了现代文明对宗法制传统的侵蚀,以及现代人与亘古不变的荒原之间的激烈碰撞,表现了女性试图超越内在性的自我,追寻主体性,追求自我实现,以及她们遇到的种种障碍,反映出哈代作为小说家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超越时代的预见性。小说大量引用神话原型描写环境,暗示人物的命运发展,描述了维多利亚时期有着传奇色彩、如救世英雄般的男主人公克林和女神之称的女主人公游苔莎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他们在爱格敦荒原上的命运归属。
神话是人类文学的初始形态,神话批评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广泛的关注,尽管用神话原型作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未免失之偏颇,然而这个理论的确为文学批评注入了活力。研究表明,有相当一部分文学家将作品植根于神话与民间传说的沃土之中,旨在以神话的思维方式,解决现代社会中人们面临的问题。
精神分析学家荣格认为,人的心理分为有意识与无意识两部分,无意识又体现为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中充满着全人类共有的原始形象与主题,如神的死亡与再生,代表着正义的天神与代表着邪恶的魔鬼之间的争斗,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等等。这些内容超越了具体的时空界限,深深地沉积在个人的无意识中。荣格强调的是属于同一种族、同一集体的经验与意象,它超出个体的经验范畴,潜藏于人类意识的深处,形成了所属成员心灵的共鸣区,使他们追求共同的理想,遵循一致的行为准则。
本文试图通过神话原型视角,对《还乡》进行重新解读,重新揭示和发现哈代作品中的深层次意义,使这部经典文学作品焕发出熠熠的时代光芒。
2.荒原的原型
小说中,哈代巧妙地运用了象征和神话与原型意象,使得爱敦荒原不只是作为静止的景物出现,而是与特有的风土人情相连,成为悲剧故事的有机参与者。小说第一章描写了爱敦荒原,它有着漫长的历史和伟大奇特的壮观景象。哈代在小说中赋予荒原生命形态,在他笔下,爱敦荒原是一个有生命的庞然大物,暴雨是它的情人,狂风是它的朋友,它是残酷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力的化身。多少世纪过去了,人类历经沧桑,而荒原却无动于衷,依然神秘、强大。荒原以抑郁寡欢的面容,等待最末一次的危机,等待天翻地覆的末日,暗示着即将发生的悲剧故事。小说中的荒原是古希腊神话中巨人泰坦的形象:“它那泰坦一般的形体,每天夜里,老仿佛在那儿等候什么东西似的。不过它那样一动不动地等待,过了那么些世纪了,经历了那么些事物的危机了,而它仍旧在那儿等候,所以我们只能设想,它是在那儿等候最末一次的危机,等候天翻地覆的末日”。①P3荒原还“是一片长满杜鹃、荆棘、石楠的野地,灌木丛生,苔藓遍地”。在古希腊神话中,浓密的植物世界往往表现为一片不祥之林或一座邪气横生的园林;在《圣经》里,则有死亡之树、禁果之树、被诅咒的无花果树等不祥意象。在《还乡》中,这种茂密的、丛生的植物意象,正是象征着邪恶、凶险或宿命。哈代通过大自然中植物世界显现的不祥预兆,隐喻地表达了他的关于自然法则不可抗拒的观点:凡是企图反抗与背叛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的人,都终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小说不仅全部情节的展开限定在爱敦荒原,而且人们性格和意识的形成,以及他们的命运等都受到荒原的制约。荒原塑造着荒原人的性情,不仅那些原本居住在荒原上的人们,而且恨它入骨的游苔莎,其“女神”属性也是由荒原形成的。喜欢热闹、繁华的都市文明的游苔莎在被动地来到原始、封闭、荒凉、孤寂的爱敦荒原后,其性格与却爱敦荒原格格不入,便不择手段、不顾道德地追求巴黎那种大都市奢华的享乐生活,强烈渴望能够挣脱爱敦荒原,最后却造成了自我的毁灭。
3.人物的原型
3.1游苔莎的神话原型
哈代笔下的游苔莎美艳绝伦,她的家庭出身,她早年在资本主义化的城市——蓓口的放任生活,使她带上了资本主义城市文明的深刻烙印:独立不羁,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道德和基督教文明,想过“文明”的浪漫生活,与尚处宗法制的荒原格格不入。她被姚伯太太误解为“贪图享乐的懒惰女人”,被村妇苏珊、南色当做女巫当众侮辱。她的美貌、知识、热情在荒原得不到认同、赏识,性格日趋孤僻、偏激。她对乡民一概否定,鄙视乡村生活的守旧和简陋,对人们的劳动生活、风俗习惯、艺术等抱有偏见,看不到他们淳朴、善良的天性。她热情好动,急于追求美丽的有趣味的生活,她的情感要求比荒原上的任何人都要精致、强烈得多。她像一只笼中鸟被困在她所厌恶的荒原,她是荒原上一个骚动不安的孤独者,是激情的化身,是七情六欲特别强烈的异教女神。小说中,在面貌上,哈代直接地把她比做古希腊神话中女神:“她头后面要是有一钩新月,那她就可以说是阿耳忒弥斯;她头上要是戴着一顶旧盔,那她就可以说是雅典娜;她额上要是勒着一束巧合的露珠做成的后冕,那她就可以说是赫拉。”①P107游苔莎是一个美丽、聪颖、活泼、浪漫的女性,随祖父到爱敦荒原之后,她的浪漫追求被荒原钳制,她成了荒原的囚徒,整日整夜不安地四处游荡,渴望爱情和自由,这与阿耳忒弥斯的形象相符。她落落寡合,不愿与当地的居民往来,却耽于浪漫主义的幻想。对于荒原人的习俗,她也是不屑一顾,平日别人都劳作时,她独自休息,而到休息日那天,她却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干家务活。而且她厌恶正统的宗教,憎恨礼拜天,好容易去了一次教堂,却被苏珊·南色刺伤了胳臂,从此她就再没去过了,也不觉得有任何愧疚。她所崇拜的英雄是“胜利王威廉”“司揣夫得”和“拿破仑”。可见,她所欣赏的人,都个性强硬、暴戾严厉,这与雅典娜渴望喧嚣和战争厮杀的特性如出一辙。游苔沙见风使舵,善于变换情绪来迷惑和吸引她所需要的男人,而最终她落水而亡的结局,彻底粉碎了她高贵的女神形象,还原了她可悲可怜的本质。
3.2克林的神话原型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克林生于荒原,离开荒原,又回到荒原。他有着荒原的根,是带着外面的文明来改造荒原的人,是荒原淳朴的民风奠定了他的价值观。成功后的克林没有留恋都市的繁华,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广漠的荒原才是心灵的归宿。他身上浸润着荒原的气质,“还乡”是他心灵深处一直追寻的梦。“他希望以牺牲个人为代价来提高整个阶层,而不是以牺牲整个阶层为代价来提高个人。而且,他随时准备立即把自己作为第一个牺牲的单位”。①P261克林热爱荒原,热爱他的同胞,他不能忍受看见整个人类“在痛苦中呻吟劳作”而自己却逍遥自在的生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上一半的人因为没有谁去认真着手教育他们怎样勇敢面对那与生俱来的苦难而走向毁灭”。①P261克林身上这种这种牺牲自我、克己利人的基督教精神与救世主耶稣克己隐忍,拒绝任何的诱惑,将自己与民族的幸福融为一体,心甘情愿地为了世人的赎罪和国土的富庶牺牲自己是不谋而合的。然而他却没有实干家的精神。他拘泥于书本的研读,无视现实,耽于幻想,看不到文化精神层次上的隔膜使他的教育计划很难得到乡民的认同,忽略从务农生活变到求智生活中间要经过的过渡阶段,不听母亲、妻子的劝告,最终只好放弃教育计划,放弃情感追求,通过传教进行宗教逃避。
4.结语
本文分析了小说中的荒野及人物的神话原型,引导读者从多个角度看待该小说,加深、拓广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把人物的不幸与远古的神话原型结合起来,古老的神话传说不仅为小说提供了宏阔的历史背景,而且暗示了主人公无可逃避的悲剧性命运。哈代作品中的神话原型的使用使神话借小说从远古走进现代,获得了新生;而小说则借神话从现代走向过去,小说就在这双方的互补互渗中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
注:①本文标注页码的引文均自译于网络版电子书《还乡》
参考文献:
[1]Thomas Hardy.The Return of the Native[M].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1995.
[2]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M].三联书店,1986.
[4]弗莱.批评的解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