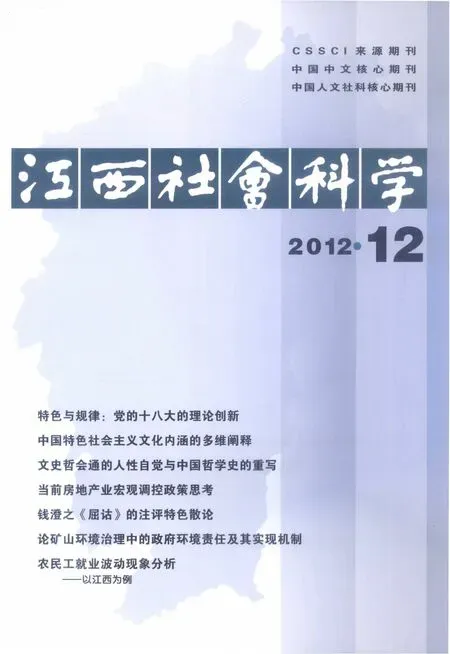试论明清鄱阳湖区域民间信仰的道教化
■程宇昌 温乐平
自20世纪90年代,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可以说是风生水起,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论著宏富。民间信仰是指民间存在的对某种精神体、某种宗教等的信奉和尊重。它包括原始宗教在民间的传承、人为宗教在民间的渗透、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1](P11)朱海滨认为,民间信仰一词,主要是为了区别于教团宗教而提出来的。与教团宗教相比,民间信仰除了没有教义、教团组织等特征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民间信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是地方社会共同体的信仰。[2](P140)恰是其地域特征,民间信仰才与当地宗教如道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趋向道教化,即民间信仰由粗陋、随意、简单的信仰形式转化为具有道教基本特征的信仰形式,表现为有相对固定的信仰领地与信徒、规范的教义、周期性的仪式、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巫术、禁忌等。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神灵众广,在湖区众多的神灵中,有的被纳入道家神灵体系,建有宫观供祭拜,这些湖区民间地方神灵与道教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笔者在考察明清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的同时,发现学界对鄱阳湖区域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较少,回顾该研究学术史,①可说少之又少,在某种程度上,笔者之研究尚具一定的拓展性,其意义不言而喻,为此,本文尝试探析明清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的道教化问题,以期方家赐教。
一、明清鄱阳湖区域民间信仰体系
鄱阳湖位于长江之南,江西省北部,与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等五大河流(以下简称“五河”)尾闾相接,形成似盆状天然凹地,受长江、河(五河)水位制约及水量吞吐平衡而形成的连河湖。这个湖在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因水域扩展到鄱阳县境内,隋朝人命名为“鄱湖”,沿袭迄今。[3](P14)如今鄱阳湖的水域、湖滩等地,分隶属沿湖11县市,分别为南昌市、新建县、进贤县、余干县、鄱阳县、都昌县、湖口县、星子县、德安县、永修县及九江市的行政疆域,亦泛指人们常说的鄱阳湖区域。根据地方文献的记载,笔者对明清鄱阳湖地区主要信奉的神灵进行了初步分类,具体为:
(一)忠臣信仰
在明清鄱阳湖地区,忠臣崇拜盛行,现存忠臣庙也不少见,如余干县有1所,鄱阳县有1所,南昌县有2所,九江县有1所。②在鄱阳湖康郎山忠臣庙专祀明鄱阳湖大战中忠心护主战死的韩成、丁普郎等三十六忠臣,该庙建于元末明初,所祀三十六忠臣为明太祖亲自下诏而设,历经六百余年,忠臣庙几经修葺和重建,迄今仍屹立于鄱阳湖康郎山上,可见,忠臣崇拜在鄱阳湖地区经年不衰,源久流长,深入民间。
(二)许真君信仰
许真君信仰在江西非常盛行,万寿宫的建造自江西而遍布全国,许真君信仰也分布全国各地。笔者在查阅明清江西九县方志的过程中,发现各县均有许真君崇拜,如余干县许真君庙有8所,鄱阳县有1所,德兴县有1所,湖口县有2所,彭泽有1所,南昌县有1所,德安县有1所,安义县有3所,星子县有1所。③显见,对许真君崇拜遍布江西各地;除许真君信仰,民间对道教尊神关圣帝的崇拜,非常普遍,特别是明清时期,关圣帝经过皇家敕封三公,对关圣帝的信仰已达顶峰。
(三)城隍信仰
城隍信仰在明清时期,经过皇家敕封,纳入祀典。明清鄱阳湖地区,城隍信仰非常普遍,只要府治所在其必有城隍。笔者翻阅各县志中,明清鄱阳湖地区府县治所均有城隍庙,且各为一。城隍之神,其原仅为城镇守护之神,官府必祭,后经变迁,具有监察人事之能,在生老病死及各种灾难降临时,可御灾捍患,百姓深信。
(四)水神信仰
明清鄱阳湖水神崇拜中,最具代表为元将军信仰,指鄱阳湖大战时,太祖朱元璋在危急时刻,被一老叟驾舟所救,太祖回望时见是一“鼋”,为感恩“神鼋”,太祖敕封其为元将军。后随时日演变,元将军慢慢演变成水神。至清代,后又加封“显应”,故有“显应元将军”称号。显应元将军又称为定江王,意在风浪之天可镇江、定江之能。元将军崇拜在湖区比较普遍,都昌县有庙2所,星子县有3所,南昌县有1所,余干县有1所。④
(五)社稷与自然神灵信仰等
笔者在查阅地方文献时,统计了明清鄱阳湖地区有代表性的11县(府)的有关资料,11府县均有社稷坛、风雨雷电山川坛及先农坛,且均仅为一,由此可见,对社稷、山川雷雨风云等祭祀均是国家祭祀,老百姓不能随便祭祀,故在祭祀坛建设方面仅为一所并在各府治所。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呈多元化,一是以人物为原型的神灵崇拜;二是以动物为原型的人格化神灵崇拜;三是以自然为原型的自然神灵崇拜。湖区民间神灵信仰体系的形成,与湖上行走的商旅船夫亦有莫大的关系,这些在鄱阳湖上往来的商旅船夫,来自四面八方,个性及信仰互为不同,因湖面上风浪很大,多往往祷告神灵及祈求神灵的庇护,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信仰在湖区的传播与扩散。对于生活在湖区的百姓而言,他们多信仰水神,希望水神能护佑他们,旱时多雨,洪时无灾。对湖区各县地方官员们言,他们多信仰国家祀典在记的诸神,希望诸神护佑他们官运亨通,所辖地区无灾无患。对膝下无子的宗族乡绅及百姓言,他们多为信仰观音菩萨,特别是送子观音,期望子孙绵延,后代兴旺。对将军战士言,他们多信仰忠臣或战神之神灵,希望战神护佑,建赫赫战功。由此可见,民间信仰具功能性和世俗化的特点,千姿百态,具多样性特点;显见,明清鄱阳湖区民间信仰呈多元化色彩是必然的。
二、明清鄱阳湖区域民间神灵信仰的道教化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正式创立始于东汉末年,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为标志。[4](P39)随着道教自身的发展及其得到朝廷的支持,唐宋时期臻于兴盛,形成了许多派别,至元代时汇合成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流派,明清时期道教慢慢开始衰落。道教的神灵系统,原本根植于民间信仰,它是与民间信仰最接近的宗教;[5](P50)美国学者Kenneth Dean认为民间信仰是道教走向民间并与之融合的产物;[6](P65)范正义认为民间神信仰与道教是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发展。[7](P39)著名学者卿希泰、唐大潮认为道教把民间俗神集中到自己的信仰中来,使其成为道教神仙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道教又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这些经过道教化的神灵返回到民间,更深更广地影响到民间的神灵祭祀活动。[4](P428)总之,民间信仰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道教神仙谱中的灶神、水神、关羽神、城隍神等无不是民间俗神,这些民间神灵信仰是底层民众精神渴求的体现,这些神灵在他们信仰世界里,无教义和教规束缚,体现出民众信仰的道德性与社会性。
对于余干县的忠臣信仰,是明太祖建国后抚今追昔,对在鄱阳湖的康郎山大战难以释怀,故建立忠臣庙以示纪念。据《明史》所载:“洪武元年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各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着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8](P1306)在访求的对象中,三十六忠臣自然是重点。太祖对中书省的臣子们说,自古代以来,忠臣烈士忠义可嘉,如在鄱阳湖大战效忠殉国的忠臣,若不祭祀他们,实在难以安慰这些亡灵,应让人们每年祭祀,以激励生者,倡导忠义之气。太祖不仅对三十六忠臣全部封赐,而且下诏在康郎山建立忠臣庙,为三十六忠臣塑像,“有司岁致祭。”
忠臣庙的建立,是在明朝根基未稳,社会动荡不定,明太祖为激励战功,鼓舞士气,为取得明朝根本性的胜利而采取的措施和办法,其中反映明太祖思忠臣、良将之心态,但更多的是基于崇德报功,告慰亡者之灵,尚忠臣,激励士气的目的。这是忠臣庙建立的初衷,明确其社会道德价值,并没有赋予这些忠臣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同时这些“祭祀”仪式只是纪念性仪式,还不具有真正宗教意义的祭祀仪式。
然而,时光流转,历经六百余年风雨,忠臣庙破败几度,几度修缮、重建。在修缮、重建过程中,不断被赋予神性力量的主导作用,增加其神圣性。在明代,有文献记载维修重建过七次。嘉靖辛丑(1541年),知县冯汝弼重修忠臣庙并作《修康山忠臣庙记》,《余干县志》载:
嘉靖辛丑秋,八月二十一日,余偕邑博郭君智、颜君奎、阮君世铨,修祀事于国初死事忠臣三十六公之庙。庙在县西北百二十里番湖之浒,康山之麓。时邑事旁午至,则约诸君以星夜三鼓祭,祭毕可一日归也。乃至齐舟中。方就寝,梦典礼诸生张淑等前白余曰:此地有陈老先生者,公当召之。……越明年二月,春祀届期,余恐其久而弗传也,命工镌石于龙津水次。月既望,余适以公务宿水次官仓,则谛思所谓钟陈其姓者为何如人,忽自悟曰,钟陈即忠臣也,遂跃而起曰:兹意也!历三时而未达,今兹顿悟,殆神有以启之。欤夫,神发其机于祀庙之时,而启衷于镌石之际,信乎英灵之不敏也。遂命工纪诸石。[9](P1098-1100)
知县冯汝弼白日午梦见神灵授意,此即忠臣庙显灵,托梦冯汝弼知县,梦中有(钟)陈先生出现,顿悟“钟陈即忠臣也”,方知这是“神有以启之”。冯见忠臣庙“栋将颓,壁将仆,颓垣圯岸,四顾萧然”,于是决定修葺忠臣庙。此时,忠臣庙崇拜的盛行,有相对固定的信仰领地和信众,每年有定期的膜拜仪式,充分显示其时历史人物已经神化和道教化,属于典型的道教神灵化表现,因此,忠臣崇拜已经开始道教化。
除忠臣庙以外,还有对鄱阳湖地区的老爷庙元将军的信仰。对老爷庙元将军的传闻,源于元末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与伪汉陈友谅大战鄱阳湖,太祖初失利,走湖滨遇险,是一老人驾舟将太祖避险,太祖赐予金环,返顾之,见是一鼋也。《都昌县志》记载:
元末明太祖与伪汉战于鄱湖,初失利,走湖滨,遇老人舣舟近岸,太祖得济,赐以金环,返顾之,则鼋也。[10](P744)
太祖朱元璋得以神助,鼋现原身护主,为鄱阳湖大战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元将军传说由此流行,元将军是以鼋为原型的动物精灵。明太祖建国以后在此地修建元将军庙,纪念这一精灵,为这个出身低贱的农民皇帝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象征其皇权神授的合法性,去除内心无法忘却的自卑情绪。此后,元将军庙历经几百年时间,几度毁坏,但其信仰仍为流传。《南康府志》记载:
国朝康熙二十二年,知县会王孙以行舟过此,往往风涛叵测,用土人议,建庙三楹,以妥其神,患乃息。教谕熊永亮记,嘉庆十五年,知府狄尚絅详请巡抚先福奏奉。[11](P158)
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知县会王孙行舟路过,“往往风涛叵测,用土人议”,重新建庙宇,“以妥其神,患乃息”。这是最早记载元将军显灵要求重新修建庙宇的神话,并通过以地方志记载下来,不仅仅传承这一个神话传说,而且通过元将军显灵来加强这一集体记忆,说明至康熙年间元将军信仰已经超越了精灵信仰的层次,上升为宗教神灵信仰的高层次。清知府狄尚絅曾为元将军庙撰写碑文:“湖神元将军庙正临其陿,两岸礓砾无际,而堆埼逼束,水行峻急,注成深潭,章水南来,会之势益湍捍,通省漕艘,必经此险,商民往来,日不可殚记,猝遇风涛,长年莫措其手,一祷于神,即安然得泊。”[12](P1325)地势险、湖水深、水流急等地理因素,造成这里的水势环境非常险恶。时日久远,过往此地的船夫渔家都拜求于此,从而元将军在百姓的观念中,一个历史上传说的动物精灵变迁为“湖神”了,故狄之碑文中,已称“元将军”为“湖神”。因此,人们对元将军的祭祀仪式和规格也发生了变化,由“附祀”转变为“专祀”;其功能也发生变化,开始具有护航护渔的神职。清《皇朝经世文续编》云:
都昌元将军,明洪武间,仅附祀于湖神庙,嘉庆十四年,前抚臣先奏请,立祠专祭,敕封显应元将军,春秋遣官致祭,帆樯顺利,粮艘遄行,神之为灵,昭昭也。[13](P985)
《都昌县志》有一段更加详细的记述:
特旨躬亲飨献,臣尚絅在执事之列,是日,天微阴,祭毕,豁然开朗,观者大悦,爰请于疆吏曰,将军功烈盛矣,惜前史所佚,未得领于祠官,且旷无号谥,今因睿鉴而请焉,民所望也。疆吏据以覆奏,下礼部议,礼部复咨请疆吏,核神惠以闻,赐号曰显应,有司春秋祭祀,着为令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2](P1325-1326)
此时,元将军被敕封为“显应”封号,狄尚絅举行盛大仪式,“如礼,于是观者万余人,益欢欣和会。”、“众皆顿首欢呼,声溢洲渚”[12](P1326),万民同欢,欢呼顿首,将元将军崇拜推向高潮从而抬升了元将军信仰的社会性。同时,对老爷庙元将军的祭拜仪式和供品上有明确的规定,模仿道教祭祀规格,一般供品为帛一、羊一、豕一、尊一、爵三,主祭官蟒袍补服,行二跪六叩礼。每年春秋致祭,并将此载入祀典。《同治都昌县志》载:
嘉庆十五年,巡抚先福题请左蠡元将军,巡抚秦承恩题请致祭许真君之例,其需用祭银亦照例于征收耗羡项下,每祭支银六两,春秋共支银十二两,嗣后即以春分、秋分日致祭,永为定期,载入祀典。[12](P165)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要求祭拜元将军之礼仪同于许真君之例,明显说明元将军等同道教尊神许真君的地位,祭祀所需银两照例征收,可见其重视程度,亦见元将军祭祀规格之高,民间信众之盛,同时,元将军祭祀又有专门的仪式与祭辞,这一切已然将元将军纳入道教神灵,元将军信仰的道教化已然可见。
此外,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还出现了巫术化的表征,巫术是传统道教的要素之一。如《余干县志》载一佚名作《里巫行》:
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欲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莫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此止,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9](P847)
另《德安县志》载清代诗人刘鹏程作《德安竹枝诗》:
城中无日不招魂,才见南门又北门。
信是神灵肥庙祝,牲牢酒食魇晨昏。[14](P732)
作者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家人生病时请巫、迎神、驱鬼、招魂的场景。百姓信巫,因“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们祈福道禳灾、医治疾病。”[4](P28)巫师的作用不言而喻,乡民信巫拜神驱鬼时,非常虔诚,家中儿女齐到,摆放案台,上陈有羊、鱼等祭品,巫师击鼓而歌,手舞足蹈,同时家人按照巫师的指点参拜神君,祈求神君的帮助,驱赶疫鬼,巫师离去,家人还爬上自家屋顶叫魂,祈望病者魂魄在外游荡时,在家人的叫引下而归位,从而魂魄归位,病人康复。民间百姓信巫、迎神、驱鬼、叫魂等活动,与道教中的天师道相吻合。因“天师道除了信奉‘神’和‘仙’外,还相信鬼的存在。”[15](P50)《太平经》中说“昼为阳,人魂常并居,冥为阴,魂神争行为梦,想失其形,分为两,至于死亡。”民间多有叫魂之术亦可想而知,意使病者魂魄归位,元神一体,此典型的天师道与民间信仰的交融与互动,亦民间信仰神灵道教化的具体表现。
总之,鄱阳湖区域地方神灵崇拜众多,在众多神灵崇拜中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及宗教色彩,这些民间神灵如忠臣信仰、元将军信仰等都随着时年演变,由一地方普遍神灵逐渐演化为道家神灵。
三、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道教化的原因
明清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神灵的道教化色彩非常浓厚,可说比比皆是。纵观鄱阳湖区民间神灵道教化之因由,笔者认为有三:
(一)国家力量的介入,利用道教形式改造民间信仰
任何民间信仰,最终目的是集道德性与社会性功能为一体,任何仪式、神话、神秘力量都是被添加到信仰事物上去的。民间信仰神灵的道教化之因由,首推国家力量的介入,利用道教形式改造民间信仰,从而加强道德教化,稳定地方社会,服务当朝政治。当一地方民间神灵上升为国家祭祀,使得民间信仰神灵的道教化色彩非常浓厚,在明清鄱阳湖区民间信仰中的忠臣神灵信仰,忠臣神灵原型为陈友谅和朱元璋鄱阳湖大战中为明英勇献身的三十六忠臣人物,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明清两朝地方官均予祭祀,从而地方百姓多加祭拜,以至环鄱阳湖区域忠臣信仰盛行,随忠臣信仰的深入与发展,其道教化日益彰显。
《余干县志》载:
土人云:神之为灵,每形人梦寐。近有附人而称管理河道,获理漕艘贾舶者,则其忠魂往来于湖上,以赞助熙隆无疑也。浩然常存之气,不与日星河岳相辉映于天地之间也哉?又门前树植,环栏培惜,枝叶复茂,岂非神灵而物亦灵。[9](P789)
往来于鄱阳湖上来往的商贾、船夫、渔民等,无不泊船入庙膜拜、祭祀,以求忠臣神灵的保佑,求财求平安。因“则其忠魂往来于湖上,以赞助熙隆无疑也”,可见,信众认为忠臣神灵常在鄱阳湖上行走往来,能帮助他们渡过各种难关。甚至于庙前的树木,枝叶茂盛,也似乎是受到忠臣神灵的佑护,神灵验,树也具有灵气了,忠臣神灵的道家神仙形象跃于纸上,这一切之根源,在于国家力量的介入即国家祭祀的作用,使得明代的历史人物逐渐演化变迁为道家神仙之形象。
又如水神元将军崇拜,庙宇几经重建,历经几百年而不衰,并明清两朝祭祀,祭祀礼仪也参照于道教尊神许真君,亦有专门的礼仪、祭辞等等,这是典型人为地赋予它具有神的力量和信仰仪式,以更好地服务于政治。显然,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元将军崇拜逐渐走上道教神坛并逐渐演化为道教尊神。
(二)民间百姓信仰的强烈诉求,倾向于具有周期性仪式、拥有神秘力量的道教神灵
明清鄱阳湖区民间信仰神灵众多,特别是在重大灾难或节假日来临前,百姓对神灵的渴求异常强烈,这些强烈的诉求,使得民间信仰神灵发生道教化的偏向,再者,道教本身在民间的影响较大,其神灵系统也主动将民间信仰纳入。如城隍庆生,民间百姓尤为重视,《彭泽县志》载:
前三日,扫道清尘,临期出巡,扮伯爵旗卫,满街结彩,香案迎迓,各街坊装台阁,故事备极精巧。观者盈市。[16](P47)
城隍神出巡,在民间极其重视,备受欢迎,“满街结彩”,“观者盈市”。城隍神原型本为民间信仰的神灵,后完全转化为道教神灵,其守护城池,佑护一方。对下层阶级而言,民间神灵的信仰是不分教派的,只要传说神奇,名声大,求拜的人多,自然他就信奉。再者,对于官府倡导的神灵,在百姓的眼里,自然更受到重视,城隍神的拜祭,在百姓脑海里留下深刻的烙印,每次城隍出巡,是百姓最热闹最开心的日子。《彭泽县志》载李天英的《龙城竹枝词》:作者生动展示了城隍出巡的一幅画面,城隍神信仰在民间深受欢迎,展示了古代社会百姓娱神场景。对于民间城隍神信仰,道教亦编撰了专门祭祀的经典文书,即《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其中开卷经偈曰:
台阁儿童别样新,先期洒道更清尘,
一声萧鼓人如市,知是城隍又出巡。[16](P361)
稽首皈依城隍尊,威灵煊赫镇乾坤。
护国安邦扶社稷,降施甘泽救生民。
统辖大兵巡世界,赏善罚恶日同明。[17](P747)
将民间城隍神位列道教尊神,这与民间百姓对城隍神的强烈诉求直接相关。
同样,加封元将军为“显应”封号,狄尚絅举行盛大仪式,“如礼,于是观者万余人,益欢欣和会”、“众皆顿首欢呼,声溢洲渚”,欢呼顿首,万民同欢,足见百姓对民间神灵的渴求和祈望,正因百姓对民间神灵信仰的强烈诉求,使得民间神灵信仰根植于道教土壤,从而使民间信仰神灵迅速向道教神灵转变。
(三)道教信仰本身固有范式的优势
在民间神灵信仰体系中,道教信仰为我国本土化神灵信仰,根植于民间,土壤深厚,也贴切民众,贴近生活。在道教神灵体系中,其固有的范式,道教斋醮科仪等活动,具备一定的神秘性和惑众性,百姓在祈求神灵帮助时,通过道教人士的导引及表演,使得道教信仰更具有一定的神秘性,使得更多的百姓膜拜和信仰。在现存的斋醮有开坛、洒净、奏请、符水、诵经、神像开光、上疏奏表、焚表、存思;阴事的有:破狱、摄招、宝箓符等内容,这一切可谓精深博大。又如开坛,做道场法事活动等,开坛必须选择吉日,在黄道吉日开坛,这很大程度上让百姓更加信服道教神灵的灵验。如水神元将军祭祀,有专门的祭仪、祭辞等,官府人员带头祭祀,这些固定的祭仪,在仪式和形式上与道教趋同,本质上说其更大程度上受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道教信仰本身的固有范式促进了民间神灵的道教化,或者说民间神灵的祭拜仪式与道教信仰固有范式的趋同,更大程度上使得民间信仰道教化。
注释:
①对鄱阳湖的研究,主要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鄱阳湖研究》一书,其中涉及明清的一些社会经济史内容;魏嵩山和肖华忠合著的《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中关于鄱阳湖经济开发与文化发展等内容对本文具一定的启发;许怀林的《江西史稿》、《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中也涉及鄱阳湖区的社会变迁问题;南昌大学扶松华的硕士论文《环鄱阳湖的民间信仰》和暨南大学斯军的硕士论文《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区域典型水神信仰变迁研究》,为本文观照江西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②参见《饶州府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第568页;《南昌县志》卷十六,民国二十四年重刊本,第248页,第259页;《九江府志·建置·寺观》卷十三(同治十三年刊本),第140页均有载。
③参见《余干县志·坛庙》同治十年,卷四,第575页;《饶州府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第589页;《九江府志·建置》卷十三,第149页;《南昌县志》卷十六,民国二十四年重刊本,第228页;《九江府志·建置》卷十一,第127页;《南康府志·建置》卷七,同治十一年刊本,第162页,第184页,第147页。
④参见《同治都昌县志·坛庙》卷之二,第42页;《星子县志·建置志上·坛庙》同治十年,卷三,第24页;《南昌县志》卷十六,民国二十四年重刊本,第249页;(清)欧阳寿等纂:《同治彭泽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第54页。
[1]王景琳,徐甸.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2]朱海滨.民间信仰的地域性——以浙江胡则神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09,(4).
[3]鄱阳湖研究编委会.鄱阳湖研究[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4]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Kenneth Dean.Taoist Ritual and Popo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New Jersey:Princeton UiversityPress,1993.
[7]范正义.民间神信仰与道教的互动——以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例[J].华侨大学学报,2005,(4).
[8](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清)区作霖.余干县志[M].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
[10]都昌县志编委会.都昌县志(卷之十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11](清)盛元等.南康府志[M].同治十一年刊本.
[12](清)黄昌蕃等纂.都昌县志[M].狄学耕等修.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
[13]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十三).礼政三·大典下[M].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4.
[14]孙自城.德安县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5]张金涛.中国龙虎山天师道[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16](清)欧阳寿等纂.彭泽县志[M].陈文庆,赵宗耀修.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
[17]道藏编委会.道藏(第34册)[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