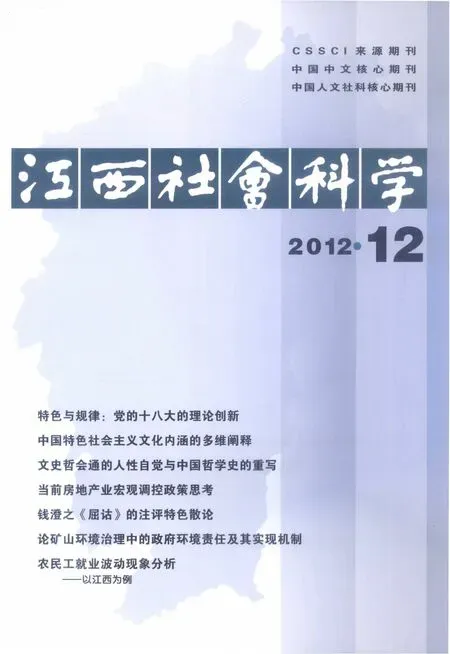叶紫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陈文芳 曾纪虎
从1919年“兴女学”提出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到1925年前后鼓吹的“独立女性”,再到1930前后倡导的“革命女性”,原先只有男性参与的革命和政治等社会活动中逐渐出现了女性的身影。这一时期的左翼作家叶紫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刻画了很多这类女性的形象。她们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自主而积极参与各种斗争。本文简要考察叶紫小说和散文中的一些女性角色,并以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为基础,浅析他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叶紫的文学创作始于1933年左右。他最早的小说《离叛》就是以一个女性人物作为主人公。在他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还有:福生妻子(《杨七公公过年》)、刘翁妈(《向导》)、尤玉兰(《菱》)、桂姐儿《偷莲》、信仰佛教的胖妇人(《在电车上》)、妓女秀兰 (《湖上》)、少云婶(《刀手费》)、王小姐 (《毕业论文》)、云普婶 (《丰收》)以及《星》中的梅春、木头壳的妈妈、柳大娘、麻子婶、黄瓜妈,等等。
叶紫的小说多以农村生活为背景,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对农村女性抱以最大的同情心。叶紫关注农村女性的命运,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大概是《离叛》的出师不利。他应该从这本书的失败中意识到自己并不擅长把握都市女性。周葱秀对叶紫的这篇《离叛》做过这样的评价:“叶紫最熟悉的是农村生活的题材和旧军队生活的题材,而对于《离叛》中所写的这一类生活题材并不那么熟悉,很难触发他的某种深刻认识和情感;同时,‘革命加恋爱’这种故事框架,前几年就被许多作家反反复复地写过,大约他觉得很难加进一点什么独创性的东西,很难说是成功的创作,因此,叶紫便渐渐消失了创作、加工《离叛》的兴趣。”[1](P65)其二,在1923年“问题小说”的衰退与1926年革命文学的兴起之间涌现了一批乡土文学作家。这些作家的写实风格既展示宗法制社会背景下的民风民情,也融入了一批出自农村并由古典转向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尴尬之情。“一位古代的老太太叨叨柴米油盐,为什么她进入书写的视阈是悠然的,而一位现代的老太太同样在叨叨柴米油盐,而她的被书写却是麻木而愚蠢的呢?唠唠叨叨的老太太其实没有变化,之所以在两种被书写中展示出的不同的面貌是在于书写者的变化,现代书写者与被描写对象之间不再存在古典时期的那种共通性与亲和力,他和被书写者是隔阂与疏离的。”[2]但是,乡土文学也为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作为一个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叶紫没有理由不关注这些作家描写农村的手法。
在叶紫的小说中出现的女性角色往往非常传神,几笔下来,一个活生生的农村女性形象就跃然纸上。她们不再如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那般漠然和麻木;因为叶紫熟悉她们的生活。而且,叶紫也不是一个受严格的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他1922年(虚岁12岁)考入长沙妙高峰中学,1925年考入华中美术学校。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汉,叶紫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6月,益阳局势剧变,叶紫父亲、二姐遇难,全家成为该县恶霸曹明阵的搜捕对象,叶紫从此外逃奔波。残酷的现实迫使他摒弃知识分子的气息,不再关注宗法制社会的穷困和漠然,而代之以关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对立,关注肆意践踏他人者的残暴、被压迫者的悲苦以及悲苦者积蓄力量奋起反击的过程。可以说,叶紫笔下的女性不再是民俗学意义上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虽然她们一度是男性的宰制对象或权势人物的压迫对象,但是在被宰制和被压迫的过程中,她们不再默默地承受,她们慢慢觉醒,进而奋起反击。
至此,叶紫引入了一个萦绕他短暂一生的事件——1925年前后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叶紫的很多小说中都能看到农民运动的背景,它也是激活一摊止水般的宗法制社会的一个因子。如果没有这个事件的进入,平滑的小说叙事也只能述说一段又一段冷漠的悲苦民情。这个事件导致宰治者的凶残呈几何级数增加,被宰治者再也无法忍受自己的悲苦。这样,小说的情节就变得跌宕起伏,让死气沉沉的宗法制社会变得暗流涌动。
在这种背景下,奋起反击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会迅捷吸引读者的眼球。《向导》中的刘翁妈,《星》中的梅春就是这些反戈一击者的女性代表。刘翁妈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又被白军杀害。为了将白军引入红军的包围圈,她故意将自己的腿打断。如果说刘翁妈展示的是妇女参加农村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时遭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极为惨烈的迫害,那么梅春则增添了妇女解放在农村社会所面临的更富戏剧性的命运。这一点也暗合了叶紫在文学写作的初期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只不过是他将自己并不熟悉的“时代女性”从城市移到农村,也更细致地表现出叶紫对广袤中国大地上的女性命运的思考。小说中的梅春,承受了“贤妻良母”式的忍耐后再自由恋爱,在失去一切之后,她选择出走——走向罗罗山(暗指罗霄山脉)。显然,叶紫似乎认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农村女性的解放唯有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坐标上才有可能实现。
除此之外,叶紫还出色地描写了众多其他的女性形象,如福生妻子(《杨七公公过年》)、尤玉兰(《菱》)、桂姐儿《偷莲》、妓女秀兰(《湖上》)、少云婶(《刀手费》)、云普婶(《丰收》);以及《星》中的木头壳的妈妈、柳大娘、麻子婶、黄瓜妈等。通过描写这些在神权、宗法权、夫权之下备受煎熬的各个年龄层次的女性,叶紫把旧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表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叶紫散文中的中性形象也可分为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在《现代女子书信指导》中出现的。1932年,叶紫为女子书店编辑《女子尺牍》一类的书刊,1935年2月1日,他用妻子汤咏兰的名字出版了《现代女子书信指导》,该书被列入《女子文库》。其中的女性形象约略有:一位破碎家庭的可怜主妇 (《灾难与友谊》)、廉姑(《囚笼》)、女诗人罗琇芬(《打听女诗人的消息》)、女学生徐静蓉(《初恋》第二封)等。第二个系列出现在他的《社会问题散文》;叶紫多以“我”的见闻作为这些散文的写作背景,他身边的两个女性(母亲和妻子)自然就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散文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女性人物,如孕妇(《长江轮上》))、中年寡妇和她11岁的童养媳 (《还乡杂记》)、小店的老太婆 (《行军掉队记》)、读书人的母亲 (《行军散记》)、姐姐 (《好消息》)、老船夫的儿媳(《古渡头》)、玉衣(《玉衣》)、旅店老板娘及其女儿(《南行杂记》)等。
有人把叶紫的散文称为“社会问题散文”并评论说:“叶紫的散文属于‘社会问题散文’。他把散文创作引向了当前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由表现身边的琐事到表现人民的苦难,由抒发个人的哀愁到控诉社会的罪恶。”[3](P581-582)叶紫的散文中出现的那些命运多舛的女性足以形成一组受压迫的女性群像。比如,一个因灾荒而外逃的孕妇,无钱买票,轮船上的账房和茶房又刻薄无比。虽有“我”和“我”母亲的帮助,但还是被毒打至早产(《长江轮上》))。中年寡妇带着她8岁的儿子和11岁的童养媳开了个小饭店。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让童养媳陪客人睡(《还乡杂记》)。五人行军掉队,寻找午餐,小店的老太婆闭门不纳;军人们冲进小店,她不但不卖饭给他们吃,反而向他们索要儿子,还找出剪刀与五个男人拼命,结果被绑起来,强行卖了饭食 (《行军掉队记》)。老船夫辛辛苦苦地将儿子带大并为他娶了媳妇,儿子却被抓了壮丁;生了一个小孩的儿媳妇另嫁他人,还把老船夫的小孙儿也带走了;她要等他有了钱才肯把小孩送回(《古渡头》)。《玉衣》发表于1935年10月28日至29日的《申报》副刊《自由谈》,聪明可爱的小女孩玉衣一出生,父亲就双目失明;父母将她看得如猪狗一般。文中写道:“前年大水,卖掉她的第一个姐姐;去年天干——第二个;今年,又轮到她头上来了。”这些散文道尽了满目疮痍的社会下农村女童的悲怆之音。
在关注外部世界的困苦的同时,叶紫还将笔端移向自己内心的隐痛。在他的这些散文中,他不时提到母亲和妻子。比如上文提到的《长江轮上》中的“母亲”,叫醒并吩咐“我”救下一位被吊在空中的孕妇,并向茶房求情。然而天一亮,孕妇还是遭到了茶房的毒打,并且导致早产。母亲为孕妇接生、募钱,但旅客给的不多。母亲几乎难过得要哭了。《好消息》从母亲盼望亲人的平安信入手,开头就写母亲对平安信的殷切期盼,而“我”却接到一封姐姐的报灾信。母亲见“我”在读信,便要“我”读出信的内容。“我”哽咽着将一封报灾信念成平安信。母亲听完后微笑着说:“真好啊!”母亲的欢欣起到了反衬效果。如果再联想到叶紫的母亲在大革命前后遭遇的丧父、丧女之痛,被逼疯之后的一直有异于常人的精神状态,读来就会更加令人心痛不已。发表于1935年10月1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的《殇儿记》,就是叶紫以自己的丧子之痛为背景写作而成的。其中的“妻子”形象虽然落笔不多,只作为“我”的倾诉或发出看法的一个道具出现,但她的酸楚和柔顺令人深表同情。
叶紫散文中的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都有着乡村生活的背景。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萧条、困苦。而农村女性的生活状况更值得怜悯。他通过这一组悲伤的群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旧中国的黑暗面,揭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
叶紫在短暂的文学生活中塑造了诸多女性人物形象,与同一时期关注农村生活的作家不同的是,叶紫在文学创作活动之前就开始关注女性问题。1932年姚名达和夫人黄心勉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女子书店并创办《女子月刊》,倡导妇女解放运动。叶紫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大概就是这时萌芽的。1935年,他在《艾伦凯与柯仑泰》这篇文章中提到艾伦凯与柯仑泰这两位妇女解放的先驱,并对艾伦凯的观点(一、结婚应以恋爱为基础;二、自由离婚;三、母性复兴)进行详细解读。他说:“中国妇女,受了数千年封建遗毒的折磨,怎么也抬不起头来。即使智识妇女,也还有许多是脱不了樊笼的。她们感受的只有痛苦与压迫。国民革命后的现今,又何尝不是一样呢?”[1](P198)此时,叶紫对妇女解放的看法有点类似于1925年前后鼓吹的“独立女性”,并且还没有完全摆脱五四时期的自由风气的影响。这篇文章的架构顺应当时的潮流,以信件做铺陈,这种风格的文章虽然延续了五四的浪漫风潮,但情绪的渲染大过“问题意识”。比如,在解读“母性复兴”时,叶紫的理论准备明显还不够充分,因而他援引的资源只能来自日常生活,导致文章的思路不太清晰。因为他把母性复兴、自由婚恋放在一起考虑,必然会导致逻辑的混乱。除去几个具有强烈抗争意识的人物之外,他对女性人物悲苦的考虑往往超过了对自由的考虑。
叶紫的文学创作时间并不长,留存下来的作品也不算丰富,但他的作品中却断断续续地出现了近三十位女性人物。他笔下的农村女性不再如乡土小说中的女性那般逆来顺受,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作品远远胜过了2世纪20年代按照“人的文学”创作出来的那些乡土文学。更为可贵的是,在灾难和被奴役的命运面前,出现了一些为了自由而斗争的女性。“革命女性”的来源由城市移向农村,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连接起来,将女性解放的最终可能性投入到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去。
[1]周葱秀.叶紫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何桂英.论新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特质[J].求索,2011,(5).
[3]胡从经.叶紫文集(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4]胡健.论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形象及主题特征[J].求索,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