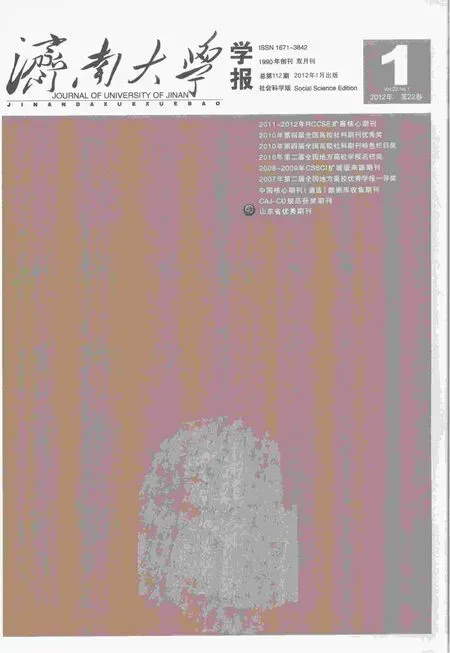山东情义文化的思想渊源
毛新青
(山东政法学院 新闻传播系,山东济南 250100)
山东情义文化的思想渊源
毛新青
(山东政法学院 新闻传播系,山东济南 250100)
情义是山东地域文化的重要资源,也是山东早期思想家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孔子确立了“情义”的基本价值和内涵,限定了后世儒家关于“情义”论述的道德取向。孟子从内在心性的理路上论证了“情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能性,而荀子则将“情义”的实现诉诸外在的礼仪制度建设。与儒家关于“情义”理论的主流建设不同,墨子将小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互利原则引入了情义内涵的考量,体现出要求公正、平等、互助的平民意识。
情义;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公平
“情义”文化作为山东文化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流变都与山东的地域特色相关,对于“情义”内涵的开掘与系统阐发是山东早期思想家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并且奠定和影响了此后情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孔子是第一位对于“情义”进行系统讨论的思想家,他确立了“情义”的基本价值和内涵,限定了后世儒家关于“情义”论述的道德取向,使“情义”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色。孟子从内在心性的理路上论证了情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能性,而荀子则将“情义”的实现诉诸外在的礼仪制度建设。如果说儒家关于“情义”理论的建设体现出上层贵族的主流意识,那么墨家学派的情义思想则是民间立场的鲜明表达,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和功利色彩。不同的思想资源在多元互动和融合的过程中,以其精微的“情义”内涵参与了山东地域文化的建构,渗透和积淀成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型塑着山东文化内涵的独特品格。
一、“情义”的主流建构——孔子“情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儒家的情义思想最早是作为“立人之道”而被提出的,《周易·说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仁”最基本的含义即指“爱”的情感,《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当代学者也注意到了儒家伦理的情感特质,如有的学者评论说“情感是孔子仁学的第一原则”[1],蒙培元先生则将儒家哲学称之为“情感哲学”,他认为儒家将“情感放在人的存在问题的中心地位”[2],并认为孔子的仁学就是建立在对人的情感讨论的基础之上。“仁”是孔子伦理中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但同时它更是一种道德情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的核心和根本是家庭内部的亲情关系,即子女对父母的“孝”与子女之间的“悌”,这种亲情关系的重要性被后世儒家称之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仁者,人也”是对于人的本质的规定,只有具备“仁”德的人才能称之为人,由此“亲亲之爱”也是人的本质构成的基础。不仅如此,孔子还将其作为社会道德秩序构建的基本,认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亲亲之爱是管理者进行社会治理和社会统治的表率,“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当然仁爱虽然始于亲,但不终于亲,它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推己及人”的伦理情感结构。情感在伦理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更体现在对于无血缘之情的他者生命的关爱之上,具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的普世情怀。
义的基本内涵是合宜,“义者,宜也”(《礼记·中庸》),就是应该或应做之事应与社会正当行为相联系。如果说仁和人的血缘之亲与自然情感相关,那么义则涉及到人的社会理性和义务责任。义具有兴利除害,维护社会正义的品质。孔子认为“义”是道德高尚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君子义以为上”(《论语·微子》),“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因此“义”是对君子与小人进行区分的一种价值标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不同,君子将维持人间正义视为自己的使命,而小人则仅仅局限于物质财富和政治权势上的得失。当然义还是个体所具有的责任意识,“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义”包含着主体对于主流社会的价值认同,内在地蕴含了对于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和遵循。反之,“不仕无义”,当国家面临危难,不能勇敢地挺身而出,在灾难面前挽狂澜,就意味着丧失了铁肩担道义的政治责任感。
二、“情义”如何可能——孟荀对孔子“情义”思想的发展
“情义”作为宝贵的精神价值,既关乎个体生命存在的提升,也是人际关系互动和社会秩序整合的基础。怎样保证“情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是孔子之后儒学大家们探讨的问题。孟子的思路是依赖于内在心性的个体修为来实现,荀子则将之诉诸于外在礼仪符号的制度建构。
孟子从内在心性的理路上论证了“情义”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可能性,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人类天生具有的内在本性,是人天生即有,不证自明的,也是人之成为人的内在根据,他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有无善端是人与禽兽之间进行区分的内在标志,在他看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但是这些善端只是端与源,要靠主体在后天的实践生活中加以保持、培养、扩充、发展,否则就会流失。“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能否保持善端,是君子与庶民的重要区分。在德性四端中,孟子把“恻隐之心”作为“仁”的源泉,将“羞恶之心”作为“义”的起点,它们都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所以人天性就有仁慈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如果遇到小孩掉进井里,每个人都会产生慈悲之心,伸出援手进行施救,这是仁的内在性。而义的实现和保障则依靠主体内心的道德体验,这种道德体验是人们违反义时所产生的如内疚、惭愧、羞耻、自责等情感活动,义与非义的标准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内在良知自觉和良心发现。
孟子对于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张扬,对于情义内在性的凸显,从实践经验上来看具有合理性,因为义虽然是一种客观伦理秩序和客观伦理精神,但是义发挥社会作用则主要通过主体的道德自觉,它必然与主体的道德情感相连。孟子的情义思想为普遍的形式规范奠定了个体存在的基础,将理性形式与情感实质相结合,彰显了人存在的独特性和根本性。
孟子对于义的坚守使道德主体呈现出人性的光辉与魅力,“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对于万物生灵而言,生命具有无上崇高的价值与意义,但当生命的存在与社会道义发生冲突时,“舍生取义”就成为有道之士的庄严选择。孟子认为有德之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看是否符合道义,符合道义便做,不符合道义便不做,行义之事积累的多了,便会凝聚成充沛的力量,这股力量孟子称之为“浩然之气”。浩然之气表现为“至大至刚”,“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是一种生命的刚健之气,是“义”在个体生命中所呈现出的不可战胜的道德力量,只有执着于维持天地正气、人间正道的人才具有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与孟子向内寻求依据不同,荀子将“情义”的实现诉诸于外在制度的建设。荀子从情感与形式的角度揭示了各种各样的礼仪制度与情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认为礼仪形式能够为情义内涵提供外在的保证。他曾这样解释“三年之丧”这一礼仪制度:“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故曰:无适不易之术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礼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荀子·礼论》)丧失亲人的痛苦情感要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才能够得以表达,“三年之丧”的礼仪制度可以使这种痛苦得到恰当的宣泄。丧礼中的物质形式如丧服、丧仗、守丧之庐、所食之素粥、所睡之席薪等都是痛苦情感得以外在宣泄和表达的物质载体。丧葬制度中的形式与人的内在情感互为表里,以这些精微细致的外在形式可以达到对于人的情感内涵进行调养的目的,也即荀子所说“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荀子·礼论》)。但是这一系列的礼仪制度,并不是任意的安排和对生活的随意补充,而是根据个体身份地位的不同有着严格的规定限制,而这些规定和限制所蕴含的正是“义”的标准。
荀子将“义”看成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之所以在天地间最为高贵,就在于人不仅有生命,有情感,而且还有“义”,“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制礼义以分之”、“义以分则和”,义对人群进行分类的目的不是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是在分的基础上实现辩证沟通,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内在和谐。礼仪制度是内在之“义”的外在表现形式,通过可感可触的外在物质表现形式,内在的情义得以体现。因此在荀子看来,礼仪制度为自然生命的安顿与文化生命的提升提供支持,“文理情用互为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荀子·礼论》)。礼仪制度的存在表征了人类群体生存的文化状态,而文化状态又是与人类的个体情感相互关联,互为表里的,脱离了情义内涵的外在礼仪制度毫无生命可言,没有外在制度的表征,情义也就丧失表达的渠道。因此,“情义”的实现要诉诸于外在的礼仪制度建设,他认为:“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出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为安,若者必危;苟情悦之为乐,若者必灭。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荀子·礼论》)如果站在体现社会准则的“礼义”立场上追求个体的情欲,那么情与义两者可兼而得之;而站在个体情欲的立场上追求欲望,那么情与义两者将一无所得。因此,外在礼仪制度的建设既是对个体情感的调节与限制,又是个体情感表达的保障,外在礼仪制度和丰富情义内涵的统一对于个体身心的平衡与社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情义思想的民间立场——墨子的情义内涵
墨子,今山东滕州人,早年曾学习儒家学说,《淮南子·要略训》上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学在学术渊源上和儒家有密切关系,但又是对儒学弊端的纠正。重情守义是儒墨两家理论内容中的重要方面,但在理论旨趣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如果说儒家的情义是主流意识的理论建构,那么墨子的情义则是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的表达。
《吕氏春秋·不二》中有:“孔子贵仁,墨子贵兼。”指出了儒墨两家情义思想的内在差异性。“兼”,即“兼爱”,它的基本含义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利,即“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墨子认为天下无序起源于人们之间情感的冷漠,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培植“爱人如己”的思想情感,才能够使社会稳定,实现天下大同。“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在赋予别人关爱的过程中,自己也从中获得爱,只有自己先付出了爱,才能够得到别人的爱,“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夫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墨子将小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互利原则引入了对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考量,带有强烈的现实功用性质。现代情感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社会交换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社会交换的存在“不仅在市场关系中而且在友谊中,甚至在爱情中,以及在这些以亲密性形式出现的极端之间的多种社会关系中”[3](P141)。与其他社会领域进行交换所追求的外在利益不同,情感交换所产生的效果不是外在的物质性报酬,而是内在的精神上的满足。交换过程的平等性和互惠性也不是通过外在的权力、社会地位进行衡量,而是内在的责任、感激和信任等心理感受,由此实现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力量主体的社会关系的整合,即墨子所说:“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墨子·天志上》)墨子的兼爱要求每个人不管其出身地位如何,都应以兼爱的准则来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试图将社会各阶层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而造成的利益不同的客观状况消除在同一的兼爱秩序之中。
对于“义”,墨子同样以交换过程中的“利”释之,认为只有产生“利”才能算得上是“义”。墨子说:“义,利也。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墨子·经说上》)义即是“利”,只有有益于天下人的事才能是义,这种“义”,是为天下牟“利”,而不是为个别的人所用。因此,义首先是对于他人权利的维护,因强调和突出个人的权利以至于侵害别人的权利为自己牟利就是不义。墨子“以利释义”的方法实际上缓和了义利之间对立的关系,建立起了内在的同一性。但这种一致性必须是建立在“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公义思想基础之上。
墨子认为义是最宝贵的精神价值,《贵义》篇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还说“义,天下之良宝也”。对于社会的存在而言,“义”具有无上的价值和意义,“义”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义出自于天,“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天为贵,天为知,“然则义果自天出也”(《墨子·天志下》)。因为天是高贵的、智慧的,出于天的“义”是公正的、客观的,它可以作为衡量天下一切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义”内在地蕴含了天下平等、客观公正之价值,即“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德行、君上、老长、亲戚,此皆所厚也。为长厚,不为幼薄”(《墨子·大取》)。不论亲疏厚薄,不论长幼序列,也不论上下等级,唯有“义”可以作为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准。
墨子对于“义”的理解,体现了其对于天下之公义的追求,反映出情义内涵的民间思考。与贵族阶层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形成的生活空间及生活方式不同,手工业者为了维持生存,必然要突破血缘、地域等自然因素的限制,在无血缘亲情的关系基础上重新建立起平等互惠的情感纽带作为内在的支撑,以相互之间的义务保持团体成员之间的协调与平衡。生产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主体对于公共价值理解的不同,墨子的“情义”思想不仅突破了个体的一己之私利,也打破了阶层、等级的限制。现代社会,人的实践活动空间有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科技的进步缩小了人们交往的时空,人际关系呈现出从私人性向公共性转型的发展趋势,墨子情义思想中蕴含的公正、平等、互助对于新型人际关系的建设更为普遍有效,对于促进社会风尚的转变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语
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情义”思想的内涵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不同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其进行了各有侧重的阐释,形成了贵族与民间、主流与边缘的多元互动,渗透和构建着山东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情义”思想中对于人类亲情和友情的坚守,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在日益物化的现代社会不仅没有被遗忘和淘汰,反而有不断强化和发展的趋势,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正常社会所需要的情感和理性追求,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普适的价值。挖掘山东情义文化的宝贵资源,重塑情义文化的山东品牌特色,不仅对于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也具有推动作用。
[1]谢寒枫.理性与情感维度下的仁[J].齐鲁学刊,2002,(2).
[2]蒙培元.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家哲学再阐释[J].社会科学战线,2003,(2).
[3]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G09
A
1671-3842(2012)01-0039-04
2011-06-03
毛新青(1975-),女,山东高密人,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原理。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山东‘情义’文化的源流、价值与品牌传播——以增强区域‘软实力’为视角”(2010RKGB2102)。
责任编辑:陈东霞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