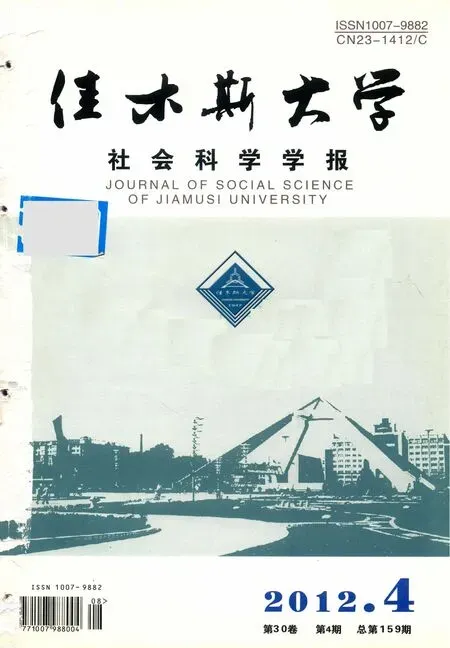佳木斯地域文化源流①
于秀丽,杨彦华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佳木斯地域文化源流①
于秀丽,杨彦华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一个民族的文化,因为其地域的自然差异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出地域性差别,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就同一个地域文化区域内而言,也存在着因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而导致的差别。佳木斯地区作为关东文化(或东北文化)的子系统,有其特殊的区域文化风貌。在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前提下,研究城市的特色文化,形成新的群体价值认同,对城市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并且有利于民族认同感的具体化,从而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地域文化;佳木斯;流人文化;闯关东精神;东北小延安;垦荒精神
文化作为自然的人化过程和成果,必然体现出民族化的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化,又因为其地域的自然差异,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表现出地域性差别,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就同一个地域文化区域内而言,也存在着因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而导致的差别。在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前提下,依据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研究城市的特色文化,形成新的群体价值认同,对城市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及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并且有利于民族认同感的具体化,从而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佳木斯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发展历史,研究以佳木斯市为中心的佳木斯地域文化,同样具有上述意义。
一、佳木斯、地域文化释义
“佳木斯”为音译词,在1720年出版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佳木斯市的位置标注为“甲母克寺噶珊”,噶珊是村或屯的意思。1778年出版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标注战迹图》则把佳木斯市标为“嘉木寺屯”,《三姓志》中则称此地为“贾木司”。满语专家穆哗俊认为“佳木斯”为满语,即清代的佳木斯噶珊,意译为“站官屯”或“驿丞村”。在赫哲语中,“佳木斯”则是“尸骨”的意思。“佳木斯”作为正式地名,1930年3月1日正式使用,改东兴镇为佳木斯镇,后来变市,几经沿革,目前下辖四区四县两个县级市,为黑龙江东部最重要的城市,经济文化和交通枢纽。
“地域”在现代汉语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面积相当大的一片地方;二是指地方,多指本乡本土。这里的“地域”不是严格的行政区划,因为即便是在近几十年,佳木斯的辖区也有变化,我们所讨论的“地域”只是大致上的“一片地方”,行政上以佳木斯城市为中心,地理上以三江平原为主体。
“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特指精神财富。物质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地理因素影响,精神财富的形成则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较多。文化是人化自然的过程,也是人化自然的成果,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而每一种文化都因经济的地域性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表现出地地性、阶段性以及连续性的特征。地域文化在这里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在长期的生产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表现为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和生产方式等内容。地域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到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
二、佳木斯地域文化形成的自然基础
佳木斯位于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而成的三江平原腹地,纬度区间为北纬45度56分至48度28分,经度区间为东经129度29分至135度5分,是我国最东端的城市。东隔乌苏里江、北隔黑龙江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比罗比詹相望。境内有富饶广袤的三江黑土平原;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有森林覆盖的张广才岭东部、完达山北部和小兴安岭余脉等低山丘陵;有大面积的湿地和草场,地形多样,资源丰富。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长夏短,无霜期130天左右。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农耕、畜牧、渔猎、采集提供了充分的优质资源。林业资源和矿产资源丰富,不仅有一定储量的木材,还盛产多种山野菜和食用菌类,已发现的矿物质包括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冶金辅助原料、建筑材料和其它非金属矿等50余种。生态环境良好,动植物种类繁多,农作物盛产大豆、水稻等多种作物,并栽培多种水果和蔬菜。盛产多种淡水鱼类。
丰厚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农耕、渔猎、游牧三者相兼的文化模式,多样的物产,特别是在黑土地上一年一熟孕育出来的米粮蔬菜以及山珍野味、冷水鱼类赋予了当地人高大强健的体魄。开阔的地域上人群稀少,形成了当地人粗犷大度、热情好客、喜大好侈、不拘小节的性格。长期的游牧和渔猎文化传统,使当地人形成了勇猛尚武的习俗和开放包容、追富而迁的观念。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当地人不必付出更多的劳动就可以获得足够的生存资料,因而形成了靠天吃饭的依赖心理。这种心理又因佳木斯市较早的创建了现代工业企业,在抗战结束后作为大后方较早地发展为工业城市而得到进一步强化。
一方面,自然环境形成了相应的经济模式,也构成了当地民风民俗和居民性格中的普遍特征,成为佳木斯地域文化的基因。另一方面,地域文化受到当地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佳木斯地区的地域文化,属于关东文化的子系统,带有浓厚的关东文化的共性色彩,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因素,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因子。
三、佳木斯地域文化形成的人文要素
(一)少数民族文化遗存
据“新开流文化”和“莺歌岭文化”出土文物资料证明,早在6 000年前,佳木斯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在公元前两千多年,这里就是肃慎人的繁衍生息地之一《,山海经》中有“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的记载。汉晋时代,肃慎改称为挹娄,南北朝时称为勿吉,隋唐时称为,均臣服中原王朝。唐朝曾设立黑水都督府,管辖今佳木斯一带。辽时改称女真,辽王朝在依兰以下沿松花江、黑龙江两岸建立五国部,管辖这一地区。黑龙江包括佳木斯历来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汉族人较晚迁入,17世纪中叶黑龙江“尚无汉人”,都是满洲即满族人,生活条件艰苦,杨宾《柳边记略》中载“,富者缉麻为寒衣,捣麻为絮,贫者衣狍鹿皮,不知有布帛”。目前,佳木斯市有42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有蒙古族、回族、朝鲜族、满族、赫哲族等,其中赫哲族是佳木斯特有民族。
佳木斯地区少数民族包括清朝入关后留在这里的满族掌握文字的人较少,所以少数民族文化多以服饰、饮食、生活习惯和口头文学等形式保留下来,较少有文字记载。至今许多习惯源于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如冬季喜欢吃粘米做的豆包,吃咸菜大酱和淹酸菜,这些习惯源于满族人,吃杀生鱼则源于赫哲人。更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体现在当地人的粗犷尚武的性格中。
(二)“流人”文化的影响
清初实行“文字狱”,受珠流的人遭流放,主要流放地为关东、云南、新疆,其中关东最多,此外反清志士、政治犯、刑事犯等也大量发往关东。“流人”的到来对当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带来了人口,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书箱和文化。特别是因文字狱而流放的人,都饱读诗书,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到苦寒的流放地大多以教书讲学为业,以著书赋诗为寄,留下了大量的文史著作和诗文,也为当地的文化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流人的文化影响是东北地域文化特色,对佳木斯而言,可以说流人文化是佳木斯地区雅文化的开端。
(三)中原汉文化的融入和“闯关东”精神的形成
东北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南部为汉人区,在辽宁和内蒙古东部四盟境内,北部为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在吉林和黑龙江。中原汉民迁入东北最早始于商周,此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特别是汉末大量中原汉民迁入关东,但大多迁入南部,而北部特别是黑龙江则汉民族迁入较晚。佳木斯地区到清初少有汉人,大多为少数民族。汉民族大量迁入始于清朝对龙兴之地封禁放松特别是废除封禁令之后。
虽然迁入的汉民多为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生活艰难的底层百姓,但同样给当地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文化影响。首先改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状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影响了当地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再次,由于汉民迁入东北,生活条件艰苦,基本上从事垦荒、伐木、淘金等艰苦的开发性劳动,克服种种困难在东北生存下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开拓性精神,“闯关东”精神,这种精神是佳木斯东北地域文化中的重要内涵之一。此外在服饰、饮食和建筑习惯等方面,汉民族与佳木斯本土少数民族也相互影响、相互适应。
(四)外国移民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影响
在东北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朝鲜、日本、沙俄,沙俄对东北实施了半殖民统治,而日本则在东北进行了14年的殖民统治。外国移民和殖民对中国东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佳木斯地域文化中有明显的体现。
东北境内的朝鲜族人据史料记载,不是历史上的高句丽王朝的后人,而是上纪二三十年代迁入的朝鲜人,目前佳木斯境内有朝鲜族人口六万两千多人,在桦南和汤原有两个朝鲜族乡。佳木斯盛产优质大米,其栽培技术源于朝鲜族人,佳木斯的饮食习惯也受到朝鲜族的影响。佳木斯与俄罗斯之间边境线长达五百多公里,隔江相望,很早就有生意往来和人口流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俄国人移民中国或旅居中国,更多是由于沙俄不断扩张,特别是随中东铁路的修建而来到东北。黑龙江人民抗击沙俄的军事和经济侵略,为争夺路权而斗争,但对俄罗斯文化并不排斥,也相互通婚,东北包括佳木斯在内曾经有许多中俄混血儿,俗称“二毛子”。许多俄罗斯语言成为东北方言,如巴篱子(监狱)、畏得罗(水桶)、葛娃斯(清凉饮料)、嘎斯(乙炔)等。
日本对中国东北实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文化侵略是日本对东北的一个重要的策略,他们对民众灌输奴化思想,推行愚民政策,强行以日语为国语,教习日本风俗,摧残东北的教育事业,推行殖民教育,插手社会教育和殖民活动,对一切文化事业实行严厉的统治政策。在其进行殖民统治期间的确培养了部分亲日汉奸,但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的殖民文化也如风吹云散一般,并没有留下更多的遗迹。
(五)“胡匪”、“抗联”精神的历史遗存
东北自古民风尚武好勇,在灾难和战乱中豪强四起,加之日本14年残酷的殖民统治,使民间武装林立,“胡子”和“抗联”并存。由于伪满政府的殖民和侵略性质,“胡匪”和“抗联”具有抵御外辱,保家卫国的共性,并且抗日期间有许多所谓“胡匪”直接加入抗联组织,抗击日本侵略者。其间有多支抗联队伍转战在佳木斯地区,如著名抗联名将赵尚志和周保忠等,当时赫哲族人民也组织了自己抗日队伍,参加战斗。抗日艰苦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有一些抗联成员由于种种原因沦为“匪胡”,如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后来都成了佳木斯地区最大的“胡子头”。胡匪和抗联均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历史,但二者的影响至今长存,前者更多体现在地域性格中,好勇好斗,后者更多体现在地域品格中,爱国爱乡,热爱自由独立,勇于牺牲。
(六)“东北小延安”时期的文化繁荣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拥军支前无私奉献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佳木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为最早解放的城市之一,解放全国的大后方。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派遣两万干部、十万部队进入东北。那时侯,延安大学、东北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总政文工团、延安鲁艺文学院、延安青年艺术剧院、东北文艺工作团、延安《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新华广播电台、延安电影团等革命文化团体、机构纷纷迁入,云集佳木斯,仅1946年佳木斯地区就成立了东北书店佳木斯总店、东北文艺出版社、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佳木斯分会、东北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文化单位团体,并有《东北画报》、《东北文化》、《人民音乐》、《合江农民报》等刊物创刊。佳木斯成为北满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东北革命文化的摇篮”,被誉为“东北小延安”。这不仅使佳木斯地区的革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也培养了佳木斯“东北的延安精神”,长存至今。
作为解放全国的大后方,佳木斯为支援全国解放做出巨大的贡献。青年踊跃参军,地方武装升为主力开赴前线,群众组织慰问团、服务队、担架队上前线,为前线治愈康复伤兵550多名使其重返战场。捐献大量现金、棉被、冬装、粮食、干菜、生铁、铜以及其他日用品,紧急生产制造武器弹药、用粮食交换武器弹药支前,成立军粮加工厂为前线生产粮食,征调司机、车辆、马匹等支援前线,支持全国解放。佳木斯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一直继承发扬至今,是全国首批双拥模范城市。
(七)“垦荒精神”和知青文化的注入
“北大荒”对于佳木斯意味着一种垦荒精神和一段大规模的移民历史,一次全新的文化融合。北大荒的移民由六部分组成,分别是:1958年春天,各地各军兵种、部队、院校十万官兵转业进军北大荒;1959年5月到10月,六万山东支边青年开赴北大荒;1966年3月,万名从沈阳军区所属部队复转官兵到黑龙扛垦区;1968年6月,沈阳军区三千现役军人进驻黑龙江垦区;1968年至70年代,50万城市知青从京、津、沪、浙和黑龙江省各城市,插队落户北大荒;1958年春天,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制造出来的一批当代“流人”“右派队”1500人包括著名文学家、美术家、电影艺术家,如聂绀弩、丁玲、艾青、吴祖光、尹瘦石、丁聪、李景波、于绍康以及陈沂少将等进驻北大荒。
毋庸置疑,垦荒团队的到来改变了佳木斯的经济状况,改变了佳木斯的自然面貌,更主要的改变了这里的人口结构,影响了佳木斯地域文化,改变了当地的生活方式。前后二十年中共计近七十万人开垦北大荒,尚未包括佳木斯本地下放到农村的干部和其他城市居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是知识青年,有从事各种专业、有特殊专长的解放军官兵,有大量的文艺工作者,甚至是文学艺术大师。他们对佳木斯地区,乃至整个黑龙江产生的文化影响是清初的流人文化无可比的,不仅产生了大量的以北大荒为背景和素材的“北大荒文学”作品,还产生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板画”,形成了兵团文化、知青文化。垦荒精神是佳木斯地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八)城市文化的新融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佳木斯的城市规模不断壮大,通过工作调动、毕业分配、随军和军转安置、外来人口迁移和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佳木斯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影响到佳木斯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也改变着佳木斯的文化状况。以佳木斯市为中心的佳木斯地域文化融入了新的力量和内涵。
佳木斯市在寻求自己的城市文化定位,一座东北解放区革命根据地文化名城,一个东北边塞的中等城市,一个重要的商品粮产区,一个生态魅力城市,一个松花江边养育了强壮勇敢的诸民族人民的城市,其文化也必然是在自然环境基础上整合了社会历史因素而成的,具有地域特色又具有中华文化整体特质的文化。
地域文化不仅是地域和民族心理认同的基础,也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为分析研究城市文明的现状和制定城市文明建设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
[1]蒋宝德,李鑫生.中国地域文化[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
[2]李治亭,等.关东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佳木斯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6.
[4]桦川县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K892.2
A
1007-9882(2012)04-0121-03
2012-06-20
佳木斯大学科研项目:佳木斯地域文化与城市文明研究(w2010-164);三江地区生态旅游农业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研究(w2011-003)
于秀丽(1971-),女,黑龙江肇东人,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伦理学和地域文化。
[责任编辑:田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