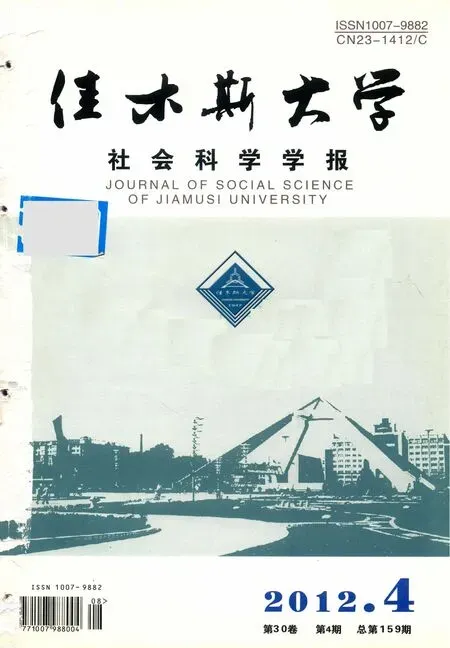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英国田园诗歌解读①
韩利敏,梁晓冬
(1.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2.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453003)
生态批评视角下的英国田园诗歌解读①
韩利敏1,梁晓冬2
(1.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芜湖241000;2.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新乡453003)
英国田园诗歌源远流长,是人类文明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但长期以来田园诗歌一直被视作消极遁世的文学而没有进入研究的焦点。然而纵观整个英国田园诗歌,不难发现大量诗作中表达出超前、明显的自然意识和生态思想。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批评理论为研究田园诗歌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试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客观全面地重新解读田园诗歌,探寻其中蕴含的积极生态思想及其对生态理解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从而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一步推动国内外对田园诗歌多视角、多元化的批评与解读。
生态批评;田园诗歌;生态思想;局限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范围内自然生态日益恶化,在这一大背景下,生态批评兴起并于20世纪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西方田园诗歌源远流长,有两千多年的古老传统,它根源于人类对圣洁伊甸园的向往、对城市生活的逃遁和对工业文明的反动,是人类渴望远离尘世喧嚣、逃避世间纷争、寄托人生理想的产物,田园诗人歌颂自然,敬仰生命,崇尚人与万物的和谐,痛斥人类对自然的贪欲与迫害。总之,田园诗歌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田园诗歌怀有极大的偏见,认为充斥于田园诗歌中的闲情逸致、归隐避世、怀旧返古等倾向使它有了“消极”、“空想”、“乌托邦”的意味。因此,英国田园诗歌一直被视作消极遁世的文学而没有受到批评家应有的重视,对它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本文试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重新解读英国田园诗歌,以批判的眼光客观地审视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同时也指出其生态意识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这将有助于打破传统批评对田园诗歌的消极定型和误解,进一步弥补国内外对田园诗歌研究的不足。
一、生态批评理论
20世纪60年代,工业文明高速发展,人类开始肆无忌地追求经济利益,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成为全球广泛关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生态批评开始兴起,于是文学评论界开始转评,试图从现代生态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救治失衡的生态。生态批评选择自然生态圈作为文学批评的大语境,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和评价,充分挖掘作品中蕴涵的积极生态意识,从而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批评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它将文学研究推向更加广阔的生态学视野,倡导文学理论研究应以自然为中心,摒弃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文学批评。生态批评的任务就在于通过重新审视文学经典中的“绿色思想”,实现文学繁荣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目标;生态作家的使命在于关怀自然,用审美的方式来救赎失衡的生态,痛苦深刻地反思与批判人类的恶行,从而表达对生态失衡的忧思和责任意识,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学者王诺对生态批评的定义是:“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1](P156)
总之,生态批评作为一门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和文化研究来重新审视与探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使人类理解到跨入高速发展的工业时代自身所面临的困境,进而呼吁人类保护自然、与自然和睦共处。作为生态文学批评的重要研究对象,英国田园诗歌可谓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历经不同的历史时期,田园诗歌得到长足的发展,大量田园诗歌散发出生态思想的光芒,传递出自然与人类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精神家园的理想,这正是生态批评永恒的主题和思想。
二、英国田园诗歌的生态思想解读
西方田园诗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拥有两千多年的古老传统。最早的田园诗歌起源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亚历山大时期,田园诗歌的创始人是古希腊诗人忒俄克利托斯(Theocritus),“田园”一词(pastoral)源于拉丁语,本意是“牧羊人”的意思。所以最初的田园诗又称作“牧歌”(pastoral poems),一般是关于牧羊人的诗或歌,描写他们居住的自然风光,他们的生活、思想及爱情[2](P36-38)。田园诗歌自文艺复兴时期传入英国,并与其他文学体裁相结合逐渐繁荣起来,自此田园诗歌的发展贯穿于英国文学史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本文主要从其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来解析田园诗歌蕴含的生态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歌
历经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黑暗,田园诗歌在14世纪传入英国,时值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英国文坛成了田园诗歌创作的大舞台,英国的诗人们继承了欧洲田园诗的牧歌传统:对恬静自然风光的渴望,对田园宁静生活的憧憬和对尘世纷争的逃遁。这个时期杰出的田园诗人代表有埃德蒙·斯宾塞、菲利浦·西德尼、克里斯托弗·马洛和约翰·弗莱彻等。在诗歌中他们表达了对神秘自然的敬畏,对美丽自然的赞叹。一方面,那时人们心目中的自然是神秘莫测、危机四伏的,人在自然面前必须谦卑恭敬;另一方面,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它渐渐成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和朝夕相处的好伙伴。因此,诗人们把自然当作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留下了大量赞美自然美景的田园佳作,如托马斯·纳什的《春》:
榆树山楂漫山野,
村村舍舍生气盎,
羊羔欢欣喜洋洋,
牧童整天笛声扬,
百鸟欢歌总在耳边响,
恰恰,咯咯,啾啾,
哥哥插禾
好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从中我们读出了诗人眼中自然的瑰丽、生命的涌动和生态的和谐,诗人对自然的敬仰正是现代生态批评所倡导和追求的主题之一。
在牧歌中,诗人还表达出对和谐宁静的牧歌生活的向往,这一表达往往是通过“牧羊人”形象来实现的,因为牧羊人过着和谐恬静的理想化的田园生活:居住在诗情画意般的田园乡村中,过着悠闲、散漫与惬意的生活,有着质朴纯真、率真浓烈的情感追求。这样生机勃勃的场景展示了人们对于纯真质朴、远离污染、天人合一的田园生活的守望。《多情的牧羊人》就是田园诗歌中的佳作,它代表着马洛的最高艺术成就,诗中描述了一幅诗情画意的田园图景:田野、群山、丛林、岩石、牧羊人、羊群和鸟儿悦耳的歌声,这些意象的勾勒使此诗充满了浓郁的田园气息。同时,马洛在这首牧歌中把自己比作牧羊人,把他的情人比作牧羊女,用召唤的方式来呼唤他的爱人来到他的身边、做他的爱人,从而告诫人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宫廷的尔虞我诈,回归纯朴、幽静的乡村生活[4](P96)。与其他田园诗歌不同的是,斯宾塞的《牧羊人日历》对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国社会有了更多的关注,针砭时弊、贬恶扬善,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传统古朴的宗法制社会的逝去扼腕叹息却又无可奈何。这一时期的诗人开始对日益纷繁复杂的世界无力掌控,于是逃避到自己诗歌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来寻觅那些逝去的好时光,所以此时的田园诗歌被认为具有怀旧避世的特点。其实在笔者看来,怀旧是对社会现实曲折、间接地反映,诗人正是通过勾勒理想中的自然之美来否定现实中的自然之丑,正是通过追忆美好的旧时光来衬托现实的社会和精神生态危机。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歌已表现出朴素的生态思想,体现出对自然美的崇拜与敬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含蓄探讨,对构建和谐自然生态文明的展望,这与生态文学属性中“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的特点不谋而合。只是这时期的田园诗歌过分美化田园生活,脱离实际生活,带有乌托邦的空想,田园诗歌主要充当了诗人们展露才情的平台。因此,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尚处于萌芽状态,是一种朴素的尚未觉醒的生态意识。
(二)浪漫主义时期的田园诗歌
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是诗歌争奇斗艳的黄金时代,“浪漫主义文学之父”卢梭发出“返回自然”的倡议,呼吁人们回到大自然、回归人类精神家园,受他的影响,浪漫主义诗歌表现出明显的田园倾向。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如火如荼和极端理性主义的泛滥,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加剧,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愈演愈烈,社会矛盾加剧,人性异化扭曲,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面临重重危机。社会环境的极度恶劣使诗人纯真的心灵失去了平衡,他们极端厌恶工业和机械文明,诅咒城市庸俗的生活。为了摆脱尘世的羁绊,缓解自身与社会的冲突,他们借助瑰丽奇特的想象,直抒胸臆,感物言志。在此背景下,田园抒情诗歌得到蓬勃发展,当属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相比,这个时期的田园诗歌对自然的描述更加真实客观,而且关注的主题也发生了改变,诗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对类人心灵的影响、城市文明与田园生活的强烈碰撞和人类在工业化时代的精神生态危机,这一切都体现出浪漫主义时期的田园诗人对人类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责任。有着“自然诗人”美誉的华兹华斯把田园诗歌推向了极致。在诗歌中,他总是把大自然视为他崇拜的老师,认为大自然是一种精神力量,使人变得善良和纯净;在他看来,自然“会用宁静和美打动”人们,自然“有一些力量能使我们的心受感染”,能“引导我们从欢乐走向欢乐”,雏菊能教会人“在困难时候不丧失希望”,水仙花能治愈创伤的心灵[5](P71-73)。他在诗歌《丁登寺》中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大自然对人的心灵感悟,以切身的体会惊叹大自然与人类心灵的相通之情。这里,诗人强调了自然生态对人类心灵的极大影响,再次印证了生态批评的观点:只有自然生态和谐,人类社会和精神生态才能和谐。另外,城市文明与田园生活的对立冲突也是这一时期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诗人们怀念牧歌世界的纯粹,感伤田园生活的逝去,质疑批判城市化、机械化、甚至整个现代文明,因为工业化的巨轮践踏了可爱的家乡,一切面目全非:牧场、草地、农田全都消失,到处机器轰鸣、烟囱林立,乡人的宁静心灵被打破,变得骚动不安、欲念横生。在华兹华斯眼中,城市是一潭“绝望的死水”,那里人们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纯真善良荡然无存,传达出对社会生态失衡的深深忧虑。威廉·布莱克在其《伦敦》一诗中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城市文明图景:行人“衰弱、痛苦的脸”、“婴孩害怕的号叫”、“扫烟囱孩子的喊叫”、“不幸士兵的长叹”、“年轻妓女的诅咒”,这一切都暗示出现代化的城市是龌龊的、肮脏的、令人窒息的,跟大自然比起来它就是人间的地狱[6](P64)。总之,诗人们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不可分离,强烈反对脱离自然、践踏自然的机械论自然观和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这无异证明他们已经加入到了生态批评的阵营中为生态的保护振臂高呼、摇旗呐喊。综上所述,浪漫主义时期田园诗歌的生态属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诗人们用充满想象、激情、近似颓废的激进方式高歌田园生活,并以此来逃避城市文明和理性文明,这使批评家质疑它们能否承担文学之生态批判的重任;在这些诗歌中,自然被简化歪曲、重塑成一位被动、驯服、人们可以随时隐退其中的地方,诗歌中也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自然简单,社会复杂,这是对自然歪曲化的理解。客观地来看,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浪漫主义时期田园诗歌的生态自觉意识还没有形成,而只有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批判才真正成为可能。
(三)20世纪的田园诗歌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摧毁了英国传统的乡村文明,打破了人民宁静祥和的乡村生活;20世纪四五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人类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社会满目疮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信仰迷失、人性异化。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希望逃避到传统的农耕文明以医治那饱受创伤的心灵,警醒的文人们也开始意识到挽救和守候传统的必要性,于是诗人再次创作出大量的田园佳作,为战后备受煎熬的人们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安慰。诗歌的主题多为对自然生态的忧虑、对工业文明的痛恨和蔑视、对人类世界异化和精神坍塌的担忧以及对战争的控诉。这个时期主要的田园诗人有D·H·劳伦斯、托马斯·哈代、爱德华·托马斯和R·S·托马斯等等。
作为一名自然诗人,劳伦斯在诗中盛赞原始生态的自然美景,赞美自然生命的神圣美好,痛斥人类的“铜臭气”,挞伐工业文明和机器文明对人类的异化,呼唤人类回归原始生态自然,崇尚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在他的众多生态主义诗歌中《鸟·兽·花》是控诉人的行为最直接最强烈的一部诗集,里面有一首诗《美洲豹》,主要表达的是人类对自然的侵害,里面有这样一段描写:
攀越着一月的雪地,
进入洛博峡谷,
针枞木逐渐变暗,
凤仙花慢慢变蓝,
溪水仍未冰封,
哗哗流淌,
小径依然明晰可辨[7](P330)。
自然是那么的原始、静谧、美丽、和谐,假如没有人,这个诗情画意的梦境将一如既往地延续。
人!
两个人!
人!世上令人惧怕的唯一动物[7](P330)!
人的出现使自然界的生灵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使它们经历了血淋淋的遭遇与死亡记忆。诗中还对比了美洲豹的优雅华美、与自然的融洽相处和人的心胸狭窄与卑劣行为,从而表现出对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蔑视,同时也揭示了诗人平等地看待自然界的一切生灵,人类并非是自然的统治者和占有者,而应该与其他自然生灵和谐相处、诗意栖居在地球上,劳伦斯的这种生态整体思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叛,这恰恰是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观。
与浪漫主义时期的田园诗不同,这一时期诗人的眼中,自然已不再那么美丽宜人、温情脉脉,相反自然是可怖的、阴郁的、残酷的、凄凉的。哈代便是这样一位现代主义田园诗人,他认为自然充斥着萧瑟和残酷:萧瑟的晚秋、凄凉的寒冬、枯萎的花朵、苍莽的天穹、被刺瞎的鸟儿和充满杀戮的密林等,所以评论界认为他的自然观延续了他一贯的悲观人生观。事实上,这些阴郁悲凉的诗行恰恰代表着哈代对自然生态的忧虑,对人类摧残自然的谴责。另外,哈代对摧残人类生命的战争深恶痛绝,因为战争破坏了人际关系的美好,摧残了人性的真善美,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残酷,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诗人以此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生态失衡的哀叹和惋惜。有一首诗《一次失约》(A Broken Appointment):
你没有来,
而时光却沙沙地流去,使我发呆。
倒不是惋惜失掉了相见的甜蜜,
是因为我由此看出你的天性 ……
当指盼的钟点敲过,
你没有来,
我感到悲哀
该诗表现出哈代的悲哀和消极的情绪,诗人用一句“我感到悲哀”表达了对人际关系缺乏诚实、坦诚和仁爱的失望情绪。在哈代看来,人对自然的掠夺不仅伤害了自然,同时也使人类社会原本的质朴与和谐荡然无存,这种观点符合生态理论“生态可以分成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方面,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观点。
这一时期杰出的田园诗人还有威尔士诗人爱德华·托马斯和R·S·托马斯,在诗歌中他们歌颂了英格兰美丽的乡村风光、恬静的农耕生活,表达了对机器文明的反感和对战争的诅咒;诗歌关注自然以及自然状态下人的生存,充分体现那个动荡的、颓废的时代给人类以及自然造成的创伤。R·S·托马斯以自己的家乡为背景,用写实的方法描述了威尔士自然环境下的禽鸟、花卉、山水以及那里人们淳朴宁静的生活方式,素描出一幅幅清新脱俗的威尔士风俗画。在《乡村》一诗中,他选取一个偏远、宁静的小乡村作为一个参照点来审视现代文明,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人类的本性不会改变,宁静和谐永远是人们向往的最高境界”[9](P213)。由此看出,作者认为远离现代文明的小乡村是现代社会永远无法摆脱的根,这是对碎心沉湎于现代物质追逐的人们一个适时的惊醒,无疑体现了生态诗歌“生态预警”的功能。
田园诗歌是人类追求淳朴生活、寄托人生理想的一种文学体裁,同时也是对技术文明征服自然的反动。英国田园诗歌源远流长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对三个不同时期田园诗歌的分析,可以发现田园诗歌的发展正好折射了英国乡村文明的发展进程:原始的农牧业——传统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并行的大农场经济;同时也随着人类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而愈发显现出其生机与活力[10](P206-209)。
通过对不同时期田园诗歌的生态批评解读,可以发现人们对生态的关注古已有之,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歌用怀旧、幻想甚至逃避的方式表达了朦胧的“回归”主题和朴素的生态意识;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们高歌田园生活,关注自然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展现城市文明与田园生活的强烈碰撞,生态意识显而易见,然而诗人对自然歪曲简单的理解并没有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预设;20世纪的田园诗歌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自然的理解更加客观甚至悲观,诗人更多的关注战争和工业化对人类心灵的异化,展现对精神生态的关注和忧思,诗歌中暗含着明显的生态思想,此时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批判成为可能。随着生态批评对田园诗歌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人类生态意识的不断曾强,田园交响曲必将成为人类构建和谐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主旋律。
[1]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56.
[2]姜士昌.欧洲田园诗歌溯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2):36-38.
[3]王佐良.英国诗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77.
[4]何功杰.英美名诗品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96.
[5]张宏峰.重返精神的伊甸园——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拯救观[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71-73.
[6]杨岂深,孙铢.英国文学选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64.
[7]Lawrence D.H.The Complete Poems of D.H.Lawrence[M].Wordsworth Edition Ltd.,2002:330.
[8]飞白,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312.
[9]刘守兰.英美名诗欣赏[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13.
[10]姜士昌.英国田园诗的传统及其嬗变[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1):206-209.
An Research on British Pastoral Poem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HAN Li-min1,LIANGLiao-dong2
(1.C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2.C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3,China)
British pastoral poems,as invaluable spiritual wealth in human civilization,are longstanding and well-established.However,for a long time they were regarded as negative,pessimistic and evasive literature,unable to enter critics’research focus,and accordingly research on them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far from sufficient.Through an overview of the whole British pastoral poems,it could be discovered that far-seeing,obvious natural and ecological senses or thoughts were expressed in many pastoral poems.Fortunately,the ecological criticism,coming into being in 1970s,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on pastoral poems.Therefore,this thesis will have an objective and overall analysis of pastoral poem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theory and digout the positive ecological thoughts and their narrow-minded and limited understanding on ecologyor nature as well.This thesis helps to build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it will also help to boost the multi-perspective and multi-layered research on pastoral poems.
ecological criticism;pastoral thoughts;ecological thoughts;limitation
I106.2
A
1007-9882(2012)04-0072-04
2012-05-25
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2SQRW073);安徽工程大学青年基金项目(2010Y Q025)
韩利敏(1982-),女,河南濮阳人,硕士,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梁晓冬(1961-),女,河南新乡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
[责任编辑:黄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