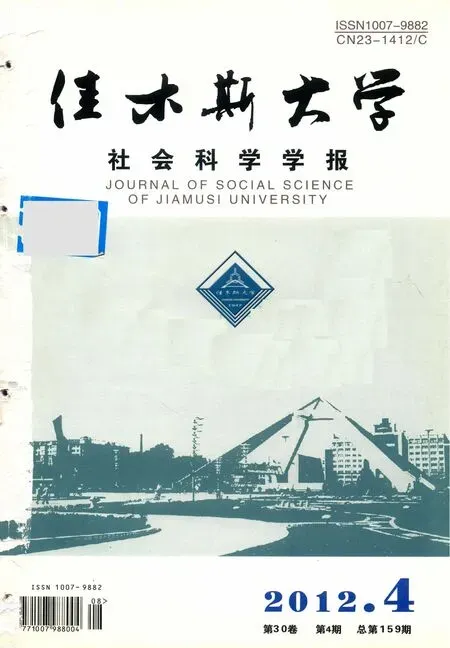试论意识形态理论功能①
黎 政
(喀什师范学院,法政系,新疆 喀什844000)
试论意识形态理论功能①
黎 政
(喀什师范学院,法政系,新疆 喀什844000)
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问世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对意识形态功能从不层面、深度、广度、空间、向度自圆其说,为意识形态提供了超前的施展空间,赋予了它崭新的活力。本文拟从对意识形态概念界定、功能整合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期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是我国的一元指导思想,坚决抵制西方腐朽意识形态侵蚀。
意识形态;理论功能;崭新活力;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论述。国内外学者都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轴心,兴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研究热潮,对意识形态功能从不同层面、深度、广度、空间、向度自圆其说,为意识形态提供了超前的施展空间,赋予了崭新的活力。本文拟从对意识形态概念界定、功能整合以及影响等方面进行探究,以期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始终是我国的一元指导思想,坚决抵制西方腐朽意识形态侵蚀。
一、意识形态概念界定
专家学者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为何热烈?意识形态到底有何秘密?有何重要意义?学术界众说纷纭,百花齐放,自圆其说。
(一)国外学者的界定
随着各种理论文献的丰富,意识形态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已经耳熟能详。前苏联学者统计,那时就有150多种,最早是法国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提出,他用“意识形态”表示观念的科学。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等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套连贯且成系统的信念”。[1]波兰学者M·杜勃罗西乐斯基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一种自我理解和自我表现形式。”[2]特定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认为:“意识形态是承诺要改变政治系统(古典保守主义似乎是个列外,他力图使系统不至于转变得太快)。”
(二)国内学者的界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者对意识形态的界定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特定的社会集团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要求的自我意识和自觉表达。”狭义指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思想体系,即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朱兆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以一定社会集团的礼仪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一定价值观为核心,以一定政治目标或社会理想为标示,以一定的话语系统表达出来并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确立起来的系统的思想观念。”[3]
因此,笔者以为意识形态与具体的历史时代有一致性,也离不了过去历史的积攒,包含哲学、理学、艺术、政治、社会等领域利益的思想、意识、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以及价值取向。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马克思早期对意识形态的论述主要是从批判意义上出发,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反杜林论》中。由于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把现实社会进行了颠倒和歪曲,为此马克思以贬义之意把它作为“神秘化”、“虚幻化”的化身。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随时代的不断变化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以至于不同于一般的意识形态。
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自觉地体现了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想观念体系,即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二、意识形态功能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4]刘英杰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而有意识制造出来的价值观念、信仰甚至空想、骗局,而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更广泛的内容,一切具有价值导向和控制功能、维护现实秩序、消解否定性向度的东西都被称为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消费方式、商品等都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5]
笔者以为,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每个阶级为达到自己的特殊利益都要把自己的观念、思想说成是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以及刘英杰所认为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而有意识制造出来的价值观念、信仰等等,无不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统治功能的高明所在。
(一)整合、调节、运用功效
任何一个阶级、阶层、社团、集体以及个人为了维护和加固自己意识形态,都把特殊利益说成是全民的普遍的合理又合法的利益,给意识形态披上一层华丽的外衣,把统治的面具扮演得一应俱全,就像一些学者把意识形态比作“水泥”作用,这里就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整合、调节、运用。
张骥 、程新英从意识形态的整合机制角度认为,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主客、内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键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内容结构与客观现实的契合程度……在整合机制与方式上要实现从简单语境中整合到复杂语境中整合、从强制压力型整合到说明感召型整合、从单一灌输式整合到多方式渗透型整合的转变。[6]张惠玲、张陟遥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和价值整合上认为,意识形态乃是信念的系统性丛结,它集合了众多思想家的精华,规定了理想秩序的见解,其作用是推广某种信念及行动纲领。[7]王蔚认为,二战之后国外一些政党意识形态出现了兼容化倾向,政党之间不再刻意宣扬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和对立。[8]魏崇辉认为,在政治实践中,意识形态总是试图发挥统一多元利益诉求,试图将各种利益、各个阶层、集团的思想统一起来,使得各个阶层和集团向其自身的意识形态靠拢。[9]
笔者以为,从各位学者所言以及结合历史的不断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意识形态昔日功效就遗忘在统治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等之间。如今,意识形态在批判的实践中会披上崭新的外装,这种整合、调节、运用功能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加发展。
(二)“分化”、“西化”、“淡化”功效
江泽民同志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国际敌对势力把中国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10]还指出:“所谓西化,就是企图在政治上用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用资本主义私有制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思想文化上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1]胡锦涛同志指出:“文化上,西方敌对势力四处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12]
笔者以为,西方国家推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蚕食、侵吞的政策,美国的“华盛顿共识”、“天赋使命”以及“救世精神”就是具体体现,这种意识形态所到之处,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比如,拉美地区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以及对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其实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惯用伎俩表现。
三、意识形态的影响
全球化的今天,意识形态这“冷战”形式日趋多样化、新颖化、时代化、普及化,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向东方推行“华盛顿共识”、“天赋使命”、“普世价值”以及“救世精神”等意识形态,扩大影响,美化自己,丑化他人,痴心妄想逐步取代其他意识形态,成为主宰世界的主流意识。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时指出,我们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精辟的话语告诫我们,对意识形态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忽视,这样的影响在国际国内有着深刻的教训。
(一)自由化思潮意识
自由化思潮正是意识形态的体现,它的发展直接冲击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正是西方自由化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泛滥蜕变的结果。
张骥 、张爱丽认为,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意识形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苏共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存在严重错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13]刘友田认为,尔巴乔夫要求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都要有“新思维”、“经济新思维”……“政治新思维”。其实质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多党制……在党的组织上实行全民党。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相背离。在实践中导致苏联共产党日益社会民主党化并由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自我降格为议会党.最终丧失政权。[14]邓小平同志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 ,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 。”由此可见,有些人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把人们的灵魂玷污,其实这是在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思想,站在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公然挑战立场上。
笔者以为,几位学者对苏联的解体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得出一致结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才能正确把握时代脉络,否则,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苏联的解体到1989年的北京风波,都是意识形态领域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所致。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5]
(二)网络意识形态
网络是本世纪以来意识形态传播最新、最快的途径: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物联网等,网络这虚拟的平台,看得见摸不着,对主流意识形态抑或非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抑或非马克思主义、统治阶级抑或非统治阶级、上流社会以或非上流社会以及不同阶层的人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但是所主宰网络意识形态的对象、主体不同,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
蒯正明、杨新宇认为,由于网络政治参与者的利益、立场、观念的差异……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借助网络不遗余力地推销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使得一些人的传统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对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功能、整合功能形成挑战。[16]杨静娴认为,网络的开放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优势,西方强势而又隐蔽的网络意识形态冲击着我国的价值领域,被误读或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借助于网络迅速传播并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网络聚焦的各种社会问题消解着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无疑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17]吴克明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直面网络文化,同时具备运用网络文化资源、主导网络文化舆论和应对网络意识形态挑战的能力,做到领导带头、求真务实领航网络文化。[18]
笔者以为,网络成为一种崭新的开放性的传播捷径,致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威胁,只有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引领下,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民主与法治相结合,充分发挥它的价值取向,才能为大众的、民主的、科学的、和谐的社会服务。
四、意识形态在我国
自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中国的发展前途。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数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以《新青年》为进步刊物,为工人开设补课班、夜校班、俱乐部,这就把中国工人阶级逐步结合起来了。
笔者以为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无产阶级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我们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思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指导,坚决抵制西方多元化思潮
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指导,是历史的选择与实践的呼唤,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是坚定不移地加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当今体现。
胡锦涛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教育科技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19]由此可知,我们必须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坚决果断地抵制和克服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侵蚀,强化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观,科学有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在我国的的主导地位。倘若实行思想上的多元指导,结果必定是社会政治动荡,思想大乱、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灾难很快就会降到人间,国将不国。
笔者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指导,正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论。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同志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指导必不可动摇,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摇社会主义基本的价值观念体系,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
(二)增强青少年意识形态责任感,正确驾驭文化“火车头”
毛泽东同志所言“青少年正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国家的栋梁。增强青少年意识形态的责任重于泰山,特别是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尤为巨大。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20]
邓志强认为,市场化对青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他们的经济意识增强了,但政治意识淡薄了,道德意识弱化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增强了,但集体主义观念淡化了;他们的竞争心态强化了,但投机心理增多了;他们的商品经济意识增强了,但拜金主义也开始盛行了。还指出,对青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就必须以青年为中心,密切关注其思想特点、心理特点、成长规律及变化趋势,关注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他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入手。[21]
笔者以为,青少年正是长知识、增见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思想更新最快时期,引导青少年正确驾驭文化“火车头”,让他们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熏陶下健康发展,坚决抵制不良意识形态的“分化”、“西化”、“淡化”,让青少年成为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意识形态日常生活化
在每天的生活中,人们必须应对天天发生的事情而过着自己的生活。尝尽各种酸甜苦辣,也有对美好憧憬的期盼。这就是他们的日常意识,也可称得上生活意识。因为日常意识的各个方面是分散流动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混杂无序的,这就成为日常意识的显著特征之一。诸如,烧饭、洗衣服、冲冲忙忙吃完早餐乘车上班、正在看电视时突然来电话告知某位亲戚病重等情形,都属于日常生活。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里指出,劳动是维持自己和家庭生活的手段,同时也是适应社会生产需要的活动,更是人们在体、智完美结合的唯一途径。劳动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意义是不一样的,是变化着的。因为劳动可以被剥削、可以被异化。比如,在封建社会,奴隶主和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意义就不一样。
人们的日常意识既有日常生活的规定而不能脱离,又因个人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第一,快乐志向的意识。这是一种视生活为快乐对象的意识,由于快乐和不快乐是个感觉问题,这和日常生活的“此处和此时”(“这里”和“这时”)的特性相适应,因时而异,往往不思考明天的事,而知向往刹那间的追求。比如,下棋对某些男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快乐,但对他们的妻子来说不见得是快乐;在休息日,她们读读侦探小说也许是最大的快乐。快乐内容千差万别,但都是对快乐需求的满足。第二,尊重劳动的快乐。这是在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价值意识。不管喜欢与否,将劳动作为优先价值来考虑的理由并不是难理解的,因为对多数人来说,劳动是维持生活的唯一手段,并且是老后的保障。因此,劳动是追求利益价值的一种方法。尽管劳动很辛苦,但它毕竟是沟通个人与社会的桥梁。因此,在一切社会都有日常生活,没有日常生活的社会是没有的。
(四)强化意识形态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观察社会,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形式和实现途径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持续探索的。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发展、升华,文化意识就在此题义之内。
罗甜田、邓淑华认为,既然先进文化建设是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前提条件,那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应是先进文化要提供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吸引力的贡献。[22]洪梅指出,意识形态是维持现存秩序的观念体系,而信仰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信仰与现实利益具有统一性,信仰牵导着现实利益的发展,现实利益的发展映照着信仰的价值,……可见,信仰的感召力无疑是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核心。[23]朱悦怡、樊宏法认为,在一个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对保持社会稳定,缓解社会矛盾,引导大众行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4]
为此,笔者以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蕴涵的文化意识和理念信仰正是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的独到之处所在,这高雅的意识形态使不同的民族从心底里认可、钦佩,还增强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自信心、自豪感。江泽民同志指出:“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认真、刻苦、全面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对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必须摆在学习的首位。全党政治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信念上的坚定,是全党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和具有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必须自觉地意识到两大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社会功效,只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才能更好地适应于并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1]杨海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4.
[2]M.杜勃罗西乐斯基.科学.意识形态.世界观[J].姜其煌,译.国外社会科学,1985,(3).
[3]朱兆中.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0.
[5]刘英杰.意识形态转型:从政治意识形态到科技意识形态[J].理论探讨,2007,(5).
[6]张骥 ,程新英.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回应[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2).
[7]张惠玲,张陟遥.论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J].重庆社会科学,2006,(11).
[8]王蔚.国外政党意识形态的兼容化倾向[J].科学杜会主义,2006,(3).
[9]魏崇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意识形态分析的可能路径[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11).
[1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
[1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73.
[12]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13]张骥.张爱丽.论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教训及其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8,(5).
[14]刘友田.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因及启示[J].高校理论战线,2010,(5).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5.
[16]蒯正明,杨新宇.网络政治参与对党执政的影响及其应对[J].理论探索,2010,(5).
[17]杨静娴.网络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及维护[J].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理论月刊,2011,(7).
[18]吴克明.网络文化视角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09,(1).
[19]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
[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6.
[21]邓志强.新时期青年意识形态教育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学报 ,2010,(4).
[22]罗甜田,邓淑华.从强化意识形态吸引力看中国先进文化建设[J].社会科学研究,2012,(2).
[23]洪梅.信仰感召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的核心[J].前沿,2011,(16).
[24]朱悦怡,樊宏法.“构建和谐社会”——意识形态整合的象征形式[J].社会主义研究,2007,(3).
B022
A
1007-9882(2012)04-0034-04
2012-06-12
黎政(1974-),男(土家族),新疆喀什师范学院法政系2010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陈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