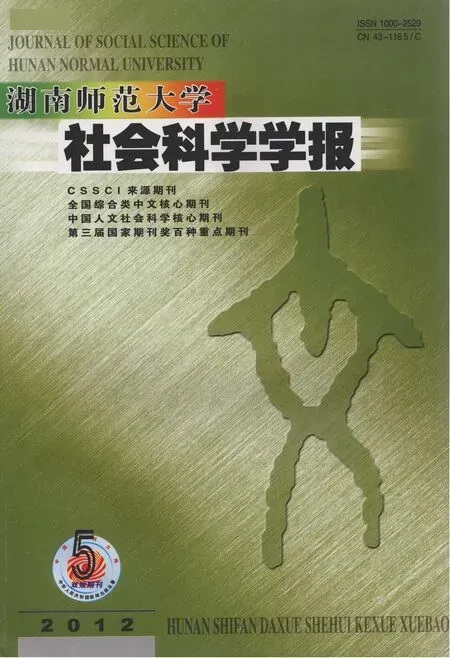休谟的怀疑论与知识的二重性
刘玉军,陈明益
休谟的怀疑论与知识的二重性
刘玉军,陈明益
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怀疑论本质上包含这样一个共同的观点:我们没有知识。同样,休谟的怀疑论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缺乏知识。但是,休谟虽然否认我们拥有排除怀疑的确定性意义上的知识,却并不否认我们拥有后来所称的“得到辩护的真实信念”这种意义的知识。休谟的知识观由此可以称作知识二重性论题。这种知识的区分虽然预示人们所熟悉的分析与综合的二分,但同时也暗示蒯因后来对这种区分的攻击以及这种二分的消解。
怀疑论;知识;分析/综合的区分
一、怀疑论的基本观点
从哲学史来看,怀疑论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哲学立场,并始终伴随着认识论的发展。古希腊时期,怀疑论哲学以皮罗(Pyrrhon)学说为代表,这种怀疑论主要是针对独断论而言的。独断论者相信自己发现真理,怀疑论者则认为真理是不可知的。按照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概述,怀疑论起因于获得“灵魂的安宁”,怀疑论者为事物中的各种矛盾所困惑,对二者择一加以接受产生怀疑,因而对事物的真假不做判断。皮罗说,“万物一致而不可分别。因此,我既不能从我们的感觉也不能从我们的意见来说事物是真的或假的。所以我们不应当相信它们,而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发表任何意见,不作任何判断,对任何一件事物都说,它既不不存在,也不存在,或者说,它既不存在也存在,或者说,它既不存在,也不不不存在”[1](177)。因此,皮罗主义的怀疑哲学可以称作一种过度的怀疑论或激进的怀疑论(radical scepticism),它主张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外在世界的可靠知识,因为我们和外在世界的接触只有感官这个唯一通道。如果知觉系统性地误导我们,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就都是假的。显然,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激进的怀疑论,也就意味着感官所提供的“资讯”是不可靠的,我们就无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近代哲学家笛卡尔提倡一种普遍的怀疑,他要求我们怀疑我们先前的一切意见和原则,还要求我们怀疑自己的各种官能。如果我们想要确信官能以及由这些官能得出的知识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必须根据一种没有错误和不受欺骗的原始原则来一丝不紊地推论出来。因此,笛卡尔实际上排除了激进的怀疑论立场,他相信有一种绝对确定的东西,基于这种绝对确定的基础,我们可以建立我们的知识,包括外在世界的可靠知识。这种确定的基点就是“我思”,或者说“怀疑”本身。换言之,“我思”或“我怀疑”本身是不能怀疑的。休谟区分了古希腊皮罗的激进怀疑论(Pyrrhonian scepticism)与温和的怀疑论(mitigated scepticism),以及前件怀疑论(anticedent scepticism)与后件怀疑论(consequent scepticism),但是他并没有给他自己的怀疑论观点提供任何明确暗示或论述。正如大卫·诺顿(David Norton)所言,“怀疑论这个术语,似乎意味着不同的事物。尽管休谟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还是很难说已经有多少种怀疑论被鉴别出来,其困难在于许多的范畴相互重叠”[2]。自休谟以后,怀疑论的种类不断增加。尽管如此,一般的观点都认为,怀疑论通常意味着否定我们人类拥有知识。例如,皮特·克莱恩(Peter Klein)将怀疑论概括为这样一种观点:我们缺少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同样认为休谟的怀疑论与知识有关。例如,摩尔(G.E.Moore)通过对休谟的怀疑论的细致研究发现休谟的怀疑论正是基于对“知识”概念的特定理解,这种理解“对什么成其为知识的标准限制过紧”才产生怀疑论[3]。也许,休谟主要不是在“我们缺乏知识”这个意义上来考虑怀疑论的,但是我们姑且认为休谟的怀疑论也可以被理解“我们缺乏知识”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在休谟那个时代,怀疑论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与知识的否定相联系的,而且休谟似乎也有某种知识的概念,他的论证意味着如果按照他所认为的知识的概念,那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知识的,也许在这种规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休谟被看作为一位怀疑论者。
二、休谟的怀疑论与确定性的知识
后世对休谟通常持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休谟主要是一位消极的思想家,因为他抽取了经验论的含义而发展了一种激进的、整体的(global)怀疑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休谟是一位积极的自然主义理论家,因为他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解决哲学问题当中去[4]。后一种观点,即将休谟看作一位积极的自然主义理论家的人们却面临着一个难题:休谟在其所有著作中的怀疑论证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该如何对休谟的这种怀疑论证作一番合适的定位?正如帕斯莫尔(Passmore)所言,“休谟的体系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建立在怀疑论基础上的科学”[2]。因此,不管任何人如何来解释休谟,他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怀疑论这种令人惊恐不安的立场。
既然怀疑论总是与知识相关,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休谟的怀疑论,我们必须理解休谟的知识观,也即在休谟看来,知识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性。休谟在《人性论》第一卷第三部分第一节“论知识”中谈到七种不同的哲学关系,分别是类似、同一、时空关系、数量或数的比例、任何性质的程度、相反和因果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完全决定于我们所比较的各个观念”,比如三角形的三个角等于两直角和的关系取决于我们的三角形观念(在欧几里得几何学范式内);另一类“可以不经过观念的任何变化而变化”,比如两物体间的接近和远隔关系可以依位置改变而变化,无需经过它们观念的变化。然而,休谟似乎将知识严格地限制于观念的关系。他说,“这七种关系中,只有四种完全决定于观念,能够成为知识和确实性(certainty)的对象。这四种是类似、相反、性质的程度和数量或数的比例。”[5](86)由此可见,休谟将知识与确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人类理解研究》中,休谟表达了类似观点:
人类理性或研究的一切对象可以自然分为两种:观念的关系(Relations of Ideas)和实际的事情(Matters of Fact)。属于第一类的,有几何、代数、三角诸科学;总而言之,任何断言凡有直觉的确定性或解证的确定性的,都属于前一种。‘直角三角形弦之方等于两边之方’这个命题,乃是表示这些形象间关系的一种命题。又如‘三乘五等于三十之一半’,也是表示这些数目间的一种关系。这类命题,我们之凭思想作用,就可以把它们发现出来,并不依据于在宇宙中任何地方存在的东西。自然中纵然没有一个圆或三角形,而欧几里得所解证出的真理也会永久保持其确实性和明白性。[6](26)
从休谟的有关知识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休谟像他的前辈或同时代人那样坚持认为知识要求确实性或确定性(certainty),因为确定性是局限于观念的关系范围内。在休谟看来,知识是产生于观念的比较(comparison of ideas)而获得的信据(assurance),而确定性则是一种排除怀疑的确信。在《人性论》中,“怀疑”和“不确定性”被交替使用,所以怀疑和不确定性是同义的。换言之,一个人能够确定p当且仅当他不能怀疑p。但是,尽管知识与确定性紧密相连,免于怀疑的确定性对于知识而言却是不足够的,因为确定性仅仅源于观念的比较,而S知道P当且仅当(1)S赞同P来源于观念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ideas);(2)S确信(is certain that)P。因此,要理解休谟的“知识”概念,我们必须理解他所谈论的“确定性”概念。实际上,确定性在休谟那里有两层意义。如我们刚才所言,一层意义是与怀疑相对立,也即真实的确定性是完全排除怀疑的确信,因为怀疑排除任何种类的确定性。另一层意义的确定性包含合理的怀疑度。休谟认为,一位公正的理性者(reasoner)在进行任何判断的过程中必须拥有一个人应当有的怀疑水准。具言之,在决定如何获取适当的确定性时,我们应该使我们的信念与所获得的证据相称,因为信念的证据有助于决定适当的怀疑水准。例如,哥德巴赫猜想必定为真或假。假定我证明了(affirm)哥德巴赫猜想,并进一步假设它为真,那么我可以说我肯定它为真,但理由不是由于我占有任何证据,而只是由于我的固执,我有一个不愿意放弃的肯定信念:它必定为真。然而,我不应该确信(be certain of)哥德巴赫猜想,或对其采取任何明确的立场,因为我对它的肯定或否定没有任何充足的理由或证据,一个公正的理性者对于哥德巴赫猜想至少应该保持某种程度的怀疑或不完全的确信。因此,我们应该明确某人提出一种知识理论与断言他拥有知识是不同的。依据休谟的理论,知识是限定于观念的关系,并要求一种确定性,而且这种确定性是不受公正的理性人所应具有的合理怀疑的影响。但是,当我们根据休谟的知识理论断言人们是否拥有知识或获得某种知识时,尽管我们也是在确定性的意义上来断定,这种确定性却是基于人们具有的信念与证据的相称性,因为理性的人们必须保持一种合理的怀疑度。
那么从真实的确定性的意义上讲,我们是否拥有知识呢?在《人性论》第一卷第四部分中,休谟谈到理性的怀疑主义:
一切理证性的科学(demonstrative sciences)中的规则都是确实的(certain)和无误的(infallible)。但是当我们应用它们的时候,我们那些易误的、不准确的官能(faculties)便很容易违背这些规则,而陷入错误当中。因此,我们在每一段推理中都必须形成一个新的判断,作为最初的判断或信念的检查或审核;而且我们必须扩大视野去检视我们的知性曾经欺骗过我们的一切例子的经过,并把这些例子和知性的证据是正确而真实的那些例子进行比较。我们的理性必须被视为一个原因,而真理为其自然的结果;但是理性是那样一个原因,它可以由于其他原因的侵入,由于我们心理能力的浮动不定,而往往可以遭到阻碍。这样,全部知识就降落为概然推断(probability)。随着我们所经验到的知性的真实或虚妄,随着问题的单纯或复杂,这种概然性也就有大有小。[5](206)
休谟认为,数学家无论进行多少次计算来核对结果,他们对结果的信心的增加不过是概然推断或概率(probability)的增加,这些计算过程并没有产生确定性的知识。因此,休谟将这种不确定性主张扩展至所有理证性的科学。由于这些理证性科学为知识提供唯一来源,所以人类研究所得出的一切结果都没有达到可靠知识的完美状态。换言之,由于知识是一种产生于观念的比较而得出的确定性,然而现在没有这样的确定性,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知识。那么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确定性呢?在休谟看来,确定性与不可错性或绝对可靠性相联系,也即绝对可靠性是确定性的标志,而可错性则是不确定性和怀疑的标志,所以说绝对可靠性暗含错误的不可能性。但是,这种不可能性既非逻辑的不可能性也非心理的不可能性,因为休谟论证所有判断(包括数学判断)都是不确定的,而他并非意味着1+1≠2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也非意味着人们对数学陈述的掌握是不可错的仅仅由于人们在心理上不可能不相信这个数学陈述。具体说来,如果知识p要求确定性,那么休谟要求的既不是非p的逻辑不可能性,也不是一个认知者抛弃p的心理不可能性,而是要求任何真实的或可靠的知识主张能够超越合理的怀疑,例如,我们能够合理坚持认为不可能理性地怀疑这种主张,因为不可错的或绝对可靠的知识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休谟也认为我们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理性地怀疑每一个主张,所以没有任何主张是确定的,我们缺少知识。正是从他否认我们拥有任何可靠知识的意义上说,休谟是一位整体怀疑论者。
休谟的怀疑论立场表明,有关观念的关系的任何陈述都要经受怀疑,一切思想或论证(包括经验证据)都要经受怀疑,所以“全部知识只是概然推断”,我们没有可靠知识。正如休谟所言,“知识与概然推断是极其相反而分歧的两种东西,它们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互相渗入,这是因为它们是完整而不能分割,而必然是完全存在,或是完全不存在的”[5](207)。也即是说,尽管我们有关于必然真理或观念的关系等信念,但是这些信念都是可错的。因此,知识与信念的本性完全不同。然而,如果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本性,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休谟所言的“知识降落为概然推断”呢?毕竟,知识转变成概率如同“鳄鱼变成金子”那样不可能,休谟的这种论证似乎与他自己的认识论相冲突。对此,大卫·欧文(David Owen)的解释是我们可以用某人有p的知识的可能信念来代替他有p的知识的主张,所以知识的主张嵌入到信念的主张(如概率判断)当中。但是,假如知识主张仍然体现在信念主张当中并保留知识的地位,那么就不是一种“降落”或“退化”(degeneration)。即便如此,由于休谟认为知识和概率是本性如此相反的东西,我们就很难理解知识主张如何体现于信念主张当中。[2]第三,休谟明确地说到“全部知识既然都归结为概然推断,而且最后变成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证据一样”[5](207),因此假若知识体现于信念主张中,那就破坏了知识主张以致它的本性发生改变。如此看来,休谟的本意应该是真的知识不可能“退化”为信念,然而我们当作知识的东西却能够“退化”为信念。根据休谟的标准,真的知识要求确定性,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是确定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知识。人们所认为确定的知识主张实际上是概率或信念,休谟检验所有这些声称是知识的例子(例如简单数学判断),发现它们都不能满足知识所要求的严格确定性标准。真的知识不能被怀疑,并就其本性而言与信念不相容,但所有声称为知识的主张都退化为信念,因为来自容易犯错的人类所声称的任何知识主张能够被怀疑,所以它们都不能满足知识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将休谟的论证解释为一种归谬论证。这种归谬论证如下:假定我们拥有知识,而知识要求确定性。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任何事物,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能够知道简单的数学真理,由此就可以得出这些所声称的(purported)的事例应该免于怀疑。但是休谟认为甚至所有这些简单的数学判断也要经受某种怀疑。如果它们免于怀疑,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由于以上所讨论的理由重新核对计算。因此,这些所声称为知识的范例既应该免于怀疑,也不应该免于怀疑。因此,我们有知识的这种假定就导致矛盾。
三、知识的二重性论题与分析—综合的二分
我们已经看到,休谟是一位知识的怀疑论者,正如他的先辈和他的同时代人那样理解知识,譬如唯理论者认为从自明的天赋观念出发经过理性演绎可以获得可靠知识,经验论者则强调从客观的感觉经验出发借助归纳推理才能获得可靠知识,这样的知识才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绝对确定性。休谟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信念(即使是关于简单计算的信念)是如此神圣而可以超越怀疑。因为真的知识排除怀疑,所以没有知识。然而,休谟似乎并不否认我们拥有知识,这就要从休谟所谈论的“确定性”意义上来看。从真实的确定性意义上说,我们没有知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确定性”还包含另外一层意义,也即合理的怀疑度。比如数学家们通过计算来核对他们的结果,他们可以增加计算次数,从而绝对地肯定他们的结果是正确的,这样看来,他们还是获得了一种确定性。这两种不同层次的确定性的确出现于休谟的论述当中,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就会误解休谟。休谟说过:“虽然在自然中从来没有一个圆或三角形,但是欧几里德证明的真理将永远保留它们的确定性”。这难道不与我们所读到的休谟否认一切事物(包括数学和几何学)的确定性相冲突吗?因此,我们认为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休谟使用这个术语由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当前观点”,并且他当然不是意味着它们在它们是确定知识的对象的意义上是“确定的”;其二,对于休谟来说,“确定性”和我们所理解的“概率”一样有相同的模糊性。他可能用另外的语言说,欧几里德的真理是“确定的”(例如,有1的客观概率)。在休谟谈论“关于理性的怀疑主义”中,我们看到:“在所有证明性科学中规则是确定的和绝对可靠的,但是当我们应用这些规则时,我们易错的和不确定的官能(uncertain faculties)非常容易背离它们,并陷入错误当中”[7](98)。我们注意到“确定的”的第一次使用是应用到规则自身。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说欧几里德证明的真理是确定的(必然为真),即使我们不应该说这些公理和定理都免于所有可能的怀疑。休谟在《人性论》第一卷的结尾处说道:
我们不但容易忘掉我们的怀疑主义,甚至也容易忘掉我们的谦逊,而应用这一类的词语,如显然、确实、不可否认的;我们对于公众如果存着适当的敬意,或许就应当避免这类词语。我也可能曾经照着别人的榜样陷入这种错误之中;不过在这里,我要申请大家不要再提出在这一方面所可以提出的任何驳斥,我在这里声明,这一类词语是由我对于对象的现前观点所逼出来的,并不意味着独断的精神,也不意味着对于我自己的判断的自负的看法;我非常清楚,这一类意见是不适合于任何人的,而对于一个怀疑主义者则更不合适。[5](305)
由此,我们可以说,休谟虽然在知识标准的意义上否认知识,却暗示了现在流行的“知识”定义: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实信念。正如杰塞菲·皮特(Joseph Pitt)所言,“看待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解释的发展的一种方式就是将其看做从一种更古老的、非常漫长的传统演化而来的(在这种传统中知识意味着确定性),并朝向一种更新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休谟的经验论相联系,即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实的信念”[2]。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休谟的怀疑论其实蕴含了一种知识二重性论题,也即知识包含确定性与或然性两个方面:我们没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我们拥有或然性知识(概率或信念)。这种知识的二重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是休谟依据确定性和可靠性标准来对知识的区分,“如果我们把确定性分层或弱化,原来不是知识而只是信念的命题就可能成为另一层次上的知识,这就直接影响我们对归纳结论的接受”[8]。因此,确定性的分层预示着知识的分层,休谟对归纳推理的质疑可以理解为归纳结论的确定性问题。换言之,归纳结论是否能够接受为知识,休谟问题因而可理解为知识接受问题,他的怀疑论也可进行知识论的解读。约翰·洛西认为,休谟将知识细分为关于观念关系的陈述与事实的陈述,这两种知识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对这两类陈述提出的真理要求的类型不同”:关于观念关系的陈述是必然真理,关于事实的陈述是偶然地真;另一方面,“用以确定两类陈述真假的方法不同”:观念关系陈述的真假无需诉诸经验证据,而关于事实陈述的真假必须诉诸经验证据。由此,“休谟达到了数学的必然陈述与经验科学的认识陈述的分界,从而加深了牛顿的形式演绎系统及其应用于经验之间的区别”[9](106-107)。然而,知识二重性论题并不意味着两种知识之间有着绝对明晰的分界。相反在休谟看来,知识与信念之间或者说关于观念关系的必然真理与关于事实陈述的偶然真理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甚或模糊的界线。休谟所言的“所有知识都退化为概率”(all knowledge degenerates into probability)正暗含了这一点。因此,即使休谟关于观念关系的知识与事实的知识的区分预示了后来的分析与综合的二分,它同样暗含着这种二分的消解。蒯因对分析/综合的区分的攻击是20世纪哲学史上的最著名事件之一。蒯因虽然赞成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纲领,但是他使用这个纲领中的一些经验论资源来破坏这个纲领的一个核心区分。按照凯文·米克尔(Kevin Meeker)的观点,根据蒯因自己对分析/综合的区分的理解,他明确承认他的攻击是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圣人”(patron saint)大卫·休谟那里继承了这种“同质性的破坏精神”(a kindred subversive spirit)。[10]休谟看到“知识退化为概率”的方式与蒯因看待“分析陈述退化为综合陈述”有很大相似性。当然我们不是在暗示休谟和蒯因都支持所有相同的论题。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蒯因总结了现代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二是“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的还原论。蒯因认为“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由此提出他的整体论思想。根据蒯因的整体论,“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有人甚至曾经提出把修正逻辑的排中律作为简化量子力学的方法,这样一种改变和开普勒之代替托勒密,爱因斯坦之代替牛顿,或者达尔文之代替亚里士多德的那种改变在原则上有什么不同呢?”[11](40-41)蒯因的整体观是说在分析陈述(定义性陈述或根据成分的意义为真的陈述)与综合陈述(根据事实为真的陈述)之间没有精确的划分线。这种区分崩溃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我们不能排除综合陈述可能转变为(overturn)分析陈述。具体而言,在蒯因看来,来自科学(物理学)的经验考量与一些分析陈述(诸如逻辑的排中律)的可接受性有关。休谟的观点很相似:观念的关系与事实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当然休谟可能保留了一种类似于分析/综合的区分。他可能在判断的“对象”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种区分:关于观念关系的判断是关于必然真理,而关于事实的判断则是关于偶然真理[12]。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事实可能使我们赞同观念的关系(甚至是简单的数学真理)的可接受性产生问题。简言之,休谟和蒯因都允许经验证据能够影响非经验的事实(如逻辑和数学)的可接受性。当然,蒯因并没有将他反对分析/综合区分的大多数例子建立在可错性问题上,相反他更多地依赖迪昂的考虑以及迪昂用来攻击这种区分的不确定性教条。但是,蒯因关于物理学修改逻辑的评论揭示出他的整个理论包括了允许经验考量能够影响分析陈述的可接受性,这是一种非常类似于休谟的结果。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Kevin Meeker.Hume On Knowledge,Certainty And Probability:Anticipating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nalytic/Synthetic Divide?[J].Pacif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7,(88):226-242.
[3]黄 敏.怀疑论、常识与实践[J].现代哲学,2007,(4):101-106.
[4]Francis W Dauer.Humean Natur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Induction[J].Ratio 2000,13(2):123-137.
[5]休 谟.人性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休 谟.人类理解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M].Oxford:Clarendon Press,1896.
[8]顿新国.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J].南京社会科学,2005,(6):16-21.
[9]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10]Kevin Meeker.Quine on Hume and the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J].Philosophia 2011(39):369-373.
[11]蒯 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2]伍远岳,郭元祥.论知识的个性化意义及其实现[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1,(1):56-59.
(责任编校:文 建)
Hume’s Scepticism and Dualism of Knowledge
LIU Yu-jun,CHEN Ming-yi
Various kinds of scepticism in history of philosophy essentially contain such a common view that we humans have no knowledge.Likewise,Hume’s scepticism can be understood as that we lack knowledge.Although Hume denied that we had the knowledge in the sense which contained certainty excluding skepticism,he didn’t deny that we had the knowledge that was justified true knowledge.We consider Hume’s view of knowledge as a thesis of knowledge dualism.The distinction of knowledge indicates the well-known 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 while it implies Quine’s assault on this distinction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is two distinction as well.
scepticism;knowledge;analytic/synthetic distinction
刘玉军,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4)陈明益,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