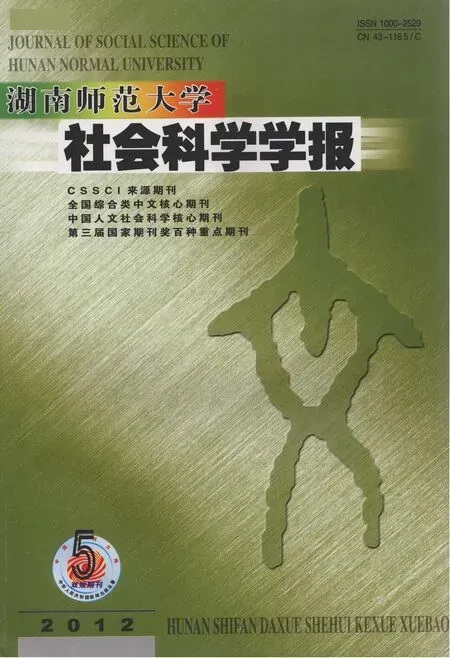农地抵押的法理考量
——超越物权法的思考
左平良
农地抵押的法理考量
——超越物权法的思考
左平良
我国农地抵押存在多元法理基础。不仅现行物权法的内在逻辑暗含了农地抵押的法理可行性,而且从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义务、农民金融权利发展的意义,以及农地抵押的利益性质等方面来看,农地抵押也存在法理基础。农地抵押的法理正当性,还要求国家仅在公益目的范围以及农地抵押市场调节失灵的情况下才能去干预农地抵押关系。
农地抵押;法理;社会保障;农民金融权利;国家干预
很少有学者从法理上对农地抵押进行系统的研究,不过,梳理有关农地抵押的研究成果,仍可从中发现学者们关于农地抵押法理思考的一些思想片段。如,梁慧星等认为农地是农民生产与生活的基础条件,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因而不能抵押[1](251);王利明等认为农地权利属于用益物权,赋予农地权利以抵押权能有利于发挥其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的价值[2](377);温世扬等认为农地抵押是一种比农地转让更为有限的处分行为,既然现行法律已经允许农地转让,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原则,自然应允许农地抵押[3](456);等等。上述研究从农地权利的功能、性质,以及物权法等的逻辑体系展开,总体上属于一种物权法视角的思维。由于研究的视角较为单一,有些观点仍然值得商榷。因此,关于农地抵押的法理考量需要更为宽广的视野。
一、从现行物权法的内在逻辑看农地抵押的法理基础
1.现行法上相关概念的发展暗含了农地抵押的法理可行性
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80条首次在民事基本法上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概念,并在性质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看待,从而模糊地肯定了农地权利的用益物权性质。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第2条和《土地管理法》第2条允许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处分权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从概念的种属关系上讲,农地权利属于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因此,“土地使用权转让”概念的提出,对于农地权利转让也应是适用的。1995年的《担保法》第34条提出了“荒地使用权抵押”的概念,首次在法律上肯定了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效力。从农地的分类上讲,“荒地”大致可以被理解为能够利用而未利用的农地,因此,“荒地使用权抵押”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农地权利权能扩张的又一进步。2002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同时采用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和“荒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概念,这是农地权利用益物权化的关键一步。因为,财产的转让与抵押是财产权利人将财产由低效率的利用方式向高效率的利用方式转换的先决条件,《农村土地承包法》上同时采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和“荒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概念,表明立法者已开始重视农地权利的用益物权性价值的发挥。2007年的《物权法》首次采用了“用益物权”这一概念,并在体例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重要类型予以规定,这一做法反映了我国农地权利立法与国际通行做法的正式接轨。至此,我国农地权利的用益物权化步伐可以说是基本完成。上述相关概念的发展表明,我国农地权利的用益物权化程度不断加深,农地权利的权能总体上处于一种不断扩张的状态,农地抵押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2.现行法律所确立的相关财产权原则给农地抵押留下了空间
从现行法的规定以及当下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思想意识形态整体上来看,给农地抵押留下空间的农民财产权原则大致可以归纳为:
(1)农地有效利用原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在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同时,也确立了农地的有效率利用原则。《物权法》在总则部分也规定,物权立法的宗旨之一就是“发挥物的效用”。这些规定强调要促进农地的有效率利用,而农地抵押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农地的资本化,这与农地的有效率利用是一致的,也符合建国以来农村土地政策要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要求[4]。
(2)土地物权平等保护原则 《物权法》第4条确立了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原则,即不因物权主体身份的不同而受到差别化的对待。这一原则的核心是物权本身的平等性,例如,同是土地物权,市民的土地物权与农民的土地物权的权能应该基本平等。根据这一原则,城市的土地使用权能够抵押,农民的土地权利也应能够抵押,特别是在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下更应如此。
(3)促进农民的平等发展原则 《物权法》第3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发展权利,这当然包括保障农民平等的发展权利。而农民的发展与其土地资源是否能够被激活又具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农民来讲,土地是其主要的生产资料,盘活有限的土地资源对于农民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允许农地抵押恰好是盘活农民土地资源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发展战略实施的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农民的财产权原则应有利于这一发展战略的实现,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对农民财产权的限制应尽量放宽,或者说,除非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一般不要对农民财产权进行限制。
3.现行法律禁止农地抵押的规定与有关农地处分规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承包法》允许农地转让却不允许农地抵押,在法理上讲不通。财产转让与财产抵押比较起来,财产转让是一种更为彻底的处分方式,因为财产转让会导致标的物在权利主体之间的转移,而财产抵押导致标的物的最终转移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因此,农地抵押在财产处分的力度上比农地转让要轻,根据“举重以明轻”原则,既然允许农地转让,自应允许农地抵押;二是《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允许债权性成分较重的荒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却不允许除荒地以外的物权性成分较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在法理上讲不通。《物权法》第133条规定了荒地承包经营权,《物权法》的这一规定似乎表明这种权利属于物权,但是,由于这种荒地的承包经营权主要是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取得的,其权利义务关系主要由承包合同约定,因此荒地的承包经营权仍具有较为浓厚的债权性质。从物权与债权的法理上讲,物权是一种支配权,即物权人享有依自己的意志对标的物直接进行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债权是一种请求权,即请求特定人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因此,通常来讲,物权性质的权利比债权性质的权利的处分效力更强。既然法律规定通过招标、拍卖取得的荒地的承包经营权这一债权性较重的农地权利可以抵押,自然更应该允许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物权性较重的农地权利可以抵押。
二、从农地权利与社会保障义务的关联性看农地抵押的法理基础
1.农地权利与社会保障义务并不具有内在的法理关联性
农地权利属于一种古老的物权形态,例如,罗马法上就有永佃(租)权的规定[5](414),我国宋代也存在比较发达的自由地权制度,不仅农地所有权可依时效取得[6],而且出现了永佃权的萌芽,明清时期,永佃权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华民国民法典》第842条则正式确认了永佃权,新中国成立后,农地权利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农地权利不断发展的结果来看,农地权利的物权化程度在不断加深,农地制度的利益取向越来越倾向于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有效利用。因此,虽然农地资源具有稀缺性,国家立法对农地权利的行使有一定的限制,农地权利具有一定的公法属性,但是,农地权利本质上仍属于一项私权,其行使具有自愿、平等、有偿的特点,其利益基础主要是农民私人利益保护理论。而社会保障义务属于新近发展起来的一种义务形态,它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老年和残障保险法》等社会保险立法,1935年美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1944年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费城宣言》正式使用社会保障概念,之后,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各国得到普遍的发展[7](13)。我国1986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作为高层次正式文件使用了社会保障概念,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3条首次在根本法上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关于社会保障的界定,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宣言》将其定义为“每个人为其自己及家庭健康与幸福,对于医食住医疗及其必需社会服务设施应有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而对于失业、疾病、残疾、寡居、老年等情况以及由个人不可抗力遭遇到生活危机,无法为生时,有权利获得保障”,我国学者一般将社会保障制度界定为“国家和社会按一定的立法对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特殊困难和意外灾害提供保障的福利制度。”[8](1474)从上述相关规定与学理界定来看,社会保障本质上属于一项公法上的国家和社会对全体公民的义务,即社会保障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和社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社会保障的义务主体包括国家/政府、企业等用人单位、工会等社会组织[9](37),社会保障的权利主体则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社会保障义务具有普遍性、强制性,其理论基础在于社会利益平衡理论。因此,从法理上讲,农地权利与社会保障义务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
2.不能将农地权利的社会保障替代功能事实状态混同于法律义务
农地权利的社会保障替代功能与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义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农地权利的社会保障替代功能是一种事实状态,而农村社会保障义务则是一种法律义务,即国家立法所确认的国家和社会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义务,不能将这种事实状态混同于法律义务。事实上,我国农地权利上的社会保障替代功能事实状态的形成,恰恰是农村社会保障的国家和社会法律义务虚置的结果。长期以来,在城市和工业优先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国家和社会仅仅只是注重对城市市民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社会保险、就业和福利待遇,而没有承担起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义务,正是在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农地才不得不充当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工具[10]。因此,农地权利的社会保障功能事实上是一种替代功能。即使如此,农地权利的社会保障替代功能也只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现象,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这一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对农村的社会保障供给将不断完善,事实上,2004年以来,随着农业税的废除,以及各种农业补贴、合作医疗、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和保障制度的实施,农地的生活保障功能正在日益弱化。而国家与社会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义务则具有终极性,不管社会经济发展到何种程度,国家与社会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义务都不会消灭。因此,不能借口农地权利具有暂时的社会保障替代功能而强化农地权利与社会保障法律义务的联系,否则,对农地的社会保障替代功能强调得过分,无异于否认国家和社会对农民社会保障所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这对农民是不公平的。
3.农地抵押与农地承担社会保障功能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
认为农地抵押会导致农民生活不安定继而引发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观点,不仅得不到经验证据的支持,而且从理论上讲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
一方面,农民作为一般经济人的理性,以及农地抵押契约双方行为的性质,使得农地抵押绝不会像有学者所担心的那样轻易发生[11](65)。农民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主体,具有起码的经济理性,那种担心农民缺乏经济理性的认识是对农民的不信任,从信息的拥有量来说,至少农民比政府更懂得权衡农地抵押的风险与收益,因此,允许农地抵押并不等于农民会轻易去抵押土地。而且,农地抵押行为是一种农民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双方契约行为,农地抵押契约的缔结必然经历一个农民与金融机构讨价还价的过程,即使农民有抵押土地的冲动,这一冲动也会受到金融机构行为理性的制约,因此,农地抵押的发生也绝对不会是农民冲动的结果。
另一方面,一般而言,农地权利权能的多少与农地价值的关系是一种正比例的关系,即农地权利的权能越充分,农地的价值越高,反之,农地权利的权能越受限制,农地的价值就越低。因此,允许农地抵押,有利于提升农地的价值,相应地,农地对农民的保障能力也会提高。例如,调查发现,在武汉试行农地抵押的农村,由于投资人增多,农地转让方选择的机会也增多,农村产权价值得到提升,目前武汉土地流转价格比一年前提高近20%,农民成为最大受益者[12]。反之,如果农地不能抵押,农民因为资金问题难以对土地进行深度利用,农地的使用价值难以提升,而且,因为农地不能抵押,交易对象对农地价值的预期较低,以农地为交易对象的其他交易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从而使农地的交换价值也会越来越低。因此,禁止农地抵押,反而会弱化农地对于农民的保障能力。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某位农民不幸得了大病,需要做手术,他丝毫指望不上他的承包地和宅基地。”[13]因此,所谓农地抵押会削弱农地对农民的保障能力因而应禁止农地抵押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三、从农地抵押对于农民金融权利发展的意义看农地抵押的法理基础
1.农地金融权是农民自古以来就享有的一种金融权利
一般认为,农地金融是一种古老的金融形态。例如,在古希腊、古罗马就存在比较初级的农地金融形态[5](427),相关的金融史著作也反映,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农地金融的发生也较普遍[14](190)。我国在唐代时开始出现农地金融形态,其时,法律允许农地抵押,办理农地抵押贷款的机构是一种具有独立贷款资质的质库,宋代王安石制定的《市易法》反映了国家提供农地抵押贷款的情况,明清时期钱庄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农地抵押贷款也是钱庄贷款的一种形式[15](21)。农地金融的普遍发生,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农业社会,农地是一种重要的资产形态,人们出于养老、荫后以及娱乐等各种目的竞相投资农地[14](190),金融机构也乐于接受农地作为抵押的标的物,因而农地金融成为农业社会的重要金融形态;另一方面,农地金融的普遍发生,也是农地与金融自然结合的结果。农地的保值增值功能与金融的风险防范要求,使得农地与金融具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国家对农地用途的限制,农地的价值大大降低,比起工业厂房和城市土地来,农地作为抵押的标的物已不再为金融机构所青睐。但是,农地金融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获得了新的形式,例如,鉴于商业性的农地金融难以为金融机构所接受,德国、美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允许商业性农地金融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又通过立法赋予农地金融更多的政策成分。如德国1949年的《农业地产抵押银行法》(该法2003年进行了修改)、美国1934年的《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法》、日本1951年的《农林中央公库法》等的颁布,使农地金融获得了新的形式的发展。因此,从上述农地金融的历史及其发展来看,农地金融始终存在,农地金融权是农民自古以来就享有的一种金融权利。
2.农地金融权对于促进农民发展的独立意义
近代以来,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民的弱势,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农民难以获得必要的金融服务的现象,这严重妨碍了农民的发展。在农民及其代言人的抗争下,20世纪以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通过立法承认农民享有合作金融以及政策金融的权利。如德国、美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以后都开始通过立法大力发展农民合作金融与政策金融。然而,农地金融权仍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是因为:
一方面,发展权的普适性以及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使得促进农民发展的义务越来越变成向农民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的义务。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宣言》第8条规定“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公民平等发展的权利。”这一规定使得实现农民的平等发展成为缔约各国的共同义务。在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的今天,这一义务又表现为向农民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的义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大力发展农民合作金融与政策金融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农地金融的积极意义。
另一方面,农民合作金融与政策金融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农地金融恰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局限性。例如,农民合作金融属于一种农民组织内部的金融,这种金融主要是与小额金融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政策金融因为对财政的依赖度大,也难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要克服这些局限性,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就需要肯定商业性的金融服务对于农民发展的意义。鉴于商业性的金融服务又总是与农民能够提供有效的担保物联系在一起,发展商业金融就需要允许作为农民主要财产的农地抵押,这进一步说明了农地金融权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
3.农地金融权应成为我国农民金融权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农村金融主要表现为有限的国家金融,农村金融的国家供给以及政府干预色彩严重,农民的金融权利发育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多种经营发展的需要和农民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农民的金融权利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1983年与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农村信用社应坚持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从而模糊地肯定了农民的合作金融权利;1986年的《民法通则》赋予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法律地位,农民自此获得了法律上的市场主体资格,与此同时,农村金融的商业化改革也开始起步,农民开始以自己的身份缔结金融服务契约,这是农民商业性金融权利的初步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针对贫困人群出台了金融扶贫政策,《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出台以后,国家针对贫困农户的金融扶贫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大,这可以看成是农民政策性金融权利的初步发育。然而,我国农民合作金融权利、政策金融权利在经历初步发育以后,一度出现了停滞发展的状态,可以说,自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出台以后,我国农村的金融供给出现了泛商业化的趋势,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例如,农民信用合作社与农民合作银行往往是有合作之名而无合作之实,而唯一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也在经营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偏离了政策金融的目标[16](14)。由于商业金融对担保的内在要求和法律规定,商业金融发展的前提是市场能够提供数量足够、价值合适的有效担保物,没有担保物或者担保物的价值不足,都会影响到商业性金融服务的提供。然而,我国立法将农民的主要不动产——房屋与土地都排除在担保物以外,这使得农民能够提供的有效担保物严重不足,尽管《物权法》第180条对担保物的范围有所扩大,例如允许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动产可以抵押,但是,调查发现,这些动产在金融机构眼里是很难成为有效的抵押物的。笔者2011年暑假期间对岳阳县农业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调查时发现,除了大型机械设备以外,动产抵押基本上不为金融机构所接受。由于有效担保物严重不足,农民难以获得金融服务。因此,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矛盾除了农民合作金融与农民政策金融的发展不能满足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以外,还表现为农村金融的泛商业化与农民不能提供有效担保物的矛盾。因此,解决有效担保物的不足已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考虑到农地在农民的财产权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允许农地抵押已成当务之急,试想,如果农民的土地不能抵押,农民还有什么财产值得抵押呢?这一矛盾的有效解决需要从立法上确立农民享有农地金融权,这种权利与农民合作金融权、农民政策金融权一道是构成农民金融权利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
四、从国家干预农地抵押关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看农地抵押的法理基础
1.农地抵押关系的私人性质本质上排斥国家的干预
从我国现行法的农地权利结构及其所反映的利益关系性质来看,农地抵押关系本质上属于一种私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主要应由市场去调节,农地抵押规范主要应是任意性规范而不是强行性规范。在我国,除少量农地属于国家所有以外,绝大部分农地属于各级农民集体组织所有,因此,农地权利结构主要呈现为农民集体享有土地所有权与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农地抵押关系人是农民、农民集体组织与金融机构,国家无法以土地私权主体的身份介入到农地抵押关系中。国家介入农地抵押关系的唯一理由是这种农地抵押关系已经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例如在涉及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等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国家才能以公权主体的身份介入农地抵押关系中,除此以外,国家是没有理由干预农地抵押关系的。正因如此,近代各国物权立法是严格限制国家随意干预农地抵押关系的。既然农地抵押关系主要是一种私的利益关系,国家立法就不宜直接禁止农地抵押,而是应该将农地抵押关系交由市场调节去解决,否则,就可能导致国家公权对私权关系的过分干预。
2.国家仅在公益目的范围以及市场调节失灵的情况下干预农地抵押关系
由于农地本身的特殊性,农地抵押关系并非一种纯粹的私人利益关系,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这是国家干预农地抵押关系的基础。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17],国家对农地抵押关系的干预也应仅是补充性的,即国家的调节仅在于补充市场调节的不足。
在我国,农地承载了太多的功能与负担。对于绝大多数农民而言,农地既是他们的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而言,农地是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方面的主要物质载体,对于国家而言,农地承载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不同主体在农地上的利益交织,使得农地具有多重属性,即农地不仅具有私益性,还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农地的公益性决定了农地抵押关系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这是国家干预农地抵押关系的基础。
但是,国家干预农地抵押关系毕竟只是补充市场调节的不足,因此,需要考察农地抵押的市场失灵情况。由于受到农地规模等自然禀赋条件、交易成本,以及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等市场经济条件的影响,即使像德、美、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农地抵押市场调节失灵的现象,这主要表现为农地抵押不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所看好,农民通过农地抵押获得商业性金融服务仍存在不少障碍。在我国,由于土地产权限制、农村金融信息不对称、农村金融中介市场发育不足等问题的存在,农地抵押市场失灵的情况更为严重。从我国东、中、西部农地抵押试点实践来看,许多地方的农地抵押并未能取得实际的效果,例如在湖南长株潭地区,2009年政府即出台政策允许进行农地抵押试点,但至今仅有株洲的天元区开展过几笔农地抵押贷款业务,多数地方的金融机构仍不愿接受农地抵押,因此农地抵押试点并没有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为解决农地抵押的市场失灵问题,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通过立法对农地抵押关系进行有限度的干预,国家干预的领域主要限于中长期农地抵押贷款业务,对于短期农地抵押贷款业务仍交由市场去调节,国家干预的方式也主要表现为财政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如由财政提供初始资金设立农地抵押贷款机构,待其经营稳定后再行退出;为农地抵押贷款机构发行债券提供担保;对农地抵押贷款带来的经营损失提供有限度的利息与亏损补贴等。我国农地抵押立法也应将商业性农地抵押与政策性农地抵押区分开来,商业性农地抵押是基础,政策性农地抵押一般应限于农业中长期低息贷款领域,商业性农地抵押由市场调节,政策性农地抵押由政府调节,并且在调节的具体方式上也应采用财政与市场相结合的做法。
五、结 论
从上述农地抵押相关法理考量来看,农地抵押的法理基础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结构,不能单从物权法的视角去狭隘地看待农地抵押的法理问题,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义务、农民金融权利发展的意义、农地抵押所涉及的利益关系性质,以及农地抵押市场调节的失灵等问题都是农地抵押法理考量所不能忽视的。总的来讲,在我国,农地抵押具有多元法理基础,即不仅从物权法的内在逻辑体系,还是从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义务、农民金融权利发展的意义,以及农地抵押的利益性质等方面来看,农地抵押都存在法理基础,因此,我国立法应允许农地抵押。当然,我国立法应将商业性农地抵押业务与政策性农地抵押业务区别对待,国家仅在公益目的范围以及农地抵押市场调节失灵的情况下才能去干预农地抵押关系,否则,国家对农地抵押关系的干预就可能失去法理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1]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温世扬,廖焕国.物权法通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4]胡 穗.论中国共产党制定农村土地政策的历史经验[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12-15.
[5]周 枏.罗马法原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6]陈秋云.宋代自由地权法制的历史意义与当代启示[J].法商研究,2011,(2):154-160.
[7]陈信勇.社会保障法原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8]夏征农.辞海“社会保障制度”词条[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9]周宝妹.社会保障法主体研究——以利益平衡理论为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赖华子,詹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社会保障性初探[J].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06,(1):25-27.
[11]孟勤国.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2]田豆豆.武汉启动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试行1年贷款过亿[EB/OL].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27149 87.html,2010-9-14.
[13]李成贵.国家与农民:关键在于权利[N].南方周末,2009-8-27(C19).
[14][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第2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15]袁远福.中国金融简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16]白钦先,李钧.中国农村金融“三元结构”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17]周作翰,张英洪.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农民权益保护[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2):5-11.
The Legal Considerations to the Farmland Mortgage——Beyo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ality of Laws
ZUO Ping-liang
The farmland mortgage in China has multiple legal bases.Not only the internal logic of property laws impl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farmland mortgage,but also the farmland mortgage has the legal basis views from the social security obligations of farmers,th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ing financial rights of farmers and the interest nature of farmland mortgage.Moreover,the legal justify also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the farmland mortgage only on the the purpose of public welfare or under circumstances of the failure of farmland mortgage market.
左平良,中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理工学院政法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3)
(责任编校:文 泉)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农地融资立法研究”(08JC820014);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农民金融发展权”(11YBA147)
The key words:farmland mortgage;legal theory;social security;financial rights of farmer;government inter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