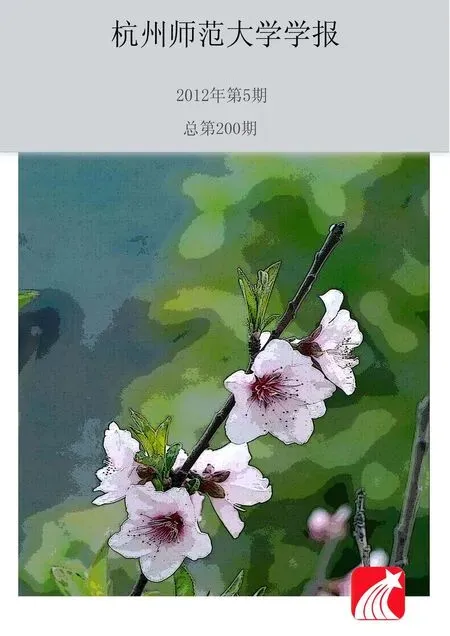主体与社会理论:马克思与卢卡奇论黑格尔
[美]Moishe Postone著,任致均译
(1.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美国 芝加哥;2.渥太华大学 历史系,加拿大 渥太华)
学术访谈海外及港台学者访谈之五
主体与社会理论:马克思与卢卡奇论黑格尔
[美]Moishe Postone1著,任致均2译
(1.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美国 芝加哥;2.渥太华大学 历史系,加拿大 渥太华)
通过勾勒卢卡奇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不同阐释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资本主义里的劳动是历史特定的,他试图阐明一种特殊的准客观的社会媒介与财富(价值)形式。这种形式架构了资本主义当中的生产过程,并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性进程。因此,劳动和生产过程,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当中剥离出来,也不能与之对立,而是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这一分析,允许我们把资本理解为社会构成的核心,并将之与诸多表面构型剥离开来。
卢卡奇;黑格尔;马克思;劳动;资本主义
要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主体与批判社会理论的问题,就绕不过卓越的卢卡奇。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写就于俄国革命的余绪之中。在这本书里,通过重新强调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层面,卢卡奇完成了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根本上的理论决裂。在此基础上,他批评了科学主义与线性历史进程,认为这些观点是社会民主的深层理论基础,在世界历史当中,它们既无法在1914年阻止战争的发生,也没能在1918-1919年带来激进的历史性转变。
通过理解黑格尔,卢卡奇把主体性问题及实践的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由此扩展并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他把马克思的批判理解为实践的辩证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意识的理论。这完全不同于第二国际机械而简化的马克思主义。
然而,即使有卢卡奇强有力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当中的黑格尔与黑格尔转向仍然不免于受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强烈批评。对于后者来说, 诸如整体性和历史主体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是反解放的支配概念。尽管如此,近几十年间的全球性历史转变——包括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出现——强调了历史进程问题的重要性;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却无法恰当地解释这些历史进程问题。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简要描述这样一种对马克思的理解,它既受惠于卢卡奇,同时又试图超越黑格尔与反黑格尔批判取向的对立。我将指出,马克思的成熟理论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有别于卢卡奇所描述的那样。当然,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性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批判的基础,它既批判了卢卡奇与后结构主义的短处,又吸收了二者的长处。
一
卢卡奇的实践理论并没有把马克思成熟理论中诸如“商品”这样的范畴简单地当作经济范畴来加以把握,这一点在他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尤其明确。相反,卢卡奇把这些范畴解释为现代社会生活主体与客体层面的决定因素。*由此,卢卡奇批评了思斯特·布洛赫,因为后者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仅是对经济的批判(而非对定义了真实人类生活的形式系统的分析),并由此将宗教乌托帮作为其补充。主体与客体层面是内在地交互关联的,卢卡奇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精巧完善的关于意识与知识的社会理论,并由此展开对笛卡尔哲学、对主客体二元论的根本性批判。他的实践理论声称,主体既造就了这一辩证过程,又是这一辩证过程的产物。其结果是:
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这不是说它们是互相“符合”,互相“反映”,他们是互相“平行”或互相“叠合”的(所有这些说法都以隐蔽的形式包含着僵硬的二重性的思想)。它们的同一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现实的和历史的辩证过程中的环节。[1](P.229)
在卢卡奇范畴性分析的框架之内,“在这种生成之中,意识就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的组成部分”。
在意识与历史的交互关联性分析中,卢卡奇的首要关切就是勾勒出革命阶级意识的历史可能性。同时,他展现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社会性、历史性的精妙分析。在卢卡奇看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试图对生活之特殊抽象形式所造成的问题展开攻势,而此种抽象形式正是资本主义背景之特征。同时,这种思想又受到资本主义环境直接的外在表现的限制。因此,它错把特定语境下所生成的问题当作是超历史的、本体论的。在卢卡奇看来,正是马克思首先恰当地应对了现代哲学所纠缠的问题。他更改了提问的方式,将它们历史性地置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之下,而这种社会形式,正是由诸如“商品”这样的范畴来加以表达的。
恢复这一分析模式之后,卢卡奇提供了一个针对现代哲学、社会学思想的社会性、历史性分析。尤为显著的是,卢卡奇的分析,其首要的考量并非阶级利益。卢卡奇并没有聚焦于诸如在阶级统治这样的社会统治系统之中思想的功用,相反,他把思想的本质置于构成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形式中,而商品就是这样的社会形式。
通过把生活的社会层面与文化层面内在地连接起来,这一对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的阐释,决定性地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概念分道扬镳。经济基础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二元的——经济基础被理解为最根本的社会客体,而上层结构被看作是社会主体。卢卡奇的方式与另一位伟大的实践理论家葛兰西也有所不同,卢卡奇把思想形式与社会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而不是把二者的关系当作是外在的或是功能主义的。它不仅阐明了这些形式的霸权功用,同时描绘了一种历史特定的主体性形式,在这样一种总体框架之中,与阶级相关联的差异发生了。换言之,卢卡奇的方式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形式的性质提供了一个起点。
卢卡奇在他的《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提供了一个精密的主体性历史理论之基础,此外,他还将批判资本主义的聚焦点转移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之重要特征上来。他对马克思的范畴的解读,远远超出了传统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与私有财产的分析,而把韦伯所强调的理性化与科层化过程视为问题的中心,并且把这些过程置于马克思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构造形式的商品的分析之中。卢卡奇认为,塑造了现代制度的理性化与量化过程正是根植于商品形式当中的。与马克思如出一辙的是,他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特征归结为人类受时间支配,同时把工厂看作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构造的浓缩形式。这一构造同时体现了现代科层的本质。通过把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置于马克思的范畴之内,卢卡奇试图阐明,韦伯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生活的“铁笼”正是资本主义的结果之一,因此它是可以转变的。
卢卡奇论物化的文章证明了一个以范畴为基础的批判理论的力量与严谨,这一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既是关于文化、意识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的理论,又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的批判扩展到阶级支配与剥削这样的问题之外:理性化与量化的过程、权力的抽象模式、无法被理解为具体的个人或群体统治的统治形式,卢卡奇的批判理论所寻求的是对这一切加以批判性的理解和社会性的认识。 在卢卡奇的分析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比传统所理解的以私有财产和市场为基础的剥削框架更为深远宽广。也即,他的概念意味着,私有财产和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另一方面,卢卡奇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概念的严谨性,这种严谨性为大多数现代性的讨论所忽略。它指出“现代社会”一词基本上是对一种社会生活形式的描绘,严格说来,这种社会生活形式更应当被当作资本主义来加以分析。
然而,尽管卢卡奇给资本主义的批判带来了深度,他却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所完成的显著的理论转向的中心层面,因而没能意识到马克思描述的范畴性批判的希望。其结果是,尽管卢卡奇的方式展示了一种在根本层次上比传统马克思主义更为丰富而恰当的资本主义批判,但他最终仍然局限于这一理论的根本前提。这弱化了卢卡奇为20世纪打造一个恰当而根本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所做的尝试。
二
为了展开上述论点,我将扼要概述卢卡奇对黑格尔的理解和马克思成熟期作品当中对黑格尔的理解,我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众所周知,黑格尔试图超越并克服传统理论当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他认为,自然现实与社会现实,主观现实与客观现实,都是由实践——精神的客观化实践,世界历史的主体——构成的。通过外在化的过程,精神构成了现实,在这一过程当中,它反身性地构成了它自己。只要客体性与主体性二者都是在精神的辩证展开之中构成的,它们就都属于同一个实体。二者都是一个本质上同质的普遍整体的瞬间,这一普遍整体就是整体性。
对黑格尔来说,精神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它是同一的主客体,是同时作为主体的实体:“而且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2]
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把黑格尔的精神这一概念加以人类学意义上的转译,他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历史进程中的主客同一体,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通过自身的劳动,构成了社会世界及其本身。与此相关的是,卢卡奇把社会当作一个由劳动构成的整体性来分析。在传统意义上,劳动被理解为一种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媒介的社会活动。在卢卡奇看来,整体性的存在被分裂而又特殊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所遮蔽。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秩序,无产阶级将会成为历史主体;它所构成的整体性将实现自身。因此,整体性与劳动提供了卢卡奇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出发点。
卢卡奇对范畴的阐释以及他对黑格尔的理解,尤其是他把无产阶级与主客同一体等同视之,以及他对整体性的肯定,常常被看作是马克思自己的观点。但细读《资本论》可以发现,马克思成熟期作品中对黑格尔的解释与卢卡奇根本不同。这也表明,马克思与卢卡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是大相径庭的。
《资本论》一开篇,马克思就把价值称为一种“实体”[3](P.51),视之为抽象的人类劳动。马克思不再像早期著作那样,把“实体”简单地当作理论的现实化,而是把它理解为价值的属性之一,也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特殊的、以劳动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实体”是既定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表达。在《资本论》中,他通过逻辑性地展开引致社会关系之复杂结构的商品与货币形式,而考察了社会现实。起初,马克思用价值来决定资本,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价值。截至目前的阐释当中,马克思对“资本”这一范畴的表述,显然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相关联:
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从而变成一个自动的主体。……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交替采取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自行增殖着。……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3](P.176)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清楚无误地把资本的特征归结为自行运动的实体,也就是主体。通过此种方式,他含蓄地暗示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体确实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内。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并不把主体看作是任何一个譬如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群体,也不是人类。相反,马克思对历史主体的理解,所依据的正是由资本范畴表达的客观化实践所组成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以资本范畴为依据的对历史主体的阐释,揭示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是非常特殊的,这种社会关系也包含了黑格尔赋予精神的属性。这也指明了,要想恰当理解位于马克思批判之中心的根本社会关系,只看阶级关系是不够的,而需要从诸如商品和资本这样的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媒介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主体正与黑格尔的主体相同:它是抽象的,不等同于任何一个社会行动者,它时间性地展开,独立于意志之外。
作为主体的资本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在黑格尔这里,主体是超历史且全知全能的;而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主体是被历史所决定、所遮蔽的。资本,一方面它本身是由实践的既定形式组成的结构,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实践的形式与主体性的组成部分。作为自反性的社会形式,它有可能召唤出自我意识。但与黑格尔的精神不同的是,它并不具备自我意识。换言之,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主体性与社会-历史主体必须区别对待。
马克思把主客同一体与社会关系的既定形式等同起来,这对于主体性的理论是极其重要的。在认识论层面上,原来的个人主体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这里被重塑为社会媒介的形式(由实践构成的)问题,它被看作是社会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决定因素。知识的问题成为了社会媒介决定形式的主体层面的问题。
这一对《资本论》的解读借用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的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等范畴的理解。然而必须同时指出,这些范畴的意义与卢卡奇赋予它们的意义并不相同。卢卡奇间接地把劳动(泛指的、超历史地理解的劳动)当作是主体的组成物质,而主体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阻碍而无法实现自我。卢卡奇的历史主体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主体的集体形式,通过“劳动”构成了自身与外在世界。也就是说,“劳动”的概念与资产阶级主体(无论是当作个人还是整个阶级来加以阐释)的概念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卢卡奇的阐释含蓄地把资本主义关系视为是外在于劳动的。尽管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确实包含了对工厂劳动的批判,但是它深层的预设呼应了传统理论在本质上把资本主义当作市场与私有财产来处理的方式,也就是说,以外在于劳动的方式来处理资本主义问题。
上述观点虽然在社会主义传统当中占主导地位,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与此截然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关系看作是外在于主体的,相反,他分析了这样一种关系,其特征是准客观的形式,它们构成了黑格尔所理解的历史主体。这一理论转向意味着马克思成熟期的理论并不局限于这样一种观点,亦即像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行动者构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元主体,并将在未来的社会里实现自我;相反,马克思的理论其实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批判。
类似的差异也存在于马克思和卢卡奇对黑格尔整体性概念的理解之中。在卢卡奇看来,社会整体性是由“劳动”构成的,但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遮蔽与碎片化而无法自我实现。它表征了针对资本主义当下之批判的立场,并且将会在社会主义下得到实现。然而,马克思则把资本当作历史主体,这样一种范畴性判断表明,整体性以及构成整体性的劳动已经成为了批判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一个本质上同质的社会“实体”构成的。因此,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性存在的。其他社会构型并没有如此程度的整体化;这些社会构型下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本质上同质的,它们并不能由“实体”概念来加以把握,无法从一个单一的结构性原则次第展开,也没有表现出一种内在固有的、必然的历史逻辑。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而不是无产阶级或者人类,才是整体性主体,这清楚地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否定所需要的并不是整体性的实现,而是整体性的废止。促使了这一整体性展开的矛盾,并不能促使着整体性达到完全实现,反而是导向了整体性的历史废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通过超越整体性,矛盾表明了整体性在时间上的有限性。
把资本作为历史性主体,这一判断把资本主义的进程置于历史特定的社会关系(商品,资本)之中,这些社会关系是由实践的结构形式组成的,而同时又是异化的:他们获取了一种半独立(quasi-independent)的存在,并使人们受制于一种半客观(quasi-objective)的束缚。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资本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过程,由于它是半客观、可量化而又独立于意志之外的,因此将自己表现为一种逻辑。在这样的框架之下,历史逻辑的存在并不是人类历史本身的特征,而是一种特定于历史情境的、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征,然而黑格尔(还包括卢卡奇以及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却把这种历史逻辑超历史地投射到全部人类社会生活上去。马克思成熟期的分析转换了讨论历史的条件。对于历史逻辑,他既不是肯定地加以处理,也并不将之视若梦幻泡影,而是把历史逻辑看作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之中的支配方式。
吊诡的是,这种对历史的特定理解包含了一种解放的瞬间,这不同于那些或直接或间接地把历史主体与劳动阶级等同起来的立场。这种“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阐释通过把某一阶级或人类安置在历史主体的位置上,试图以强调人类在历史之创造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来增强人类之高贵尊严。在这样的阐释框架之内,这些立场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解放的, 因为历史逻辑之存在的本身就是他律性的异化实践的表达。与之相应的是,对主体之完全实现的诉求只能意味着一种异化社会形式的完全实现。
根据这样的理解,马克思分析的批判其实在某些方面与后结构主义的倾向较为相似,它们都造就了对整体性、对主体、对历史的辩证逻辑的批判。然而,马克思把这些概念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之现实的表达,后结构主义的倾向却否定了它们的存在。这种立场忽视了异化的社会关系,也未能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后结构主义方式与其扩展人类自由之境的初衷背道而驰,其最终结果是带来了批判力的严重弱化。
那些以肯定的方式声称整体性之存在的立场,与为着保有自由之可能性而否定整体性之存在的立场,其实是互相关联的。两种立场都是片面的,尽管用着相抵触的方式,二者都在认清整体性的存在与肯定整体性的存在之间设置了一个超历史的等同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把整体性当作异质的现实来加以分析,以此来发现它最终废止的历史性形成的条件。
三
在这里,我将简要概括一种对马克思的范畴的理解,它受惠于卢卡奇对范畴的专注,但与卢卡奇的理解截然不同。这一理解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它将为超越并克服卢卡奇的二元论提供基础。
卢卡奇以植根于商品形式的理性化过程为参照,分析了现代性的中心层面,譬如工厂、官僚、国家与法律的形式等等。他把这一过程描述为质被量所囊括,在资本主义里,作为其特征的趋势是越来越强大的理性化与可计算性,这消除了工人们质量的、人性的、个体的属性。与之相关的是,卢卡奇强调,时间也失去了它质量的、变量的、流动的本质,而成为充满了量化之物的量化的连续体。在卢卡奇看来,正由于资本主义造成了量对质的全面统治,由此呈现出其抽象、普遍而形式化的单一特征。
卢卡奇主张,尽管由商品关系影响的外部世界的理性化似乎已经完成,其实理性化仍然局限于它本身的形式主义。其局限性在危机时期尤其明显,在这样的危机时期,资本主义表现为一个由诸多不完整的系统偶发性地关联组成的整体,一个由高度理性的局部组成的非理性的整体。换言之,这种危机展露了质的条件附属于资本主义量的关系,“不仅有能够立即相互进行比较的一些价值总数并存着,而且也有一些一定种类的使用价值并存着,它们在生产和消费中必须履行一定的功能”。[1](P.170)因此,资本主义无法作为理性的整体性来加以把握。在卢卡奇看来,关于整体的知识将带来资本主义经济实质上的废止。
接下来,卢卡奇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当作形式主义的问题来把握,把它作为一种没有内容的社会生活的形式。这也揭示了一点,当他宣称商品形式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他对商品形式的理解仅仅是在它抽象、量化、形式的层面上,也就是价值的层面。因此他把使用价值的层面当作是“真实的物质基础”,当作是准存在论的内容,可以与形式相分离。
在这样的框架之内,超越资产阶级思想意味着超越这种思想的形式理性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形式与内容的剥离。卢卡奇认为,这种超越需要一种形式的概念,它指向物质基础的实际内容;这种超越需要实践的辩证理论。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指向了这样一种理论,它把历史当作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全面的辩证过程。然而卢卡奇又宣称,尽管黑格尔发展的辩证方法把握了人类历史的现实,并且展示了超克资产阶级思想自相矛盾的方式,他还是不能在历史当中发现主客同一体。取而代之的是,他将之唯心地设为外在于历史的精神。它招致了一种神话学的概念,再一次引进了古典哲学的所有二律背反。
在卢卡奇看来,对这种自相矛盾的超克使得一种黑格尔式的社会历史观成为必然。无产阶级提供了恰当的“解决之道”,无产阶级能够以其生活经验为基础而在其自身发现统一的主客体。卢卡奇接下来发展出一套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与马克思不同,卢卡奇的阐释并没有以资本的发展为参照,诸如剩余价值之本质的改变所带来的可能性,以及生产过程之发展的相关变化。取而代之的是他勾勒了一种直接性与媒介之间、量与质之间的辩证,指向了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奇怪的是,他的描述完全缺乏一种历史性进程。在卢卡奇的认知里,历史是人类之自我构成的辩证过程,他对于历史的分析并没有以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为参照。
在卢卡奇的讨论当中,资本主义是本质上静态而抽象的量的形式,它既把自己强加于具体的、质的社会内容之上,同时又遮蔽了这种社会内容。在卢卡奇的框架之内,由实践构成的历史辩证运作于一个“真实”社会内容的层面上,也就是阶级关系;它最终是反对资本主义这一范畴的。而这些范畴又遮蔽了实践所构成的、它们本身所实践的范畴。据卢卡奇的理解,历史所指的是实践的层次,是“真实”社会内容,在这里,经验的“事实”运作于经济范畴的层面之上。
那么,卢卡奇是怎样处理资本主义的进程的?他的确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固有的进程,并将其特征归结为资本支配劳动的体现之一。尽管如此,卢卡奇最终并没有把这一进程当作是一个历史性进程——一个盘踞于资本主义核心的准独立的社会现实——而加以认真对待。相反,他在讨论中把它当作是一个更为根本的社会现实的物化体现,当作是一个幽灵般的运动,遮蔽“真实的历史”:
这是一幅僵化的现实的图画,这种僵化的现实却又在幽灵似地不停运动着。一旦这种现实熔化为其推动力是人的过程时,这幅图画就立即变得充满了意义。然而只有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才能看到这一点。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些倾向中表现出来的过程的意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消灭,因此对资产阶级来说,意识到这一问题就等于是精神上的自杀。[1](P.269)
在卢卡奇看来,“真实的”历史是由实践构成的辩证历史过程。它运作于社会现实的更根本的层面上,而又指向了对这个社会的超越。这个“更深刻”、更本质的社会现实层面被资本主义形式的直接性所遮蔽,对这一现实的把握必须以突破直接性为基础。对卢卡奇来说,这一突破在结构上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实现的可能。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超越与克服,也就包括了对形式主义而又量化的现代社会生活(价值)维度的超克,由此使一个真实的、实质的、历史的社会本质得以出现,并历史性地实现自身。
接下来,卢卡奇提出了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实证唯物主义形式。卢卡奇肯定了由无产阶级实践所构成的历史辩证过程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主客同一体的阐释,是以资本这一范畴为依据的。如前所述,从黑格尔那里移用的辩证历史逻辑的理念、整体性的概念、主客同一体等,它们在卢卡奇看来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而马克思恰恰把它们当作是资本的特征。那些卢卡奇所理解为社会本体论的、外在于范畴之视界的东西,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的范畴中,却被当作是内在于资本的东西来加以把握。
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把量与质,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式与内容,加以区别并对立起来。这种对立受限于他所理解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关系以及商品形式。卢卡奇把商品当作是一种历史特定的抽象形式(价值),它附加于一个超历史的具体的实质内容(使用价值,劳动)之上,这一实质内容构成了那个“真实的”社会本质。对于卢卡奇来说,在资本主义里,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是偶发性的。反之,与内容相结合的形式概念则指向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然而,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并非如此。马克思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具有“双重特性”,它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指的是一些体力劳动在所有社会当中都充当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抽象劳动”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抽象的具体劳动,或者是作为整体的劳动,它是完全不同的范畴。它意指的是,在资本主义里的劳动力还具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媒介功能,这并非是劳动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它成为了一种准客观形式的社会相互依赖的媒介。“抽象劳动”,作为历史特定的劳动的媒介功能,正是价值的内容与本质。在这里,形式与内容的内在关联正是由资本主义所根本决定的。
资本主义当中的劳动,既是我们的常识所认知的超历史的概念,又是历史特定的社会媒介活动。由此,它的客观化既是具体劳动产品,又是社会媒介客观化的一种形式。根据这一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特征的社会关系既具有一种独特的准客观特征,同时又是二元对立的,表现为抽象的、普遍的、同质的维度与具体的、特殊的、物质的维度之间的对抗。两种维度都更多地体现为自然的而非社会的,同时又决定了对自然现实的社会性认知。
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构成资本主义的媒介形式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支配形式,它使人们服从于非个人的、日趋理性化的、结构性统辖与命令的社会支配。人类被时间所支配。这一时间性的支配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它无法在阶级支配,或者具体的社会群组的支配,或者国家经济的制度性中介这样的层次上恰当地理解。它居无定所,虽然由确切的社会实践形式构成,却又表现为非社会的。进一步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所分析的时间形式的支配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卢卡奇所认为的历史是被资本主义所遮蔽的动态的真实,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被批判性地看作是受资本主义规律所影响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资本论》里,商品形式的不稳定双重性生成了一种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辩证互动,它造就了支撑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历史进程。在这里,使用价值的层面并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的基础结构形式,而是整体的一个瞬间。价值与使用价值的辩证所产生的这一进程:一方面,其特征表现为生产与整体社会生活的不断转变;另一方面,这一历史进程不断将它自己重构为一成不变的社会生活之特征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说,价值被重构,而劳动实现了社会媒介,无论生产力达到了什么程度,人力的劳动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从社会整体来看)。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永不停歇地创造着“新”,同时再生了“同”。它既创造了另一种组织社会生活和劳动力的可能性,同时又阻碍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马克思对黑格尔成熟的批判不再是后者唯心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人类学意义上的倒置。相反,某种意义上,它是黑格尔唯心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正当化。马克思含蓄地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所谓的“理性核心”正是它唯心论的特征。它是由异化的关系组成的支配模式的一种表达。关系从个人那里取得了一种准独立的存在,将一种强制的形式强加于个人。因为关系具有一种特殊的双重性特征,因此也具有辩证的特征。它们所造成的内在动态无法直接理解为个人或群体的行动。历史主体是构成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媒介的异化结构,资本的矛盾指向了主体的废除,而非主体的实现。
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所阐明的非线性的历史进程为经济增长以及资本主义当中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工业生产提供了批判性理解的基础。也就是说,卢卡奇批判性地描述的理性化过程在这里成为范畴性的分析。这一取向既不是假设了一种指向超越现有结构与劳动组织的线性发展模式,也没有将工业生产和无产阶级当作未来社会的基础来处理。相反,它指明了,资本主义既创造了不同的增长与生产形式的历史可能性,同时又结构性地破坏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在这种阐释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既不是分配(市场和私有财产)与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现存资产关系与工业生产之间的矛盾。它呈现为现有的增长与生产形式和之后所可能出现的增长与生产形式之间的矛盾,在后者中,社会关系不再由劳动以一种准客观的方式来加以调节。*通过把社会形态的矛盾特征建立于商品与资本范畴所表达的二元形式之上,马克思指出,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现实或者普遍的社会关系在根本上是矛盾而辩证的这一观念,应当被视为一个形而上的前提。但他没有提供足够的解释。
我在此简略讨论的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的阐释并与之分道扬镳。这种传统的阐释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其依据是以市场与私有财产为结构的阶级关系,把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主要理解为阶级统治与剥削,同时构成了一套以劳动和生产为立场的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批判(在这里,劳动与生产被超历史性地理解为人类与物质自然之间的互动)。我的观点是,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资本主义的劳动是历史特定的,他试图阐明一种特殊的准客观的社会媒介与财富(价值)形式,这种准客观的形式构成了一种支配的形式。这种形式架构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并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性进程。因此,劳动和生产过程,既不能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当中剥离出来,也不能与之对立,而是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
马克思的理论远远超越了对资产阶级分配关系(市场与自有财产)的传统批判;它把握了现代工业社会本身的资本主义特质。马克思的理论把劳动阶级当作资本主义的基本因素来加以处理,而非把它看作是否定资本主义的化身。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新阐释意味着从根本层面上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可能的历史性转变。
四
资本霸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构型,在历史上是各不相同的,从重商主义,到19世纪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到20世纪的国家中心福特主义资本主义,再到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每一种构型都引出了一系列深入的批判,举例来说,这些批判或是针对着剥削与不均衡、不平等的增长,或是针对着技术统治与官僚主义模式的支配。
然而每一种批判都是不完整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无法完全等同于任何一种历史构型。通过勾勒卢卡奇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不同阐释,我试图把两种倾向加以区分:一种倾向,无论怎样周密翔实,最终只是针对资本的一种历史构型的批判;而另一种倾向,允许我们把资本理解为社会构成的核心,并将之与诸多表面构型剥离开来。
作为社会构成之核心的资本,如何区别于资本主义历史特定的某一构型?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种区分变得越来越重要。马克思主张,即将来到的社会革命必然从未来当中汲取诗意。先前的革命专注于过去,错误地认知了历史的内涵。
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以他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借用为基础,退向了无法把握的未来。卢卡奇的方法造成了错误的认知,混淆了资本在19世纪的构型而无法超克资本主义。其结果是,他含蓄地认可了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当中托生的新国家中心的构型。吊诡的是,尽管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丰富的批判性描述也反对社会的科层化,但是他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范畴的具体理解并没能恰当地以这些批判性描述为基础。
对资本主义的新构型无意中的认可更多地体现在7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反对黑格尔并且转向尼采的特征。这种思考也是退入了一个无法恰当把握的未来。他们虽然否定了卢卡奇对国家中心秩序的含蓄认可,但是他们的否定也无法批判性地把握继福特主义国家中心资本主义之后而兴起于东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在更深刻的理论层面上,反倒是肯定了这一秩序。
把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作为社会构成的最基本核心来加以阐明,我们重新思考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我试图用这样一种思考为当下的资本主义批判做出贡献,这一批判摆脱了把资本主义当作它诸多历史性构型之一的概念上的束缚。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论法的研究[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
[3]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TheSubjectandSocialTheory:MarxandLukcsonHegel
Moishe POSTONE1, tr. REN Zhi-jun2
(1.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SA; 2.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Ottawa, Ottawa, Canada)
By draw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ukcs’s critical appropriation of Hegel and that of Marx, this article outlines a reading of Marx that, while indebted to Lukcs, seeks to get beyond the opposition of Hegelian and anti-Hegelian critical approach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Marx’s analysis of labour in capitalism as historically specific seeks to elucidate a peculiar quasi-objective form of social mediation and wealth (value) that is constitutive of a form of domination. This form structures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ism and generates a historically unique dynamic. Hence, labour and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re not separable from, and opposed to,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capitalism, but constitute their very core. This is an analysis that allows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 as the core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separable from its various surface configurations.
Lukcs; Hegel; Marx; labour; capitalism
2012-07-10
Moishe Postone,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犹太人研究中心“自我、文化、社会”协会主席、芝加哥大学当代理论中心负责人。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性转型研究,著有《时间、劳动和社会统治》(1993,获美国社会学联合会理论奖)、《历史与他律性:批评性短评》(2009)、《马克思重装上阵: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再思考》(2007)等。即将出版《批判性社会理论与当代历史转型》;任致均(1985-),男,天津市人,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末民初时期亚洲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
A81
A
1674-2338(2012)05-0044-09
(责任编辑:沈松华)
——回望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