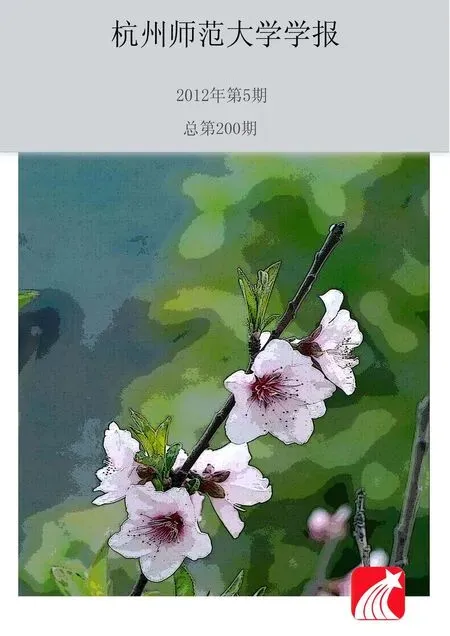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会通
杨祖汉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台湾桃园 32001)
21世纪儒学研究
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会通
杨祖汉
(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台湾桃园 32001)
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宋明理学中分属不同的义理形态,两者难以融通。不过引入康德“自然的辩证”思想可以发现,朱子学与阳明学都对道德实践中的感性的反弹有清楚的认识,并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在朱子学,是从“常知”经格物而进入到“真知”来克服;在阳明学,是强调“无善无恶心之体”,达至“无善之善”来克服。从克服“自然的辩证”来理解,两者是针对同一生命问题的不同解决理论,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宋明理学;朱子学;阳明学;康德;自然之辩证
朱子与阳明在宋明理学中分属不同的义理型态,据牟宗三先生的分判,他们是宋明儒三系中的两大系。牟先生认为,象山、阳明系与五峰、蕺山系是可以相通的两个型态,此二系是同一个圆圈的两个来往,故是宋明儒的大宗;而伊川、朱子则为宋明儒中的别子。程、朱与陆、王、胡、刘有横摄与直贯的分别,依此分判,二者是不能融通的。[1]
学界当然也曾探索朱、王二系是否有融通的可能,但主要的做法是从朱子的心性理气论可以与阳明的理论相通上着手。如唐君毅先生认为朱子与象山或阳明的第一义之不同,并非在于本体论上心与理为一为二之问题,而是在于工夫论之不同。[2]又有学者认为朱子所说的心除了思虑见闻之义外,还有道德本体之心之义,可以与陆、王言心相通。[3]这些见解虽可参考,但朱子论心与阳明、象山所说的良知、本心确有不同,从此处求其会通,是很困难的。心即理与心不即理,及工夫论上的格物穷理与明本心、致良知的分别,确如牟先生所说,有逆觉与顺取之不同,故二系的义理不易和会。本文认为,朱子与阳明的学说都对道德实践的“自然的辩证”即感性反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解决之道,如此,二系是否可理解为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决方式?如果可以这样看,则伊川、朱子系与象山、阳明系便可以看作是殊途同归的理论,二者可以相通,或互相补足。
一 从伊川、朱子之区别“常知”与“真知”说起
程伊川有“常知”与“真知”的区分,是他很有名的讲法。①“真知与常知异,……若虎能伤人,虽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见《二程遗书》卷一,《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16页。此段未标明是谁的话。《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载有“昔若经伤于虎者,他人语虎,则虽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终不似曾经伤者,神色慑惧,至诚畏之,是实见得也。得之于心,是谓有德,不待勉强,然学者则需勉强。古人有捐躯殒命者,若不实见得,则乌能如此?须是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固有杀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此段见于《二程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应是伊川的讲法;但该卷前有小注云:“或云:明道先生语。”故此段也有可能是明道语。但在《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载:“向亲见一人曾为虎所伤,因言及虎,神色便变,……盖真知虎者也。”(第188页)据此可见以“谈虎色变为真知”,确定为伊川的说法。从伊川此一说法,虽不足证他所言之心有本心、心为心即理之心之义,但可以看出,伊川认为人人对于德性都有了解,但这种了解是初步的,不一定能贯彻成为真正的道德实践。一般人所谓的了解,应该是指:道德行为是无条件的,只是为所应为,不能因着别的目的而从事。伊川所说的“常知”当是就此义而言。此一对道德意义的了解,不需要通过经验的认识,人们只需要反省一下行为的动机,就可以给出是否道德的判断,明白无误。如果伊川所说的“常知”不就此意而言,便很难索解。因为若是从经验上认知才可以理解何谓道德,则“常知”一词所涵的“人人对道德都有了解”之意,就不能成立了。伊川有“德性之知不假见闻”[4]之语,可以与“常知”关联在一起来看。由此可证伊川肯定了一般人都了解道德之意义。
一般人对道德虽有了解,但那只是“常知”,要从“常知”进到“真知”,才可以由知德贯彻为行动,而产生真正的道德实践。伊川举例说曾亲见遭遇过老虎伤害的农夫,会谈虎色变,该农夫是真知老虎的可怕;假如从事道德实践的人真知道德性理的意义,自会见善必为、见不善如探汤,便能无例外地行所当行。显然,伊川持敬穷理的工夫,是在对道德法则有基本了解的“常知”的情况下,作进一步的了解;而不是原来对道德性理茫然无知,希望通过格物致知来明理。不能因为他主张须由穷理而达至真知,便批评他完全依靠后天的经验认识来理解道德之理。同样,在朱子的学说里,也常常提到“常知”与“真知”的区分,及顺着“常知”而进一步达到对于理的真切了解。如朱子《大学·格致补传》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又朱子注《大学》“明德”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5]他所理解的明德,应是指人心本来就具备德性之义,其中也隐含了人心对道德之理本来就有了解这层意思②关于“明德”究竟是心或是性,是需要详细讨论的,本文暂不能及。。类似观点,朱子是常常提到的。因此我们可以将所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理解为:朱子肯定,人人都有对于道德法则的了解。一般人即使在经验知识方面十分贫乏,但一旦讨论到道德问题,都可以给出明确的判断,都懂得真正的为善必须出于纯粹的存心之义,而行动的存心究竟是有条件的或无条件的,一般人也很容易分辨。正如王船山所说:“愚夫愚妇是至愚而又至神”③转引自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八讲》,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所谓“至神”即指就行为是否有道德意义给出明确分判。因此,对于一般人都能了解何谓道德的事实,伊川与朱子应该是肯定的。如果以此为格物穷理的起点,则以为伊川、朱子是意志的他律的伦理学,或是用讲知识的方式来讲道德,恐怕非伊川、朱子原意。
二 所以要由“常知”进到“真知”之故
如果伊川、朱子肯定一般人都有对道德的“常知”的了解,则何以他们不像象山、阳明所主张的,当下本着道德本心或知是知非的良知而扩充出去,承体起用,直接生起道德的行为;而要绕出去从事格物穷理的工夫,希望对道德法则作进一步的了解?牟先生便根据此义来判定伊川、朱子是横摄的系统,而陆、王(也包括五峰、蕺山)的发明本心、当下致良知是“逆觉体证”的系统。牟先生认为只有“逆觉体证”的工夫才能让道德之理当下呈现于人,从而挺立人的道德主体,这才是恰当的了解道德之理的途径。如果把道德之理当作外在的对象,通过认识、分辨来探索,便是把理当作知识的对象,此时心是认识的心,而理成为静态、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依着这种了解,伊川、朱子因为主张心理为二,不能当下体证本心,故需通过认识事事物物来理解道德之理。而程、朱这种做法是以讲知识的方式来讲道德。
但根据上文所说,伊川、朱子对道德法则是有了解的,而且肯定这种了解是人人都有的,则对于他们所以要主张的格物穷理的工夫,就需要有另外的说明,不能只因为用格物穷理的方式来了解道德法则,便被理解为视理为外在的对象,本不知何谓理,要从然追溯所以然,或以存有论的圆满来规定道德。然而,以存有论的圆满概念来规定善,是在对道德之理没有了解或没有常知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对何谓“圆满”的探究,来了解善。如果以此义理型态来了解伊川、朱子,便不合于他们对理有“常知”的肯定,故用“以存有论的圆满来规定善之他律型态”来诠释程、朱应该是不恰当的。但如上文所说,如果是对理有常知,何以不本着此“常知”而承体起用,作扩充的工夫,而要去格物穷理呢?这里可以引入康德“自然之辩证”之说来作说明。关于此问题,我已经有几篇论文讨论,不拟详说,只略说大意。④请参考拙著《程伊川、朱子“真知”说新诠——从康德道德哲学的观点看》,《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8卷第2期,2011年12月,第177-203页。康德认为,人在对道德法则或义务有所了解时,便会产生感性的反弹,使本有的德性之知变成暧昧不明。这一感性的反弹,很是关键。人的道德行动是完全由理性直接决定的,不能夹杂其他的原因或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感性欲望或求幸福的要求,是完全没有地位的。然而人的感性性好之要求满足,或人追求其人生的幸福,也是很合理的;但在人自觉实践道德时,感性的性好却完全不被承认,甚或遭受藐视,于是在理性显示其实践的作用时(理性成为实践时),感性性好便会产生反弹,质疑这种纯粹依理而行、直接由理性决定的做法或要求是否合理。人一旦遭遇到感性性好的反弹,便会使原来清楚明白的、道德的行为理性之事实,或可说是不由经验而有的德性之知,变成暧昧不明,甚至怀疑是否真有这种理性的事实或德性之知的存在。于是便从无条件的实践,转成为有条件的行动,即迁就感性的欲求,为了其他的目的来从事道德行为,如借道德的善行来谋取个人的私利。这种因感性性好的反弹而产生的行动之存心的滑转、自欺,康德名之曰“自然的辩证”。[6](PP.33-34)
康德此一说法,正好给出了伊川、朱子何以要由“常知”进到“真知”的理由。即是说,只依靠人人本有的对道德的一般了解是不够的。这并不是说人对于何谓道德的了解有问题,一般人对道德的“常知”的了解是很准确的,是没有错误的;但这种对道德的了解——要求理性直接成为实践的,而不能掺杂其他的要求——会因为感性的反弹而造成自我怀疑、暧昧不明。这可说是自己对自己的质疑:顺着感性性好的要求,而对于自己这种本有的、甚为清楚的,该当只以道德理性作为实践动力,完全不可以考虑其他的想法,产生了自我怀疑。顺此怀疑,而使自己本来是为所当为的无条件的实践,渐转而为有条件的,甚至以善作为工具以遂其私。这是人的道德之恶所以会产生的原因。此一道德之恶的产生,人人不能避免,因为人不能没有感性,不能不受感性的影响。如果不克服此一生命实践的困境,就不可能真正、长期地实践道德。据康德的说法,只有从对道德法则的一般理解进至哲学的理解,才能克服。[6](P.34)所谓对道德作哲学的理解,即是康德所谓的实践哲学,是把“常知”中的道德的纯粹意义、道德法则抽出来,而作明白的分析。康德又有“道德形上学”之说,即对道德作形上学的解释,认为道德的律令是无条件的律令,道德法则是先验的,其价值不依于行动的任何结果,而内在于依无条件的律令而行的行动本身,道德行动的价值并非世间的幸福、功利所能比拟。明白了这些道德本身的意义,才能克服“自然的辩证”。即是说,在康德看来,只有对道德法则或道德性本身作思辨的、哲学的分析,以充分展现其本义,才能克服因知德而引发的感性性好的反弹。康德此说甚有理据,表明了在人的道德意识之生发处就是恶的根源之所在,此意非常深微,确实对人性有深刻的洞见。
依康德此一思考,伊川所强调的从“常知”到“真知”,或朱子所重视的“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之工夫是有必要的。伊川、朱子必然已认识到,所谓“常知”是不可靠的,由道德的常知会引发感性的反弹。因此,虽然肯定了对道德法则本有所知,但不能据此便不要求进一步求道德之知;故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而对道德作真正的了解,并不必是心理为二的形态。即在要求对道德之理作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可以把心中本知之理抽象出来,进行哲学性的思辨,以充分了解理本身。而这种对道德之理的思辨的、哲学的理解,如果可以充分展现道德行动所根据的道德之理的意义,便可以让人明白道德行动的价值是自足而无待于外的,甚至是绝对的。如此,则在感性反弹而产生对德性的怀疑时,就可以起到消解、对治的作用;因之,通过进一步透彻地知善、明善而消除自欺,这便是由明善而诚身(《中庸》语),而《大学》所说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也可以得到顺当的解释。依此义,程、朱之所以要讲“格物穷理”,便是要克服因为知德而产生的自然的辩证。由此可以了解朱子何以批评象山,谓象山不知气禀之复杂的缘故。朱子明白,人在知德的同时,亦会怀疑道德;在知善的同时,内心会产生不欲为善的想法。⑤朱子曰:“自欺是个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当为,却又不十分为善;知道恶不可作,却又是自家所爱,舍他不得,这便是自欺。”《朱子语类》卷16,第327-328页。又《朱子语类》所载《诚意章》之旧注云:“人莫不知善之当为,然知之不切,则其心之所发,必有阴在于恶而阳为善以自欺者。故欲诚其意者无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朱子语类》卷16,第336页。此段旧注虽后来不为朱子所取,但其中所说却明白表示要为善时会产生感性的反弹之意。故强调致知对于诚意的重要性。而对此一生命现象的了解,也成为朱子依循《大学》的实践次序,强调以致知为诚意的先决条件之理由。如此理解也可以回答阳明对朱子的批评。阳明曾质问,纵使格得天下之物之理,又如何能诚得了自家之意?⑥阳明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阳明认为诚意是当下在意念上作去妄存诚的工夫,以达到目的之事;而去妄存诚,靠的是自身良知的力量,并不能依托外物。但如果按照上文的理解,进一步的明理可以对治在知理时引发的内心之不诚,则诚意也确实需要格物致知以明理的工夫。
三 从“自然之辩证”看朱、王会通之道
据上文所说,对道德的“常知”之所以不可靠,是因为知德的同时便产生了对道德的怀疑。如果这是人实践道德时的普遍现象,则不肯安于对于道德的一般的了解,而要求获得“真知”,是很合理的想法,不能说以“格物穷理”来深化对道德之理的认识,是绕出去作与道德实践不相干之事。阳明批评朱子是求理于外,此一批评也不能真正驳斥伊川、朱子之说。反过来说,于良知之生发呈现处,实行致良知之工夫,确是洞见本原、生发真正之实践的做法;然良知是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知善便应有感性之反弹生起。对此王学亦应有体会,并思有以对治之。我认为阳明的“四句教”所以会以“无善无恶心之体”为第一句;王龙溪所以强调“四无说”,认为心、意、知、物要以“无心”来浑化;而周海门在“九谛九解”的论辩所以会说无善之善方是至善,而了解此“至善”是最重要工夫之故,阳明学这些理论的发展,其实都可以从响应此“自然的辩证”的问题来理解。以下大略论述其中的含义。
阳明论良知也有深浅良知的分别,认为要从浅浅的良知进至较深的良知,即就良知而言,亦可有常知与真知之分;此意虽不见于通行本的《传习录》,但也应是阳明及阳明弟子意识到的问题。[7](P.159)陆、王所言之本心良知当然就是心体,知即是理;而程、朱所说的“心知理”之“知”并非实体性的本心,两者并不相同,但此处未必是需要严格分辨的关键问题。上文论述的重点在于:对于道德作为无条件的、理所当然的行动之认知,会引发感性的反弹。在这个问题上,若能证明程、朱对于德性的了解有所谓常知之肯定,就可以说明问题。阳明所说的良知虽然是实体性的本心,体证此一本体虽然可以涌现相应于道德法则而起的道德行为,但于良知之起处,即要面对从无条件的实践要求而引发的感性性好之反弹,故阳明言良知,重“致”的工夫,又强调“知行合一”,即强调良知本具实践之动力,而这一实践的动力可以克服感性性好的反弹。从畅通行动实践的源头着力,当然可以克服随着躯壳起念而来的对实践的阻力。故在强调良知必须往前致,知必须要在行动中完成的重实践的说法下,似乎并不需要讨论“自然的辩证”的问题。但从阳明所说的“四句教”以“无善无恶”为首句,及龙溪强调良知自然而然呈现,心、意、知、物都在无心的意义下通而为一之义,也可以看到上述的问题。我认为从“无善无恶”来说心体,除了牟先生所说的心体是绝对的至善,其为善是超越于相对比较的善恶一义外,还有自然而然、为善而不自以为是善之义,而且此一义可能更重要。从心体的超越于相对的善恶而为至善来理解“无善无恶心之体”,固然认识到心体是至善,超越于一般善恶判断之上;但还是舍不下“善”,与“四无说”所说的“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之言不相类。可能阳明、龙溪所说的“无善无恶”是偏重于牟先生所说的“作用层的无心”之义,对于存有层上的“有”之义比较不重视。后来周海门与许敬庵作“九谛九解”的论辩,周海门即完全强调“作用层的无”的意义,他说:“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而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我认为他们这些说法,正是面对或试图解决“自然的辩证”的问题。如上文所述,所谓“自然的辩证”是知道德性行为的无条件性而引发感性的反弹,问题是出在对于德性之善或对道德法则的意义有了解之处,因为知道了道德的无条件性,而使得人感到自己的感性欲求受打压,而起反弹。故为善而如果不以为是善,则这种因明善而来的反弹应该就能避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阳明、龙溪以至周海门以“无”来形容心体,应该便是避免突显本体之善,以免因善恶的对比而产生上述生命的毛病。这有点像《老子》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之意。而如果能为善又不自以为是善,则是最高层次的道德实践,能达到这个境界是需要有绝大工夫的。从这个角度可以了解龙溪“四无说”所谓“从无处立根基”之义,即他要人体悟一至善无善的本体——不只是体悟一超越的至善本体,而是进一步连“至善之善”也要放下,如此才能让真正的心体自由活泼地如如呈现。周海门的《九解》认为,不能舍弃善的道德实践是会引生很大毛病的。他举东汉末年党锢之祸为例,认为正人君子每每自以为善,激化两派的斗争。周海门此说其实是借古讽今,批评了当时的东林党人。东林党人之忠孝节义固然令人敬佩,但天下间自以为善的人所作为者,往往产生恶事,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其所造成之祸害未必比小人的为轻。周海门说:“学问不力之人,病在有恶而闭藏;学问有力之人,患在有善而执著。”[8]为善之人如果不舍掉其善,或会在自以为善的情况下肆行自己的恶,周海门此义表达了为善执著的问题,但其实可以加上“自然的辩证”来说明之。即是说,在知善的同时,会引发感性的反弹,会在为善的表象下暗中满足自己好名、好利及其他各种感性欲求的欲望,因感性受到压抑而反弹之故,这些欲望更加炽热强烈,此时如果不加省察,很容易有借为善而行其自私的欲求的危机。我认为阳明门下所以那么强调“无善”或以无为体的意义,其理由也在于此。周海门便用此义来解释《中庸》所说的“明善诚身”之旨,他认为如果要明白的是一般所谓的善,并不困难;何以《中庸》会说明善才能诚身,以明善作为最后的工夫呢?所以此善应该是“无善之善”,即既知道德天理之为善,又进一层觉悟到此天理自然无善可名,要明白这更高层次的善,非要对良知本体作最精微的体悟不可。周海门此一分辨也略同于程伊川的要从“常知”进到“真知”之说。
如果以上的诠释是可通的,则阳明、龙溪及周海门强调从“无”来体悟良知本体,是很切于道德实践的,不能说是“虚玄而荡”,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往虚玄处发展,则此虚玄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面对从事道德实践时会发生的深微的生命毛病而起的对治工夫,必须要达至“无善之善”的体会,才可以克服因明善而引发的感性反弹。
以上可见程、朱与陆、王二系的工夫论,都可以康德所说的“自然的辩证”为核心来理解。伊川、朱子不止步于常知,而要进一步通过“格物致知”来达到真知,此一做法如果是为了克服“自然的辩证”,则是有必要的。吾人不能根据“意志自律”义认为理即心,于是主张不必把理当作认知对象来进一步求理解,而以“格物穷理”为歧出。又程、朱都肯定人对于道德之理本有了解,故不能说明理的工夫是求理于外,心与理为二,心、理不能凑泊。对于道德之理的了解,依伊川之说是虽然三尺童子都能知道的,而根据伊川、朱子对于道德之理的分析,也可证他们对道德之理之为无条件律令是有了解的。引入康德的说法,应该可以证成伊川、朱子“格物穷理”的工夫论对于以成圣为目标的儒家成德之教是可行的工夫。
在陆、王心学方面,本心良知固然是实体性的本心,体证此本体当然可以承体起用,当下有直贯创生的道德实践的大用,而使实践成为当下可行的简易之事,似乎不需要如伊川、朱子般作曲折的学问思辨工夫;但从阳明强调的以“无善无恶”形容心体,及龙溪、海门对“无”或“无善之善”的强调,可以看出他们对实践时产生的善恶分别,及由此分别生成的问题,是深有体会的。具体来说,从他们对“无善无恶”、“无善之善”的强调,及要从无处立根基,可见他们向往一不分别善恶、而又能自然为善的境界。何以会向往此一境界?笔者以为,他们很能体会到为善而又自以为善所引生的问题。牟先生分析“无善无恶心之体”及“四无说”,或是强调心体的绝对性,或是强调圣人实践的化境,论述当然深微,但如上文所说,强调心体的绝对至善并不合于龙溪、海门的体会;而从圣人的化境上说,“四无说”没有工夫对治的意义,即那是工夫后的化境,并非用工夫的地方。我现在提出的解释是良知的知善知恶固然是本心的明白呈现,但在知善恶的良知呈现时,很容易引发感性的反弹而有“自然的辩证”的现象。而由知善恶进到体认良知本体本无善恶之念,只是行所当行,不是为了善而为善,或不是有意为善、有意去恶,所谓为善去恶而自然。体证到这一层的意义,即既知良知知是知非,又进一步体悟此知本是无是无非的,就会化去体证良知时所产生的善恶对待的情况,如果能去掉善恶的对待,感性欲望便不会因为道德意识的兴起而产生反弹。故如果直接切入本来是无善可为、无恶可去的自然无欲的良知本体,就可以生发纯粹的道德行为,而此道德行为的流行,是自然而然、行所无事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更能说明王门良知教的发展的工夫论涵义。重“无”或“善而无善”,是紧扣突破为善时所会引发的感性欲望的反弹来用心,故此一发展是切于道德实践的问题的,不能以“虚玄而荡”来批评。后来刘蕺山虽然对良知学作出修正,但他也强调或保留了“四无说”所强调的道德实践是自然而然之义,蕺山认为人体证到的好善恶恶之意根,其好善恶恶的表现是如春夏秋冬的变化般自然而然、一气流行的。他不满意良知教由“知善知恶”来对治善恶的意念,认为这是后一着的工夫。蕺山之说应该也是意识到了感性反弹的生命问题。程朱、陆王二系义理型态的确不同,我们不能强行牵合或会通,但他们面对的是共同的生命问题,即感性欲望会在人要去从事德性的实践时,因无条件的德性命令所刺激而引发反弹;而他们提出的不同工夫论,其实是针对同一个生命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法,从这个角度看,或者也可以说,程朱、陆王二系是殊途而同归的工夫论。
四 引文献以证义
(一)林致之问先生曰:“知行自合一不得。如人有晓得哪个事该做,却自不能做者,便是知而不能行。”先生曰:“此还不是真知。”又曰:“即那晓得处,也是个浅浅底知,便也是个浅浅底行,不可道那晓得不是行也。”后致之多执此为说:“人也有个浅浅的知行,有个真知的知行。”以方曰:“先生谓浅的知便有浅的行,此只是迁就尔意思说。其实行不到处还是不知,未可以浅浅底行,却便谓知也。”致之后以问先生,先生亦曰:“我前谓浅浅底知便有浅浅底行,此只是随尔意思。”[7](P.1597)
按此条见于日本所藏的《阳明遗言录》,资料来源未知是否真确,若此条真为阳明所说,则阳明的良知教也可以有真知、浅知之分别,如上文林致之所说,人有个浅浅的知行,也有个真知的知行。
(二)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曰:“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9](PP.1011-1012)
(三)黄勉叔问:“心无恶念时,亦需存个善念否?”曰:“既去恶念,便是善念,若又要存个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燃一灯。”[9](P.1012)
(四)问:“善恶两端如水炭,如何谓只一物?”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善,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9](P.1012)
(五)薛侃去花间草,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侃未达,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则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曰:“然则无善无恶乎?”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9](PP.1012-1013)
按以上数条阳明的言论见于周汝登(号海门)所编撰的《圣学宗传》,周海门选录阳明的文献特别注重为善而不自以为是善之意。阳明原文确表示要化去有意为善的念头,如后来周海门的《九解》所说的意思;海门虽是承王龙溪的说法而来,但于阳明也有据。阳明或龙溪、海门都认为,为善而不自以为善,是为善而自然,达于道德实践的化境,消除了应然、实然的区分;他们也意识到,在为善时,善恶的分别会引发自然生命的反弹;而在为善时没有善恶分别的意识,应该是避免感性欲望反弹的最好方法。这样的思路也可以为我们理解王龙溪《天泉证道记》提供一些切于工夫论的诠释。如所谓“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恶故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着于有矣。”[10](P.1)本着无善无恶的心体直接流行,是神感神应不容自已的,而如果有善恶的分别,便非自然流行,非自然流行的道德实践总会出问题。这两种实践的区分,是以对本体是否有真切的体认所引致的,如云:“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10](P.2)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的心体,故其实践行动都从无生,即上述所说的不落于善恶对待,从而避免了自然之辩证,故能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表现了虽是道德行为但与日常自然行动没有两样的善而无善的境界。而如果未悟得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他的道德实践便是为善去恶,逐渐归于无善无恶,此一层次的实践,固然是勉力为善,也算不容易,但未必不会产生毛病。而悟得本体是无善无恶可说是真知,若以为本体只能用善来形容,便是浅知。钱绪山也有近似的言论:
(六)人之心体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无恶”亦可也,曰“无善无恶”,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无疑,又为无善无恶者何也?至善之体,恶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体,虚灵也。即目之明,耳之聪也。虚灵之体,不可有乎善,即明之不可有乎色,聪之不可有乎声也。目无色,故能尽万物之色,耳无声,故能尽万物之声,心无善,故能尽天下万事之善。今之论至善者,乃索之于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谓定理者,以为应事宰物之则,是虚灵之内先有乎善也。[9](PP.1067-1068)
按绪山对心体的看法,认为至善无恶与无善无恶都是恰当的形容,他所了解的无善无恶是至善之体本无恶,善亦不可得而有,这也是体会到真正的为善是不会自以为是善的。而龙溪、海门的看法则更进一步,专从无善无恶来说心体,依上文的理路来看,龙溪、海门对于有其善或有善恶的分别所引发的生命问题,有更深切的体会。王龙溪下面一段文字似乎可以解释为,只有浑化了善恶的分别,才能对治声色货利引发的毛病:
(七)今人讲学,以神理为极精,开口便说性说命,以日用饮食、声色财货为极粗,人面前便不肯出口。不知讲解得性命到入微处,一种意见终日盘桓其中,只是口说,纵令宛转归己,亦只是比拟卜度,与本来性命生机了无相干,终成俗学。若能于日用货色上料理经纶,时时以天则应之,超脱得净,如明珠混泥沙而不污,乃见定力。极精的是极粗的学问,极粗的是极精的学问。[10](P.3)
龙溪此段要破去以神理(天道性命)为精,日用饮食声色货利为粗的分别。此处应含康德所说的自然的辩证之义,即一般人都以道德仁义为至精,而鄙视声色货利、饮食男女的感性欲望,其实这种分别反而会引发感性欲望的反弹。在这种分别下从事道德实践的人,他们的实践只是“比拟卜度”,即都是有为、做作、模仿的,而非真实生命的流行。而他们谈论至精的道德仁义时,都有“一种意见终日盘桓其中”⑦《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收有此条,而此句作“意见盘桓,只是比拟卜度”。,使自己的论说只成口头说说而已,此即由于精粗之分别,引发了感性之反弹,而随时遭受自己感性的质疑,对自己所讲其实是没有自信的。如果不在此处起分别,不先存在何者为精、何者为粗之想法,则无知之知即于生活上任一种情况起作用,如是便能在日用饮食上用功,使至精的天理表现于至粗的声色货利上。故没有了精粗的分别,才能使道德实践得以真切地表现。至精与至粗者的浑化,也同于无善无恶之境,这一证悟到无善无恶的心体是克服感性欲望的反弹的最佳方法。
王龙溪强调良知本来虚寂,知善知恶之知本来是无知之知,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我认为龙溪是从义利之辨体会到本心虚寂之意义,并非从佛老的学说来。此意可从下一条见之。
(八)夫学,一而已矣,而莫先于立志。惟其立志不真,故用功未免间断;用功不密,故所受之病未免于牵缠。是未可以他求也。诸君果欲此志之真,亦未可以虚见袭之及以胜心求之,须从本原上彻底理会,将无始以来种种嗜好、种种贪着、种种奇特技能、种种凡心习态,全体斩断,令干干净净,从混沌中立根基,自此生天生地生大业,方为本来生生真命脉耳。此志既真,然后工夫方有商量处。譬之真阳受胎,而收摄保任之力,自不容缓也;真种投地,而培灌芟锄之功,自不容废也。昔颜子之好学﹐惟在于不迁怒、不贰过,此与后世守书册、资见闻全无交涉,惟其此志常足,故能不迁;此志常一,故能不二。是从混沌中直下承当,先师所谓“有未发之中,始能者”,是也。颜子之学既明,则曾子、子思之说可类推而得矣。[10](PP.28-29)
由此段可知,龙溪所谓的从无、或混沌中直下承当,是通过义利之辨的省察,抖落种种感性的嗜好,斩断贪欲、习气而后体证的境界。如此言虚无,虽似道家的境界,但其实不同:这是由道德的省察而恢复纯粹的本心之境,虚无是形容道德本心之自由、自主,纯粹而毫无夹杂。如此言虚无,似乎更为合理。而由此虚无的本体引发道德实践,可以说明道德的实践是根于本性,自然而然发出来的。依此义,则应可以避免康德所说的“自然的辩证”的现象。因此,龙溪所说的虚无之义是从义利之辨的道德意识切入的,仍为儒家的正宗义理,不能说龙溪已经离开了儒学宗旨,“昧于‘化成精神’与‘舍离精神’之大界限”[11]。由自信本心直下,从虚无之本体建立根基,是当下逆反现实生命之习欲、计较之成心,让纯粹之本心呈现之工夫。此处需有绝大的自信自肯及觉悟的力量,并非无工夫可做。它有似于佛教禅宗的顿悟,但是由相信人性之善,及由本心引发的道德创造之力量而悟,与禅宗之悟不同。龙溪又云:
(九)今日良知之说,人孰不闻,然能实致其知者有几?此中无玄妙可说,无奇特可尚,须将种种向外精神打并归一,从一念独知处朴实理会,自省自讼,时时见得有过可改,彻底扫荡,以收廓清之效,方是入微工夫。若从气魄上支持、知解上凑泊、格套上倚傍,傲然以为道在于是,虽与世之营营役役、纷华势利者稍有不同,其为未得本原、无补于性命,则一而已。[10](P.29)
由此条可见,龙溪所谓的心性虚无,是从本心纯粹、完全不受感性意欲的影响之意来规定。人在作出行动时,因为感性意欲的影响,习惯地以满足本能欲望为先。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龙溪也有很深的省察,称之为“功利之毒”:
(十)功利之毒,沦浃人于人之心髓,本原潜伏,循习流注,以密制其命,虽豪杰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于此时,而倡为道德之说,何异奏雅乐于郑、卫之墟?亦见其难也已。所幸灵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未尝亡。故利欲腾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尝不存乎其间。譬诸宝鼎之沦于重渊,赤日之蔽于层云,而精华光耀,初未尝有所损污也。[10](P.31)
若不消除这功利之根而论道德,是完全无效的。而体悟良知,此功利之根便可化去。如果可以这样理解,则阳明、龙溪所强调的无善无恶,正是使人心彻底摆脱功利想法之工夫。
(十一)吾人之学,不曾从源头判断得一番本念与欲念,未免夹带过去。此等处,良知未尝不明。到本念主张不起时,欲念消煞不下时,便因循依阿,默默放他出路。……胸中渣滓澄汰未净,未见有宇泰收功之期,源头上不得清澈,种种才力气魄只在功利窠臼里增得一番藩篱,与先师良知宗旨尚隔几重公案,未可草草承当也。[10](P.90)
此条也明白表示,以虚无为心体是从源头上廓清一切功利性的想法,如果不从源头上判断何为本念与欲念,则虽良知未尝不明,但仍会因循依阿,所以要有更进一步寻求真知之工夫。如果以此来了解龙溪所谓的“顿悟本体”,则此工夫应该还是儒家应有之义。而如果以此了解虚无的心体为顿悟,则可以模拟伊川所说的“真知”之义,即了解良知的知是知非是一层,而了解良知的无是无非是更进一层,真正的道德实践必须要体证良知本无是非才可以。如云:
(十二)良知二字,是彻上彻下语。良知知是知非,良知无是无非。知是知非,即所谓规矩;忘是非而得其巧,即所谓悟也。[12]
“知是知非”与“无是无非”本不能分离来看,但一般人只会从“知是知非”来体会良知,若如此便会着于“有”,即会自以为是善,而有善便有恶;若悟良知本无知,至善本无善,则良知是在自然而然、神感神应中创发道德的活动,便不会引发感性的反弹。
(十三)罔觉之觉,始为真觉;不知之知,始为真知。是岂气魄所能支撑?此中须得个悟入处,始能通乎昼夜。[10](P.87)
此处以“不知之知”为真知,可以对照伊川所说的“常知”与“真知”之分:阳明及其门下似以“知善知恶”之良知为常知,而悟此良知本无知,知善知恶本来是无善无恶的,是为真知。必须要从知善知恶而进到无善无恶,才能使良知之活动不会引发感性的反弹,而落于有为造作之层次,这也是周海门《九解》中所说的“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之意,此真亦可说是“真于良知有所知”。这一境界之达成虽然龙溪强调是“悟”的工夫,但据前文所述,也可以理解为根据义利之辨的道德省察,抖落一切感性的影响而至,或可说此悟是由道德省察而达到的最高境界。此省察工夫,不只是抖落经验现实中的感性影响,也要深入地剥落根深蒂固的功利意识。如果从此义来看,龙溪所谓的“悟本体”,并非凭空顿悟,而是有道德意识引发的当下自信,绝去一切妨碍心之本体呈现的习气,故龙溪的工夫与禅宗的顿悟还是不一样的。又上文所述,应该符合龙溪所言阳明的晚年境界:
(十四)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丽空而万象自照,如元气运于四时而万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10](P.87)
时时知是知非,而又时时无是无非,应是对良知的真知,由此体悟才可以保住良知的时时呈现。
五结语
以上可证,王门所言之良知,确有常知与真知之别,必至于真知良知,使体虚无之良知呈现,才能免于因知善而引发的感性反弹,而有真实的道德实践。如是,则阳明及其后学对良知教的发展,偏重于无善无恶及无知之知之义,有其义理发展及工夫实践上的必要性。
而如果我们从克服“自然之辩证”来理解这种发展,则朱、王二系都是面对同一生命问题,而其消解之道都强调“真知”,于此可说此二系实有其相通处。
[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1 册[M].台北:正中书局,1968.42-60.
[2]唐君毅.朱陆异同探源[M]//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1968.531-536.
[3]金春峰.朱子哲学思想[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41.
[4]程颢,程颐.二程遗书[M]//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317.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3.
[6]牟宗三.康德的道德哲学[M]//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5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
[7]王阳明.阳明先生遗言录[M]//吴光,钱明,等.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五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8]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一·南都会语[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
[9]周汝登.圣学宗传(二)[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
[10]吴震.王畿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1]劳思光.中国哲学史:第三卷上册[M].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493.
[12]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M]//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81.
The Combination of Zhuzi Xue and Yangming Xue
YANG Zu-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Central University,Taoyuan 32001,Taiwan)
Zhuzi Xue and Yangming Xue in Neo Confucianism have different doctrines and patterns,which are difficult to be integrated.However,from Kant's“natural dialectic”,we may find out that both of them had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ceptual response in moral practice and put forward their own solutions.For Zhuzi Xue,it depend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to extend from“general knowledge”to“genuine knowledge”.Yangming Xue focused on“no good no evil as the object of the heart”to attain“good of no good”.Therefore,by understanding and going beyond“natural dialectic”,both schools aimed at the same issue of life with different theories,which shared similarities.
Neo Confucianism;Zhuzi Xue;Yangming Xue;Kant;natural dialectic
B21
A
1674-2338(2012)05-0030-09
2012-07-20
杨祖汉(1952-),男,广东新会人,曾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争》《中国哲学史》(修订一版,合著)等。
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