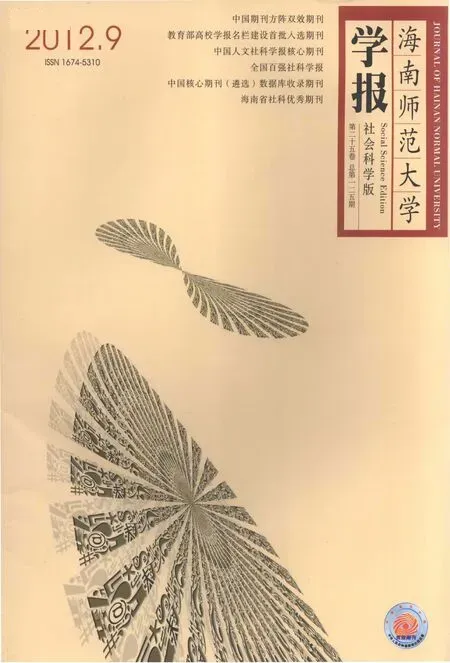我国社区参与现状及对策研究
黄朝阳
(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机关党委,海南海口570203)
党的十六大指出了要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让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通过培养和锻炼,提高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自治的能力与水平,这是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理解居民社区参与的概念,发掘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索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有效性的对策,就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意义。
一 社区参与的概念
社区是指人们共同生活的一定区域,如学校、公园、居委会等。在这固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各方通过社区参与维系并促进相互的社会关系,共同发展。而出自对社区参与的主体的理解不同,社区参与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参与全行为和参与全过程。此时社区参与的主体不仅包括社区居民,还包括政府等社区建设的其他参与方。[1]狭义的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同时作为社区管理的客体和主体,参加社区各项事务的行为。[2]此时社区参与的主体仅限于社区区民。本文探讨的对象为狭义上的社区参与,即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
1955年,联合国在《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中提出的10条基本原则包含了:社区发展要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社区发展工作特别要重视妇女和青年的参与,进而扩大参与基础。可见,社区居民长期而持续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力量,也是社区建设的目标和本质所在。[3]
二 居民社区参与的分类
关于居民社区参与,从不同的角度,可得到不同的分类:
根据居民社区参与涉及的内容来分,社区参与包括了政治性参与和非政治性参与。政治性参与是指与国家政治事务或本社区运作有关的公共性参与,比如居委会的选举、社区自治管理或社区治安等;而非政治性参与则是指与社区权利运作不相干的,仅仅与居民日常生活有关的事务性参与,比如组织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社区志愿服务等。[4]
根据居民社区参与的主动性与否,可分为自主型参与和动员型参与。自主型参与的前提是自愿,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居民社区参与。这就要求社区参与的行为主体具有明确的行为意图;而动员型参与的前提是被动,是通过他人引导、宣传、动员等方式产生的社区参与,行为主体往往不具有明确的行为意图。[5]
按照居民社区参与的范围来分,可分为社区政治参与、社区经济参与、社区文化参与和社区社会参与。社区的经济参与是指社区参与者从自身和对社区共同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出发,进行社区参与;社区的政治参与侧重于政治角度,是指社区成员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区有关的政治事务中来,比如居委会选举等;社区的社会参与是指社区内的成员对社区社会活动的参与,主要涉及社区环境建设与社区治安维护等方面;社区的文化参与则是指社区成员参与到社区举行的各种文化活动中。[6]
三 居民社区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社区建设问题,积极拓宽居民社区参与的途径,丰富居民社区参与的内容,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是笔者对海南某个社区的走访调查结果表明,居民社区参与仍存在着一系列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参与多为动员型
目前居民的社区参与很大程度仍依靠社区居委会的动员、组织和推进。很多情况下居民社区参与的自主性不高。居民往往是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说服甚至是硬性规定下参与社区各类活动。调查中发现,有相当大一部分(60%左右)的居民是在社区居委会的硬性要求或者统一组织下才参与的。而在剩下的40%中,“跟风参与”、“凑热闹”的比率超过一半,真正自主参与社区活动的人数占被调查总人数约16%。可见居民社区参与的自主性过低,实效性随之偏低。
(二)参与成本过高
居民社区参与要花费时间、资金和劳务等各种成本。不同地区的社区参与制度、居民年龄构成、居民文化素质、居民参与热情等情况各不相同,社区参与成本也没有一个准确、权威的统计和计算标准。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目前的调查结果表明,接近80%的居民认为,在工作压力剧增的当今,花费过多的时间或财力在社区参与上使得社区参与的机会成本太高,是不值得的。真正“舍得参与”的居民仅占3.75%。可见居民社区参与的成本高于心理接受度,大大影响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三)主体结构扭曲
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结构决定了参与的程度、方式和结果。主体结构的不合理,会成为制约社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所调查的社区中,参与主体主要是离退休老人、寒暑假的学生以及低保居民等三大类人群。其中离退休老人占总体的57%,寒暑假的学生占据了23%,二者共占了80%。受老人的精力以及寒暑假学生的特殊状态影响,80%抽样显示以上的人员一周最多进行一次社区参与,并主要以自发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为主。主体结构的扭曲造成社区参与的整体质量并不高。
(四)以非政治性参与为主
目前居民社区参与大多为非政治性参与,体现为热衷文体娱乐性参与,涉及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等政治性参与相对较少。居民在政治性参与中的参与价值和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加上参与空间和权力受限,直接导致居民政治性参与热情很低。调查中有部分居民认为,社区居委会脱离了群众性的自治组织的范畴,更多是扮演着社区行政机构的角色,直接对社区政治性事务作出决策,而居民的社区参与更像是一种形式工程而已。调查数据表明,对于社区文体活动表示有兴趣的社区居民占总体的68.5%;而72%的居民对参与社区政治性活动缺乏兴趣,特别是社区选举,表示有兴趣的比例不到一成。
(五)制度保障不够
居民社区参与主要是依靠社区居委会来宣传组织,较少主动参与。由于社区居委会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保障无法达到理想参与状态的要求,使得社区活动数量相对较少,活动的质量也不高。在接受调查的居委会和部分居民中,90%以上认为社区居委会的财力等无法满足需求,使得很多时候活动仅仅是为了响应上级行政部门的要求而临时开展,无法对居民的参与活动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动员,并造成恶性循环。
总而言之,居民社区参与主动性不高主要是因为缺乏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和观念创新。居民的需求与社区组织的供给之间无法匹配,使得居民对社区参与漠不关心,即使参与,效果也很差。
四 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社区发展的源动力是居民参与与社区自治。如何有效地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有效性,成为学术界与实践者共同的探索主题。针对我国社区参与存在的问题,应积极采用以下的对策以提高居民社区参与的有效性。
(一)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
居民的社区意识渗入居民社区参与的各个方面。只有凝合共同的社区意识,同一社区的居民才能被维系在一起。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得到加强,才会有兴趣关注本社区的事务,积极地参与本社区的公共活动。所以应从提高居民当家作主意识入手,加大教育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强化他们社区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加强居民参与的非营利组织建设
非营利组织是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贴合度更高,更容易得到居民的认可。通过合唱队、兴趣小组、体育俱乐部、志愿者团队等等将居民组织起来,加强成员的沟通,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通过宣传引导,营造有利非营利组织运转的舆论环境,进而提高居民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三)重视资源保障
各社区掌握的现有及潜在资源远远无法满足社区组织发展的需要,加之居民自主社区参与的成本过高,从而大大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应加大政府财政支持,设立专项基金,争取社会赞助,重视社区自筹,多渠道多方位铺开,解决社区参与经费缺乏的难题,为吸引居民参与做好物质保障。
(四)转变社区居委会的职责
转变社区居委会的职责就是要把居委会真正建成一个居民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要想得到居民的认同,只有转变其主要任务,通过向政府表达和维护居民权利,才是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表,才能发挥开展社区事务的组织能力,社区居民才有参加居委会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居民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也才能得到拓展。
结语
居民社区参与是一项综合性强、复杂度高的长期持续工作,需要调动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合力推进,使社区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推动居民社区参与的关键在于加强观念转变、提高居民参与意识、培育社区非营利性组织、建立服务社区的利益推动机制。
[1] 王骥洲.社区参与主客体界说[J].鲁行经院学报,2002(05):3.
[2] 王刚,汪丽萍.社区参与简论[J].城市研究,1998(05):53.
[3] 陈思.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现状与思考[J].公共管理,2009(06):61.
[4] 朱淋.城市社区参与研究述评[J].法制与社会,2010(01):177.
[5] 苗贵安.从群体性突发事件看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03):28.
[6] 施文妹.简析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参与——以绍兴市为例[J].百家论坛,2009(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