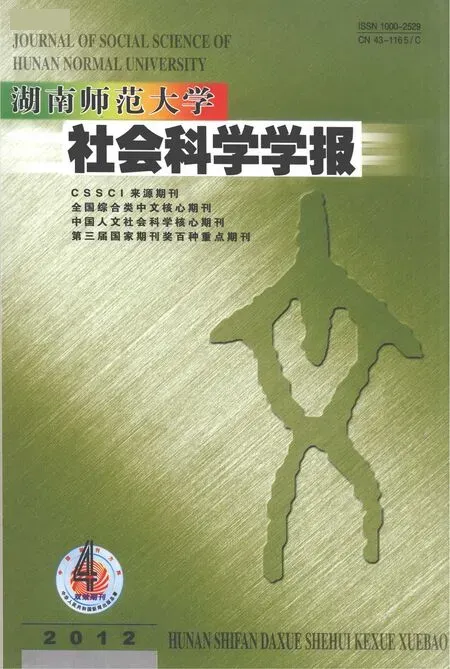试析多维视野中人格的生态化转型
彭立威
试析多维视野中人格的生态化转型
彭立威
生态文明建设客观上要求实现人格的生态化整体转型。从心理人格和道德人格的角度来看,人格的生态化意味着这些非生态人格要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转型过程中获得生态内涵;从法权人格的角度来看,人格的生态化意味着法权人格应该在越来越普遍的意义上成为生态环境的权利主体,且使这个权利主体同时担当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人格生态化同时包含心理人格、道德人格和法权人格的生态化,是人格的整体的、历史性的转型。
生态人格;心理人格;道德人格;法权人格
人格是指人的品行、价值和尊严的总和,是人的道德品质和心理品质的集合,是对人在现实生活中应当如何安身立命的规定。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来看,每当文明发展出现重大转折,人格的问题就会被频繁提起,因为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达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文明背景形成了不同的人格样态。当前,生态文明帷幕的拉开在客观上要求人的实践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等方面都要不断发生改变,即人格要产生全新的蜕变,实现人格生态化的整体转型。
一、从心理人格与道德人格的角度看人格的生态化转型
心理人格是指人的个性,包括人的性格、气质、能力、兴趣、爱好等,是个人相对稳定的、持久的心理特征的总和;道德人格是指个体人格的道德规定性,是一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在探讨人格的生态化时,我们可以把心理人格与道德人格放在一起作为同一种类型来加以考察。这两种人格类型似乎具有跟生态环境无关的特点,因而可以被称为“非生态人格”,即完全独立于生态环境而独立得到确立的人格。因为当人们把心理学所考察的心理人格仅仅当作对于自我意识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所具有的一种主观意识,或者把心理人格当作一个人稳定的心理结构和素质时,人们一般地并不考虑这种同一性意识或稳定的心理结构同外部生态环境有什么关系;同样地,在传统伦理学中,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被理解为一种具有道德意义的关系,道德关系仅仅局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道德人格的确立,似乎也与生态环境无关。
基于此,我们认为:从心理人格和道德人格这类“非生态人格”的角度来看,人格的生态化意味着这些非生态人格要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历史转型过程中获得生态内涵,即确立这些原本似乎跟生态无关的人格同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
关于心理人格的生态化。按照传统的理解,心理人格作为人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属于主观意识的范围,我们可以暂时撇开它同外部生态环境的关系而单独地对之进行研究。但是事实上,任何意识,都是对于某个对象的意识。而意识的这个“对象”除了是意识自身以外,当然还包括其他一切同意识具有本质区别的物质世界、外部自然界。正是这样一种洞见,使我们讨论心理人格的生态化有了可能。所谓心理人格的生态化,意味着要把心理人格的确立同外部生态环境关联起来,把生态环境作为完整的心理人格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心理人格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整体,思维方式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价值观则构成心理人格的内核。因此,心理人格的生态化,自然也意味着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生态化。所谓思维方式的生态化,一方面是指我们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把自然生态环境作为思维的对象来加以确立,另一方面则指我们要以全面的方式来思维生态环境,不再仅仅把生态环境当作谋取短期经济效益的手段,当作机械的、无生命的、可以任意宰制的机器来看待。所谓价值观的生态化,是指我们在对我们的各项工作或活动进行价值评价的时候,要把此项工作或活动是否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标准。
关于道德人格的生态化。在康德伦理学中,道德人格是由理性主体对道德义务的担当而成就起来的。所谓对道德义务的担当,是指道德主体对康德所说的道德法则即“绝对命令”的自觉遵守。这个道德人格诚然是一个自觉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的主体,具有理性和自由意志,但是,传统伦理学所说的道德义务并没有包括对于生态环境的义务。也就是说,传统伦理学始终没有把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当作道德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传统伦理学的这种狭隘的视野有待拓展。人们必须把道德关系不再局限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而是拓宽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与此相应,人们必须把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当作文明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道德义务或责任来加以确立。在这方面,生态伦理学事实上已起着独特的、重要的作用。生态伦理学极大地拓展了伦理学的领域,它被说成是“关于自然道德的学说”,或者说,“它研究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1](47)正是由于这种研究领域的拓展,生态伦理学才有可能把道德人格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对它而言,道德人格作为道德责任的承担者不仅需要承担在人际关系方面所应该承担的一切道德责任,而且需要担当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中理应履行的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
二、从法权人格的角度看人格的生态化
法权人格指的是人作为权利和义务(责任)主体的资格。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在论述法权人格的时候,已曾非常明确地把人格同生态环境联系了起来。正是由于法权人格在这些思想家的眼中事实上已经跟生态环境有了一种真实的关系,所以,法权人格的生态化,便有了不同于“非生态人格”生态化的独特的含义。
我们认为,法权人格的生态化包含两层主要含义:一是要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使作为法权主体的人拥有对于生态环境的权利;二是要使具有生态权利的法人切实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一般而言,法权人格意味着人是一种法权意义上的主体,该主体拥有各种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权利。但是,法权人格所拥有的权利,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理解。人们一般谈论的,是法权人格应该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如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等权利。所以,法权人格的生态化,便意味着人格作为法权主体并不仅仅拥有各项政治权利,而且首先拥有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财产”权,成为对于生态环境的真正的权利主体。人们很容易理解:如果法权人格作为权利主体不拥有对于生态环境的权利,那么,法权人格就始终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学或法学概念,而不具有经济学的意义。但是,一旦突出法权人格对于生态环境的拥有权,则法权人格的经济学内涵便清晰地体现了出来。
黑格尔已经清楚地论证了法权人格作为独立的自由意志要现实地确立起来,必须将外部自然界作为自己的财产来加以占有。他的这些法权论思想,代表着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试图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的市民争取包括生态环境权在内的广义财产权的要求。当时的许多思想家还试图从劳动的角度,来论证拥有自然环境中各种资源的正当性:人们对于环境资源的权利,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劳动争得的。例如,谁在某块土地上进行耕作,谁就有资格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市民争取财产权的这种做法,是具有阶级局限性的。而且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有了严重的分化:一部分人拥有了大量的财产,占有了大量的地产和自然资源,另一部分人却沦为无家可归即丧失了自然环境所有权的无产者。这种分化乃至对立,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集中关注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非常精辟地指出:工人不仅丧失了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事实上也丧失了他们用来进行生产的整个自然界——劳动对象。按照谁劳动谁有权利拥有劳动成果和劳动对象的法权理论,工人和农民等劳动者自然应该是他们自己劳动产品、劳动对象和劳动过程的主人,但事实上,他们的整个劳动过程和成果、包括整个自然界却为拥有大量资本的资本家所占有。在此意义上,劳动者还不是真正拥有财产权的法权主体,因此不具有真正的法权人格。我们也很容易理解这一点:要使劳动者成为真正的法权人格,必须使他们拥有对于他们自己的身体、劳动能力乃至整个劳动对象的权利,这个劳动对象,内在包含了今天人们所说的生态环境。总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推出:法权人格的生态化,意味着在现实中的“无产者”也应该拥有生态环境,工人、劳动者也应该是自己的“无机的身体”即大自然的主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确立起自己真正的法权人格。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曾试图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的方式,来真正确立无产者的“法权”。后来,许多国家陆续爆发了革命,并推行财产的公有制。在公有制的形式下,自然环境自然成为一个国家中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财富。但是,由于各种深刻的历史原因,无产阶级革命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了各种挫折,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依然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制度,而且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没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在这种现实的历史条件下,当然还不可能实现世界上所有公民对于整个自然界的共同占有,这始终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理想。
在一个财富占有量严重悬殊的世界里,不同的人对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占有量当然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过,尽管这个世界中还有穷人和富人、穷国和富国的区别,穷国、穷人却毕竟多少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自然资源。而且我们必须看到,有一些公共的自然资源如空气、水等等,确实是为一个社会、一个地区中的所有人所共同拥有的。所以,即使是只占有很少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贫穷者,也同样要承担起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责任。当然,在一个形式上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一份自然资源而实际上拥有量却相差悬殊的社会里,不同的个体理当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是有大小的区别的。如果一个人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或者利用自己的巨额资金进行投资,通过消耗巨大的自然资源来进行大型生产活动,以便谋取丰厚的利润,这样的人自然应该承担更多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这样一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已经消耗巨量自然资源而先行发达起来的国家,当然要担负起比尚未发达或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所担负的更多的保护环境的责任。
无论如何,在不能实现地球上所有人对整个自然资源的共同占有的现实条件下,要使贫穷的国家或弱势的贫穷个体也成为真正的法权主体,就应该尽量扩大自然环境中属于公有的那一部分。例如,在一个城市里,就要尽量增加公共绿地的面积,让贫困者也能够在充满挤压的现代城市里保留一份能够跟别人共享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份自然领地。另外,在像中国这样的广大的农村里,对自己的那份土地拥有使用权的农民,也能够作为法权主体来确保自己的土地不轻易地被受利润驱使的投资商所掠夺。在我们看来,增加城市公共绿地的面积、尽量维护农民的土地等自然资源,都是我们在实现人格的生态化转型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重大的现实问题。此外,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居民,都有维护本国或当地生态环境的权利。
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看,这种自觉地维护每个国家中的每个人的生态环境权的要求,正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在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当今世界,把生态环境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环境权是指公民和其他法权主体(如企业等)对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环境使用权、环境享受权、环境参与权、环境救济权、环境自卫权等等[2]。
法权人格是权利和责任的统一。显然,拥有各项环境权的法权人格,当然也必须承担各项法定的保护环境的责任。于是,我们得出了法权人格生态化的又一层更重要的含义:所谓法权人格的生态化,意味着拥有环境权的法权人格,必须履行法定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而由于现实中确实有许多在占有和使用生态环境资源的人并未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所以,法权人格的生态化,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也意味着必须实现由掠夺自然资源的“反生态人格”向依照法律的形式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型人格的转变。
这里所说的“反生态人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作了深刻而确切的刻画,它集中体现在疯狂追逐利润的资本家身上。他们由于拥有大量的金钱或资本而能够占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之成为他们资本不断增殖的手段。他们丧失了丰富而全面的感觉和精神能力,而只剩下了拥有感或占有欲,尤其是对物质财富和金钱的占有欲,在这种片面的欲望驱使下,他们展开了疯狂地从自然界榨取资本利润的经济活动,而根本不顾及这种经济活动对自然界和社会所具有的长远影响。资本不断增殖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资本家这些“人格化的资本”身上。在疯狂追逐利润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他们确实具有占有和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而未能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应该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评的这种人格类型,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后来逐步以淡化的方式出现。尽管资本家始终不会放弃对最大的经济利润的追逐,但是,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们生态危机意识的强化,越来越多的国家首先在政府层面展开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在这种背景下,人们逐步强化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其中自然包含了保护生态环境或至少不破坏生态环境这项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公众在评价企业或企业家是否具有良好的行为性质时,大多会考虑到企业活动是否会威胁到公共自然环境和员工的工作环境。“这种看法对企业改进其行为所产生的作用比其他任何观点都有效。起初,空气和污染问题集中在吸烟及烟窗所产生的令人厌烦的烟雾方面,这些烟雾可能会导致呼吸系统感染。然而,这些问题相对局限在某一地区,以至于只有在当地居民遭受到严重污染时,当地的政府才考虑拟订污染控制规划,但即使这样做了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控制措施会有效实施。人们直到最近才认识到与空气污染相关联的其他两个问题:一个是酸雨,它污染了水域、腐蚀了树木;另一个是地球臭氧层变薄。……意识到需要采取措施以治理水污染问题的时间表与考虑解决即将耗尽的臭氧层问题的时间表是一致的。……许多企业声称他们并无可行的以合理成本消除空气和水污染的技术,因此无法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提供消除空气和水污染的服务。但是,一旦了解到企业行为对人类自身安全所造成的短期和长期威胁之后,社会公众就会在特定利益团体的领导下,开始对企业和政府施加正面的压力,以提高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安全性标准。”[3]
可见,从世界范围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判过的那种极端的反生态人格,在当今世界由于政府采取立法等各种手段对危及环境的经济行为的管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资本家的逐利动机是不可遏止的,他们在被管制的形式下出于自身利益更大化的考虑而有可能不做出违反生态保护法律的事情,但由于他们仅仅出于利益的考虑而暂时不违犯这些法律,而难以对这些法律本身有一种自觉的尊重,因此他们也常常有可能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做出违犯生态保护法律的事情来。
法权人格生态化的关键是促使法权人格真正担当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在谈论法权人格的生态保护责任时,我们当然要看到不同的个体所须承担的责任是有大小的区别的:企业家、尤其是大型企业的法人代表或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由于其活动对生态环境有更大的影响,因而应该承担比普通公众更大的责任。在这里,应该贯彻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原则:谁拥有更大的生态权益,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保护生态的责任。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的公民之间,而且也应该适用于不同的国家之间:发达国家由于比欠发达国家享用了更多的自然资源,它们当然应该承担更多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但是,贯彻这项原则并不意味着欠发达的国家就不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了,也不是说普通公民就可以置身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之外了。其实,任何国家、地区的任何公民,由于自身的活动或大或小都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因此,作为法权主体自然毫无例外地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在促使法权人格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时,我们还需要看到:事实上,享用生态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是密切相关的。在许多时候,对自身生态环境权利的自觉维护,就是在履行自身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总之,从法权人格的角度来看,人格的生态化意味着法权人格应该在越来越普遍的意义上成为生态环境的权利主体,但更重要的是要使这个权利主体同时担当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至少是法定的责任。
三、人格的生态化作为人格的整体转型
尽管我们可以从心理人格、道德人格和法权人格等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人格的生态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格的生态化可以完全孤立地分别从心理、道德或法权的角度自行展开。事实上,人格生态化这一提法,已经同时包含了心理人格、道德人格和法权人格的生态化。人格的生态化是人格的整体的、历史性的转型。
我们先看看道德人格的生态化与法权人格的生态化是如何契合的。
道德人格的生态化的要义是道德人格作为道德责任或道德义务的主体不仅要承担针对自己和他人或社会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而且要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显然,这一道德责任与法权人格应该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定责任完全一致。两者的区别在于:法权人格在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定责任时,它往往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权衡、考虑,即出于功利的动机在履行责任,例如,它很可能由于害怕法律的惩罚而未实施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而道德人格在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时,它并不是出于功利的动机,而是出于对责任、义务本身的敬重。显然,如果一个人作为人格在承担法定义务和责任时同时有了一种康德伦理学所说的“为义务而义务”、“为责任而责任”的意识,他便由单纯的法权人格升华成了道德人格。与此相关,法权人格与道德人格对保护生态环境这一责任和义务的履行,在具体贯彻的路径方面也有所区别:法权人格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的履行,是通过外在的法律强制地执行的,而道德人格则是基于自己对责任的自觉意识,而非强制地执行的。
显然,不论是被迫还是自愿,不论是出于对责任的尊重还是出于利益的权衡而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这个责任的内容本身是一致的。但是,出于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而自愿履行保护生态环境责任的道德人格,在层次上要高于依照外在法律的强制要求、基于功利的考虑而被迫履行保护生态环境责任的法权人格,于是,人格的生态化,在此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进一步被解读成:由被迫履行保护生态环境之责任的法权人格进一步升华为自愿履行保护生态环境之责任的道德人格。一个人,如果能够依照法律的要求而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我们便可以说他有了生态化了的法权人格,他成为一个享有生态权益、并尽到了自己法定义务的合法的公民,但是,这个人尚未具有道德上的尊严,仅当他出于对责任本身的自觉意识而自愿地、为了责任本身而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时,他才赢得了道德上的尊严,它才有了一种崇高的、生态化了的道德人格。
我们再来看看法权人格和道德人格生态化同心理人格的生态化具有何种关联。
从人格心理学研究的角度,心理人格似乎是一个同外部自然界无关的孤立的、仅仅局限于人的意识的概念。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考察一下法权人格和道德人格同心理人格的关系,就会发现:法权人格和道德人格实际上始终建立在心理人格的基础之上。这是由于每种人格作为权利和责任的主体,始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心理结构,能够把自己的各种意识活动都统一在一起,并使之归属于一个统一的“自我”。心理人格是人作为意识主体所具有的一种特定的、对自己统一的意识主体来加以自觉意识的能力[4]。它代表被自觉意识到的自我,其本质是一种统一的自我意识。没有这样的心理人格,就等于人丧失了统一而稳定的自我和自我意识,于是就根本谈不上成为权利和责任的主体。
正是因为心理人格构成了法权和道德人格的基础,所以,法权人格和道德人格事实上也内在地包含了特定的心理人格。前面所说的那种由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所代表的反生态的“资本人格”,很明显就建立在一种扭曲的心理人格的基础上:它在突出自我的地位时,又把拥有感或占有欲当成了自我的片面的本质,要求自己尽可能多地占有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各种“财富”。于是,它把社会中的其他人和自然物都当成了自己占有欲的对象,不能以包括审美态度在内的全面的方式来占有对象世界,而是统统把对象当成了自己片面的占有欲得以满足的手段、工具。正是这种扭曲的、把自我的占有欲放大至极端的心理人格,构成了那种疯狂掠夺自然资源而不注重生态保护的反生态人格的心理基础。从思维方式上说,这种心理人格内含着一种反生态的思维方式:它只想从生态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利润,只想把自然资源作为经济财富来加以占有,因而不能以全面的方式来看待生态环境,更没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种心理人格把自我的占有欲当成了一切价值评价的最高准绳,想使一切东西都变成这种占有欲得以满足的手段和工具。没有端正的心理人格,则没有健全的法权人格和完美的道德人格。在此意义上说,没有心理人格的生态化,则没有法权人格和道德人格的生态化。[5]
心理人格同法权人格和道德人格的上述内在的关联,决定了法权人格和道德人格的生态化过程,始终同时是包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在内的心理人格的生态化过程。因此,人格的生态化转型,也就始终是一种包含法权人格、道德人格和心理人格在内的人格的整体转型。
[1]刘湘溶.生态伦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李爱年,彭本利.环境权应成为环境法的重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4):78-83.
[3][加]莱昂纳多·J.布鲁克斯.商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刘霄仑,叶陈刚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4]李廷睿,侯玉波.儒家式应对的心理结构及其验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3):11-18.
[5]毛晋平,文 芳.主动性人格:概念测量及其相关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2):106-119.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tails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personality,which means non-ecological personalities like psychological personality and moral personality acquir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in the transition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In terms of legal personality,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means it should become the subject of right in an increasingly general sense and assum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In this sense,personality ecologicalization involves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psychological,moral and legal personalities and is an all-round and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personality.
Key words:ecological personality;psychological personality;moral personality;legal personality
(责任编校:文 建)
On the Ecological Transition of Personality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PENG Li-wei
彭立威,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湖南 长沙 410081)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祛魅复魅生命境界——文化反思视野中的环境伦理与人格塑造研究”(08CZX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