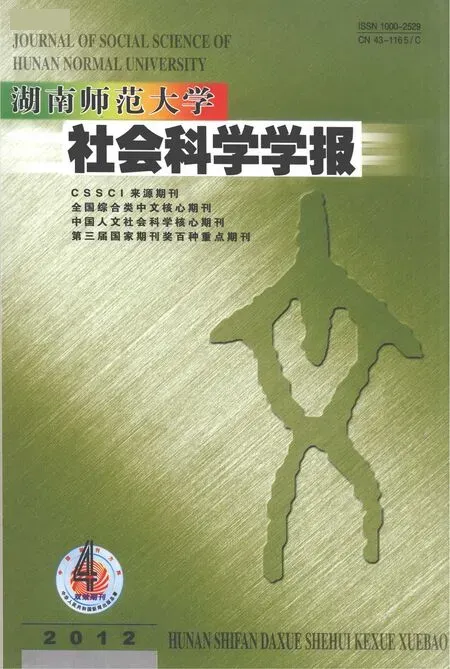彼在
周德义
彼在
周德义
一切事物因时因地因缘而在,“在时”、“在场”、“在缘”之意谓“彼在”。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彼在”与海德格尔所思、所讲的“此在”是有所区别的,“此在”是“生存之在”,是“我在”,具有特许的含义。因此,“彼在”与“此在”构成了一种普遍的“在”与特许之“在”的关系。应先有“彼在”而“此在”,有“此在”而思想,有思想而语言,也就有了现实的世界、概念的世界与思想的世界。本体论研究有“在”(老子的“无”、“道”、黑格尔的“有”、“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在”)→“彼在”→“实在”(老子的“有”、黑格尔的“实有”“实在”、海德格尔的“此在”)→万事万物的存在几个层面。“彼在”也就是道、在、此在及万事万物的存在。世间万物凡是时间之在、空间之在、因缘之在。一切无非时间、空间、因缘的产物,都会随着它们的出现而涌现,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它们的消失而灰飞烟灭。
在;彼在;此在
一、怎样认识现存的一切事物
现存之物有的是自然地生成之物,有的是人为地创造之物。对于自然之物,我们一般通过抽象、归纳的方法,通过对事物的现象与本质的认识——如同林耐创立的植物分类学一样——赋予自然之物以门、纲、目、科、属、种的区别与定位,从而获得对它们的认识。因此,对于自然之物,可以说,是存在先于本质的认识。先有了存在,然后才有对于存在之物的本质的认识,对于这一点,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即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决定本质,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存在之物,亦是本质的存在、抽象的存在,它与你的认识与否是没有关系的。
然而,对于衣物、面包香肠、车船和建筑物等等人为地创造之物,无一不是先有了关于事物的设想,有了关于物体构建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概念的存在,有了本质的规定性,然后才有创造的实践与不断地改进,才有了创造之物的产生与存在。也就是说是先有了本质观念的东西,然后才有实在之物的。
因此,对于存在者的分析和认识,我们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具体来说,对于人为地创造之物,是需要进行有关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描述的,“人为”包含了人“何时为”、“何地为”、“何以为”,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为了什么目的创造此物的,又是怎样地不断地改进此物,使之演变成为今天这等模样的。“历史”记载着这一切的发展变化,也能够说明这些变化产生的原由。例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即造纸术、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历史不仅记载了其产生的前因后果,也揭示了它们的本质特征,还记载了它们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史产生的深刻影响。
但是对于自然之物,是“何时为”、“何地为”、“何以为”的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产生此物的呢?又是怎样地不断地发展变化使此物演变成为今天这等模样的呢?面对自然之物源始的存在,以往的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等等,无不为此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搜集证据,企图寻找这些存在者产生和演变的原因,虽然他们其中有的人穷其一生,一无所获,但是经过无数人的不舍追求,迄今为止,科学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远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之前,地球上面已经是植物、动物的世界;再往前走,在微生物、单细胞藻类变形虫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地球上面火山肆虐海啸频发,地壳运动变化剧烈;再往前走,宇宙万籁俱寂,没有风雨,没有声音,没有阳光,死一般的静寂;再往前走,再往前走,也就进入到正如老子所言之“无”,是无何有之乡的境界。万事万物归结于无。“无”是什么也没有。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任何条件的存在。
“无”是老子《道德经》[1]的“无”,也是黑格尔《逻辑学》[2]的“有”、“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3]。不同的是,或者是命题的存在,规定其没有规定性,如同老子的“无”,黑格尔的“有”、“存在”只是一个外壳,是一个其中什么也没有的纯粹思想的外壳、言语的外壳、无内涵的外壳;或者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是由存在者推导出来的“存在”,是去除掉、消散了其中内容的存在。存在只是存在而已,其他什么也没有。
具有“无”的含义的“存在”是怎样与现存在之物,即现存的万事万物对接与联系起来的呢?我们是怎样地从“存在之物”出发,推导出“存在”的呢?哲学通过无穷地追问是如何达到起始之地的呢?我们回家的路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无疑,这是一个方法与路径的问题。我们只能从真实的现实的存在向回走,沿着已有的路标,按照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去探寻着走向存在的“无”。
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基本的哲学观点是“我思故我在”。我思想,因为我存在;因我在,故我思。只有“在”,才能“思”。因此,“在”是前提,是基础。一切都是从“我在”开始的,然后再是从我的思想进入到下一个开始。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说:“思就是在的思……思是在的,因为思由在发生,属于在。同时,思是在的,因为思属于在,听从在。”可见“思”是“在”的结果,或者说“在”是“思”的前提与原因。这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人表现为有所言谈的存在者。”“人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是人‘存在的家’,人在说话,话在说人。”[3](192)语言是人的思想的产物,是思想的外壳,是思想的载体。相比之下,是“在”产生“思”,进而产生“语言”,而“语言”的世界即是概念的世界,是人类生活的场所。所以说,人在说话,话在说人。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在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时,设定“存在”是最枯燥最贫乏的形式存在,具有逻辑学开端的价值。他说:“本原应当是开端,那对于思维是首要的东西,对于思维过程也应当是最初的东西。”“开端若是思维的开端,便应该是全然抽象的、全然一般的、全然没有内容的形式;这样一来,我们除了一个单纯开端本身的观念之外,便什么也没有。”并且确定以“有”或者“存在”作为开端[2](52-59)。笔者考虑到“存在”是不可以定义的,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在《说“在”之“道”》[4](102-104)一文中,曾将其称之为“前概念”,意思它是概念之前的存在,或是概念以前的具有概念意义的东西。一切概念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由它发展起来的。因此“存在”是最前端的概念,拥有“自在自为的”的意蕴。由于既不可有更高级或更原始的概念来定义,也不可以由后来的概念来定义,于是则只能自我定义,也就是不可以定义的“前概念”。黑格尔从设定的“存在”逻辑地推导出“实在”和概念之在,与海德格尔从现有的“存在者”上溯推出“存在”,二者的研究方法是颠覆性的,但殊途同归,如出一辙。海德格尔“此在”与黑格尔的“实在”的含义是相近的。
海德格尔最为关注的是“此在”。他思索,在众多的“存在者”中间,究竟谁能充任“此在”呢?他认为,“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3](11),“同其他一切存在者相比,此在具有几层优先地位。第一层是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这种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是通过生存得到规定的。第二层是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此在由于以生存为其规定性,故就它本身而言就是‘存在论的’。……第三层优先地位就在于:它是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条件。”[3](16)“是以存在者的方式领会着存在这样的东西。”[3](21)进而,他认为,首先必须“在”,然后才有“在者”;绝对不可能根本就不“在”,就会有了“在者。”因此,是存在先于本质,决定本质的。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在者”在什么样子还不明了的时候它的“在”已经明确了呢?他认为只有“我”是这种“在者”,只有“我”是在成什么样都还不清楚的时候它的“在”已经悄然明朗了。因此,他认为“我在”即“此在”。“此在,也就是说,人在。”[3](30)“此在本质上就包括:存在世界之中。”[3](16)因此,此在的本质存在于世界里。它与领会、生存、存在论等相互关联着。也就是说,“此在”是特定的“我在”。
因此,相比而言,只有海德格尔是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目光,在创造性的无穷追问之中,在对于“存在者”的反思中,从现有的众多的“存在者”中逼问出“存在”来的,从现存的存在者之中找出一条通达或者回归存在之路。他说:“我们应当在哪种存在者身上破解‘存在’的意义?”[3](9)是“实在”、“现成性”、“持存”、“有效性”、“此在”、“有”……而似乎每种存在者中都有“存在”的影子。在存在者所有的抽象中最为高级的抽象是什么?它必然离“存在”的距离最近、离“存在”的时间最短,包容性最大的性质上。而发问者,这个特殊的存在者的发问本身规定了存在者的发问规定性,是“由问之所问”规定的。所以,他认为,就是这种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由“由问之所问”,我们追问“在之所在”。于是,我们用“此在”来称呼这种存在者。从而使本体论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他最具代表意义的命题,是提出了“此在”的概念,并由此生发开来,从而使本体论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高度而为世俗所称道。并且只有他不是从假设出发的,是严肃地穷根究底式地用哲学的方式,回答哲学问题,从而开辟了一条能够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
二、“彼在”为何及其与“此在”的关系
我们在探寻认识事物起源的过程中,既不可以想入非非地从设定出发,而应当学习海德格尔依从现实之在为向导走向历史之在、本真之在,也不可以陷入由人及人的路子,这样的哲学研究还不及达尔文《物种起源》阐述的生存法则所揭示的生物进化所包含的本体论研究深度,是注定沦落为人学的,而应当坚持走由己及物、由表及里、由此及本的探索道路。
“无”先于“有”,“存在”先于“生存”。现存的事物,历史的事物总是在特定的偶然的变化之中逐渐地形成新的面貌、形式和内容,这些变化,通常是在一定的时间(或者叫做“在时”)、一定的空间(或者叫做“在场”)、一定的机缘(或者叫做“在缘”)的条件下发生的。众所周知,时间么,是直线的,有过去、今天、未来之区分,时间是具体的;空间么,是立体的,是由物体的移动产生的,由长、宽、高等因素构成的存在,有前后、左右、上下之区分;因缘,是条件,是因素,包括内在的外在的、各式各样各个方面的条件。一定的“时”、一定的“场”、一定的“缘”会产生或者毁灭不同的事物。同时,对于不同的事物,不同事物的不同个体,“在时”、“在场”、“在缘”发生的存在状态是不同的。因此,任何事物都是特定的“在时”、“在场”、“在缘”的同义词,任何事物及其一定状态只不过是特定的“在”、特定的存在、特定的实在、特定的“有”。这个世界亦是如此。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一切事物都是因时而生,因地而生,因缘而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因时因地因缘而在,称之为“彼在”。这是广泛意义之“在”,是既包含生存之在,又先于生存之在的在。这种普遍意义的“在”是与海德格尔所思、所讲的“此在”是有所区别的,因为海氏之“此在”是“生存之在”,是“我在”,具有特许的含义。因此,“彼在”与“此在”构成了一种普遍的“在”与特许之“在”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如果有人以为“彼在”与“此在”是一对相对而在的概念,则要防止陷入传统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为如果说与之对立的话,“彼在”不仅与“此在”相对,而且还与“在”相对,与所有的“存在者”相对。否则就会大大曲解我的意思。
只有“彼在”是距离“存在”最为近邻的东西。我们知道,凡事都是有产生存在的规则的。凡事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因而在由此走向彼的进程中,如同我们今天在进行任何游戏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制定游戏规则,在游戏时则按照游戏规则活动。对于由存在者走向存在的探索中,我们首先应当探明与掌握由存在走向存在者的规则,这种规则当然不是我们制定的,它是自然存在的,相似于老子的道、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等意义上的自然法则,那么这个共同的规则是什么呢?这个共同的存在必然是与“存在”最近的“存在”,是由存在走向存在者的必由之路,这就是“彼在”。
由于“存在”,有了时间,即有时;有了空间,即有场所;也有了产生存在者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即有缘。此时、此地、此缘的契合,也就有了彼在,有了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存在者。在某时、某地,由于某某原因,产生某种存在者。在岁月的长河中,一切都随着时间涌现出来;在空间的变化中,一切都随着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在物与物的相互关系之中,一切都因为相互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它们都是彼在之物。由于彼在,一切存在者都在默然之中悄悄降临。所以说,“彼在”不是在,“彼在”亦是在。彼在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之物,只是确实具有着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彼在是一种泛泛的能在。“彼在”包含着除去“存在”的所有的“能在”。而只有可能之在才是真正的存在者之母。我们知道,事物具有无限的规定性,因此事物也就具有无限多的能在。
彼在是因时而在,因地而在,因缘而在。当空壳的存在一旦有了时间、地点、因缘,接下来一切存在者就会如同泉水一般地涌现出来。这些不仅在生存论上,在存在论上,在逻辑理论上,都是能够成立的。
哦,彼在!可以是有生命的存在。此时、此地、此缘由,既有生也有死,存在者生生不息,但是都包含在彼在之中。在存在的外壳之中产出时间、空间、原由,再才是形成稀奇古怪的存在者和概念之物。
彼在是必然之在。
彼在是离开空洞之在最为有效的规则之在。但是却不是实在的概念之在,而是确定存在规则的在。在现有的存在物里,由它们的产生到死亡的整个存在的中间,不可能没有规则之在。只有规则之在才能有实有之在、概念之在。
彼在是离开存在最近而离开存在者最远的存在。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话表示,彼在是在存在之后“首须提及之在”。
一切的存在者都是由彼在而此在地成为时下之在、现场之在、因缘之在的存在者。
“彼在”涵盖所有的存在者。“彼在”既是未来之在,亦是永恒之在,彼岸之在。关于“彼在”的研究与实践,召唤着此在的我们去创造未来世界,实现千万种可能,而不像预设理论一样地束缚人,令人迷惘和窒息。
“彼在”没有过去,只有“此在”。如同田径场上比赛前的寂静,人们屏住气息,等待着裁判员吹响比赛开始的哨声。这时的时间相对于“跑”来说是“无”,虽然确实存在着,但是没有意义。只有当哨声响起来,跑步才正式开始,于是也才“有”了时间的概念。这只是比喻而已,对于本体论研究来说,“此时”如同赛跑运动开始的时间,是哨音响起的时间,是具有开端意义的时间。哨音未响没有开始的此时等于无。“此地”是运动员凝固的起跑线,也是无。只有当哨声响了,时间有了,运动也有了,空间也出现了。才有了“这时”、“那时”,“这里”、“那里”,于是也就有了万事万物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时间似乎可以说明解释一切。因为似乎时间有了,空间也就出现,因缘也随之产生。难怪乎,海德格尔在探讨存在与概念之在的关系的时候,用“此在”作为二者的桥梁或者中介,其著作取名为《存在与时间》,他为什么不写“存在与空间”或者“存在与因缘”呢?我估摸他以为时间是唯一的或者关键的原因,而空间只是随着时间的产生而产生,因缘是随着时间的出现而形成的。他说,“此在的一切基础结构,就它们可能的整体性、统一和铺展来看,归根到底都须被理解为‘时间性的’,理解为时间性到时的诸样式”。他还就时间性进行“此在的分析”和“阐释诸本质结构”[3](347)。他感叹道:“我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向着无意蕴沉降,而借此被展开的世界则只能开放出以无因无缘为性的存在者。”“这样一来它便荡然全无因缘而会在一种空荡荡无所慈悲的境界中显现。”[3](390-391)“只要此在到时,也就有一个世界存在。”[3](416)“世界不现成存在在空间中,空间却只有在一个世界中才得以揭示。”[3](418-419)从而,海德格尔把时间与存在并列起来进行探讨,“把时间性设为此在整体性的存在意义”[3](423)。
严格地也是实际存在意义上,存在者存在于一定的时间里,同时也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和个中缘由里。只有某一具体的存在者才是一个实物的概念,作为此在的存在者才是具体的彼在。在时间、空间和因缘关系的三个要素之中,光是数学的分析,会有多少不同的排列和组合呢?!在相同的时间或者空间或者因缘里面,又有多少不同的存在者?!对于一定的时间位点一定的空间里发生的展现的事物无疑是一定的。但是,对于一定的时间位点上不同的空间里或者对于不同的时间位点上一定的空间里发生的展现的事物一定是不一定的;对于不同时间位点上面发生在不同空间里面的事物更是不会相同的。而在一定的时间位点一定的空间里面,给予不同的条件时所产生的情形,也是不会相同的。只有在地点和条件确定之后,一定时间发生的事件才是一定的。所以历史所发生的展示的在都是彼在,未来之在亦是彼在,尽管我们由时间或者空间或者因缘可以展开与面对一个新世界。我们不仅可以从时间出发,也可以从空间的变更出发,特别地可以从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缘由分析中逻辑地历史地找寻到自己的回家(回归)之路。
所有的所有包括时间和空间,包括因缘都是“此在”。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只有当发问者(人、我)是“此在”时,才有了其他的所有的特定的“概念的在”。而我们觉得,只有“彼在”最贴近“在”,是“在”与“此在”之间的桥梁。进一步说,“彼在”之“在”,包涵着“此在”(即海德格尔意义的“此在”)。也可以说,“彼在”是立足于“此在”的追问而上溯出来的“在”,是先于一切存在者包含一切存在者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有概念的“在”、前概念的“在”,是什么使得“在”而“在”,“在”而得以“在”呢?也就是说,决定“在”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认定了走在“在”、“时间”、“空间”前面的事物是不再具有了。出现“在”,也就有了时间和空间。惟一的可能令“在”而“在”的,不是“在”,而只是令“在”而“在”的缘由,是令“在”而“在”的道理、道路,因为“在”而有“在”,从“在”而走向“在”。这个东西,没有名字,我们就勉强为其取个名字吧,就叫之为“道”吧!如果说其有,套用现在的说法,说它有,可以命名为“大”,广大而无际无涯,在空间上,无限的大就可以消逝,也就最容易接近于原初的东西;在时间上,说它“远”;说它是物质,说它是精神,说它是一种无法描述的一种特殊的存在。这样我们就似乎赶到2500多年前聆听中国哲学的老祖宗——老子描述的“道”[1](《老子》第25章)。大道通天,其可左右。“在”而得“在”,“道”之故焉。
三、本体论研究的几个层次及其意义
先有“道”方有“无”。有了“无”,才有“有”。“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存在于一切时空。而又是因为有“道”方才有“在”。老子以为,世界的本原是“道”,道化生万物。没有“道”,又何来“在”、“无”、“有”、“万物”、“世界”、“宇宙”、“人”……“道”是“在”、“无”、“有”、“万物”、“世界”、“宇宙”、“人”……“道”是最为原始之存在,最为原本之物,是能够自我复制,自我再生,能够产生万物的存在。万物都是包含在“道”中。于是乎,他有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老子》第 42 章)之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宇宙生成模式,这些也就是自然的和情理之中的事情。
如是说,那么对于已有的本体论研究,我们从存在者出发,就可以作出如下的推理,或者说,至少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层面,即:
①万事万物的具体的个体的存在者→②“实在”(老子的“有”、黑格尔的“实有”“实在”、海德格尔的“此在”)→③“彼在”(用虚线表示“彼在”意谓相邻于也可以将其归纳于“在”)……→④“在”(老子的“无”、“道”、黑格尔的“有”、“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在”)。
应当先有一般意义的“在”即“彼在”的前提之下,才有“此在”。相对于“此在”的“彼在”是一种遥远的“存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的“存在”。而“此在”是可以触摸、可以呼吸得到的足下的“存在”、周边的“存在”、自我的“存在”。而“彼在”则不然,是“在时”、“在场”、“在缘”之“在”。“彼在”是广大的万事万物之在。“此在”是狭隘的人之所在。
有了“彼在”,也就有了“此在”,这样子,我们的认识路径更是清晰清新而不会完结的了,因为我们的认识是从“此在”即人出发的,我们是从人的自身出发的,我们是从有限的追求出发去实现无限的意义的。我们是可知论者。因为我们是清醒的,我们足踏实地,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一定的,是可以期许的,可预期也是可以实现的,我们的行动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利弊成败、功过是非,都是可以评说的。总之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虚无飘渺的,更不会莫名其妙地引发无端遐想,产生不着边际的与生存与生活与人类无益甚至有害的想法。更不会用一个所谓预设的本原标准去糊弄人吓唬人,使聪明的人不知道怎么说,使愚昧的人不敢说。
如果用心揣摩,不难发现,“彼在”就是“道”,就是“在”,就是“此在”,就是万事万物。世间凡事都是时间之在、空间之在、因缘之在。一切的一切无非时间、空间、因缘的产物,来了的,去了的,还会来的,都会随着它们的出现而涌现,随着它们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它们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谁知道谁会发生,谁知道会发生谁,无非是种种的可能而已。如果说是必然的无非是对于可能性在发生之后的一种诠释。这个世界没有上帝,只有我们;没有先验的存在,只有我们;没有限定,只有我们。沿用海德格尔的意义只有“此在”,按照佛家的说法只有当下。于是乎,我们既生活在现实的可以感觉的世界里,也生活在已有概念的世界里,我们还生活在各式各样的个人的思想的世界里。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时间的因素,改变事物的发展变化道路,也可以通过改变空间或者其他条件,来改变事物的发展变化方向和轨迹。一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至此,我们可以梳理一下,现存的、已经灭绝消失消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和未来将会“因”而出现的万事万物都拥有共同性,它们统一于“在”,它们因时而生,因地而生,因缘而生,统一于一定的时间“时”、一定的空间“场”、一定的条件“缘”,是“在时”、“在场”、“在缘”的统一体。而“在时”、“在场”、“在缘”的“在”称之为“彼在”,其中自然包含着特定的人的存在即“此在”和万事万物。有了人的存在之“此在”,也就有了人的思想。从“此在”出发,也就是从思想出发,也就是从人出发。接下来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悄悄地来临了。包括这个世界和宇宙。但是,我们不但要从我出发,从人出发,我们的思想还应当上溯,上溯至没有人的存在,再上溯至没有事物的存在,没有我们的思想能够达到的超越思想的尽头,从那时那里出发,从那出发去探求仅有之“在”。
不知道是不是思考明白了,是不是表述清晰了,“在”如同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空壳,不仅里面没有盛装任何的内容,其本身也不是由任何实质之物构成的,只是一个先行存在的思想、语言的空壳而已。按现在说法只是一种纯粹的理性的抽象而已。一旦这空壳里面盛装下具体之物,即是有了(内容),它也就有了具体的内涵,也就是代表着物、事和意义了。这个空壳里的“在”,实质上也是时间之在、空间之在、因缘之在,也就是“彼在”;一旦有了,出现了,产生了,发生了,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在了,也就是有了某某的具体存在;当赋予“此在”为“人之在”时,也就赋予这个空壳特定的涵义,并且是存在于世界之中;当赋予这个“此在”具体的概念,原本意义上的“此在”——相当于普遍意义的“在”,或者说“彼在”——也就蜕化变质不再“此在”了。“此在”它哪里像“彼在”,那么的空旷、浩翰、无为,深不可测、重不可量、广大无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要心领神会就可以了,似乎多说一个字也就超出了“在”,不再是“在”。只有“彼在”是等于或者相当于、无限地接近于“在”,我们把它看成“在”,等同于“在”,就是“在”,而且肯定是先于“此在”的“在”。
[1]老子.道德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2006.
[4]周德义.哲学的深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Being There
ZHOU De-yi
Everything exists due to time,place and reason;“on time”,“on place”and“on reason”means“being there”.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kind of“being there”with universal meaning and“Dasein”what Heidegger think about. “Dasein”,namely“I am”,has privileged meaning.Therefore,“being there”and“Dasein”constitut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be”and privileged“be”.It should have“being there”and then“Dasein”,“Dasein”and then thought,thought and then language,and will have the real world,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thought.In ontology research,there are“being”(Laozi’s “Absence”,“Tao”,Hegel’s“being”,Heidegger’s“Sein”) ……→“being there”→“be”(Laozi’s“Presence”,Hegel’s“has”,Heidegger’s“Dasein”) →The existence of several levels of everything.“Being there”is also Tao,Being,Sein and the existence of everything.Everything in the world are all on time,on place and on reason.Everything is nothing but the product of time,place and reason,will emerge as they appear,change as they change,and turn to ashes as they disappear.
Sein;being there;Dasein
周德义,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湖南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湖南 长沙 41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