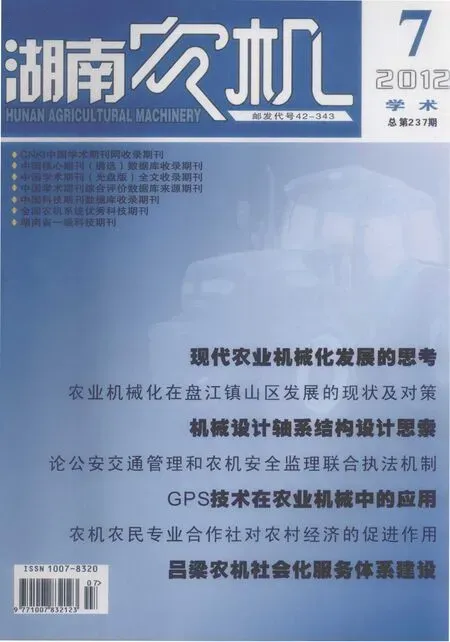实践合理性:低代价发展的吁求
陈 敏
(华南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1 我国发展过程中代价的存在及其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实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是,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相当严重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危机(动车事故、校车翻车等等),我们在实现着进步的同时也背负了巨大的代价,建设与破坏同在,进步与代价并存。当前,我国发展代价的付出情况相当复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特点:
(1)代价付出的过度性。“要想不付出代价来求得社会发展与进步,这只能是幻想。”社会发展一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环顾我国的发展现实,可以发现,我国在建设中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甚至为自然与人所不能承受,如进行经济建设肯定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这样那样的破坏,但现实中我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远超出了生态系统自身所能承受的界限,结果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失衡和生态灾害的频发,从而也把自己逼入了发展的困境;又如,合理的市场竞争是有利于经济的活跃与发展的,但是,目前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造成的一系列问题给人类自身以及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带来了灾难,比如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婴幼儿奶粉事件等等。
(2)代价产生原因的多样性。当前我国发展代价大量涌现,并且种类繁多,其产生的原因也纷繁多样:有必然性原因,也有偶发原因;有历史生成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同时,不同代价交织联系,而且,旧的发展代价尚未消解,新的代价和问题又不断滋生,新旧代价相互叠加、推波助澜,里外呼应。另外,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代价还会发生变异,使其性质和影响发生变化,从而使得代价现象异常复杂,既难以认识和把握,又难以克服和消除。
(3)受益主体和受损主体背离性的存在。由于社会社会分工的复杂性和发展主体的多样性,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此主体的受益往往是建立在彼主体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的,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的发展进步许多是以生态的破坏为代价的;当代人的受益往往是以子孙后代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某一群体或个人的受益往往是以别人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等等,这些例子的受益主体和受损主体就发生了背离。很典型的一个实例便是,当今我国频频发生的矿难事故,在这些事故背后,往往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即“老板赚钱,矿工卖命”。
2 低代价发展之于我国的必要性和意义分析
代价贯串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认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由此可见,无代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假想。低代价发展,是指所付出的发展成本和所导致的消极后果最小或最少,而发展收益最大或最显著,而在“低代价发展”这一范畴中,其实包含着具有内在联系的两个方面的要素:低代价以及发展。低代价发展的实质是在发展的同时兼顾后果,尽可能降低代价的付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阶段,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基本上走的还是一条高代价发展的道路。我们取得的成就巨大,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也非常复杂和尖锐,发展的代价十分沉重。面对发展困境,摆在我们面前的发展模式有三种:一是继续走高代价发展之路;二是停止或减缓发展;三是走低代价发展之路。事实已经证明,高代价发展是一条不可持续发展之路。而停止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发展是硬道理”,实际上,停止或减缓发展非但不能克服和抑制“高代价”,反而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恶果。
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来看,实施低代价发展意义重大:首先,实施低代价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假如说,高代价发展对应的是旧的事物为本的发展的话,那么,低代价的发展道路就应当是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对应的。可见,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找到了一条理想的路径;此外,目前我们正在讨论并积极实施构建的“和谐社会”,其实是一种低代价发展的社会。其二,走低代价发展之路,是化解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使我国顺利渡过“高风险期”的必然选择。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一样,迄今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仍然走的是一条高增长、高代价的发展道路。目前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一千美元,已进入了社会发展的高风险期。为了顺利渡过发展的高危阶段,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将发展的至上性和代价的抑制性有机统一起来,将是我们必然选择。
3 实践合理性——低代价发展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循环经济浪潮的兴起,还是国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进程的启动、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从不同侧面向人们昭示着一种新质发展实践形成的必要,即应当通过合理实践来抑制发展过程中的代价,实现社会进步。
关于合理性,甘绍平先生则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以一种方法论的形式对其进行了定位,他指出:“合理性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基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幸福的原则,来选择和调节人类行为的能力按照这一定义,合理性就不仅体现在人们对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调节上,而且也体现在人们对这一目的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上,体现在人们对行为的结果的预见和权衡上,体现在人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合理性问题显然不是一个脱离实践的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由实践本身提出来并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的问题。所谓实践的合理性即人从自身合理的需要和目的出发,根据对客观世界所做的正确认识和合理评价,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活动能力。
研究实践合理性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克服、避免、减少实践的不合理性即负效应,使实践活动向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进行,使客体的变化适合人性,使人们“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物质交换。因此,研究实践合理性的实现方法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1)大力提高实践主体的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实践主体是实践构成要素中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发展与高代价相伴的状况不能不说与许多企业主体的道德水平以及科学文化素质密切相关,例如当下的许多食品安全问题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一些企业在商业道德上的缺失;文盲、半文盲所进行的自发的、短视的实践,对于人类发展,往往利少而弊多,合理程度低,主体的道德以及科学文化水平之所以对实践效应产生影响,是因为它们在主体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确定实践目的,实践方式的选择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进行全社会的道德宣传与教化,提高人们对环境以及资源利用状况的认识,增强社会的环境危机意识势在必行。
(2)实践观念的合理性。实践观念是实践主体在现实的实践活动展开之前就建构起来的关于未来实践活动的观念模型和理想蓝图,即对未来的或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步骤、过程、结果及其价值等预先的观念反映,是直接指导和支配实践的意向性意识。实践观念的正确建构是实现实践合理性的关键环节。相反,如果在活动之前不建构起科学合理的实践理念并在活动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人们的实践活动就只能走向盲目、任意、冲动的深渊。
(3)建立健全实践结果评价体系,规范人们的实践活动。人们通过评价实践,可以规范实践,使实践活动更趋科学、理性,例如可以利用道德和法律的力量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主体的实践活动只有在不危及整个自然系统,对人类的生存基础不构成威胁时,实践的目标和结果不危及他人乃至整个人类利益时,这种具体的实践才是可行的、积极的,因而也是合理的。与此同时,这种评价体系也应该是历史的,正如麦金太尔在谈到正义与合理性的多样性时指出:“合理性———无论是理论合理性还是实践合理性——本身是带有一种历史的概念;的确,由于有着探究传统的多样性,由于它们都带有历史性,因而事实将证明,存在着多种合理性而不是一种合理性,正如事实也将证明,存在着多种正义而不是一种正义一样。”
总之,面对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和高代价付出,我们必须进行反思。科学发展观的提倡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力图改变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模式,探究着低代价发展的路径。只有扭转不正确的实践理念,实现实践的合理化,低代价发展才有可能逐渐变成现实。
[1]丰子义.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邱耕田,张荣洁.实施低代价发展:当代发展实践的重大转向——兼论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
[3]邱耕田,张荣洁.简论低代价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甘绍平.启蒙理性·传统理性·非理性主义·当代合理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余晓菊.实践的合理性:人类走出困境的现实途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
[6]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