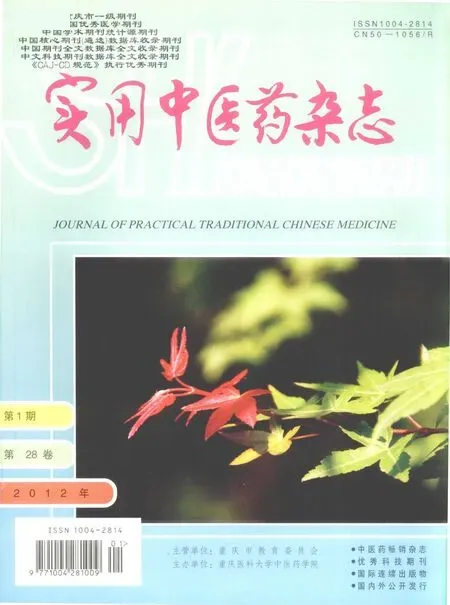“字如其人”与“方如其人”
王辉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中西医结合科,重庆400010)
签名字较之盖私章更具有法律效应,甚至可以字迹的形态,作为刑侦破案与招生选才的依据之一,这些不争的事实证明,手写之字,确是书写者的“身份证”。
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方块汉字本身就是象形表意文字,并受儒学伦理道德和感性思维模式的影响,因而对“字如其人”又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书家写的字除了书写技法的展示之外,还能流露其人品、性格、学识等精神层面的意蕴,故“书为心画”成了评价书法作品的口头禅,正如苏轼所说:“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项穆《书法雅言》说得更明白:“故论书(字)如论相,观书如观人,人品既殊,识见亦异。”字,不论形态如何,都看得出写字者的精神心态,如酒后有醉书,欢喜有狂书。颜真卿的字必然“忠义贯日月”,而赵孟頫的字固然圆转流利,究竟不能摆脱其奴颜媚骨的品相。明末清初医家傅青主,他先学赵字,因恶其“心术坏而手随之”,后改学颜体,并为颜鲁公气节所震撼,遂作字风格遒劲,气势磅礴,成为影响书坛的大家,堪称“字如其人”的典范。
中医开方,多是汉字,除“字如其人”的效果外,尚有“方如其人”的意义。中医之所以能够历千年而顽强地传承发展,是因为其与掌握这门学术的人精神气质、学问修养的紧密相联。古往今来,大凡名医,皆很重视处方书写,其中追求书法功夫者也不乏其人。如东晋著名医家葛洪,他为天台山摩崖石刻写的“天台之观”,被米芾尊为“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南北朝医家陶弘景,他留在镇江焦山摩崖石刻上的《瘗鹤铭》被黄庭坚误为王羲之所书。近代名医丁甘仁、恽铁樵、施今墨、秦伯未、程门雪等,书法皆臻上境,他们留下的处方笺,多被收集珍藏。上海十大名医之一的顾筱岩曾说:“字是一张方子的门面,是一个医生文化底蕴、学识才华的外露。”
的确,处方字迹之优劣是给人的第一印象。旧时中医带徒,入门之前常强调四句话:“一手好字,二会帮忙,三指切脉,四季衣裳。”这第一句就要求把字写得工整无误,是很有道理的。对于写字,不是要求每个学中医者都成书法家,只要平正,认真即可,这种要求并不高,稍加重视都是可以办得到的。然而就有一些医者,一旦提笔便心浮气躁,如同有人赶他似的,写出来的字张牙舞爪、龙飞凤舞、东倒西歪,或笔画不清、墨迹难辨,或随意简化、生造滥用。这种处方,不用说别人不认识,就连他自己有时也会难辨,在患者心里是啥滋味?一句话,“天书”,给人以轻浮放荡的感觉。作为医生,如果是这种态度,试问,谁敢把“至贵之性命”交给他打理呢?
当然,有人会说,而今有电脑,开处方不用手写,只需手指一敲,处方就搞定了。字虽是印刷体,但也能从处方内容中表露医者的业务水平。一个熟读经典、精通医理的医生,开具的处方一定是理法清晰,并依法遣方,加减配伍,有理有据,可从方中看得出为医者对基础知识、各家学说掌握的情况,倘《温病条辨》都未通读过,他肯定开不出半苓汤、双补汤的处方来。
还有,从一张中医处方可以看得出医生的临床思维情况。有人处方用药动辄30~50味,甚至更多,美其名曰“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或曰“寒热并用”、“攻补兼施”,但完全看不出如仲景乌梅丸一样的组方法度,也看不出方中君臣佐使的关系,这只能说明开方者头昏脑胀,到底要想解决何种问题,他自己也不清楚。
除此之外,从中医处方还能测知医者跟踪学术发展的能力。例如对传统认识已有所更正,或者对某一理论问题有所创新,或某些方药有研究成果、又被学术界所公认者,但处方者全然不知。这种情况至少说明医者平时不读书刊,又未参加学术交流。
更有甚者,在处方中出现与证候病情毫不相干的药味。如不需搜风通络,不必消肿破癥,也没有通经下乳的要求,方中用上穿山甲,且剂量不小;或迎合患者保健之意,虽胃胀腹泻,也人参、阿胶、虫草、鳖甲并进……。此醉翁之意不在酒,涉嫌另有他图,从处方中可窥见其人品与德行……,行业中的斜门歪道、潜伏规则也暴露无遗了。
古往今来,名家医方墨迹为人们收藏之珍品,病家也有保留处方的习惯,目的在于记录诊疗过程,有的效验之方可在民间沿用多年,在传抄过程中也会把某些不雅的痕迹留了下来。如果你经常悬壶开方,黑的写(打)在白纸上,又签上你的大名,这处方满天飞舞,城乡传遍,数年后遭人评点与非议,当作何感想?!
故“方如其人”,此非小事,当需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