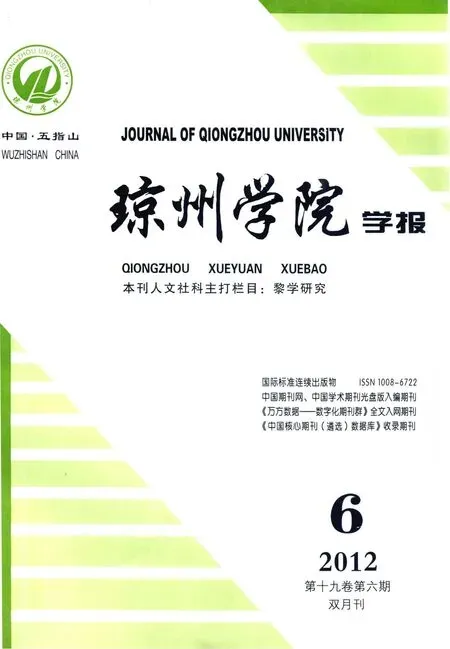从伊迪丝·华顿小说中的城市女性看其女性观
李银波
(湖南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华顿在其三部重要小说《欢乐之家》 (The House of Mirth,1905)、《国家习俗》 (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1913)和《纯真年代》 (The Age of Innocence,1921)中塑造了三位新城市女性形象,真实再现当时“老纽约”这座城市中女性的处境,叙写了城市女性在不幸生活中所经历的心路觉醒历程。
一、不愿做装饰品的丽莉
在小说《欢乐之家》中,女人被认为是一个装饰品、男人财富的象征。然而女主人公丽莉由于塞尔登的“精神王国”开始不愿做装饰品,最后以死来获得新生,她的女性意识还不够强烈去成功反抗男权体制,但向社会控诉了男女不平等,并表明她的自我意识觉醒处于萌芽状态。
(一)装饰品命运的丽莉。“丽莉·巴特Lily Bart这个名字本身就暗含有'装饰'的意味,也正是她身份特征的体现。Lily是百合花的意思,极具装饰品意味;Bart中也含有‘艺术 (art)’的成分,同样暗示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物品,一个装饰品” (李希萌,2008:143)。丽莉从小就被教育成用脸蛋去换回一切的“装饰品”,在婚姻交易的市场上,她成了男人们关注的目标,而男人们也只把丽莉当作装饰品,垂涎于她的美丽,展开攻势,但在欣赏她的美的同时,无动于衷地欣赏她的悲哀和痛苦。比如,丽莉的美吸引着富裕却胆小俗气的古莱,他想娶丽莉,却又轻易动摇、放弃。在旧纽约上流社会中,丽莉只是一个装饰品、别人的玩偶、局外者,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女性意识萌芽的丽莉。丽莉有好几次可以嫁给有钱人,进入上流社会,享受荣华富贵。古莱、乔治、罗西德都可以满足她的物质需要,提供她足够的金钱让她购买梦寐以求的奢侈物品,但她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为什么她错过那么多机会?主要原因是劳伦斯·塞尔登的出现,他的“精神王国”唤醒了丽莉心中对精神家园的渴望,使她认识到自己精神的荒芜,一次次错失婚姻和财富。塞尔登告诉她成功是一种解脱,“解脱一切——从金钱、贫穷、安逸享乐与烦恼、从一切物质生活中得到解脱” (EDITH WHARTON,1984:137)。这句话显示出男主人公身上的叛逆。“他们渴望能摆脱一切社会约束,挣脱旧的家庭观念的桎梏,超越物质享受的层面从而能够走进那个无比开阔自由、不为尘世所牵缚的‘精神共和国’之中,实现灵魂和内心的自我完善” (李希萌,2008:143)。塞尔登认为精神王国是完全抵制物质,拒金钱于千里之外。在丽莉的价值观念中,物质并不是唯一的,但她从未发觉自己内心对精神家园的渴望,是塞尔登的“精神王国”理论让她真正听到了自己的心声,寻到了方向。
(三)获得新生的丽莉。“理想王国”是莉莉的奋斗目标,但她进入不了“理想王国”,因为塞尔登的“精神王国”是虚伪和虚幻的。“塞尔登的超然物外是建立在有物可依的基础上,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可以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只不过是他自己幻想的空中楼阁或者说是他灌溉清高自傲的秘密花园罢了” (张文凤,1998:51)。丽莉不想屈服于现实,最终付出了生命来保持清白和尊严。丽莉在与世态炎凉的世界再见之前才明白,与贫穷相比,内心的荒芜、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更可怕。丽莉的死在精神上是获得了新生,是带来拯救的死,因为她已深刻体会到社会的冷漠以及自己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塔妮亚·莫德莱斯基指出,“死亡可能是个非常有力的武器,能用它来报复那些‘不欣赏我们’的人。” (TANIA MODLESKI,1982:19)丽莉以死回击了在个人价值观和财产价值观方面都不欣赏丽莉的塞尔登,对所谓的文明城市进行了控诉。精神赋予丽莉魔力,指引她踏上精神的归途,她是一个在道义上、精神上的胜利者。
二、掌控婚姻的安丁
《欢乐之家》中的丽莉具有朦胧的女性意识和追求自由的天性,但没有认清现实,总是优柔寡断、错失良机,没有为自己的幸福想出更明智的方法而勇敢奋斗;那么《国家习俗》中的安丁则打破了女性软弱的固有形象,但还是依赖男性和婚姻等手段,走向了另一极端。
(一)不满的安丁。以往的女性知难而退、惟命是从,而安丁则以莫大的勇气和毅力迎接挑战,扫除一切障碍。安丁一旦认定目标,绝不放弃,果敢行事。连拉尔夫也不得不承认,“提出切实可行建议的往往是安丁,没有任何顾虑可以动摇她的信念。” (EDITH WHARTON,1995:103)遵循着永无止境的欲望,安丁甩掉几任丈夫。她选择了不同寻常的方法去掌控丈夫:一次次地结婚,又一次次地离婚,企图通过三次婚姻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了得到通往旧纽约上等社会的通行证,能生活得像上等社会的夫人一样,故意与出身于名门望族的拉夫尔相遇、结婚。婚后不久,与马维尔的生活变得枯燥变得不满时,决定离开他,独自去法国嫁给侯爵德·谢耶,第二次婚姻让她既获得财富又取得地位。然而,不久又不满于现状,厌倦适应了封建贵族的要求,并有了更高目标。于是,毫不犹豫的与第二任丈夫离婚,嫁给亿万富翁的同乡埃尔默。然而,不满的乌云盘旋在她头上,小说的结尾暗示安丁对第三次婚姻也暗怀不满,想成为大使夫人。安丁的结婚、离婚实际上是用身体在婚姻市场上做交易,这是对当时只有男性才有离婚权这一习俗的反抗。
(二)安丁的局限。与软弱善良的丽莉不同,安丁的一切行动从利己出发,现实而精明,为达目的不惜付出一切,丝毫不考虑道德准则。为进入“老纽约”的上流社会,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貌,运用娴熟的交际手段游走于几位男士之间,对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从不善罢甘休。金钱和舒适的生活才是她唯一追求的目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安丁是“一个精力高度充沛、野心勃勃的人。她没有自我,除了渴望占有更多的金钱和拥有更舒适的生活之外,她的脑袋空空如也……”。 (McDowell,1974:35)在她眼中,父亲是她永远的靠山,丈夫是她攀爬更高山脉的楼梯,孩子则是绊脚石。与丽莉相比,安丁缺乏女人该有的内涵和基本伦理道德,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安丁给“老纽约”社会带来新的活力和变革,但不择手段对传统文化、道德规范造成了巨大冲击” (潘建,2002:162)。安丁的不满看似成功,但缺乏素质和自己的金钱,唯一的选择是成为某人的妻子;安丁很理智,但会模仿别人,伪装、扮演角色。因此,华顿心中最理想的新城市女性不是安丁,她还需继续寻求一个更符合她标准的新城市女性。
三、反叛的艾伦
在小说《纯真年代》里,艾伦具有独立人格,追求自由,不愿是男性的附属物;敢于挑战男权制度,与社会习俗背道而驰,最终,她竭尽全力,自由定义着自己的人格,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有自尊、自强意识的独立女性。
(一)反抗社会习俗的艾伦。艾伦对“老纽约”传统女性角色、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及社交圈中纷繁复杂的陈规旧习进行了大胆挑战。华顿并未在艾伦的心理活动上着墨许多,只是描述艾伦不同的穿着打扮、房间部署、言谈举止和爱情选择,多次公开反叛社会习俗的行为向读者揭示:艾伦是一位决然反抗社会习俗的新女性。
首先,艾伦时常穿着尽显气质的性感神秘的深蓝色丝绒面料的约瑟芬式长袍,美丽而性感,具有异国情调“她穿着这一身奇异的衣服,十分引人注目……她肩膀和胸部露得比纽约社会习惯看到的稍稍多了一点儿” (EDITH,1996:69)。艾伦吸引着纽约上层阶级名流如博福特、范德卢顿之辈,也让自命清高的纽兰·阿切尔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当时,女性的精神被束缚着,身体则被不自然、不实用、紧促的衣服约束着,生活无趣又无助,被男性观赏着,艾伦则用奇特服饰体现不同的品味和情趣来反抗习俗。再者,华顿多次详细描述了反映艾伦独立人格和思想独特房间:“这屋子自有一种幽冥淡雅的魅力,与他熟悉的任何房间都不相同……通过巧用几件道具,转手之间竟改造成一个具有‘异国’风味的亲切场所,令人联想起古老的浪漫情调与场面” (EDITH,1996:56)。纽约上流人士注重言谈举止恰当得体和“体面”的生活原则,害怕丑闻甚于害怕疾病。但艾伦反其道而行之,公开评论一位公爵是她见过的最蠢的男人,范·德卢顿家的住宅阴森,讽刺那些权贵的狰狞、狡诈的面孔,凸显叛逆。
(二)追求自由的艾伦。在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下,艾伦对丈夫的恶行从来不忍气吞声,不向命运低头,敢于与不公平社会习俗和价值取向挑战。她很想“获得自由”,很想“彻底摆脱过去的生活,清除过去的一切” (陶茜,2000:293)。当时的社会习俗拒绝离婚,所以整个社会附庸风雅,排斥她的勇敢行为。艾伦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做驯服的妻子,继续做他者,还是冒险追求自由,受尽指责?她选择了自由和尊严,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她正视爱情和道德,适时放弃。艾伦用自己的方式保持了做人的尊严,对社会进行抗争;她不像安丁全然不顾伦理道德,她诚实、忠诚、善良,让梅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让其儿子有父亲的陪伴,她却回巴黎独自终老。艾伦与纽伦分开之后,他们的爱情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彼此把这份爱珍藏在内心深处直到死。至此,在精神上取得自立自强的艾伦才是华顿心目中理想的新城市女性。
四、结语
在三部小说中,华顿关注城市女性生存状况,揭示社会行为准则与习俗对女性情感、智力发展的压抑与束缚,审视女性反抗心理历程。丽莉的自我意识有所觉醒,但仍逃不过悲惨命运的安排;安丁的不满看似成功,但仍要依靠婚姻和丈夫来成就自己,并且不顾道德规范,走向了极端;艾伦敢于与传统习俗反抗,自由定义自己的身份,赢得了独立的人格。华顿的城市女性形象从丽莉到安丁、再到艾伦,完成了一个从萌芽到极端再到自由定义的升华,这是华顿女性观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暗含着她对理想城市女性的探求,城市女性应该像艾伦一样敢于与传统习俗反抗,追求自由,完善自己。
[1]李希萌.《欢乐之家》中华顿对男性权威的解构 [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报,2008,[02]:142-146.
[2]EDITH WHARTON.The House of Mirth [M].New York:Bantam Books,1984.
[3]张文凤.“精神共和国”的失败者和胜利者——《欢乐之家》女主人公形象评析 [J].柳州师专学报,1998,[04]:50-54.
[4]TANIA MODLESKI.Loving with a Vengeance [M].New York:Rutledge,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