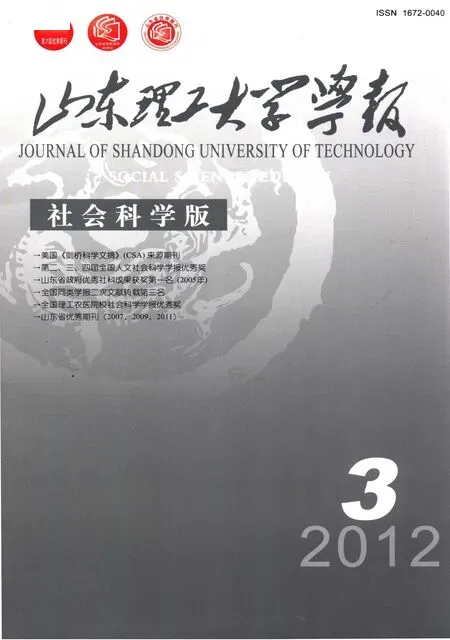书法产业化背景下为展览而创作的偏失
马鸿民
(天津商业大学艺术学院,天津300134)
一
“书法产业化”是近两年提出的新词语、新概念。“产业”本属经济学范畴。当书法艺术已经不仅仅作为欣赏用途,还衍生出分类详尽的艺术创作、教育培训、作品展览、销售、收藏、拍卖、投资等多方面的配套产业时,“书法产业化”便风生水起了。
书法产业化实现是以书法创作、展览、代理、宣传、营销、拍卖、收藏、投资等为关节点的配套产业链,在相关法律法规制约监管下进行有序的市场化运作,被认为是21世纪中国书法的发展方向。当今社会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和大众性的消费模式是艺术产业的主要运作模式。艺术产业与生俱来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它要受到艺术、经济这两个领域双重运动规律和发展逻辑的作用。书法艺术作品的丰富的价值特性,不仅取决于作品本身,更取决于包括经济、文化、政治、道德在内的社会性话语的介入。“经济话语对艺术的介入、渗透与覆盖,就是在艺术与社会生活前景中愈来愈突出的一种历史现象”。[1]334在西方,从古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寄食制,到十八、十九世纪的国家资助,再到20世纪的企业基金支持,不少艺术家得以摒弃公众和流行作为价值标准,与此同时,对读者、观众等艺术公众和艺术市场的依赖也与日俱增,并逐渐成为富有生命力的新的艺术文化话语。“这倒不是说这之中在艺术内部有强烈的经济动机,而是说,是日益发展的社会现实在事实上把一种商品化的无选择性的处境交给了整个世界,交给了别无选择的艺术家”。[1]337
任何艺术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和具有何种社会价值,决定着这种艺术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状态与前景。书法艺术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是艺术家们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的问题。这种情况和环境也促进了书法创作主体思想解放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使人们的生存内涵得到丰富,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得到结合统一,书家的个性得以张扬,将时代气息自然地融进书法。书法从单纯的士文化、雅艺术审美形式,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并由过去的士文化、雅艺术,向大众文化、通俗艺术转变,从精英文化向民间化、大众化,分流、发展,书法受众日益扩大。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涵盖范围不仅仅是书法创作过程、创作群体、展赛活动等小圈子,而应指向更广范围的文化的、社会的意蕴,应辐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书法业内各种活动被引入产业化范畴,使各类书法展赛及书法相关各类活动与“产业”、“市场”结合,在文化产业大背景下书法展赛、研讨、雅集、会议等活动的内容、形式上寻求探索与革新,这对书法的发展和艺术价值的体现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
书法产业中的供求流通体系由生产、推介、营销、接受等主要链环构成。生产方由书法创作个体、群体等构成;推介供销部分包括展览、展厅、文化推广等;接受终端指广大的书法需求方以及社会上与书法相关的消费需求方。其中展览是书法产业的重要一环,对推动书法产业化作用异常凸显。
虽然经济贸易类展览也具有传播功能和作用,可以被用作传播媒介,但是就其根本作用和性质而言,经济贸易类展览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书法展览是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和传播媒介,通过书法展览使得受众与发送出来的艺术信息完成面对面交流与沟通。随着整体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书法从私人空间走向公众空间,展览作为一种全新、优质的展示方式,成为当代展示书法的必然选择。书法展览一方面成为作者向社会展示其作品的最佳途径;但另一方面书法展览也左右了作者的创作理念,进而影响公众的审美价值取向。
虽然书法展览是一种展览性传播,但随着书法产业化的展开,书法展览的市场特性越发凸显,这充分体现展览是经济交换(流通)的一种形式,展览曾是人类经济交换的主渠道现在仍是重要渠道之一。书法展览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古已有传承有序的文人“自娱式”的创作观,让书法在创作上更加注重“艺术表现”与“市场效应”;而且“表现与市场”往往相互生发,只有上佳的“表现”,才能有丰厚的“市场”回报。
无论怎样,艺术和艺术家的意义总存在于其艺术活动和现实、历史、传统的相关性之中,我们虽然不必说经济规律强制性地支配着艺术观念与行为,但艺术与环境、艺术与社会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不能否认的。在商品时代,艺术家受制于社会功利氛围,在社会的经济的压力诱使驱促下,努力使自己的观念合乎公益世界与经济规律,也是极其自然的。“即使是在一种与世隔绝的审美静观的状态中,也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是与世隔绝的。因此,当我们考察整个知觉系统时,所谓的与世隔绝很难具有实质性意义、在决定性的水准上它其实并不存在”。[2]345
三
书法从古代文人小范围内的展示,到当代大型展览,书法所处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根本上的变化。新的传播方式必然对书法创作进行反向的引导和影响。当代书法创作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都是与书法传播方式的市场化乃至整个文化环境息息相关。书法展览的导向正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书法创作。以往书法创作中对功力和艺术修养的依赖逐步被作品的表现形式、市场意识的经营所置换。随之而来的是创作观念、心态、目的的极大改变。书家将展览当作检验、展示自己书法创作和获得艺术与市场双赢的一种主要方式。书法为展览而创作,为市场而展览,书法创作重形式表现,而乏功力、缺内涵、少自然,这些都对公众审美期待和共鸣造成挤压,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首先,出于“竞技”的性质规定,出于广泛地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宣传的需要,创作者力争使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因此“形式”被书家推到了历史以来最自觉的高度以契合“展览至上”。书法创作的幅式普遍向大幅、巨幅发展,条屏盛行,追求书法作品幅式的大规模化。与之相应,小幅作品也为追求展厅效应,划分若干块面,上下左右相续而成大幅。这反映了传统的幅式(如尺牍、文稿之类)不得不作顺应性调整。作品中较多地出现了色纸、框格,多印章,仿古格式,纸张染色做旧等层出不穷。从书体角度看,行书及行草书的艺术表现性较强故而盛行,其书体结构、墨色变化灵活。大篆、甲骨文既因其字形结构意趣多变,亦出于表现形式上的避难从易,也为书家所青睐。具体到书法的笔法、字法、章法、墨法,偏重于形式感强烈奇异的倾向也十分突出。诸如此类,形式表现之潜能得到极大发掘与发挥。
创作形式的变更只是一种花样的翻新,这种为满足欣赏者视觉暂时愉悦所采取的做法仅仅是表面化的不断升级,而并非艺术风格的深层次展现。如果“因为那穷奢极侈的人尝试过一切方式的享受,对他来说不再有什么新的享受了”。[3]140
形式刻意追求折射出功力的缺乏。功力的缺乏和对传统的漠视,使得诸多展厅作品最基本的笔墨荡然无存,作品中既没情感,又无神采,只有僵死的线条。“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4]62神形兼备当为书法不二法门。
艺术创作需要长期的技巧法度训练和对传统精神的把握,仅靠外在形式的新颖,无异于买椟还珠。歌德认为“见识和实践才能要区别开来,应该想到,每种艺术在动手实践时都是艰巨的工作,要到纯熟的掌握,都要费毕生的经历”。[5]79唐代孙过庭认为自己“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昧钟张之馀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4]125显然当今绝大多数书法实践者缺乏对功力积累的重视。明代书论家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说:“古人醉时作狂草,细看无一失笔,平日功夫细也”。[4]551
歌德在1825年谈到当时的艺术创作的现状时认为:学习先于创作,应集中精力搞专业。“如果尽早使每个人都学会认识到世间有多么大量的优美的作品,而且认识到如果想做出能和那些作品媲美的作品来,该有多少工作要做,那么,现在那些做诗的青年,一百个人之中肯定难找到一个人有足够的勇气、恒心和才能,来安安静静地工作下去,争取达到已往作品的那种高度优美。有许多青年画家如果早就认识和理解到象拉斐尔那样的大师的作品究竟有什么特点,那么,他们也早就不会提起画笔来了”。[5]77这段话对今天的书法创作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
其次,任何一门艺术必然涉及到内容和形式。席勒在谈到二者的关系时说“目的和形式之间,关系极为密切。形式由目的决定,并由目的规定必须如此,而目的得以实现,则是形式相宜的结果”。[6]50从艺术创作过程来看,艺术家总是先有一定的内容,然后才选取适当的形式,总是先考虑反映什么样的社会生活,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揭示什么主题,然后再根据内容的需要,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完美的形式,能够帮助内容的充分表达,增强作品内容的艺术感染力。在创作的过程中,艺术家在致力于创作形式时,同时洗练着内容,形式更加完美,内容也更加完善。当我们被某一完美的艺术形式所吸引时,并不觉得仅仅是受到形式的感染,而同时深深意识到包含在形式中的艺术内容。
一味强化展厅效应即视觉刺激的强度,热衷于书法的形式与技巧,在展厅适应性、迎合性上出奇制胜,势必会只注重表象而忽视内涵的充实。“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4]713形式、技巧的出新应是艺术家在为表现某种自我精神境界的追求中自然产生的。精神内容贫乏的作品虽然在形式表象上能使观者在视觉感官刺激上产生一定的新鲜感,但不能从精神意蕴上深深打动观者。
书法的“高韵深情、坚质浩气”,主要来自书家个性气质、道德情操以及所书内容的文学情境和与之相应的情感的共鸣,是书家个性精神与审美理想的艺术表现。如刘熙载所论:“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4]715书家通过毛笔起伏顿挫、轻重徐疾各种变化,产生不同的势感、形感、质感的线条,从而表达自己的情感、格调、意向和神采。书法的内容是书法家沉积于心灵的“远取万物、近取诸身”的体验,是与书法家的个性、学识修养,与当时的情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还与书法家的功力密不可分。这样“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4]126也正是基于此,书法才能成为艺术。书法的品位和持久感染力也在于此。
为了掩盖自身功力的不足和内涵的匮乏,徒以外在形式取悦,以最短的时间出最高成效,当是市场化影响下,寻求耗费少而收益多的经济学意识的折射。但所有的这一切都在使自己逐渐远离书法的本真。作品的深沉微妙处只有在静心品味时才能获得真切的感受。展览效应造成了当今书法创作普遍浮躁而热衷形式效果的取巧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当代展厅书法主要对明清书法,特别是明清大尺幅书法的效仿。明末清初特定历史时期下,书坛出现了一批个性张扬和不拘成法的书家,他们用书法来抒写个性自由,展现思想和内心情感,追求奇绝,表现“拙”、“丑”,反对因袭古人,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以往对于书法语言的审美习惯。明清书家创作的成功在于张扬自我的外在形式语言和丰富的内在人文精神内涵,在作品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艺术表现成为其创作主旨。但他们作品中的“拙、丑”被当代书法创作强化、夸张。这固然显示了当代书法审美空间的拓宽,但又往往由于作品内涵的苍白和功力的缺乏而失之于“丑怪”。
同时,现代书家为追求作品的视觉冲击力,把西方美术中的艺术构成理论引入书法作品中,肆意制造各种矛盾。正是由于这种刻意的做作,造成对自由意识与自性本真的遮蔽。作品中存在的夸张对比造成的并非康德所说的“崇高使人感动”[7]3的感动。“崇高必定总是伟大的,崇高必定是纯朴的”。[7]4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也说:“丑就是不成功的表现。就失败的艺术而言,有一句看似离奇的话实在不错,就是:美现为整一,丑现为杂多。”[8]479
当代书法家效仿明清书法,为追求展厅效果与市场效应,把书法作品的分量等同于物质材料的大小,把物质材料的“大”等同于精神的“大”。书法家的创作所选择幅式的大小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天然默契的选择,是对幅式大小“度”的恰当把握。书法家对于审美价值的理解决定了他们的创作行为,创作境界决定艺术作品语言形式,进而决定尺幅的大小。一个缺乏驾驭大幅式作品的书法家,其作品所承载的信息必然是消极的、矫揉造作的,无法看到书法家本人的生命体验。托尔斯泰说:“洞察一己之长,或者更确切地说,洞察非己之所长,这便是主要的艺术。”[9]127书法作品外在的规定性必须与内在精神层面的因素紧密地联在一起,欣赏者才能看到作品整体性的效果,感受艺术所带来的精神愉悦与升华。否则就是孙过庭《书谱》所批评的“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谬哉”![4]125
书法作品说到底是一种精神的产品。书法展览也好,书法产业化也罢,书法是精神产品这一点不能被消解。魏晋以来的经典作品大多都是尺幅较小的简札、册页、题跋,虽然简短,却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笔墨功力,充满了作者的个性与才情而日久弥新。这些作品是后人无法回避的,甚至是无法超越的。作品中呈现出高远、深邃、丰富的精神空间,蕴含着创作者兴犹未尽的高峰体验。如南北朝刘勰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现,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10]256作品神采焕发,情趣盎然是许多大幅式作品所不能比肩的。
此外,书法语言讲求点线的节简含蓄,舒朗通透,避免冗长。在这方面,明清书家创作中大多是繁笔疾书,以展现压抑、强烈的内心,这已失之于简静。当代书法家更缺乏这种简静心态,加之功力的缺乏,致使抒情阻碍,疏远了象征、暗示、隐喻这些书法不可或缺的语言特征。列夫·托尔斯泰在谈到艺术创作时说:“朴素,这便是我所希望的比其他一切更紧要的品格。”[9]122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书能笔笔还其本分,不消闪避取巧,便是极诣。”[4]705此外,中国书画讲求“师法造化,中得心源”、“道法自然”,只有当作品达到了自然的状态、是自然的流露时,作品才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和境界。再大的尺幅,如果不是自然的表达,而是强意为之,都很难产生持久的感染力。林语堂在阐释中西艺术精神时说,“西方艺术的精神较为耽于声色,较为热情,较为充满艺术家的自我;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高雅,较为含蓄,较为和谐于自然。”[11]284我们这里并不是排斥、否定西方艺术精神,而是说如果书法中没有了含蓄、自然,书法的内涵就所剩无几了。
第四,书法为展览而创作,为市场而展览,使得书法创作重形式表现,而乏功力、缺内涵、少自然,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公众对书法本应有的审美期待与审美共鸣。
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以高雅艺术形态呈现出来的书法,已经不再占据文化生活的中心,有了审美泛化的趋势,表现领域不断拓宽。“大众文化是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12]8大众文化本身就具有功利性、世俗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等多方面的特征。使得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书法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冲击。
我们无法否认艺术创作的个人化指向,但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忽视公众的存在,在艺术家开始创作之际,公众的艺术趣味以及对即将塑造的艺术形象类型的可能性反应,都成为艺术家表达尝试的重要参考值。“严格地说来,‘个人的艺术’这几个字,虽则可以想象得出,却到处不能加以证实。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民族,艺术都是一种社会的表现,假使我们简单地拿它当作个人的现象,就立刻会不能了解它原来的性质和意义”。[13]39“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和虚构的纯粹娱乐,它总是保持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并努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去改变对现实的知觉”。[14]154
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没有接受主体的参与和响应,任何艺术活动都是潜在的甚至是不完整的。作为接受主体的观众是艺术家作品的二度阐释者,但他们对艺术品的接受不是机械的接受,而是对艺术家体验的接受与升华。书法艺术从创作到鉴赏这一审美创造过程中,艺术家与公众应当处于一种良性合作的对话与交流中,这种对话交流既是显性也是隐性,是双向互动的循环流动。这无疑是对优秀作品而言的。“艺术接受的最高旨归是实现人性的复归和人性的重建”。[15]268
从艺术公众角度看,面对一件优秀艺术作品,一个有审美知觉的公众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作为鉴赏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愉悦即是审美享受。公众被艺术作品里的思想感情、艺术形象所打动,从而形成审美高峰体验;与艺术家在情感、趣味、理想达到较高的共振与沟通;审美共鸣使鉴赏者处于一种愉悦、和谐的审美情境中。公众的情感在共鸣中得到调节、慰籍、疏导和升华,公众进入艺术作品所营构的审美境界,异化的心灵得到纠正,扭曲的人格获得升华,精神上得到解放,这是一种生命智慧的飞跃。公众在挖掘、追寻艺术的深层意蕴中,达到了彻悟的审美境界。“文学艺术具有一种减轻心理压迫的功能,所有的艺术归根到底是一种抚慰,而这种抚慰主要的是来自于作品给予读者的种种解决办法,而这种解决办法必定是和读者的期待方向相一致的”。[15]299康德说“快乐是生命力被提高的感情,痛苦则是生命力受阻的感情”。[3]138公众欣赏艺术应该获得的是快乐而不是痛苦。
中国书法已经历数代,在受众中形成了广泛的审美心理共鸣和审美期待,异类的艺术样式,即使建立在深厚的内涵基础上,尚且对此期待与共鸣产生冲击,何况缺乏内涵的光怪陆离的作品,对受众审美期待的挤压与变形便可想而知了。当欣赏个体将自己的规范、标准、目标、价值取向与此类光怪陆离艺术作品中的“理想榜样”执着地联系在一起时,并对此类作品长期模拟中,个体自觉不自觉地“修正”自己的感悟、体验并与作品中的取向相参照,迟早会诱发艺术心理的片面发展。这是一种虚假的变形的审美接受。接受者尤其是艺术认知结构不尽完善的接受者,可能会一味地与这种扭曲的审美期待进行认同,而产生“共鸣”由此进一步导致审美期待的变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认知失调”理论。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环境、个人以及个人行为的,认知、观念和信念的总和,是一个有结构的认知系统。各认知元素之间存在着相应的特殊联系,它们之间一旦出现不协调,就会导致“认知失调”,主体会产生不适、不悦、紧张、焦虑和忧郁等不良情绪反应。认知失调和由之而产生的情绪的无序反应主要因为接受主体原先的接受容量、类型与接收对象之间的不匹配或冲突。当代书法创作的异样形式并伴随通过发达的传播工具,更使得接受个体无以应对。这种信息对特定的个体往往是过量的、突兀的,这已经超出了艺术接受的意义之外了。接受所构成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世界。英国艺术心理学家柏西·布克也说:“美学方面,是一个情感和想象的领域,这个领域包括人类幸福的总和——有增进幸福的,也有减少幸福的”。[16]135当代书法创作更多的是“减少幸福的”。书法被当作只有少数艺术家才能“理解”的“抽象表现”和孤芳自赏,则书法的真义也就荡然无存。就像托尔斯泰所说,“当艺术不再是全体人民的艺术并且变成富人的少数阶级的艺术的时候,它便不再是一项必需的、重要的事业,而变成空洞的娱乐”。[9]40
当代书法创作的市场意识、功利思想使得书法作品技术观念强于艺术观念,对形式敏感,对意境迟钝。这既是由于创作者文化修养、哲学与美学修养欠缺,也是书法功底积累不足所致。书法家在面对书展而准备的作品,不可能以一种志气平和的创作心态对之,功利心理上升到主导地位,由素质型创作向应试型创作心理转换。“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4]126乖合之间,天壤之别。如果书法创作的目标市场化、动机功利化,这样的作品缺乏高雅纯正的文化精神内涵的支撑,很难成为歌德所认为的培养“出我们所说的鉴赏力”的最好的作品。“这样才能培养出我们所说的鉴赏力。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估价不致于过高,而是恰如其分”。[5]32
四
书法产业包括在文化产业范围之内。文化产业化使得文化被更多地赋予了市场性。文化对社会是有教育教化作用的,过分强调了文化的经济价值,就必然掩盖了文化的教化作用,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就会忽视文化的精神内涵。书法艺术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它是民族传统文化最凝练的物化形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得以传承和发扬的一种重要方式与途径。只有承载时代文化精神和传承传统文化精神的书法才能在指向更广范围中彰显价值力量。
需要承认书法产业化使得书法生存与表现形态有了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形成了书法的利益机制,促进了书法的流通,使书法的发展从此转入多元化和向民主化发展的轨道。“孤立的、与生活不再发生关系的艺术作品,不管它如何迷人,总要成为一件无用的玩具,注定会失去它的人文价值”。[2]17艺术品创作一方面必须严格与现实世界相分离,在一种内在的操作之中孕育完美;但另一方面,艺术又在将对象材料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符号系统的同时,强调有效地把握现实事物的整体性特征。在找寻适合于新时代的新工具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在并不放弃历史的审美裁判与艺术的审美话语表达的同时,适应并接受文化市场规律的选择。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心灵”。[9]11书法创作应该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人格魅力的自然展示、人文精神的自然体现。这才应是当代书法创作追求的终极目的。因此我们说书法产业化的目的不是“去书法化”,而书法创作的最终目的也不能在产业化中消解。
[1]丁亚平.艺术文化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2]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德]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5][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德]席勒.席勒文集(理论卷)[M].张佳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德]康德.论优美感与崇高感[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8]伍蠡甫.西方古今文论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9][俄]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M].戴启篁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2.
[10]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12]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3][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4][法]马克·第亚尼.非物质社会[M].滕守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15]童庆炳.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6][英]柏西·布克.音乐家心理学[M].金士铭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
[17][匈牙利]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M].居延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