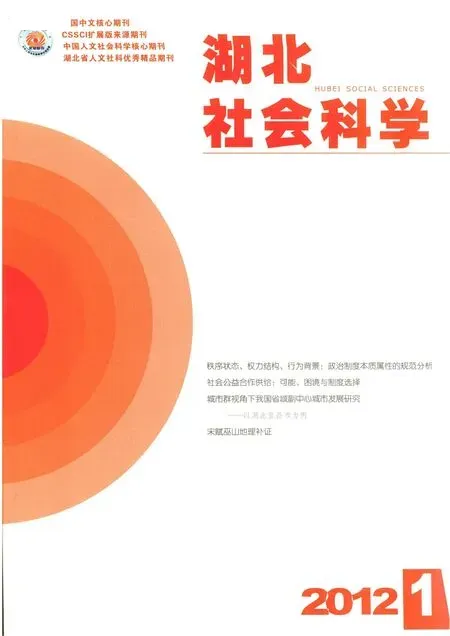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向度
屈 平
(河南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向度
屈 平
(河南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从作为一门隶属于逻辑学的技艺学开始,到今天发展为主流的哲学解释学;从规定如何解释特定文本的具体方法,到今天完成解释学的“哥白尼革命”;从局部解释的技艺和规则的汇集,经过方法论的普遍化和科学化,到对理解元理论问题的本体论变革,解释学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从后现代的观点看,认识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消亡。那种认为传统理性是人类知识的牢固基础,并试图证明它超越人类局限并与它所指的现实相符的努力,在后现代语境下不过是美丽的谎言。传统认识论要求的清晰、准确和完整在人文领域被证明是空想。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认识论是一个需要解构的传统。
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激进;有限性;解构
海德格尔说:“某物的是必须与另外的是结合才能使自身的是变得明确。”[1](p43)根据康德的命题分类,“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向度”是综合,它是“某种解释学是后现代主义的”压缩。在综合中,谓项包含了解释学的一般概念里所没有实际想到的东西——后现代主义。因此,“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向度”需要别的证明来确定,它能增加“解释学”这一概念已有的知识。那么,增加了新知——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是什么样的解释学?在此,我们权且称之为“激进解释学”。[2]虽说“权且”但也有道理,它的根据是后现代主义激进的反基础主义或“反元叙事”。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后”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一种反基础主义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3]按照利奥塔的逻辑,现代主义的本质是传统认知论的元叙事,它追求客观、普遍、必然和确定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终极性在于预设的抽象理性;而后现代主义则解构元叙事,它不承认事先设定的理性,认为这样的形而上学不仅是虚无主义的根源而且直接导致对存在的遗忘。[4](p2)显然,前者是知识的绝对论,后者是知识的相对论。以海德格尔的解释现象学观之,传统认识论无非也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建构解释学,是回归逻各斯(绝对理性)的解释学。这样看来,认识论只是解释学的一种形式。因此,从后现代的观点看,认识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消亡。那种认为传统理性是人类知识的牢固基础,并试图证明它超越人类局限并与它所指的现实相符的努力,在后现代语境下不过是美丽的谎言。传统认识论要求的清晰、准确和完整在人文领域被证明是空想。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认识论是一个需要解构的传统。
一、解释学转向
承认认识有中介还是无中介是区别认识论和解释学的关键。众所周知,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意义的世界,它教会了我们一切。尽管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如希望的那样清楚地区分了世界与自然,但谁又能否认:甚至最无所事事的人也不是靠本能生活的。事实上,我们的世界早已被我们继承的以及我们创造的各种观念和现实充满。我们是在意义中为自己赋予了一定的形式和内容。
与解释学的必然性对应的是某个假定的必然性。该假定即为人文科学不是必然的,它是意义的产物,人类历史的大量内容先于它的发明。但要给作为意义化的人类生活冠以科学之名,那么,该科学必然是解释学的科学,而且它的主题观念和实践一样具有解释学的循环性。也就是说,人文科学是以解释学为前提的解释,即解释的解释。
为了求得认知的无介性,即排除认识的解释学成分,胡塞尔提出了现象学还原:放弃对现象世界的自然立场,通过将思维与现实的关系放在括号里,胡塞尔将注意力集中到意识的纯粹或先验的被给予上。但这种胡塞尔式地追求意识的非历史性的努力证明是失败的。随着对认识本质越来越清楚,人们发现所谓认知都是 “看作”(all seeing is “seeingas”):我们只有先学会看才能有对自然、社会等的认识。
在此意义上,有另一个假定的必然性与解释学范畴的必然性相对应,那就是自然科学不是必然的,它也是文化的产物,而且人类历史的大部分内容先于它的发明。但是,如果存在着关于物质自然的科学,那么它们必然是解释学的科学,与它所最终依赖的感知觉一样具有解释学的循环;在缺乏独立于任何理论材料的情况下,它必然是解释的解释,而且它的对象将是对于构成事实的(感知上的)(再)解释(理论上的)(再)解释。由于托马斯·库恩和其他人的研究,自然科学的解释学性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
与这种解释学的四重必然性 (双重范畴的和双重假定的)相对的是第三个假定的必然性。应当有作为认识论的哲学并不是必然的,它同样是一个文化的产物,而人类历史的大部分先于它的发明。然而,如果对于人类生活在前反思的(但是解释性的)日常性和在对其科学上的一阶(解释的)反思两个方面进行二阶反思的话,那么它必然是解释学的,而作为其主题的所有四个领域 (它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学的分类)都是解释学的循环。它是一种(再)解释的(再)解释,这种解释预设了前解释。如果这不是天真的话,那么它将知道自己是如此,并极有可能自称为哲学的解释学。
在这些层次上,解释学是必然的。当哲学家,如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以及后者的追随者,福柯和德里达——谈到超越解释学时,他们并不否认我们刚才谈到的解释学的不可避免性。毋宁说,他们的哲学解释学在某个重要方面不同于别人的解释学,通常与海德格尔早期的解释学或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抑或利科(Ricoeur)的解释学不同,这样的解释学被认为保留了太多的笛卡尔或黑格尔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否认一切的“看”都是“看作”,并不否认哲学的反思和它的主题完全是解释学的。所以,确切地讲,约翰·卡普托是用《激进的解释学》为标题来表达他那具有挑战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德里达式的对“哲学是什么”问题的回答。
二、激进的隐喻
然而,说作为一种哲学反思方式的解释学是激进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正如我们今天常被告知的那样,如果概念是隐喻的,那么激进的概念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混合隐喻。它将两个非常不同的意义结合起来。在词义上,它指达到事物的根基,或用一个实际上同义的隐喻,达到事物的核心。激进(根本、本质)是与表面或肤浅相对立的;它打破表面现象而进入由它们掩盖和掩饰的真实。即使尼采主张现象就是存在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激进的,因为要达到这个真理,就必须打破这样一个“肤浅的”观点,即认为区分现象和实在是有意义的。
人类的认识似乎沿着钟摆方向在做前后运动。某个时候,如果认识满足于表面现象就是肤浅,而去寻求它们掩盖和掩饰的真实就是激进(“激进”、“基本”、“彻底”等为同一个英语单词);但在另外时候,寻求这样的真实则是表面的,认识到在深处除了表面外无一物则是激进的。那么,到底谁激进?是主张“理式”的柏拉图或是宣称“现象”的尼采?
当我们从概念出发,想到激进是一个混合隐喻并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其空间之维转向其时间之维时,这种令人迷惑的矛盾现象也许会消失。从时间上讲,“激进”就是去打破现状,去超越现状的批判。虽说忠诚的反对派也批判现状,但激进的批判对象是这样的现状:它由当下的支配力量和它们的一个或多个忠诚的反对派所构成。从激进的观点看,忠诚的反对派太忠诚了。它提倡改良而反对革命,因为它与任何特定历史阶段中占支配地位的力量有着共同的基础。激进是革命,其精神是打破为权力争论和斗争提供力量的根基。所以,马克思主义之于英美政治学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来说是激进的,当梅洛-庞蒂既否定共产主义也否定反共产主义时,他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所追求的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学,而托马斯·库恩相对于“创世科学”与达尔文主义来说也是激进的。
显然,所谓激进是相对的。18世纪的人权概念(正如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所定义的那样)是激进的,在当下许多语境中(联合国和国际特赦组织定义的)仍是激进的;但在其他语境中,例如,女权主义(她们自称是激进的),则被视为需要质疑和批判的现状的一部分。她们将一方面侵犯人权和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又崇尚人权的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看作是家族相似性的观念——要么表现出对重要人权的忽视和侵犯,要么使人权概念成为毫无希望的意识形态。不难看出,作为激进的混合隐喻会是什么。那些站在定义特殊现状的争论双方或多方之外的人,会很容易发现各种党派,包括忠诚的反对派,都同样肤浅。整个争论,而不是问题的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必须被否定;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没有达到事物的根基,达到事物的核心,这个深入的空间性隐喻被用来说明革命的时间性隐喻。又如,道德在技术和工具理性方面,总是激进的。工具理性假设(1)手段的合理性由它们的(2)目的(如经济增长)决定。这些目的本身是不言而喻的,并不服从道德评价。反过来,工具理性之于道德总是激进的,因为它否定所有这样的争论:我们应当寻求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手段是合法的,在过程中,不能将它们等同于效果。如果军事工业的工具主义,被认为是激进革命最具体的产物,那么,随着20世纪的结束,激进将采取一种道德的态度,挑战的不只是这种或那种为了获得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策略,而是界定这样一个基本的人类使命的框架,去寻找对自己的国家最有效地获得更大财富和实力的策略。
三、激进的解释学
可以看出,激进的解释学是什么将取决于我们对现状的解释。我们采取流行的方法,把“现时现在”变为“现代性”,同时接受这样的含义:激进意味着后现代;我们要解释现代性与其结局之间的界线,来澄清后现代的激进远不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专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伽达默尔和德里达都是后现代的,他们各自代表一种最低限度的激进的解释学。
我们的解释最好从军事工业的工具主义开始,因为它是现代性的最为具体的表现。这会使伦理学的问题处于前沿和核心。但最好以黑格尔的方式,使我们的终点而不是起点具体化。我们发现有一些解释对现代性来说最有说服力和启发性,它们从更抽象、有时被称为启蒙的事业开始。它们可以根据“三个目标一个手段”来识别。三个目标是:用逻各斯代替神话,用批判代替传统,用自主代替权威。一个手段是:使这样或那样的基础主义认识论发生变体,根据认识论,逻各斯、批判和自主来重新定义。所以,从抽象开始也就是从认识论开始,而不是从伦理学开始,但我们要认识到后现代对现代的挑战,最终将不得不是伦理学的,如果它们不在抽象中失去自己的话。
从认识论上讲,当我们看到基础主义是逻各斯一种特殊文化的神话时,看到笛卡尔在摆脱权威和传统的努力中如何深深地依赖学院派形而上学的权威和传统时,看到启蒙主义如何迅速成为传统时,看到“人权”和“人道主义”体现了一种不受质疑的、旧的家长式传统时,我们就开始与现代性决裂了。能看到这一切,表明我们已经洞察到了现代性的自我解构方式和由此产生的后现代。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太快地进入后现代。因为现代性,实际上就像一个个别现状,是一个复杂的实在,它忠诚的反对派和相关争论始终与它相伴。有两个这样的争论需引起注意。因为,后现代不仅否定启蒙运动和它的基础主义,而且还否定它的整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它进行争论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战胜了它忠诚的反对派。第一个争论发生在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前者努力逃避历史存在的监护,通过向前看的运动走向成人的多数和民主;后者发现儿童期与青春期同样无法忍受,渴望回到某种过去的伊甸园。
然而,浪漫主义明显是忠诚于现代的反对派,而不是对启蒙事业另外一种激进的选择,因为它与其对手的共同之处是:(1)对其生存历史性的一种敏感;(2)不愿忍受一种有如此丰富中介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不完全的;(3)通过达到某种直接性,渴望超越构成其少数的中介,即它总是在途中而决不到达的性质。这个争论是关于这种直接性的本质,在某种唯理论或是经验论的基础主义的表达中,它仍然要在一个情感的领域(它的表达只能通过隐喻和艺术形象)中去发现。对于参与者来说,这种争论是一种激烈的战斗,但它预设了一个巨大的相同之处——几乎是对现代性的定义。第二个争论是启蒙运动的基础主义和黑格尔的整体主义。后者在它的所有形式方面抛弃了直接性,从而确立起自己既与启蒙主义的对立又与浪漫主义的对立。
然而,黑格尔保持着鲜明的现代性。因为,尽管他批评了那种将其他党派统一在现代性的直接性中,但他仍保留了与启蒙主义一致的绝对知识的理想。什么是将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在直接性问题上统一了起来(尽管二者在看待绝对知识方面并不一致),我们会发现启蒙主义与黑格尔绝对知识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回答 (尽管它们在看待直接性方面并不一致)。直接性是对纠缠一起、无家可归的历史生存和惊惧状态的一种过敏反应,与之对应的是每一个阶段都达到和现象到的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完全统一。现代性充斥着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它通过总是在场的理式抵制儿童期的恐惧和缓解青春期的焦虑。
就这样考虑的现代性而言,解释学的转向总是激进的,而“激进的解释学”这个术语“是”重复的。因为解释学断言现代性的所有形式都是肤浅的,断言如果一个人深挖事物核心,那么,他会发现直接性和整体性同样是空想的。我们从没有在家,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们总是在家(决不会没有伽达默尔式的偏见,即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意义和事实的世界或生活世界),但每一个家都是临时的而不是最终的(从没有超越德里达的差异)。我们的经验必然是游牧式的。我们的历史在冒险旅行,其无家可归和恐怖是无法超越的。它们划分我们的生存界线,因为它们属于我们存在的本质。逃避它们,事实上就是逃避自我挫败的事业,如果成功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就能躲避自己。但不幸的是,我们是通过这样的逃避来躲避我自己,且不说这样的逃避是多么无效。
四、伽达默尔与德里达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发展了早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这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发展了后期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一样,都是激进的后现代。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重要和有趣的差别,但就现代性而言,重要的是他们都否定直接性和整体性,他们都承认,我们永远既不会站在我们经验的起点,也不会站在我们经验的终点。无论我们谈到语言,还是谈到世界,当我们在场时,它们总是已经开始了,当轮到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它们两者都没有完成其历史的进程。就这样我们总是在征途中。
伽达默尔的策略是根据语言与历史的中介,去重复黑格尔反对直接性的观点,然后让黑格尔思想中的这些因素去解构他欲通过逻辑学或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去达到绝对知识的断言。由于伽达默尔驳斥黑格尔在现代性方面有许多黑格尔的东西,人们常常指责他只是半真半假地与黑格尔的现代性绝交。但是,如果直接性和整体性是不可能的话,那么,这种绝交就是不可能的,而且,无论德里达怎么说,都不可能更加深这种绝交。德里达的策略是发明一种论证,对那种来自结构主义而不是黑格尔的直接性(在场)进行解构,并让这种解构去粉碎由后来的整体性提出的要求。我们从德里达学到的,从伽达默尔学不到,反过来也是这样。不过,就直接性和整体性而言,德里达并不比伽达默尔使它们变得更不可能。
当然,伽达默尔在解构黑格尔时依赖了黑格尔,但德里达解构结构主义时也依赖了结构主义。而且,同黑格尔一样,结构主义属于现代性,它是启蒙的事业的一种。伽达默尔和德里达都承认,他们的思想依赖他们所致力批判的传统。对他们来说,批判必然是内在的批判,它必然带有个人的偏好。
与德里达相似,伽达默尔站在尼采一边来反对黑格尔。与启蒙运动不同,黑格尔承认历史观点的多样性,但仍通过整体化来寻求统一。他的公式很简单,用康德的范畴表来表达就是:多样性+统一性=整体性。但如果问到如何解决下面公式中的X,多样性=整体性=X,这个回答只能是尼采。他的视野主义(perspectivism)与黑格尔一样承认历史的多元性,而否定通过一个全体化的统一来超越它的主张。在这些术语中,伽达默尔与德里达一样,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因为他们都承认视野主义的多元性,它超越了我们进行化的力量,从而不能在最后的观点中达到统一。对于他们来说,真理就是我们没有大写的真理。他们代表了视野有限论主题的两个变体。
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德里达是一个比伽达默尔更激进的思想家。这种观点有待商榷。我们认为,针对现代性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一样激进。为什么许多人不这样看呢?无疑,这主要是一个修辞、风格和强调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不同的民族风格所致。法国知识分子似乎深刻地感到需要震动和震惊。德里达的修辞和他的风格是由这一传统形成的,而且它们是表达给在同样传统中里形成的读者。相应地,鉴于启蒙事业和它忠实的反对派的瓦解,德里达几乎专门强调了什么是我们不能做和不能拥有的。与之相反,伽达默尔更愿意谈到什么是我们能做和能拥有的,即使直接性和整体性并不在它们中间。当德里达苦心研究“延异”时,伽达默尔注意到,虽然没有任何视域融合是完美和永久的,但可以有相互的理解和共识,它们对于共同的生活来说就足够了。
在最终和理论意义上,伽达默尔并不否认“不确定性”是占统治地位的,因为既不存在直接性也不存着整体性;而德里达也不否认,在最后和实践的意义上,我们能找到共同生活的道路。对一个人来说,杯子满了一半;对另一个人来说,杯子空了一半。正是这种强调上的差别,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德里达更加激进。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伽达默尔和德里达一样是后现代的。
五、解释学的有限性
我们虽然说解释学的转向是激进的,但又不是完全激进的。如果我们希望它更加激进,更有力地打破现代性,那么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令人更加惊奇的和震惊的修辞学,而是一种更加入木三分地对启蒙事业的失败以及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选择的分析。
现代性希望拥有绝对的真理,因而总是在家。它希望生活不是从“从前”开始,而是从“他们自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开始。作为视野的多元论,解释学的转向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看做是希望实现的白日梦,即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笛卡尔的梦想。与康德一样,他把有限性变成了一个比古典经验论激进得多的认识论的范畴。我们被置于我们的身体中、我们的语言中、我们的社会历史中,我们处于本原在场的伊甸园和有机整体的世界末日之间。
但是,这种有限性不是我们拥有绝对真理和永远在家的唯一障碍。当有限性的解释学通过使罪恶成为认识论的范畴而变成了怀疑的解释学时,它更加激进了。使罪恶成为一个认识论的范畴不仅是要求注意欲望对认识的影响,而且更要注意我们不能承认的那些欲望的影响,因为我们有足够的良知让它们感到羞愧。这意味着虽然怀疑的解释学含有揭露虚假意识和自我欺骗的意思,但并非每一种揭露都含有怀疑的解释学的意思,因为并非每一种虚假的意识都是有动机的,也就是说,并非每一种自我意识的扭曲都是植根于欲望;并非每一种自我欺骗(根据定义是有动机的)都是出于欲望的动机,而自我在道德上为这种欲望感到羞耻。
我们可以在梅洛-庞蒂那里找到第一个例子。在《直觉现象学》中,他同样以“我思”批判了笛卡尔,这种批判包含一个对虚假之爱的分析。[5]这很清楚是一个虚假意识的例子,但他鲜明地将它同欺骗之爱做了区分,后者必须根据自我针对自己的内在的阴谋来理解。作为有动机的虚假意识,欺骗的爱是自我欺骗。在这种自我欺骗之中,我说服自己相信某种我知道是虚假的东西。与之相反,虚假之爱与其说是出于内部的动机,不如说是外部的某物控制着我。我为强有力的情感抓住。由于我缺乏经验和认识得不够好,我将它们和爱看成是同一的。虽然我错了,但我的虚假意识(没有动机)不是一种自我欺骗。为了满足某种需要,没有认识到真理,我没有错。虽然梅洛-庞蒂的政治学常常应用一种成熟的怀疑的解释学,但他的现象学本体论仍在有限性的解释学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于时间》第二部分开头的“亲在”中找到第二个例子。无疑,我以逃避的遮蔽和安稳的日常性的态度来与作为我最本己的可能性的死亡相遇,这是出于一种内在的动机,而且是一种自欺,在这种自欺中,我试图说服自己相信我所知道并非如此的东西。海德格尔将这个动机看成是“胆小的畏惧”。而正是这种动机将海德格尔的分析与怀疑的解释学区分开来。后者的动机最好被描述为羞愧。海德格尔揭示了一种自欺,它的目的是要得到一种安慰。而怀疑的解释学揭示的这种自欺,目的是让无罪的辩解合理化,尽管在我之中出现的是我没有而且不能从道德去宽恕的欲望、情感或行为。胆小的畏惧可能是一种堕落,但根据海德格尔的例子,它并不是我试图回避的东西。它是我的死亡、我的有限的确定性而不是我的过错的确定性。
如果我们比较海德格尔的分析与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这种在动机方面的差别会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弗洛伊德使罪恶成了认识论的范畴,然而,海德格尔的分析并不是如此。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缺乏承认我们的过错的谦卑;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自欺是因为我们缺乏面对本真自我的勇气。
六、结束语:认识现象
从作为一门隶属于逻辑学的技艺学开始,到今天发展为主流的哲学解释学;①本体论解释学直接缘起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本体论变革。海德格尔在对哲学主题──存在意义的探究过程中,发现理解结构具有作为人类存在的本体论特征,“意义就必须被领会为属于领会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样式构架。意义是此在的一种生存论性质”。解释学既不是对文本进行单纯理解和解释的学科,也不是指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而是指对人存在本身的现象学解释或“事实性解释”。可见,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实质上是一种哲学。伽达默尔积极吸收并发展了这一洞见,探寻了解释的条件性、有效性、解释的辩证法、原则、标准及应用等一系列本体论问题,真正完成了解释学的本体论建构。从规定如何解释特定文本的具体方法(比如,《圣经》),到今天完成解释学的“哥白尼革命”;从局部解释的技艺和规则的汇集,经过方法论的普遍化和科学化,到对元理论问题的本体论变革,解释学一路走来,最终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然而,在其成长过程中,有一个始终为哲人们关注的要素:现象。
对“现象”的承认与否以及对“现象”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从认识论和解释学的发展史看,直接决定解释学的走向。柏拉图怀疑现象世界通向真理的可能,提出彼岸世界的超验性;康德为了解决这个认识论上的千古难题,宣称人天生具有综合和分析能力,此岸与彼岸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彼此统一。对应于认识论哲学“意义先在”的设定,解释也从局部的技艺向着方法论的科学发展,并最终由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发展为形态完备的方法论解释学。②也有学者,如潘德荣先生,称这一时期的解释学为认知论解释学,见《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由于现象世界总是对抗处在彼岸的绝对真理,如何解决围绕现象世界的种种问题以便更好地拥有绝对真理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是西方传统哲学关注的焦点。直到胡塞尔,认识论哲学仍然不能超越方法论的藩篱,而他试图通过搁置现象和思维来寻求纯粹给与性(givenness)的现象学还原也证明是失败的。只有到了海德格尔,人们才发现原来认知论(主体)哲学所怀疑、压制、甚至试图摈弃的现象世界并不是影响、扭曲、乃至颠倒终极真理的不利因素,而是恰恰相反,现象世界正是真理的寓所,认识现象世界就是获得终极真理的不二法门。
于是,原来作为中介的现象世界现在成了认识的本体,而由主体哲学所假设的物我两极的间性也在现象学哲学中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世界又回到了主客二分后再次统一的澄明之境。出于抵御无家可归的焦虑和到处流浪的恐惧而发明的现代性,随着认识论哲学的危机和解构其诱人的谎言也在解释现象学无情的分析中被生生揭破。现象不再是传统认识论的现象。在后现代语境下,现象是与理解彼此不分的存在。方法论解释学抛弃现象,本体论解释学拥抱现象,并视现象为产生真理的首要源泉。认知论中“认识何以可能”的质疑用本体论解释学回答就是“理解”。“理解”是“解释何以可能”的最本源性的条件。在哲学解释学看来,现象世界既是理解可能的自由,同时又是理解只能如其所是的局限。海德格尔的“是-在-世界”(Being-in-the-world)、“是之理解”(understanding of Being)为一切认识奠基,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视域融合”为解释提供有效的根据,而德里达的 “延异”、“踪迹”、和“播撒”则使“巴别塔”轰然倒塌。如果说前者对通过有限解释学达成思想一致还心存希望的话,那么后者则彻底放弃了重建“巴别塔”的幻想。定义现代主义的基础主义(认为任何知识都存在一个坚实的、不容置疑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在本体论解释学看来毕竟是空中楼阁。因为,基础论追求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理解本体论追求的是在语言与符号中领悟意义。本质是外在的和确定的,而意义则是内外难分、生灭不定的。如果说现代主义的特征在于认识论的明确、单一、永恒、本质、客观、普遍和终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学向度则是不定、多元、相互依赖、主体间性、差异、主观、非原则化和无中心性。
[1]Heidegger,Martin.Being and Time[M].John Macquarrie&Edward Robinson(trans.)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Chengchengh Books Ltd,1999.
[2]Caputo,John D.Radical Hermeneutics:Repetition,Deconstruction,and the Hermeneutic Project[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
[3]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ed.and trans,Geoff Bennington and Britan Mau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84.
[4]Merleau-Ponty.Humanism and Terror[M].trans,John O’Neill.Boston:Beacon Press,1969.
[5]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B089.2
A
1003-8477(2012)01-0118-05
屈平(1968—),男,河南工程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高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