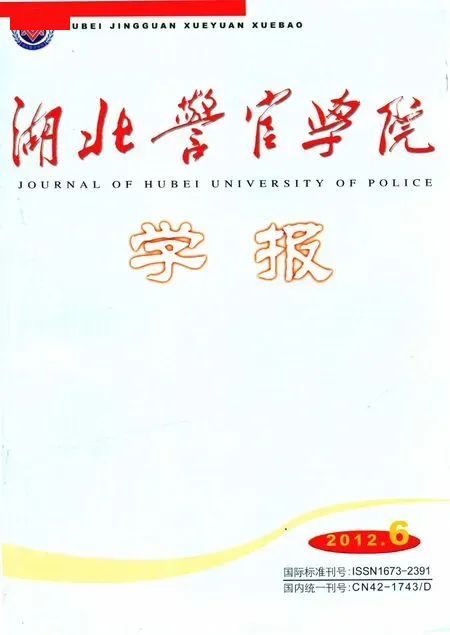浅议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
——以《合同法》第64条和第65条为讨论对象
胡醇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浅议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
——以《合同法》第64条和第65条为讨论对象
胡醇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承认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具有重要意义。《合同法》第64条和第65条并不能被解释为关于涉他契约的规定。应在《合同法》第3章“合同的效力”中添加利他契约和负担契约条款,并对第64条和第65条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合同相对性;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由第三人给付之契约
一、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意义
合同相对性原则源于罗马法,一直以来为两大法系所认可。但随着近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实质正义和社会公平的最终追求使得合同相对性原则被多处突破,且面临诸多挑战。因此,承认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这有利于完善交易制度,提高交易效率。例如在向第三人给付之契约中,两个发生在不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被连接起来。这样便能简化交易过程,在连环交易的履行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次,这是契约自由的体现。在当事人赋予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第三人可以不接受,且不会损害其利益。这符合民法中当事人自由处分权利的理念。在为第三人设定了履行负担的情况下,第三人可自主决定是否完成该履行行为:如果第三人愿意履行,法律没有必要加以禁止;第三人拒绝履行,也对其利益无任何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使合同自由适应日益复杂的交易模式,不违背私法自治的原则。
最后,这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和当事人的特定目的,如扶助第三人(使第三人直接取得合同利益)、补充第三人主体资格的不足、保护与债权人有特殊关系之第三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等。
二、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评析
(一)两种涉及第三人的法律行为的区别
在分析《合同法》第64条之前,我们必须区分以下两种情形:
1.“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此为债务履行的一种常见形式,源于德国民法理论,即债务人应债权人的要求,向第三人交付债的标的物。
2.利他契约。此为典型的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情形。一旦契约成立,第三人并非仅仅消极受领该给付,其享有独立的对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权利。而在“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的情形中,请求权仍由债权人享有。
(二)对《合同法》第64条的主要解释
对于本条的解释,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第一种为立法机关所作的释义,认为《合同法》第64条规定了利他契约[1],是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体现。这种观点认为,若不作此解释,则利他契约在《合同法》上没有依据,会导致法律漏洞的出现,使得与利他合同相关的经济活动抑或司法活动的法律指引成为空白。所以,将第64条解释为“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其指引意义大为降低,因为仅从字面意义上解读并无特殊之处,而《合同法》特设此条文,必然有特殊的立法意旨。
2.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合同法》第64条属于“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的情形,根本未赋予第三人任何法律地位。这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合同法理论,即只有合同双方当事人才有权对该合同作出法律主张。[2]
3.第三种观点认为《合同法》第64条实际上包括了两种情况:一是利他契约;二是“经由被指令人而为交付”。但是如何区分这两种情况?标准何在?这些问题都无法从条文中得出明确答案。
4.第四种观点认为《合同法》第64条就是关于利他契约的规定,或认为《合同法》第64条确立了利他契约规则。尽管这一规定过于简单,遗漏了许多问题,但毕竟使司法实践有了法律依据。[3]此观点承认该规定存在不足,如未具体规定利他契约的法律效果等。因此,就立法而言,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宜加以改进,其中应当规定该第三人对于债务人享有请求权等。[2]
(三)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不能将第64条认定为关于利他契约的规定,其也不属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范围。一方面,从立法体例上看,我国一直沿袭大陆法系的立法传统,而从合同效力的角度出发,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一般都将利他契约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类型加以规定。由于我国《合同法》第64条被列于“合同履行”一章,将其视为特殊的债务履行方式而非特殊的合同形态更为恰当,也更符合法律的体系解释原理。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法律规定角度来看,第64条只对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作了规定,未涉及第三人对债务人的独立请求权,也未规定利他契约应产生其他法律效果,如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等。因此,第64条似乎并未赋予第三人任何法律地位。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其性质只能被认定为“经由指令而为给付”。
综上,笔者认为不宜将第64条勉强解释为关于利他契约的规定。否则,法条应明确三方关系人的权利义务:不仅应肯定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将合同利益给予第三人,对第三人取得利益的前提、合同成立或生效的条件及第三人是否享有其应得利益的请求权作出全面详细说明,还要区分债权人主张违约和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
三、对我国《合同法》第65条的评析
从第65条可以看出:第三人不会因为履行合同义务而成为合同当事人;如果第三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规定,债务人的责任不得因为第三人违约而得以减轻。对于债权人而言,他只能向债务人而不能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由此,我们并不能推断出《合同法》第65条属于狭义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
有学者认为,《合同法》第65条实际上是关于负担契约的规定,类似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8条。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68条规定:“契约当事人之一方约定由第三人对于他人为给付者,于第三人不为给付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但笔者认为,《合同法》第65条不是关于负担契约的规定。一方面,第65条与第64条都被列于“合同履行”一章,且被冠以“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和“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名称,并以“履行”为核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负担契约具有担保性质,最显著的特征是债务人的义务为担保第三人依约给付。若第三人未向债权人给付或给付不当,则债务人一般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而非其他违约责任。[4]但我国《合同法》第65条并不能体现出债务人担保第三人为给付的性质,且当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履行不当时,其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笔者认为,《合同法》第65条为第三人代为履行规则,具体而言,其属于第三人代为清偿制度的范畴。虽然该条的表述与传统的第三人清偿制度有巨大差异,但是由于我国《合同法》缺乏第三人清偿制度的规定,我们不妨对其进行修改,以弥补该制度的不足。
四、《合同法》涉他契约规则之完善建议
虽然学界对《合同法》第64条和第65条的解释存在诸多争议,但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涉他契约规则存在迫切需要。如上文所述,将第64条和第65条解释为涉他契约规则并不合适,而对条文进行修改则会使涉他契约规则从属于“合同履行”一章,有违《合同法》的自身逻辑性和体系编排。所以笔者认为,应在《合同法》第3章“合同的效力”中添加利他契约和负担契约条款,具体包括下列条文:
(一)利他合同
第一,利他合同自第三人表示享受合同利益时成立。合同一旦成立即产生约束力,除非第三人同意,原债权债务人不得变更或撤销合同。第三人对当事人一方表示不欲享受合同利益,视为自始未取得合同权利。[5]第二,利他合同可以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第三人对债务人有直接请求权,但债务人可以依据利他合同产生的抗辩对抗第三人。第三,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或履行不当的,第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
(二)负担合同
若合同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给付,则该合同对第三人无约束力。第三人不为给付或者给付不符合约定,应由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此外,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也应纳入以上条款,《合同法》可整合到民法典的债权编。除了补充涉他契约规则外,还应对尚存争议的《合同法》第64条和第65条进行司法解释,阐明其准确含义,明确其合同履行规则的地位,以限定其适用范围。
[1]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12-113.
[2]邢建东.合同法(总则)——学说与判例注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51,253.
[3]冉昊.论涉他合同[J].山东法学,1999(4).
[4]尹田.论涉他契约——兼评合同法第64条、第65条之规定[J].法学研究,2001(1).
[5]张永华.论第三人利益合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4(12).
【责任编校:王 欢】
D923.6
A
1673―2391(2012)06―0080―02
2012—04—01
胡醇,女,湖北钟祥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