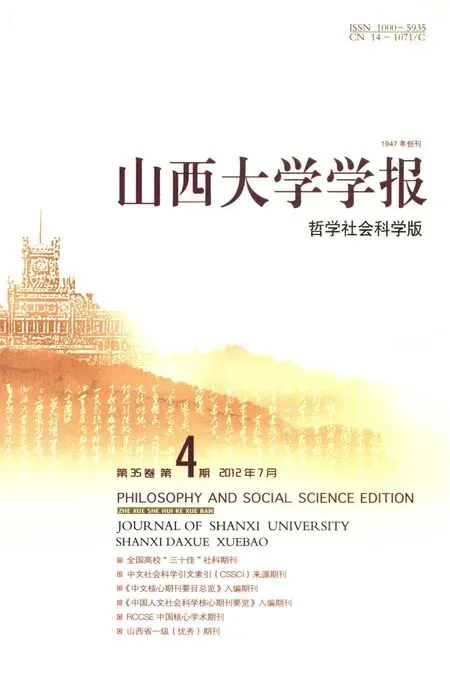论政府传播的客体
——“利益相关者”视角
刘小燕,崔远航
(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3.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871)
·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
论政府传播的客体
——“利益相关者”视角
刘小燕1,2,崔远航3
(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3.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871)
政府传播是政府议程(或公共政策)、政府施政行为等内政外交之信息和价值观的扩散、接收、交互、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作过程。文章从“利益相关者”视角,解析了政府传播的客体国内公众和国际公众的角色功能及其对主体的影响。同时论述了某种情形下,这些“利益相关者”中“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及“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文章还进而探析了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问题:web2.0新传播技术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在政府传播中另一层面的角色变化。随着web2.0的发展和普及,利益相关群体(或个人),透过某一平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联系与交流,日渐成为另一个“传播中心”。他们彼此进行讨论、质疑政府决策的优劣。通过此,利益相关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号召力。
政府传播;利益相关者;国内公众;国际公众
政府传播是政府议程(或公共政策)、政府施政行为等内政外交之信息和价值观的扩散、接收、交互、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作过程。就传播的形态和范围而言,政府传播有“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之分。对内传播是指政府面向国内公众的传播。对外传播是指面向国际社会公众的政府(国家)传播。一个国家要同国际上许许多多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的交往,这些交往对象就是政府的国际公众。
在政府传播链条中,作为信息传递对象的受众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鉴于政府传播的主体特殊性,其传播对象广泛,其信息(信息形态或载体包括行为与话语)内容又多与公众需求相关。因而政府传播的顺畅和有效,同样需要在传播过程中准确理解传播对象的角色和他们的需求。需求是人们获取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主观基础,利益是需求的社会形态。因而,本文将以政府传播中的公众作为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以考察如何保证政府传播的有效进行。
一利益相关者之于政府传播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美国、英国等长期奉行外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其原本针对的是公司管理问题,即在管理决策等公司发展层面中,并不简单将股东作为唯一考虑因素,其他任何利益相关者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股东不过是其中之一。“利益相关者”被认为与企业的生存息息相关。目前较为普遍接受的定义为:利益相关者是组织外部环境中,被此组织的行为、决策、政策、规定或目标所影响,或者影响这些的个人或群体。①弗里曼等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类似的定义。Carroll.Business and Society:Ethics and Stakeholder Management,3rd edn(Cincinnati,Southwestern)1996,p.74。R.Edward Freeman《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第二章中的表述是:“组织中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公司目标是否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早先的研究中,尤其是政府管理层面,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多偏向“受影响者”,然而近些年来研究者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更多集中于“可能施加影响者”这一更为主动角色之上。譬如Jobbins[1]、Jongman和Padovani[2]等人的研究,认为在海岸或河床管理等具体决策过程中,政府部门、地区机构、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等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都对相关决策的形成产生影响。这一界定和研究取向的转变与政府决策体制的变化、大众媒体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和影响扩大等因素相关,也与全球化大背景下社会结构复杂化、分化分层趋势增强等大背景密切相关。
“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流行恰恰与当时西方社会所提倡的“企业社会责任论”密不可分。企业逐渐被视为利益相关者之间或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并具有人格化特征。这些被称作“利益相关者”的个人和群体不仅会影响企业目标的达成,而且还会受到企业目标达成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类行动的影响。[3]而与之相应的是,从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到近百年来的政治学理论著作,尽管具体观点有所差异,然而都将国家政府视为人民通过放弃自己自然权利而达成的社会契约,同样具有人格化的特征。故而,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引入“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完全可行。作为对整个社会发展负有重要责任的国家政府而言,若要获取公众对其本身、相关政策和举措的支持和信任,就必须将公众视为利益相关者,在努力构建政府形象、兑现既有承诺之外,重在关注公众利益:通过紧密联系公众,与公众沟通、互动,了解处于不同层面的公众的各类需求,并征求他们基于自身利益所提出的各类意见、建议。这一联系、沟通、互动的过程,就是政府传播的过程。公众对政府认同度和信任度的高低,取决于对政府期望以及此期望被满足的程度,这些期望本身也是与公众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众不会不考虑对政府的信任投入带来的风险是否与其可能获取的利益相匹配。因此,政府的认同度和信任度与公众的利益表达和实现不可分割。认同度和信任度的高低影响着政府的生存和政治局势的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政府日常运作或者说政府传播中,将公众视为“利益相关者”是合乎其内在逻辑的。
不言而喻,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互动同样是政府日常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传播的过程既包括政府议程、施政行为等信息的公开,也同时包括公众对此信息的回应与反馈。作为信息生产和传输中心的政府,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将政府传播纳入整个政府管理系统中来看,这一信息活动不仅仅要求自上而下的将信息传递给公众,更要求通过这一路径使得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公众的回应和期望能够顺利表达,从而在政府具体决策的施行过程中,有效及时地获得公众反馈,并根据此反馈调整举措,从而维持或者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在利益相关者的相关理论中,众多学者认为,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对于组织管理决策的影响以及被组织活动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必要在处理利益相关者有关问题时,应先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区分。如美国学者米切尔(Mitchell)和伍德(Wood)对“利益相关者”从“合法性”(对企业拥有合法的索取权)、“权力性”(能够对企业决策施加压力)和“紧急性”(能够紧急地引起企业管理层关注)三个属性上进行评分,然后根据分值的高低确定某一个体或群体是否属于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的相应类型。在米切尔看来,要成为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至少要符合以上一条属性。若同时满足以上三条,则可被认为是“确定型利益相关者”(Definitive Stakeholders),这一类群体的愿望和要求必须被关注,并设法加以满足。若符合上述三要素中的任意两项,则可被视为“预期型利益相关者”(Expectant Stakeholders);若仅满足其中一项,则为“潜在的利益相关者”(Latent Stakeholders)。[4]亦有国内研究者将此三类更直白地表述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边缘的利益相关者”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5]
对政府传播中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同样可以参照上述标准,对其界定采用“多维细分法”[6]。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较之单个企业(或组织),其所面对的利益相关者并非某个或某几个群体,而是整个国内社会中的民众和国际公众,即使国内公众,有时也会与国际上的行为体相关联。因此政府传播的利益相关者范围要广泛得多,其内部分层也更加复杂。围绕不同事件、不同议题进行的政府传播,其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亦各不相同。
之所以要对政府传播中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公众进行分层和定位,首要的是为了提醒政府在进行信息传播之前,需要考虑其传播内容乃至传播过程可能涉及的公众,并针对此调整传播策略,旨在选准目标,直抵要害,以低成本达到良效果;在传播过程中碰到阻碍时,也能准确界定是由于哪一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而导致的传播不畅,明确症结并及时予以补救,保证整个传播过程的顺利实施。
二政府传播中的利益相关者:国内公众与国际公众
(一)国内公众
根据政府传播有“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之分,可将政府传播中的公众(“利益相关者”)分为:国内公众(国内“利益相关者”)和国际公众(国际“利益相关者”)两大类。再根据其主体身份,将国内公众区分为:利益团体、社会精英、中间阶层①中间阶层,是指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阶层,赞同社会主导价值观,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稳定力量。、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大众传媒、智库、非政府组织、政党、军队、政治团体、宗教群体及其他;将国际公众区分为:他国政府、政党、智库、民间、大众传媒,此外,还包括国际组织(以及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等不同群体。无论国内公众还是国际公众,结构是多元的,其利益诉求也五花八门。
若按照群体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进行分类,以国内利益相关者为例,则可将政党、军队、利益集团、智库、大众传媒等,划归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或“核心利益相关者”)。它们能够对政府施政直接干预、施加压力,并且能够紧急引起政府关注,从而直接对政府传播产生影响;而民间团体、普通民众(包括社会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或个体)则往往处于“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利益相关者”位置。其中像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或个体(尤其诸如中国城市路边的乞讨者、被冤枉入狱者、终年上访无果走极端者、因历史和政治造成的事实上的受害者等等),虽然难以成为对政府的直接施压者,但它却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短板”。他们的存在(或者占有相当比例),至少说明政府有失职之嫌,忽视或没有照顾好其弱势民众,那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要大打折扣。
上述诸多群体还可以再次细分,以“利益集团”为例,它既包括“特殊利益集团”,也包括“公众利益群体”。利益集团②利益集团,是指采用各种途径和方法向政府施加影响,进行非选举性的鼓动和宣传,用以促进或阻止某方面公共政策的改变,以便在公共政策的决策中,体现自己的利益主张的松散或严密的组织。利益集团一般明确表示自己的组织目标或价值标准,从而使具有共同社会身份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们聚合起来。以其成员共同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向政府提出利益要求,以影响或制约政府的决策,使政府的政策与立法有利于本集团的利益或目标的实现。利益集团还为自己的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和信息,以谋取集团利益;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情报,以影响政府制定政策。其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又可分为“极端利益集团”和一般的“特殊利益集团”。前者如美国三大“极端利益集团”:③美三大“极端利益集团”:军工产业利益集团几乎垄断了美国的战争决策权;金融寡头集团掌控、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决策;犹太裔政治利益集团对美国的政策拥有85%的发言权,正由于该集团的存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敢在美国的土地上训斥美国总统奥巴马。军工产业利益集团、金融寡头利益集团以及犹太裔政治利益集团,他们几乎垄断(或决定性影响)政府的决策权和政策话语权。而一般的“特殊利益集团”,追求其成员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一般是以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类集团。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有:工商界利益集团、金融界利益集团、农业界利益集团,还有劳工组织等。此外,还存在基于不同种族、民族、性别、年龄、宗教等的特殊利益团体。在中国,特殊利益集团,更多是指在某些重要部门占有或掌控权力或经济资源的利益团体。公共利益集团的目标范围相当广泛,凡是对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利益问题都可能成为公共利益集团的组织目标。西方国家较普遍存在的公共利益集团有: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利益协会、和平组织等。
上述国内公众中的“中间阶层”,当其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受到阻止,社会矛盾也会大大减缓。“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他们有较稳定的中等水平收入,生活状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其地位处于掌握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和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工阶级之间。他们不像掌权者那样,可以凭借政治权力或者对经济的控制和影响力,对政府决策或直接或间接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相对庞大的群体;而在中国,尚是一个弱小的阶层,尤其遭遇当今艰难超越“中等收入陷阱”④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就难以突破一万美元。处于这一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便会爆发出来,经济增长也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之时,有的人可能又滑向弱势群体一族。另一方面,“相对于最低阶层麻木不仁地生活在惯例里,相比于最高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间阶层尤其“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他们“要求不断变化”。[7]这又决定了中间阶层“希望变革”的另一面。
关于国内公众中的军队,多数国家的军队一般与政府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相安无事。而在有的国家,军队作为捍卫国家安全的机器,有时却因为权力或利益的博弈,走到与政府对立、甚至发展到军事政变的境地。此时,政府因国家陷入内讧自身难保,政府传播也很难按部就班,或许无从下手或许荒腔走板,或任由他人解读,政府威信也就可想而知。
诚然,利益相关者的分类方式本身就具有动态性,这些定位或分类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群体或个人的角色随着事件的不同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即任何一个个体或者群体获得(或失去)某些属性后,就会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比如说某一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已经拥有对政府直接干预和施加压力的权力,如果政治或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他们的诉求变得更加紧迫,那么他们就会转化成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譬如,中国广东2011年底发生的“乌坎事件”这一官民严重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受害者家属及上访村民,由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变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在问题解决之前他们与基层政府形成尖锐的对峙,一时间成为境内外媒体报道的焦点。事件若继续恶化,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给各级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该事件的妥善解决,同样给中国各地频发的类似事件的解决与避免,提供了示范功能。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当前的矛盾,除了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在博弈外,特殊利益集团还与普通民众争夺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一旦气候形成,就成为排他性的分利集团,便尽力限制分散他人的收入和价值。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往往通过俘获政府、影响甚至操纵政策制定者实现自己的目的。当今中国现实政治经济运行的逻辑是,几乎所有格局均由力量所决定,强者的利益往往优先于弱者得以实现。弱势群体常被蒙在鼓里,被动挨宰,利益受损。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挂在一起,使得普通民众的利益得不到保护,甚至是被侵犯或剥夺,致使社会更加对立。诸如房地产、证券领域呈现出来的景象,就是处于现实社会最强势的资本部分与政府机构中利益化最明显的部门结合在一起,往往侵蚀或牺牲处于社会劣势的城市拆迁户、失地农民和来自乡村参与城市建设的打工者,以及中小股民或散户投资者的利益。
在涉及社会公正、公平、正义方面,政府必须做一个重要的调解者(或调和者)。倘若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挂钩,暗箱操作,侵蚀公共资源,牺牲民众利益,尤其是容忍特殊利益集团与公权力公开结合,只会进一步破坏民生,加剧贫富悬殊,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等于政府自挖执政基础的墙角。目前种种社会不满情绪,如仇官,仇富,质疑慈善事业不纯洁,抱怨社会分配不公,痛恨权贵鲸吞民众资产等现象,恰好为此做了注脚。
在不同公众之间的利益(或权益)关系互动或博弈中,政府合格的角色应当是,一个仲裁者或中立者,而且体现在其政策的制定上,须偏向较弱的一方,犹如法律总是要同情弱者一方一样。政府透过决策或施政,对解决社会矛盾,消除社会对立和仇视等,做适当的引导或必要的支持。
本文只是列出了政府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相关者,而且,处于核心、外围和潜在利益相关者的不同位置者,会在不同情况下发生变化,因而有必要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对公众进行具体分析。
(二)国际公众
在政府(对外)传播中,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国际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同国内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不同。他国政府、媒体,以及国际组织,无疑是政府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他国民间、政党、智库、非政府组织等,则更多属于“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利益相关者”。其中,他国民间又有较广泛的含义,它既包括普通大众,又包括特殊群体,如西方国家盛行的“院外游说团体”。尤其像后者,他们专门从事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活动,向议员施加压力和影响,使国会的立法有利于自己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
若他们的雇主是某一国家的政府(或权威机构),那他们游说的对象,除国会议员外,还包括政治家、政府官员。其使命是影响或改变本国的对外政策。显然,此时的“院外游说团体”便是政府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像美国一些著名的院外游说集团如“犹太人集团”和“台湾集团”。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例,“犹太人集团”曾为以色列建国发挥过巨大作用;“台湾集团”则与美国武器制造商(如霍尼韦尔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手,帮助台湾获得了在美国的幕后影响力仅次于以色列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曾多次成为美国游说集团政治的牺牲品,集合在国会山周围的“藏独”、“台独”等反华势力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多次掀起反华浪潮。如今,在美国国会关于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赤字以及“中国威胁”的辩论背后,这股势力依然阴魂不散、魔力不减。中国政府若要破解这些魔咒,同样离不开借助美国那些肯替中国说话的“游说公司”、智库等力量。
他国政府,显然是政府传播首要的国际公众(核心利益相关者),政府对外如何决策,多数情况需着眼于他国(政府)的利益取向;政府对外政策的能否顺利实施,大部分取决于他国政府的配合与否,或者他国政府感觉到自己是否是重要的利益分享者。因此,政府与政府的互动,尤其大国之间,基于国家利益需要,几乎随时随地进行。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在政府传播中,政府与国际利益相关者互动中,既有横向的互动,又有纵向的互动。前者如,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有时要扮演相互纠纷或冲突的A国政府与B国政府关系的协调者,为其穿针引线。其前提是,该政府作为中立者,均为A国与B国所信任。当该政府立场偏向其中某一“利益相关者”时,则要承担伤害另一“利益相关者”而带来的后果。后者如,政府有时扮演A国政府与A国民间(或在野党或民众)的协调者(或离间者)和影响者。
不言而喻,国际组织(以及区域组织)也是政府(国家)传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一个国家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WTO、WBG、IMF等)及区域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CE、上海合作组织、欧盟、东盟、非盟等)关系的紧密与否,或者说一个国家在该国际组织之话语权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该国的国际(或区域)影响力之强弱。
之所以说大众传媒是政府传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是因为当政府与公众直接互动不可能完全实现时,传媒往往又是政府与其他公众间的桥梁。它既可能是政府传播具体实施的传输带,也是其他利益相关者影响政府传播或被政府传播影响的重要平台。有学者通过研究荷兰和比利时政府对尚未被议会通过的政策的传播发现,媒体记者和政府传播专家在帮助相关政策获得公众支持、最终获得议会通过起到重要作用。他们认为新闻媒体是政府建立或失去信誉的平台,赢得公众信任之战更多在媒体发生,而不是在议会。[8]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大众传媒,都对政府传播有着重要的工具意义。
同样,非政府组织(NGO),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由于其自身功能的特殊性,对政府传播不可或缺。西方非政府组织或配合政府的行为,为政府拉高声势;或补充、代替政府去完成政府不便出面或难以完成的使命。其自身固有的职能和敏锐的目光,也同样监督、警告政府。NGO力量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无疑具有工具性功能:NGO力量与国家权力互补,在政府管不过来或难以发挥作用时,它作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对国家与社会事务起促进作用。不过,它也有可能作为政府的反对派,成为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其关键在于政府自己的行为如何,以及如何借重非政府组织。
三新传播技术条件下利益相关者在政府传播中的角色
若将政府传播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进行分析,那么公众所扮演的角色在此过程中的变化更值得注意。在现今传播技术发展情况下,web2.0使得公众获取较之从前更多的话语权,使得在政府传播过程中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双向、多向的传播手段令公众成为除了政府之外,能够主动对信息进行诠释、评论并再次进行扩散的传播中心;公众本身由于利益驱动,也会主动积极采用此类传播渠道进行自我表达。因此,政府传播过程本身无法忽视传播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公众话语表达权力扩大的现实。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而言,若罔顾公众的利益需求而进行强制传播,则可能导致政府信息流通过程中遭遇噪音干扰,或本意被误读、曲解后进行再次传播;但若政府传播内容符合其利益,公众将积极推动信息的流动,保证传播顺畅,并主动消除噪音,扩大传播范围,为政府传播节省成本,达成更好的传播效果。因而,新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在政府传播过程中有必要将另一个“传播中心”——公众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纳入到传播议程之中。
传统政府传播结构中政府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作为利益相关者一部分的普通民众往往是属于被动接收信息的客体一方。信息流动是单向进行,偶尔有双向(即民众反馈政府信息)。但除了可以主动影响政府传播信息内容和流向的智库、政党、媒体等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之外,普通民众往往处于政府传播的边缘地位,并且彼此之间难有交集,也很少有交流发生。然而,web2.0等新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无论哪一类、哪一层次的利益相关者都有机会接触到精确、即时和不含偏见的信息。各类信息平台的涌现,也令各个利益相关群体(或个人),能够透过某一平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交流,彼此之间进行联系、讨论。这就意味着政府传播的信息以及政府本身成为被关注和讨论的对象。正是在这一层面,利益相关者从之前的边缘地位转移至中心,而政府则沦为被动的对象。利益相关者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告知其他利益相关者关于政府某项决策的优劣点、表达对政府所传达某项信息的好恶,在此过程中政府或政府所传播的信息的缺陷,很可能被无限放大。
而除了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的互动之外,网络技术的发展亦使得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公开场合与政府对话[9]。因此,任何一次的政府传播都很难以单方面发布信息完成,整个政府传播过程也不可能简单以政府意愿结束,利益相关者在政府发布信息后的回应(尤其是质疑或挑战),都意味着政府需要进一步对其发布的信息进行诠释和解惑,在与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不断深化原有的传播过程。也就是说,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某些利益相关者获取了直接影响政府的权力。此时,米切尔所提出的“利益相关者”分类法在政府传播中已不再适用。三个属性中的“合法性”已被广泛取得,而政府并不能忽略或排除任何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这一变化的益处在于政府与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之间不再存在障碍,政府若想吸纳利益相关者进入传播进程之中也更为便捷,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同政府的合作也更易展开。
在唐·泰普斯科特、安东尼·威廉姆斯《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一书中,作者从商业模式的角度分析了诸如博客、微博、社会网络等web 2.0的技术如何改变了商业组织对于协作关系的认识。对于政府这一公共服务机构而言,网络同样提供了一种协作机制,在其中政府或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可以与私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普通民众合作,并提供低成本、高收益的服务。2008年的美国大选,人们见证了奥巴马如何利用网络使众多年轻人参与到这场政治传播中,并有效保证了奥巴马的当选。而之后更多采用网络技术打造“政府2.0”的美国政府,通过与公众的“合作”[10],利用现有的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创造共享、开放和合作的氛围,使得各利益相关者能够支持并参与到政府的各项运作之中,并最终得以重新认识政府,增强对政府的信心和信任感。
然而这也意味着对政府的更大挑战。政府在其传播过程中无法忽略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公众的作用和影响力,而同时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利益相关者在政府传播系统中角色的变迁,使得政府不得不从执政能力到获取公众信任等各方面面对更多的挑战。若公众通过政府所传达的信息而获得的期望值,不能被政府随后的行为所满足,那么政府信息的可信度会受到质疑,而彼此联系的利益相关者则会公开质疑政府的信誉度,致使政府遭遇大面积的信誉危机。在关键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之后,边缘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在得知这一结果后,极有可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担心,变为关键利益相关群体中的一员。关键利益相关者范围的扩大,则意味着政府面对的压力和需要处理的问题的进一步加大,其可能承受的责备和质疑也相应增加、甚至由某一部门扩大到政府整体。此外,由于政府需要在传播过程中对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进行回应,政府的回应本身会再次成为其所传达的信息中的一部分,在本来单线条的传播流中形成多重传播系统,使得整体信息流向和发布、接收者等各方面愈加复杂化。
总而言之,随着web2.0的发展和普及,利益相关群体(或个人),透过某一平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联系与交流,日渐成为另一个“传播中心”。他们彼此进行讨论、质疑政府决策的优劣。通过此,利益相关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号召力。在现今的政府传播中,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更应被视为主动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传播影响着政府形象和政府的信誉度,在众多影响政府公共关系的属性中,“对政府传播的不良公共认知”[11]占据了一席之位。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处理信息的技巧,也同样决定着政府传播效果的达成。因而将公众视为“利益相关者”,有助于将政府传播、政府执政能力、政府信誉度联系在一起。而且,如何在传播过程中看待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地位、如何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不仅是政府传播顺畅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考核政府信誉度和执政能力的标准。正因如此,将公众视为“利益相关者”作为政府传播中的一环是必要的。
[1]Guy Jobbins.The effects of stakeholder interactions on capacity for integrated coastal governance in Morocco and Tunisia[J].Aquatic Ecosystem Health&Management,2003,6 (4):455-464.
[2]R.H.G.Jongman,C.R.Padovani.Interaction between Stakeholders and Research for Integrated River Basin Management[J].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2006,22(3): 49-60.
[3]陈宏辉,贾生华.企业利益相关者三维分类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4(4):80-90.
[4]李洋,王辉.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动态发展与启示[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4(7):32-35.
[5]沙勇忠,刘红芹.公共危机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模型[J].科学经济社会,2009(1):58-61.
[6]贾生华,陈宏辉.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5):13-18.
[7][德]齐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89.
[8]Dave Gelders,Rozane De Cock,Peter Neijens and Keith Roe.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about Policy Intentions: Unwanted Propaganda or Democratic Inevitability?[Z].Surveys among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Professionals and Journalists in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Communications,2007(32):363-377.
[9]Rian Van Der Merwe,Leyland F.Pitt,Pussell Abartt.Stakeholder Strength:PR Survival Strategies in the Internet Age[J].Public Relations Quarterly,2005,50(Spring):39-48.
[10]Jay Nath.Reimagining Government in the Digital Age[J].National Civic Review,2011(Fall):19-23.
[11]Brooke Fisher Liu,J.Suzanne Horsley.The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Decision Wheel:Toward a Public Relations Model for the Public Sector[J].Journal of Publec Relations Research,1990(4):377-393
On the Object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the Interest-related Perspective
LIU Xiao-yan1,2,CUI Yuan-hang3
(1.Research Center of Jourua-lismand Social Developent,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 Journalism,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3.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cess in which various information,values and opinions of government agenda,public policies or governmental acts are proliferated,
,recognized and internalized.From the interest-related perspective,the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the object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played in this proces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subject.It is also elaborated in the paper that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in those interest-related groups the definitive interest-related group,expectant interest-related group and latent interest-related group switch their roles in a more flexible way.The paper further suggests that with the fast expansion of web 2.0,muc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performed by the interest-related group in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By communicating with and contacting other interes-related groups via some platform,interest-related groups(or individuals)have become another information center.They discuss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challenge the effects with each other.And by this means,the interest-related groups are able to gain more powers,influences and popularity.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interest-related;national public;international public
G206.4
A
1000-5935(2012)04-0128-07
(责任编辑李雪枫)
2012-03-28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科研费专项资金资助)明德青年学者计划(11XNJ019)
刘小燕(1964-),女,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
要从事新闻学研究;
崔远航(1988-),女,河南林州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