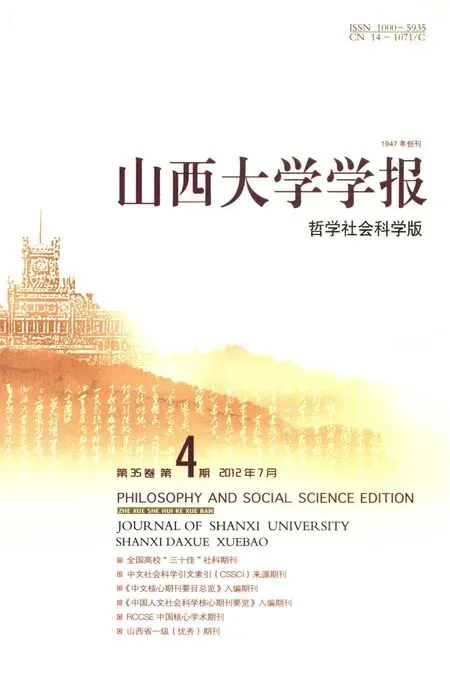近年来长篇小说叙事方式多样化趋势的分析
——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为中心
王春林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现当代文学研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研究·
近年来长篇小说叙事方式多样化趋势的分析
——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为中心
王春林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文章通过对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以及部分入围优秀作品的细读,对于近几年长篇小说创作叙事方式的多样化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艺术分析。这种多样化趋势主要体现为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等几种叙事方式。
茅盾文学奖;叙事方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
在社会上曾经引起高度关注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早已尘埃落定。理解肯定也罢,怀疑否定也罢,在当下这样一个过于喧嚣过于崇拜速度的时代,伴随时间的流逝,关于茅奖的话题似乎不再能引起公众的注意。但公众的退场并不就意味着茅奖话题的过时,某种意义上,大约也只有在公众退场之后,我们方才能够静下心来,相对比较客观冷静地重新审视这一届评奖,重新感受认识这一届的获奖小说,以及那些虽然没有能够获奖但却足够优秀的小说作品。因为茅奖的评选周期是四年一届,所以,通过分析这些获奖以及未能获奖的优秀小说作品,我们便大致能够对近四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和把握。
对于长篇小说的学术研究,可以从多个层面深入展开。本文将主要从叙事方式的角度切入,对第八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以及那些没有能够获奖的优秀作品进行一番专门的考察与研究。
一叙事意识的觉醒
虽然从根本上说小说这种文体乃是一种典型的叙事文体,但是,小说叙事之成为文学界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应该是1990年代之后的事情。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1980年代中后期,马原、格非、余华、莫言、孙甘露等一批先锋作家的创作在中国文坛逐渐开始引人注目。这些作家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特别地注重于所谓叙事形式的创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过根本性影响的马原。我始终以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一种是虽然没有写出过足称杰出的文学文本,但是这位作家的文学书写却对于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种作家可称为重要作家;另外一种是或许并没有对于文学的发展演进产生过足够大的影响,但他自己却写出了杰出作品的作家,这种作家可称为优秀作家。很多时候,重要作家与优秀作家呈现为重合状态,文学史上留存下来的大部分作家,皆可做此种理解。某种意义上,我觉得,马原的情况就属于前者。《冈底斯的诱惑》《西海无帆船》《虚构》《上下都很平坦》,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认真地想一想,这些中长篇小说还真的没有哪一部称得上是优秀。但是,由马原所开启的那样一种曾经被批评家称之为“马原的叙述圈套”的叙事方式,对于当时以及其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又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忽视的。以至于,极端一些说,如果没有马原的示范性存在,你恐怕很难想象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能够走到今天这样一种成熟程度。
其二,从学术研究界的情况来看,隶属于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叙事学理论之进入中国,并逐渐地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一门显学,也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情。我自己最早知道叙事学,是通过张寅德选编的那本《叙述学研究》。[1]虽然说更早一些时候,我就读到过曾经被收入“人文研究丛书”的陈平原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但或许是由于自身过于愚钝的缘故,当时并没有能够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理论的出现事实上已经初露端倪了。总之,正是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叙事学开始渐渐地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兴趣。不仅仅是研究者,即使是那些专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了叙事问题的重要性,也开始张口闭口不离“叙事”二字了。尽管说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乃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但很显然,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的存在,对于小说创作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还是很不一样的。作家叙事意识的自觉,无疑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小说叙事方式日渐走向成熟。
大约正是由于受到以上创作和理论研究两方面原因影响的缘故,中国当代作家的叙事意识,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普遍的觉醒时期。这样的一种觉醒,对于小说叙事艺术的很快走向成熟,自然发生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某种意义上,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繁荣,也可以被看做是叙事艺术成熟的一种必然结果。既然每一届的茅奖评选都被看做是对于当时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检阅,那么,第八届茅奖就是对于最近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状况的一种整体反映。这样,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以及那些未能获奖的优秀小说,于无形之中也就成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对于这些作品的叙事分析,实际上也正是对于当下长篇小说总体叙事成熟度的基本验证。文学创作贵在原创,就我对于这届茅奖作品的阅读观照,虽然不能说它们已经达到了多么完满的程度,但从这些作家所具体采用的叙事方式来说,却可称得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姚黄魏紫,各有所擅,呈现出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多样化图景。
二获奖作品叙事分析
随着时间的日渐推移,我们越来越发现,作家张炜本质上其实是一位富有浪漫精神的抒情诗人。这一点,在他早期的获奖短篇小说如《一潭清水》中已经初露端倪。如果说曾经获得过高度评价的《古船》可以被看做是张炜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的话,那么,从紧接着的《九月寓言》开始,伴随着从小说文体上渐渐地转型为一位长篇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张炜的抒情诗人本色也得到了越来越明显的强化。这次茅奖评选中名列榜首的那部可谓卷帙浩繁的《你在高原》,不仅小说的总体命名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苏格兰杰出诗人彭斯的名诗《我的心呀在高原》,而且,就小说的整体写作而言,也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首行吟者的抒情长诗。虽然这部巨型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家族》叙事的起始时间是20世纪的初叶,但整部《你在高原》的基本主旨,恐怕还是应该解读为张炜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艺术性的梳理与概括。具体说来,他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既是主人公同时又是叙述者的“我”即宁伽这一贯穿于小说始终的人物形象。通过这样一位不满足于庸俗的日常生活,总是不断地因为人际矛盾而去职,总是以在高原上行走为自豪满足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形象的设定,张炜非常巧妙地把诸如拐子四哥、武早、鼓额、梅子、凯平、帆帆、荷荷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和故事连缀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寻找张炜此种叙事体式的源头的话,大约可以一直追溯到艾芜的《南行记》,虽然说一是短篇小说集,一为篇幅庞大的巨型长篇小说,但其基本的叙事体式却是相当一致的。也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一种叙事体式,其主观抒情性,自然也就成为《你在高原》文体上的一大特质。关于这种主观抒情性,曾经有论者以最后一部《无边的游荡》为例做出过精辟的概括:“诗人的‘游荡’确实是‘无边’的:从乡野到都市,从平原到高山,从海洋到森林……他一路‘游荡’,一路省察,足迹踏遍江河上下,目光横扫中外古今。大自然的绝美催生了他的侠骨柔情,人世间的龌龊激发了他的义胆良知。于是一个满身正气一腔幽思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冲破物欲横流的尘嚣巍然耸立在我们的面前。”[2]正因为设定了这样一位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形象,所以一种思想宣言式的甚至多少有点神谕特点的语式就贯穿在了整部小说之中。比如“……多少年了,一切都在失去,唯独剩下一颗愤怒的心。生活用一千次的失败来征服我,让我屈服;用一万次的碰壁和挫折来胁逼我,让我退缩。将来我的孩子长大了,他是个男孩,我可一定要留给他一个像样的故事啊。关于父亲的故事总要跟随人的一生,尤其是男人。”只要认真地读过张炜的《你在高原》,就不难发现,正是在以上这种句式的强有力支撑之下,这部小说才表现出了在当下特别难能可贵的浪漫抒情精神。
长篇小说《天行者》与作家刘醒龙此前一部影响很大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对于刘醒龙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够使得《凤凰琴》真正地脱胎换骨为一部合格的长篇小说。毕竟,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小说文体。有一种说法认为,中篇小说讲故事,长篇小说则呈现命运。这就是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只要能够把一个故事相对完整地讲述清楚就可以了。在一部中篇小说中,一般不需要有更多的人物,也不需要有相对长的时段中相对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相比较而言,一部长篇小说却不仅应该有更多的人物,有更加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得通过这所有的人物与故事传达出某种深沉的命运感来。刘醒龙所完成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工作。第一,刘醒龙巧妙地完成了叙事视角的一种转换。《凤凰琴》作为一部中篇小说,采用的只是张英才的单一化视角,到了《天行者》中,从第二部“雪笛”开始,小说的叙事功能就由张英才而不动声色地转移到了更容易对于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进行总体展示的余校长身上。视角的转移与多样化视角的运用,正可以被看做是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第二,尽管说《天行者》中转正事件依然是情节的重心所在,但同样是转正事件,刘醒龙所采取的表现方式却与《凤凰琴》有了很大的不同。《凤凰琴》只是描写了一次转正事件,而且还把它处理成了具有崇高意味的正剧,而在《天行者》中,刘醒龙不仅先后三次描写转正事件,而且描写方式也多有变化。张英才的转正是正剧,蓝飞的转正是闹剧,到了最后余校长他们的转正,干脆就变成了一场活生生的大悲剧。这样看来,虽然同样是余校长、张英才、邓有米、孙四海这几位在《凤凰琴》中出现过的人物形象,但到了《天行者》中,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却已经是一种曲折深沉的命运感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小说第三部第三次叙述描写余校长他们转正悲剧的时候,我们在感受命运捉弄余校长他们的同时,在体会作家一种强烈悲悯情怀的同时,也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社会批判锋芒的存在。归根到底,余校长他们的这种人生悲剧,正是当下这个未必完全合理的社会机制所一手造成的。虽然说从更高的艺术要求来看,《天行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还是有略嫌单薄之感,但由于刘醒龙在基本的叙事方式上采用了以上两种艺术手段,所以,作品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做是一部满足了长篇小说基本叙事要求的优秀作品。
作为曾经的先锋作家之一员,莫言多年来在如何有效地拓展汉语小说叙事方式上所作出的艰辛努力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诸如《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这几部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几乎可以说每一部都有着叙事方式的新创造。某种意义上,作家莫言差不多已经成为了叙事形式创新的代名词。这次获奖的《蛙》,同样在叙事体式上有新的思考和突破。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与莫言自己此前的长篇小说相比较,他的这一部《蛙》在思想主旨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首度开始以一种不无残酷的方式审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于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姑姑一生推进计划生育,以及此后长期为此而忏悔不已的故事的讲述,小说最终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了同时身兼叙述者角色的知识分子“我”也即蝌蚪的精神世界。大约正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样一种思想主旨,莫言才在《蛙》中特别设定了一种书信体外加话剧体的叙事方式。整部小说的叙事过程,可以被看做是蝌蚪怎样收集相关生活资料,酝酿一部名字同样为“蛙”的话剧剧本的写作过程。前五封信,是蝌蚪在向杉谷义人先生介绍与姑姑、与计划生育问题有关的人与事;最后一封信,则是蝌蚪创作完成之后的话剧剧本本身。这样的一种设计,所体现出的正是如同西方的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品一样的“元叙事”的意味。所谓元叙事也叫元虚构、元小说,它通过作家自觉地暴露叙事类文学作品的虚构创作过程,产生间离效果,进而让接受者明白,叙事类作品本身就是虚构,不能把叙事类作品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现实。这样,虚构也就在小说或者话剧等叙事类作品中获得了本体的意义。在我的理解中,莫言采用这样一种元叙事方式,一个根本的意图,正是为了能够帮助读者拉开与作品所再现着的历史场景的距离,进而会同作者本人一起以更加冷静客观的姿态来认识思考历史。除此之外,从小说结构的意义上说,在一部书信体的小说中,插入一部话剧,在话剧的进行过程中,再插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拍摄过程,很有一点俄罗斯套娃的意味。在我看来,如此复杂的小说结构本身,不仅寓言式地说明表现着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且也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叙事的难题。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关于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神奇插入。莫言插入《高梦九》,其实正是要借助于这位民国年间的政府官员,来最终宣判陈眉告状一案,借助于接受巨额贿赂之后的高梦九之手,来最终宣判被侮辱被损害者陈眉的败诉。陈眉的败诉,可以说是作家莫言对所谓的后30年中国历史所做出的最为沉痛的一种批判。而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来看,这样的一种沉痛批判,正是借助于高梦九这一形象的巧妙插入,才最后得以有效实现的。这样看来,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插入,一方面充分地体现了莫言超群的艺术想象能力,另一方面,也十分有效地实现了莫言预先设定的某种叙事效果。这就充分地说明,一些实力派作家的叙事形式创新,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一种更多地着眼于小说思想精神内涵表达的形式创新。
这次获奖的作家中,毕飞宇是最年轻的一位。他的《推拿》的引人注目,一方面固然在于取材的特别,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了一向被看做弱势群体的残疾人身上,另一方面,则显然与其堪称细致内在密实的叙事方式存在着不容分割的联系。从根本上说,以盲人世界为表现对象的《推拿》,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毕飞宇的现实主义,既不同于以往那种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宏大叙事见长的传统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当下颇为流行的以真实记录底层小人物庸常琐碎的生活场景为特色的新写实主义,即便是与新世纪文坛上其他颇有些新质的现实主义作品比较起来,毕飞宇的小说都堪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陈思和将《秦腔》所代表的现实主义趋向命名为“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秦腔》是在“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通过“大量的日常、琐碎、平庸的生活故事来铺展一个社会的面貌、记录一个时代的声音”[3]。也就是说,《秦腔》所叙述的内容和人们日常的生活太像了,太贴近了,太分不出钉铆了,简直就是日常生活的翻版。而当我们阅读毕飞宇作品的时候,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产生,只不过这个焦点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而变成了日常心灵。换而言之,就是毕飞宇《推拿》中的叙事方式,已经与文本中人物的日常心理流动过程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以至于你简直都辨不清还有生活场景、还有各种客观物事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毕飞宇只是在一味地玩心理转换游戏,而是说日常的生活图景早就融入了人物的心灵流动过程当中,或者也可以说被毕飞宇的独特叙述所遮蔽了,以至于我们所强烈感觉到的便只是“心灵”二字。从根本上说,将人物的心灵以日常化叙事的方式展开,在不同人物心理的缓缓变化中完成对整部小说的建构,从而达到某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如此一种“法心灵的现实主义”,才可以被看做是毕飞宇《推拿》叙事方式的特别之处。
读刘震云的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能够让人联想起赵树理来的那样一种既朴素日常又别有蕴藉的小说语言。当然,说刘震云的小说语言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并不意味着刘震云只是对赵树理语言的一种简单重复。与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总是依循着故事情节的演进方向向前直线推进形成鲜明区别的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是在某种自我缠绕的过程中进行着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打个比方,如果说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始终在依照着同样的频率行进的话,那么,刘震云的语言则是在踏步前进的过程中不时地要改变一下节奏,其中明显地夹杂进了某种跃进的频率。而且,细细体味,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鲜明的音乐节奏感。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音乐节奏感不仅给刘震云的语言增添了美的色彩,而且也使得刘震云的小说语言更加富有弹力。叙事语言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刘震云那种类似于“连环套”式的基本叙事体式,比如说上部《出延津记》中,作家对主人公杨百顺不断错位的人生的描写,即是如此。杨百顺本来想像罗长礼一样去喊丧,然而,乖谬的命运捉弄却使得他一再背离自己的人生理想:先是想跟老裴学剃头,但没想到却被老裴借故介绍去跟着老曾学杀猪;谁知杀猪学到半拉的时候,却又因为师娘的挑拨而被师父赶走;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又只好去老蒋的染坊染布;染布不成,被迫信了自己其实根本就不相信的意大利人老詹的“主”,去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一直到后来以倒插门的形式“嫁”给了吴香香,到发现了妻子吴香香与邻居老高之间的奸情。就这样,从罗长礼到老裴、老曾,再到老蒋、老詹、老鲁,一直到妻子吴香香,到继女巧玲,故事中的这些人物直如“连环套”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地牵扯了出来。实际上,也正是在这种“连环套”的故事发展过程中,杨百顺人生的悲剧性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表现。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在这看似由日常话语以“连环套”形式展开的庸常人生中,明显地凸显了刘震云对于国人生存境遇的一种形而上意义的深入思考。即如杨百顺充满苦难坎坷的悲剧性人生,作家虽然无一字精神或者哲学意义的渲染表现,但我们却不难从中体会到某种异常强烈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况味。按照存在主义哲学的解释,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不仅生命的诞生身不由己,而且生命的存在本身也是身不由己的。总之,“被抛”、“被动承受”正是理解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以这样的一种理解比对小说中所展示出来的杨百顺的苦难人生,说刘震云对于杨百顺的描写也明显地表露出了一种存在主义的形而上意味,就是一件无可置疑的事情。
三部分入围优秀作品叙事分析
第八届茅奖五部获奖长篇小说尽管说都已经达到了相对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但由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任何一次评奖都可能会有遗珠之憾。根据我自己长期以来的阅读体会,最起码,诸如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麦河》、宁肯的《天·藏》、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刘亮程的《凿空》、郭文斌的《农历》、秦巴子的《身体课》等作品,皆可圈可点,都应该被看做是这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收获。仅仅从小说本身的叙事方式而言,以上这些未曾获奖的长篇小说也都是各有千秋。篇幅所限,我在这里只能对其中的部分作品略作探讨。
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可以说是近年来最具有史诗气魄的以对国民性的批判审视为突出特征的一部长篇力作。在阅读《农民帝国》的过程中,我经常会联想到《红楼梦》《创业史》以及《秦腔》这三部长篇小说。与上届的获奖作品《秦腔》相比较,蒋子龙的这部同样以乡村世界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毫不逊色,既有对于人性的深度挖掘表现,也有相当出色的艺术结构与语言运用。只不过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叙事时空设定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贾氏重横向的空间拓展,他的叙事时间只有大约一年左右,而蒋氏重纵向的时间透视,他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十年,可以说是对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世界的历史风云变幻进行着深度探寻表现的长篇佳构。柳青的《创业史》在文学史上一向被称为具有史诗性品格的长篇小说,这样的评价与作家当时的主观追求是一致的,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某种终极追求,恐怕就是要全景式地再现土改运动以来中国乡村世界所发生的种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期以来,这样一种被普遍看做“宏大叙事”的创作模式在文学界是颇受诟病的,之所以会有所谓日常叙事的广泛流行,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但实际上,如果远离了这样的“宏大叙事”,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产生。而蒋子龙的这部《农民帝国》,很显然带有突出的逆潮流而动的特点,可以被看做当下这个时代真正优秀的“宏大叙事”作品。一方面,由于自然生命过于短暂的缘故,另一方面,当然更由于作家所处的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过于巨大的缘故,柳青意欲全景式再现当代乡村世界的艺术理想并没有能够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蒋子龙在完成着柳青前辈未竟的艺术使命。他的《农民帝国》,以极其宏阔的艺术视野,完成了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堪称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的史诗性艺术表现,实在是当下时代一部难得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至于《红楼梦》,是说蒋子龙的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结构的设定,在某些场景的描写,在一些人物的刻画塑造上,能够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比如,小说临近结尾处,写到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失踪多年的二叔突然出现在了狱中,并且还和郭存先聊了多半宿。如果从现实生活的逻辑上看,这样的一种情节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或许有的批评家会把这种描写方式,归之于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在我看来,与其归之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反倒不如把它理解为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更为恰当。不仅如此,小说中关于二叔,关于那棵“龙凤合株”的描写,也都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中关于太虚幻境,关于空空真人、渺渺大士的相关描写。
从叙事方式来看,以近距离关注当下时代乡村社会变迁为主旨的关仁山的《麦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在一部长篇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虽然较之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方式具有更大的叙事难度,但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倒也还比较常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关仁山在《麦河》中赋予其叙事功能的叙述者白立国,居然是一位摸得着但却看不见的盲人。让一位盲人来承担长篇小说中叙述者的角色,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还是第一次见到。况且,如此一种叙事方式较之于寻常小说难度要大得多。既然把盲人设定为小说的叙述者,那么,怎样有效地克服他的“看不见”这一叙事难题,自然也就成为关仁山必须解决的问题。很显然,正是为了弥补白立国身为盲人视而不见的缺陷,才有了苍鹰虎子的出场,才为虎子预留出了充分施展自己能力的艺术空间。按照小说里的交代,这苍鹰虎子不仅具有观察描述事物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把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情形都完整无误地全部转述给主人白立国。正因为有了苍鹰虎子这一形象的存在,盲人白立国才得以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叙事使命。
宁肯的《天·藏》,可谓是一部现代主义叙事特色非常鲜明的长篇小说。《天·藏》叙事层面上的双重结构与情节层面上的双重故事,如同坛城的布局一般相互缠绕纠结在一起所构成的立体艺术图景,乃可以被看做是这部极具探索性的长篇小说文体上最根本的特征所在。在这里,叙事层面上的双重结构,主要指的就是小说中的正文部分与注释部分以相互交叉的方式逐步推进故事情节。与一般的小说中,注释只是作为正文的补充性说明不同,在宁肯的《天·藏》中,就直观的感觉而言,注释部分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如此之大比例篇幅的占据,就使得注释部分已经不复是一般意义上的注释,而是远远地超越了所谓补充说明的价值层面,极为有效且有机地参与到了小说的整体叙事过程之中。一般意义上,如同《天·藏》这样采取如此一种叙事结构方式的小说,两条不同的结构线索会以一种泾渭分明的方式分别推进各自的情节故事,然后,在某一个交叉点上发生碰撞交汇,而后再进一步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天·藏》的情形却绝不相同,正文部分与注释部分不断地相互交叉碰撞,不断地离离合合,二者实际上是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式携手前行,以此来推动小说的叙事不断向事物的纵深处发展演进。这样看来,注释部分的实际功能其实已经不再是注释,而是作家宁肯一种带有极大创造性的有效叙事手段。同样不容忽视的另外一点是,在小说所采用的双重叙事结构之外,也还有对于感性和智性双重叙事话语的混杂运用。具体到小说文本中,所谓的感性叙事话语,就是指那些主要讲述人物故事的叙事部分,而所谓的智性叙事话语,指的就是感性话语之外那些以哲学、文化等为主要谈论内容的理论性叙事部分。
《身体课》是著名诗人秦巴子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虽然只是诗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秦巴子能够一出手就写出如此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具有明显现代主义艺术品格的长篇小说来,却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强调《身体课》已经不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就是因为作家的叙事重心已经彻底地远离了传统长篇小说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取而代之的,乃是叙述者对于笔端人物形象所进行的那些堪称精彩的心理精神分析。说实在话,就我自己有限的阅读体验而言,在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写作历史上,如同秦巴子的《身体课》这样彻底地放逐了传统的故事情节,完全把对人物的心理精神分析作为文本核心构成的长篇小说,绝对是第一部。我们都知道,在一般的意义上,严谨的学术著作才会采用逻辑层次分明的理性分析式的写作方法,而小说创作尤其是长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只有采用具有强烈动作性的感性叙述手段,方才有可能吸引更多大众读者的阅读注意力。秦巴子所采用的这样一种以心理精神分析为核心的小说写作方式,体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艺术实验精神。别的且不说,单就《身体课》所凸显出的这样一种鲜明的艺术原创意味,它就应该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中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总之,自有人类文学史以来,大的文学创作方法分类似乎不外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依此作进一步的划分,我们约略可以说,诸如刘醒龙的《天行者》、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毕飞宇的《推拿》、蒋子龙的《农民帝国》、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等,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莫言的《蛙》、关仁山的《麦河》、田中禾的《父亲和她们》、刘亮程的《凿空》等,是具有某种现代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小说;张炜的《你在高原》、郭文斌的《农历》等,是特色鲜明的浪漫主义小说;宁肯的《天·藏》、秦巴子的《身体课》等,则是现代主义小说。然而,叙事方式的多样化特点固然值得肯定,但就此次评奖活动的最后结果来看,既有现实主义的小说,也有浪漫主义的作品,所缺少的,唯独是具有现代主义艺术维度的小说作品。因此可见,虽然说这一届的评奖结果基本上反映了近几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但现代主义小说的榜上无名,却说明我们评委总体艺术观念的不够开放。行将结束此文的时候,我们殷切地盼望,在下一届评奖中,这样一种不尽合理的状况能够得到明显的改观。
[1]张寅德.叙述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刘维颖.锥心倾诉,泣血歌吟——张炜《无边的游荡》印象[OL].刘维颖的凤凰博客,2011-10-15.
[3]陈思和.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J].渤海大学学报,2007(3):5-12.
An Analysis of the Diversification Trend of Novel’s Narrative Style in Recent Years: revolving around the 8thMao Award
WANG Chun-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five award-winning works as well as some nominated works at the 8thMao Dun Literature Award,the author conducts an in-depth artistic analysis of the diversification trend in narrative style of novel creation in recent years.This diversification trend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uch narrative styles as realism,modern realism,romanticism and modernism.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narrative style;realism;romanticism;modernism
I207.425
A
1000-5935(2012)04-0053-05
(责任编辑郭庆华)
2012-03-09
王春林(1966-),男,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