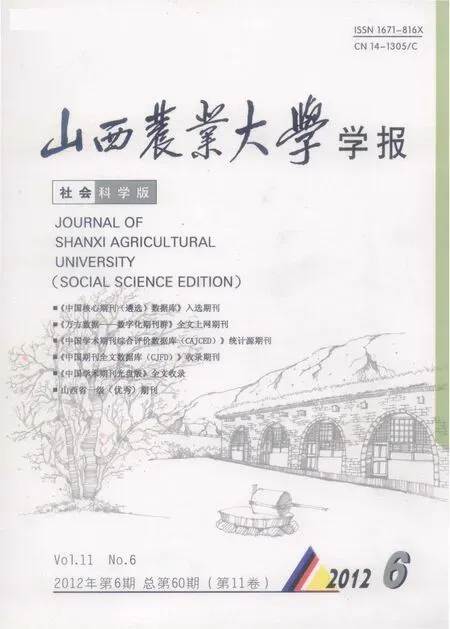从布衣平民到缙绅贵妇
——《帕梅拉》服饰政治的解读
陈栩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从布衣平民到缙绅贵妇
——《帕梅拉》服饰政治的解读
陈栩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作为《帕梅拉》中重要的叙事元素,服饰是帕梅拉定义和言说自我的重要方式,并从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她的身份和人格;服饰也是B先生控制帕梅拉身体和思想的特殊手段,是男性权力的试验场。从服饰角度分析帕梅拉的身份焦虑以及她与B先生一波三折的情感历程,从而揭示父权制社会中服饰政治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压迫。
帕梅拉;服饰政治;女性身体;身份焦虑;规训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narrative element in the epistolary novel Pamela,or Virtue Rewarded,clothing is the way Pamela defines and narrates herself which helps construct her identity and personality.Clothing is also a particular means with which Mr.B controls Pamela's body and thought and it becomes the testing site of male power.This paper examines Pamela's identity anxiety and her dramatic relationship with Mr.B to reveal the discipline and repression on female body by the clothing politics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Key words:Pamela;Clothing politics;Female bodies;Identity anxiety;Discipline
《帕梅拉》,又名《美德有报》(Pamela,or Virtue Rewarded,1740)(以下简称《帕梅拉》)是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创作的第一部两卷本书信体小说,它继承了笛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道德训诫为一体,被尊为“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英国小说”。[1]作品抓住了女主人公帕梅拉和B先生的情感纠葛以及她丰富的心理活动,以信件和日记的形式讲述了她在B宅的悲喜遭遇。作为小说的矛盾双方,帕梅拉和B先生之间存在着尖锐的观念对立和利益冲突。身兼地主、治安法官和议员等多重身份的B先生认为自己对侍女帕梅拉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帕梅拉则针锋相对地捍卫自己的清白和声誉,她拒绝B先生的威逼引诱,宁可失去生命也不肯失去贞洁。双方一波三折的情感关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展现这种关系的载体,除了评论界谈论较多的帕梅拉的道德和贞操观念,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服饰(Clothing)。
美国服饰研究专家埃里森·卢里(Alison Lurie)在其专著《服饰语言》(The Language of Clothes,2000)中指出,“服饰不但指附着在身体表面的衣料,还包括发型、与服装相应的配饰、首饰、化妆品以及身体饰物。”[2]服饰与人体紧密相连,它“既是身体的饰物又是身体的一部分,并在很多时候取得了与身体等同的地位,成为身体的隐喻。”[3]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服饰是帕梅拉作为仆人以及荣升贵妇人之后重要的身份象征,她以服饰为叙事媒介,在讲述自己悲喜遭遇的同时压制了真实的自我;服饰也是B先生欲望的直接投射,是他控制帕梅拉的特殊手段。本文从服饰角度出发,分析帕梅拉的身份焦虑以及她与B先生戏剧性的情感历程,揭示父权社会下服饰政治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压迫。
一、服饰掩盖下的引诱与反抗
帕梅拉出身卑微,但却天生丽质,被誉为“郡里最美的美人”。[4]她的日常穿戴都来自老夫人的衣柜,B先生在母亲去世后将她遗留的精美衣服悉数送给帕梅拉,他想让帕梅拉打扮得更加漂亮。而帕梅拉却感觉穿上这些衣服“实在是太奢华了”,[4]这种待遇已经大大超越了她的侍女身份,她在家信中表达了内心的惶恐不安:
“我在这里身上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适合我今后境况的;……我想,我最好是立刻就把适合于我今后环境的衣服穿上身;虽然它们跟我最近一些日子经常穿的衣服相比,看上去显得有些寒酸,但当我跟你们在一起时,我就可以把它们当作美好的节假日衣服来穿了。”[4]
帕梅拉之所以格外关注服饰形象,是因为它“不仅是性别的外在表现,而且塑造着人们的身份感,传达着自我的所有含义,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对他人的期望以及他人对自我的期望。”[5]敏感的帕梅拉意识到,只有简朴的服装才和她当下低微的身份相称。服饰象征的阶级界线是绝对不能逾越的,任何在着装上的僭越和变易将是对这种稳定秩序的破坏。服饰作为一种表征符号,是帕梅拉“生命状态的物化显现”。[6]而对穿着模式的恰当选择表明了帕梅拉明确的身份归属和角色定位,所以她宁可穿“灰褐色的土布衣服和其他简陋朴实的衣服”,[4]也不愿身着华丽的服装让邻居们说长道短。然而,当顾虑重重的帕梅拉穿上B先生赠送的新衣时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当我把一切都穿着打扮完毕以后,我把系有两条绿色带子的草帽拿在手里,然后对着镜子上下左右地打量着自己,得意地像什么似的。说实话,我在这一生中从没有这样喜欢过我自己。”[4]
帕梅拉的精心打扮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她走下楼梯时,女仆雷切尔对她行了屈膝礼;女管家杰维斯太太惊呼帕梅拉“完全变了个形状”;[4]而此时碰巧走来的B先生把她当成了“一位陌生人”。[4]服饰固有的“赋性功能”(Transnaturing power)[7]在帕梅拉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换言之,全新的造型赋予了服饰主体原本并不具备的性格特质,帕梅拉仿佛是一位颇具威仪的名门闺秀,让周围人心生敬畏。
事实上,B先生对帕梅拉的美貌觊觎已久,他赠衣的根本目的是要以服饰为诱饵勾引帕梅拉做他的情妇。B先生笃信一切年轻的东西都是漂亮的,而帕梅拉的身体一经服饰的包装和美化将更具吸引力。“男性将女性作为他的财产,并要求她提供身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8]为了破坏帕梅拉的贞操,B先生开始以各种方式对其进行骚扰:他趁帕梅拉在凉亭做针线活时试图对她越轨放肆;他还干涉她的写作和通信自由,他甚至买通信差约翰,时常拦截帕梅拉的私人信件,以为通过窃读会获得更多驾驭她的权力。书信成为帕梅拉身体的“替代品”,①书信和日记是帕梅拉身体的隐喻。帕梅拉在婚后主动拿出日记请B先生阅览,象征着她在肉体和精神上已屈从于B先生。[9]阅读她的信件也就意味着占有了她的身体。B先生的骚扰遭到了帕梅拉的坚决抵抗,她表明了自己捍卫贞洁的决心:“我能够甘心乐意穿着破衣烂衫,啃面包,喝清水,过穷苦的日子,我将会接受这一切,而决不会丧失我的良好声誉,不论这诱惑者是谁。”[4]为了逼迫帕梅拉就范,B先生不惜采取易装(Transvestism)手段,他乔装打扮成女仆潜伏到帕梅拉的卧室,趁她夜晚入睡之际进行偷窥,从中获取感官和心理上的满足:
“于是,我(帕梅拉)就到两个内室里仔细查看了一下,并在我自己的内室里像往常一样跪下祈祷,手里还拿着衬衣裤;回来时,我从那位我以为睡着了的姑娘身旁经过。我根本没有想到,那竟是十恶不赦的主人穿着她的长外衣和裙子,她的围裙则罩住他的脸和肩膀。”[4]
易装是“身穿异性服装,以从中获得性快感的一种行为方式”,[5]易装意味着“个体外在性别符号的变化,并带来社会性别角色的改变。”[10]B先生不顾着装禁忌而男扮女装,破坏了服饰固有的界定性别的功能,“性别因为服装的变幻真正成为一种表演性的属性,两性的界限变得更为模糊”,[10]B先生借助新的性别和身份达到了骚扰目的。这种易装掩盖下的窥视欲是“主动型的,并带有一定的攻击性,将他人当作欲望客体,以满足自己观看所带来的快感。”[11]偷窥为B先生积蓄已久的欲望找到了释放出口,他男扮女装“似乎在掩盖肉体和肉体下的本能冲动,实际上却是在凸显肉体和暴露欲望”。[3]可以说,易装行为缓解了B先生因无法控制帕梅拉的身体所产生的焦虑。在服饰语言中,符号(sign)和意义(meaning)有时并不对等。B先生的威逼引诱让帕梅拉对这位曾经是她眼中的正人君子失去了所有敬畏。B先生华美的衣服和他的身价并不相配,尽管“他穿着很漂亮”,[4]是个英俊文雅的先生,但他的内心却不像他的外表那么好,“对她身体的侵犯实际上是对社会规范的践踏”,[9]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已经使他整个人“变丑了”。[4]华丽的服饰已不再是区分贵贱的标准,高尚的心灵才是唯一的尺度。
不堪其扰的帕梅拉决定辞职回家,她将所有的衣物收拾成三个包裹:第一包衣服是“老夫人的礼物”,[4]以怀念她的仁心善意;第二包是老夫人去世后B先生送给她的物品,用帕梅拉的话说,这是一个“邪恶的包裹”;[4]第三个小包裹则是帕梅拉自己的衣物。这三个包裹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第一包衣物是老夫人所赠,这与帕梅拉“模糊的地位及与仆人不相称的教养有关。”[12]帕梅拉在老夫人的教导下研习上流社会大家闺秀的基本功课,学跳舞、音乐、钢琴和写作。一个出身卑微的布衣女子被调教成高雅脱俗的准贵族小姐。此外,她还常穿老夫人赐予的旧衣物,这使得她的地位不同于其他仆役。一旦老夫人去世,再穿华贵的衣服将不合时宜,因为“我不能在我可怜的父亲家里穿上这些,要不然我那小村里所有的人都会对我冷嘲热讽、指责不停的,所以我决定不要它们。”[4]第二个“邪恶的包裹”[4]隐藏着B先生的阴谋诡计,它代表了上流社会对下等阶层的轻视和玩弄的态度,这是一种“耻辱的代价”。[4]在三中选一的关键时刻,帕梅拉弃绝物质利益和“主人加诸于她的外衣和形象”,[12]毅然选择了第三个包裹,在她眼中“全世界的财富与虚荣,将比乞丐所能穿的最低劣的破布更值得鄙视”。[4]对包裹的取舍反映了帕梅拉的身份定位和道德选择,而对自身服饰的坚守则是她强化身份认同的有力手段,也是她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特殊方式。帕梅拉始终认为自己的灵魂和公主的灵魂同等重要,第三个包裹“象征着她的清白和优良品质”,[13]她的反抗是女性对自己身体权利的正义申诉,体现了她做人的尊严。
二、服饰规训下的女性身体
在清教主义占主导思想的父权制社会,女性美德主要体现在保护自己的贞洁并经受对“淑女”必备美德的种种诱惑和考验。作为第二性和下层人物,帕梅拉的美德“既是她自然习得的行为准则,又是她必须维护的立身之本”,始终以贞洁淑女自居的帕梅拉“恰到好处地维持了与贵族阶层的审美距离,显现出理性和最终合法实现世俗追求的谋略。”[14]她的抗争并非对等级制度进行革命性的否定,相反,她追求的依然是男性意识形态认可的模范女性,并试图通过有利的婚姻实现阶级跨越的潜在目标。
帕梅拉的美丽容貌和高尚心灵最终感化了B先生,他决定改邪归正向她正式求婚。帕梅拉也对男主人心生爱恋,二人终成眷属。帕梅拉由身着布衣的卑微侍女荣升为一袭盛装的贵妇:
“我穿上了华美的亚麻布衣服,缎面的鞋子,画面的白色棉布长袜,一条用垫料衬塞以后缝拢的漂亮衬裙,一件华美、宽松的绿色绸外衣;一个法国项圈,一条镶着花边的麻纱围巾和一副干净的手套;我手里拿着扇子,像一位高傲的轻佻女人一样照着镜子,几乎都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位贵妇人了。”[4]
新的服饰象征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产生,表明帕梅拉已将自己的生活纳入“一种新的生存理念和道德秩序中。”[3]帕梅拉通过合法的婚姻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然而,出身豪门的B先生屈尊迎娶贫寒低微的乡下姑娘,双方身份的巨大悬殊决定了他们婚后生活地位的不平等。夫妻关系的实质是一种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奴关系。
帕梅拉将自己的幸福生活归功于B先生的宽容大度,她不无感恩地向他保证:“我能愉快地尽到我的职责,在言行举止方面体现我对您的感激,使我自己配得上您对我继续保持深情厚爱。”[4]帕梅拉深知,只有自觉遵守上层社会男性对女性行为的强制性规定才能融入并获得上流社会的认同,而B先生也认为妻子应是淑女楷模,要为优秀的贵妇人树立良好的榜样。他在穿戴方面给她提出了具体要求:
“我希望你在吃正餐的时候,永远穿着礼服,除非发生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那是例外;不论你是到外面去还是待在家里,都要这样。这样就会使你在服装与举止方面继续保持那种从容自在的可爱风度……另外,你这样做将会使我相信,你认为在你丈夫面前,就像在你不常见的人们面前一样,你本人也必须保持优美的外观。”[4]
B先生从着装入手,以相对温和的方式规训帕梅拉,目的在于制造驯顺的身体。[15]帕梅拉没有自由穿戴的权力,衣服是“附加在穿戴者身上的社会关系的体现”,[7]她的身体演变为男性权力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角斗场。B先生通过着装规定给帕梅拉“塑身”,期望将她改造成符合男性审美趣味的“家中天使”。事实上,以B先生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审视是一种“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B先生作为观看者被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帕梅拉作为被观看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看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看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11]为了维护淑女形象和良好声誉,她被迫掩饰内心的真实感受,逐渐认同一个与自己成为对立面的自我,“我内心感到不安,但又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样才不会有什么过错归咎到我头上来。”[4]锦衣华服之下,帕梅拉的身体变成一个表演的身体(aperforming body)。苏珊·鲍德(Susan Bordo)在《身体与女性气质的再生产》一文中指出,女性身体更容易成为驯顺的身体,她们会自觉接受压迫和改造,并屈服于外界的准则和规范。[16]帕梅拉不得不戴着面具生活,她成为“一个极特殊的视觉对象:景观”,[17]这造成了她严重的身份焦虑和主体性的丧失。
三、结语
作为小说中心意象的服饰具有“隐喻的规则和文法”,[6]体现了穿戴者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是物化的意识形态。服饰不但是帕梅拉定义和言说自我的重要方式,而且建构了她的身份和人格,塑造了英国小说史上第一个既有高尚美德又有隐性世俗追求的现实模范女性形象;服饰也是男性权力的试验场,B先生借助服装将帕梅拉改造成贵族阶层认可的淑女典范,服饰成为他控制帕梅拉身体和思想的特殊手段。理查森将服饰与性别、阶级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构成张力,服饰则是维持这一三角关系的主要支撑,这在帕梅拉与B先生的情感变奏中表露无遗,并在二者的冲突融合下使服饰象征化、寓意化。
[1]Sale,William M."Introduction",Samuel Richardson,Pamela[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58:v.
[2]Lurie,Alison.The Language of Clothes[M].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2000:4.
[3]任湘云.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8,82,76.
[4][英]塞缪尔·理查森.吴辉译.帕梅拉[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39,9,8,34,15,45,46,39,6,194,189,67,69,68,3,68,69,286,341,346,341,342,274,53,274,76,12,65,110,165,16,73,380.
[5]Woodhouse,Annie.Fantastic Women:Sex,Gender,and Transvestism[M].London:Macmillan,1989:9,14.
[6]张荣国.服饰:一种隐喻的表述[J].辽宁大学学报,1999(1):19-21.
[7]Jones,Rosalind Ann and Peter Stallybrass.Renaissance Clothing and the Materials of Memory[M].Edinburgh:Cambridge UP,2000:3.
[8]Beauvoir,Simone de.The Second Sex[M].Trans.and ed,H.M.Parshley.New York:Vintage Books,1989:157.
[9]Laden,Marie-Paule.Self-Imitation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Novel[M].Princeton:Princeton UP,1987:81,74,78.
[10]边静.性别越界的狂欢——华语电影中的“易装”审美[J].艺苑,2006(11):51-55.
[11]陈榕.凝视[A].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9-361.
[12]黄梅.“英雄”的演化从茉儿到帕梅拉[A].英美文学研究论丛[C].2009(11):65-92.
[13]Doody,Margaret.A Natural Passion:A Study of the Novels of Samuel Richardson[M].Oxford:Clarendon,1974:4.
[14]李维屏.英国小说人物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91-93.
[15][法]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56.
[16]Bordo,Susan.The body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femininity[A].Unbearable Weight:Feminism,Western Culture and the Body.[C]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 of California Press,1993:2363.
[17][美]约翰·伯格.戴行钺译.观看之道[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7.
(编辑:佘小宁)
From a Commoner to a Noblewoma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othing Politics in Pamela
CHEN Xu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Shanxi 710128,China)
I106.4
A
1671-816X(2012)06-0549-04
2012-01-10
陈栩(1985-),男(汉),山西新绛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