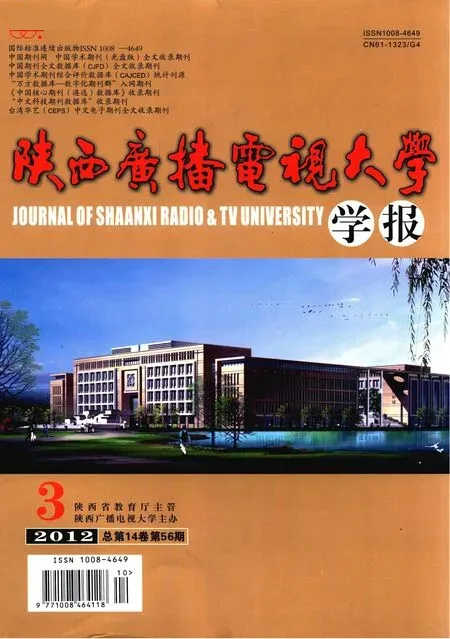论魏晋风度的个性解放思想
王 虹
(陕西画报社,陕西 西安 710068)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具有热情的时代,诞生了一群特立独行的人物。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以简约生动的笔墨记录了一些属于那个时代的名人逸事,刻画了这一时期的时代风貌和人物精神,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后世称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作为最强烈的文化印记,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和士人的“集体无意识”,彰显了士人群体的得意与失意、欢乐和痛苦,传达着士人精神的巨大张力。余英时先生曾说,魏晋士人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又不与其它个体相同,而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并期望达到为人所认识之目的。
《世说新语》大部分篇幅中的士人形象都和所谓的“魏晋风度”相联系,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士族名士特殊的言行举止。魏晋士人肯定人,重视作为“主体”的人,强调人的自由,注重自然情感的抒发、个性的张扬以及自我价值的抒发,这样的“自我”的探寻之路,包含有追求精神自由,解放个性的内涵,同时也是对于传统的反叛,而这种反叛其实是对于庄子所倡导的人性的继承,故而魏晋士人们是在以寻找“自我”的方式追求作为自然人性的复归。
一、魏晋风度的个性解放内涵
“魏晋风度”一词出自鲁迅先生那场著名的演讲,之后的学者就沿用了该词。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环……可见,药、酒、姿容、神韵,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词章,才构成魏晋风度。”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说: “魏晋名士之人生观,就是得意忘形骸。这种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魏晋风度’: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立法,不拘于形迹”,把魏晋风度归于精神气质。可以说,魏晋风度就是魏晋时期士族名流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的综合体现,是他们追求精神自由、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的集中表现。
情感和个性是自我价值实现依次经历的过程,自我意识通过情感来表达,强烈的自我意识形成独特风格,从而体现了自我的个性,不同的个性形成了带有自我属性的价值观,并有意识的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世说新语》所反映的个性解放思想,亦可以从情感流露、个性张扬、自我价值实现三个层面来剖析。
(一)情感的流露
情感是人对外界刺激的心理反应,情感抒发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表现。《世说新语》中人物流露的情感通常都是真挚、自然的,有时甚至是一种本我情感的外露,这种情感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情感,无关道德、政治层面,而是一种锋芒毕露、刺人、耀眼的情感。魏晋士人情感的抒发从两个方面散发出浓厚的自我意识。
其一是以“我”为圆心,对情感对象进行着相对自由的选择。如“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郭林宗自己“衣不盖形而处约,味道不改其乐”,对朋友的选择也有自己的要求。所以尽管袁奉高和黄叔度都是同辈的汝南先贤,他却有意识地选择了黄叔度,因为“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而“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耳”。可见士人很乐于用自己的情感标准来选择情感对象,让自己的情感得到真正的满足或者宣泄。又如阮籍与吕安的选择,“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阮籍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白眼以对。”所以嵇喜来吊丧,阮籍现其白眼,直到嵇康来,才青眼有加。
其二是在对情感对象的选择有“自我”的评判标准之后,在抒发自我感情时就拥有了相对自由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之所以说它自由和体现出时代人文精神的新风貌,是因为它有平等的指向,可以针对任何人,包括当权者。“诸葛靓后入晋,除大司马,召不起。”诸葛靓敢于对晋帝表现“吞炭漆身”的报仇之怒;陆完不畏王丞相的强权,直言拒婚;何充敢于挑战王敦的权威,直言不讳…… 《世说新语》对强权政治的话语霸权已经有了初步瓦解。士人已经开始对权威进行质疑、挑战,这种质疑和挑战来自内心对“自我”自由的无限渴望和追求。
魏晋士人在自我情感流露的背后有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这与庄子的突破世俗和自我设限,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同时,魏晋士人在追求庄子式的精神自由时,表现出了相对自由的话语权。这种相对自由的话语权也带有西方个性解放的影子,即追求没有阶级、等级之分,人人平等的思想,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言是具有先进性的。
(二)个性的张扬
个性就是一个人的整体精神面貌,是一个人较长时间形成的比较固定的特性。《世说新语》中记载了魏晋名士许多纵情越礼和毁坏礼制的言行,蔑视传统礼法、违背礼俗的言行成了他们张扬个性的主要手段,尤以阮籍、刘伶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 ‘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饮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 ‘死便掘地以埋。’”刘伶带有恶作剧性质的举动表现了对当时社会传统规范的蔑视和戏弄之情,也彰显了他特立独行、随性的个性。
阮籍更是处处与礼教规范对着干,礼教规定男女授受不亲,他却偏与邻妇一起饮酒,并醉卧其侧。《礼记·曲礼》明确规定:“嫂叔不通问。”他却定要与嫂子送别。礼教又规定母丧期间不食荤,他却大啖酒肉,神色自若。《任诞》第八条刘注引王隐《晋书》曰:“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魏晋名士言行中经常故意违礼而行并以此自持,阮籍本人就对礼法之士的指责针锋相对地反驳:“礼岂为我辈设也。”]别人奉作金科玉律的礼教规定,在他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他放浪形骸却不失赤子之心,在非礼非理中尽显其真淳至性。
刘伶和阮籍之辈的不羁行径,表现了他们蔑视名教的一面,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他们看来,名教就是统治者把孔孟对礼的种种规定和对人的道德修养的种种限制强变为外在的社会准则,要求世人绝对服从,使人的自然本性湮没在儒家礼教中。他们反对强制的约束,对抗空洞、虚伪的名教,反感被掏空血肉徒留空壳而无儒家道德合理内核、真正情义的道德戒律。魏晋士人追求的个性解放与庄子有不谋而合之处,魏晋风度中自我个性的绽放正是对庄子精神的继承。庄子认为个性解放就是抨击宗法礼制文化和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束缚,把人从世俗价值和工具价值中解放出来,主张人应该有“独志”,成为“独有之人”。所谓“独志”就是不同凡俗的独特之志;所谓“独有之人”,就是能够立于天地之间的人,也就是摆脱了宗法传统礼教文化重重束缚的人,亦即庄子在《天下》篇中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人。
(三)自我价值的实现
自我价值是指在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中,社会和他人对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肯定关系,包括人的尊严和保证人的尊严的物质精神条件。按照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理论,个体价值只能到群体之中才能得到确立,个体只有紧紧依附国家、君王身上才能求得不朽,而积极入世、仕进求禄、忠君为国、建功立业则成了士大夫确立个体价值的主要内容。中国士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普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但在封建政治、伦理、精神、文化的全面系统的压抑摧残之下,人们普遍缺乏独立的人格、“自我”的尊严和品质,没有自由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而魏晋士人却是“把自我的发现、追求和实现看成是人生最大的价值”,他们较之过往的人更注重生命存在的形式与生活的质量,“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魏晋名士对自我的肯定是无畏的,他们敢于抗争世俗礼教、排斥一切外界标准。对于传统人生价值观,他们的名言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可见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否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认识。
魏晋士人以“我”为核心,故在自我评价上往往有超高的自信。士人中颇多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狂者。“狂傲”是士人自我崇拜自我标榜的一个突出表现。刘惔是清谈家的佼佼者,当时的人对于刘惔的清谈水平多有赞誉,刘惔自己也充满了强烈的自信,《世说新语》中记载:“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在刘惔的眼中,像自己这样,才是第一流的清谈家。他的狂放、自信尽显无遗,这种普天之下,唯我独尊,毫无顾忌的自我夸耀,也许带有狂妄之气,却是对自我价值的毫不含糊的肯定。一句“正是我辈耳”尽显豪气,生动的体现了魏晋风度,体现了魏晋士人追求个性独立和解放的自由精神。一个人活在世上,作为一个个体,他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晋人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这种不可替代性,所以他们能一扫汉儒的谦恭俭让的传统教条,坚持自己的才能和价值,张扬自己的个性。
又如“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 ‘固当不同。’公曰: ‘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哪得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皆擅书法,两人技艺高下优劣另当别论,但作为儿子,王献之当别人问及他与父亲的书法孰优孰劣时,当仁不让地坚信自己的书法有自己的长处,以自己的书法殊于乃父为荣。当听到谢安说大家认为其父的书法高于他时,他更是不屑地回应:“外人哪得知”,充分表现了对自我的信心和肯定。虽然当时的士人都推崇王羲之的书法,但这毫不影响王献之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这样的自信也正是西方哲学所谓主体自觉的强烈表现。
二、魏晋时期产生个性解放思想的原因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东汉末2世纪到东晋末5世纪初,也就是魏晋以来的的三百年时间里的名士风流。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一反传统社会伦理,以追求个性解放为主要特征的魏晋风度,必然有特殊的原因和条件。
(一)复杂的社会原因
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不幸时期,自然灾害频发,政治动荡,佛教兴盛,不仅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催生出新的哲学、文化思潮。
魏晋六朝几百年间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据《后汉书》“帝纪”和《五行志》、《天文志》等资料记载,仅从和帝永元元年到献帝建安25年间,就发生水灾54次,旱灾40次,地震69次,蝗、螟灾29次,瘟疫18次,大风冰雹等41次,基本上每个年头都有灾害发生,甚至一年有多种灾害,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造成了严重损害,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在人们的心中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和震撼。长期不断的自然灾害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对于死亡的恐惧使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也迫使一些知识阶层开始思考人的生存价值以及死亡的意义等深刻的哲学问题。
同时,这一时期政治空前动荡,社会非常不安。首先是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党同伐异,迫害忠贤,激起了士人阶层的强烈义愤。士人们相互激励,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群起反抗外戚、宦官,弹劾权奸,议论朝政,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这对腐朽的上层封建集团构成了威胁,引起上层统治势力对士阶层的迫害与镇压,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致使李膺、范滂等二百多士人被杀,六七百人遭废锢、流徙。这两次锢之祸使士人开始思索什么是人生的价值,何为个体的真实存在以及怎样主宰自我生存命运,促使他们渐渐唤醒了自我意识。再者是政权不断更迭,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上起建安,下迄隋朝建立前夕,共三百八十余年,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的局面只维持了三十年,就开始了不断的征战和割据。在北方先后存在十六国,后来是后魏、北齐、周,在南方是东晋、宋、齐、梁、陈,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这种更迭与割据,必然给士人的心理造成深远的影响,因为每次的朝代更迭都会使得一批名士遭到杀戮,如何晏、嵇康等人。这使得大批名士为求自保不愿出世为官,打破了儒家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人生价值观。士人自全的心理就是魏晋士人开始关注自我的表现,残酷的社会现实将魏晋士人从心系朝政中推出去,推向了寻找自我的心路。
另一方面,佛教大约于汉明帝永平初年传入中国,到魏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佛教兴盛的原因主要是君主崇信,大力推广。如三国时吴孙权曾迎康曾会,大起佛寺;后赵石勒、石虎看重佛图澄,起寺890余所;苻坚信道安;后秦姚兴礼遇鸠摩罗什,以国师礼之;后魏孝文帝7次下令振兴佛教;宣武帝亲讲《维摩经》,寺院多至2000余,僧侣200万;南朝梁武帝3次到同泰寺舍身事佛等。因此,佛教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在魏晋社会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成功“上位”,渐渐成为一股社会主流宗教。佛教在为封建统治阶层利用来控制人民、稳定民心的同时,其广泛传播和兴盛对于唤醒人的自我意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佛祖释迦牟尼来到人间的第一句话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里要注意的是,“唯我独尊”的“我”字,并不是单指释迦牟尼本人,而是指的全体人类的每一个人。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人在宇宙中是顶天立地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宰,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不必听命于任何人或任何超乎人的神。同时,佛教的一些教义,如“彻底的认识你自己,你就会认识佛”,“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等等,都引导着人们将目光关注到自身的内心中来。佛教从宗教意义上宣扬了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和追寻自我的必要性。
(二)深刻的士人心理原因
汉武帝时期定儒学为官学,与政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慢慢渗透到政治权力中去,成了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它的学术色彩渐渐消退了。但到了汉末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坏,经学中衰,由儒家思想建立的一套人伦关系、行为准则和是非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现实生活。也就是说,这些准则失去了它们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儒家地位下降了,同时诸子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尤其是几次少数民族入侵并统治时期间接导致了儒家传统地位的衰弱。儒学统治地位的解体,进一步解放了当时的社会思想。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汉末的三国纷争,西晋统一后的“八王之乱”,晋室东迁后的王敦、桓玄等人作乱,北方十六国的混战,战乱和分裂伴随着饥馑、瘟疫,使得作为社会最敏感群体的文人,总是要同时承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煎熬。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惨遭杀戮,使文人感叹人生短促、命运难卜、祸福无常。动乱、险恶的生存环境,使得魏晋士人无法实现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加之儒家至尊地位的倒塌,儒学彻底失掉了统治人心的力量,士人便转而寻求另一种可以寄托、安慰灵魂的信仰,而这种理想人格与超越精神在中国古代常常被归属于老、庄一流,于是老、庄思想大行其道。另一方面,这时的经学不仅使士人们所依托的明经求仕的路走不通了,而且其本身也走上了更为繁琐的不再有生命力的末路。但是经学所需求的博学通识的知识风气进一步拓展了思想的资源,却为代之而起的玄学这种思辨性极高的哲学奠定了基础。于是玄学从儒家很少提及的“性与天道”这一关于人性与宇宙终极的话题出发,开始它的探讨与追问。
三、魏晋时期个性解放思想出现的时代意义
魏晋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了独特的魏晋风度,其中既有先秦老庄的自由精神,也透射出西方个性解放的影子。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具有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
“自我”意识的萌芽在魏晋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突破性的。魏晋之前的几百年间,都是儒家独尊的时代。儒家追求的是一种中庸之道,即“过犹不及”的理论,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倡最高标准的人生观为“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在一定的时代里是具有先进性的,然而随着封建专制的加深,占传统主流地位的儒家学说、哲学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制约人性发展、扼杀个人属性的“名教”。名教就是统治者把孔孟对礼的种种规定和对人的道德修养的种种限制强变为外在的社会准则,要求世人绝对服从,使人的自然本性湮没在儒家礼教中。所以在魏晋之际,适逢儒家的统治地位崩溃,传统信仰产生重大危机,魏晋士人便开始寻找新的人生信仰,而老庄之说的重新崛起,恰巧像是给了魏晋士人在黑暗中的一丝曙光。庄子的学说使得士人们开始反抗这些枷锁,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追寻和把握自我的本性。魏晋士人的“自我”探寻的背后所隐藏的是魏晋士人对于个性解放和人性复归的渴望与呼唤。他们开始颠覆过往压抑个性、过分强调人的社会功用论而泯灭人性的“名教”,实现人性的复归。因此,可以说魏晋时期的人性是庄子提倡的人性的继承,魏晋风度的文化意义在于魏晋时期士人们追求庄子自然人性的复归。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所提倡的人性思想带有避世消极的态度,但是魏晋风度则不同。魏晋士人对于寻求自我有着一份积极主动的态度,虽然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他们从外在的探索转而进行内心世界的摸索,但他们没有避世,依旧勇敢坦诚的面对残忍的世界,所以魏晋士人甚少有人得以保全性命的。尽管他们付出的是血的代价,但是他们仍前仆后继地希望通过升华自我以治世。因此,魏晋士人们除了追求精神的自由以及个性的解放外,他们仍寻求作为自由个人的一切权利。他们对自由话语权的追求与西方对于自我权利的追求是一致的,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魏晋风度中个性解放思想的的文化传承意义以及进步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诗歌中浓厚的自我人格张扬,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明显具有魏晋风度的影子。虽然后世各朝代中也时而会有这种魏晋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的闪现,但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剧等因素,都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流。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有在魏晋这个特殊的时代里,魏晋风度成为时代的主流,引领着当时的士人们走向自我的人性复归之路。
]
[1]刘义庆,刘孝标,朱奇志.世说新语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7.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739.
[3]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J].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M].安徽:黄山书社,1989.
[6]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