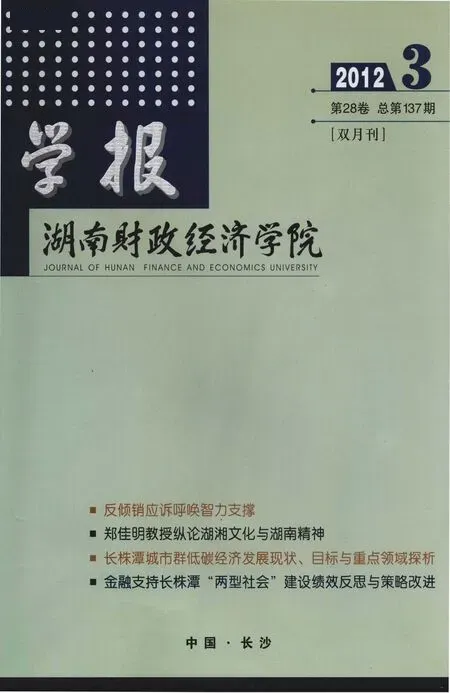富豪移民潮与遗产税的延伸
张永忠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一、富豪移民潮与政府困境
一股来势汹涌的富豪移民潮正在我国兴起。2010年,中国社科院《全球安全与政治》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2011年,胡润研究院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2011年,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的调查结果认为,近60%的高净值人群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这方面的考虑。美国国务院公布资料显示,2009财年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而来自加拿大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加拿大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其中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1]毋庸置疑,移民潮对我国经济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必将造成我国财富、人才、税收和消费的严重流失。
1、我国富豪移民潮将持续很长时间
富豪移民是冲着移入国优质的教育、洁净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完善公平的法制环境以及富人们最迫切需要的安全感等而去的,但在这些方面,我国在较短的时期内难与移入国竞争。因此,目前这股移民潮仅仅是开始,很有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而这将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长期失血。
2、我国富豪移民潮将导致财富大规模外流
尽管目前的富豪移民更多的只是移民而不是投资,即只是花钱买了一张绿卡,并未放弃我国的公民身份,大部分时间还是生活在我国国内,其大部分资金与产业主体也依旧在我国,是移“名”,不移“资”,因此流出的财富并不很多,但这也只是暂时的状况。正如武汉大学尚崇生教授所言:“这一代富豪的生活还在中国,但很多富二代、富三代们或在外国读书,或在外国长大。他们可能成为外表黄皮肤,内里完全西化的‘香蕉人’。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代富豪的财产最终会传给下一代。而当这些孩子们都是在国外长大的,甚至后辈都是在国外出生时,财富就有可能外流。”[2]也就是说,真正大规模的财富流出时期尚未到来。
3、富豪移民潮将对社会大众心理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股移民潮还将对一般民众和其他企业家的心理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会使一般民众更加不平和不满,会强化其他企业家的不安全感,而这会使一般民众和其他企业家对我国经济前景失去信心。总之,这股富豪移民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尤其是潜在的影响,绝不容小觑。
这股移民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重大,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政府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努力改善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法治环境,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富豪移民潮问题,但这在短期不可期待;政府可以而且必须禁止非法致富的富豪移民,对其进行严厉查处,绳之以法,但这只能是对一小部分富豪而不是全部;对于富豪移民中的绝大部分,即合法致富的富豪,基于自由迁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绝对不能采取愚不可及的“设限”措施,阻止富豪移民,但舍此,似乎再无其他措施,能在短期内有效缓解富豪移民潮,以防止或减轻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这股富豪移民潮使我国政府陷入了困境之中,为此,需要进行积极的理论探索。
二、遗产税原理与延伸制度
对于富豪移民,尽管绝大多数的公众不赞成政府对其设限,或禁止,但同样的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公众对富豪移民内心不满。不赞成设限或禁止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公众理解自由迁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内心不满的原因则是,绝大多数的公众认为移民的富豪充分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但未尽先富带动后富的责任,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潜意识中感觉到,富豪占有的财富中有不小的部分是社会公众应得的,富豪移民使其将这部分财富完全据为己有。遗产税原理正好说明了绝大多数公众感觉的正确性。
为什么巨富应该缴纳遗产税?是因为一小部分国民占有了他人应得的巨额财富,才成为巨富。为什么一小部分国民能占有他人应得的巨额财富?是因为一小部分人在社会上处于强势,对本应属于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形成了垄断,进而利用其垄断地位,制造了有利于自已的分配方式,在分配中占有了其他人应得的财富。垄断本身常常就是一小部分国民对全社会已有财富的独占,垄断又使这些人得以在新创造的财富中对他人应得部分不断占有,由此形成巨富、暴富。这就是所谓的赢家通吃,胜者全得。而能被垄断的各种资源,也不只是技术,除个人天赋、个人能力和个人努力以外的土地、森林、草场、矿产、环境、人文、历史、知识、资本、权力、信息、组织、人气、话语权等等形形色色,无一不是。因此,赢家通吃,胜者全得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能够通吃或全得的赢家或胜者尽管是国民中的一小部分,但绝不是个别。这些资源属于全社会,因而称其为社会资源。因为这一小部分国民的巨额财富中,有相当多的份额应属于全社会和来自全社会,因而应该归还给全社会,而不能遗赠给自己的后代。而能承担起这一归还角色的,非国家莫属,国家能据以完成这一归还任务的最佳方式,就是税收。这就是遗产税。因为遗产税的这些基本原理能被“垄断”、“资源”和“社会”及其相互关系较好地概括,因此,我们称其为社会资源垄断论。[3]
既然巨富们占有了社会公众巨额的财富需要归还,为什么不要其生前归还,而要其死后归还?这是因为许多资源垄断的形成往往与个人的天赋、能力和努力关系极大,人类的法律总是对其难以有效遏制的,而且这些与个人的天赋、能力和努力关系极大的各种资源垄断常常是有效率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需要的 (比如对知识产权的垄断),是需要法律保护的,要那些能人生前就归还其占有的应属于其他人的财富,就会破坏这些社会所需要的垄断,破坏那些能人进行创造的平台,而要其在死后归还就没有这样的效率损失。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只要那些能人的后代同样很有能耐,就可以继续占有,不用归还。因为如果这些后代们真正有能耐,就能靠自己打造起创造的平台,而不必依赖父辈。[3]
上述遗产税原理只是说明了绝大多数的社会公众对富豪财富构成感觉的正确性,但毕竟遗产税的征收以富豪的去世为条件,现在巨富只是移民,并不是去世,怎能对他征收遗产税呢?这是因为遗产税的原理也说明,如果发生不再能促进本国效率或使遗产税这种“归还”成为不可能的特别事件,就需要巨富立刻归还占有的应属于社会公众的财富,而不能等到其去世。由此就产生了遗产税的延伸制度:遗产税本来只是对富豪去世后遗产征收的税,但是这样的税,富豪通过在生前将财产转移,比如赠与子女、直接隔代赠与孙子女等方式,就可以被轻易规避,即发生使遗产税这种“归还”成为不可能的特别事件,便需要巨富立刻归还占有的应属于社会公众的财富,而不能等到其去世。为此,世界各国制定了赠与税和隔代转移税等遗产税的辅助税种予以防杜,这就是遗产税的延伸制度。这种办法事实上是在特别情况下,对活着的富豪征收了遗产税。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富豪移民,同样遇到的是遗产税被轻易规避的问题,既是不再能促进本国效率的特别事件,又是使遗产税这种“归还”成为不可能的特别事件。这同样是遗产税的特别情况,同样应该对活着的富豪征收遗产税,只不过是将遗产税延伸到了国门,是对富豪准备移出国境的财产征税。只不过,在这里,税收的国家属性更加鲜明。可以参考隔代转移税的名称,将这种对富豪准备移出国境的财产的征税,称其为移居转移税。
三、移居转移税制设计与基本功能
1、移居转移税的制度设计
与赠与税、隔代转移税一样,移居转移税只是遗产税的一个辅助税种,是特别的遗产税,是在巨富并未去世但需要提前征收遗产税的特别情况下征收的税种,是在特别情况下对遗产税的替代。移居转移税的这种辅助税的性质直接决定了其制度设计必须以遗产税为基础,以协调配合遗产税为其根本目标。
(1)转移税不应单独立法,应当包含在遗产税法中
过去“遗产税和赠与税法”、“遗产和赠与税法”、 “遗产赠与税法”等提法都是不妥当的。一是这种提法将遗产税与其辅助税种等量齐观,抬高了赠与税的地位,给人一种对一种行为征收两种税的感觉;二是这种提法本身无法囊括隔代转移税、移居转移税等新生遗产税辅助税种,但又不可将其称为“遗产税和赠与税、隔代转移税、移居转移税法”。也就是说,不管遗产税有多少辅助税种,都是遗产税的延伸制度,都应该作为遗产税制度的一部分处理。
(2)移居转移税基本的税制要素应与遗产税完全相同
其特别之处,一是纳税人应仅为在国内外拥有的财产总额超过遗产税的起征点并将其财产转移出境的拟移居富豪,二是其计算方法应为按其国内外拥有的财产总额计算的“遗产税额”乘以实际转移出境的财产额占总财产额的比例。
(3)移居转移税应实行制连续征收制
即为防止纳税人以分次将其财产转移出境的方式规避高税负,应税的富豪每将其财产转移出境一次,都要与以前所有转移出境的财产额累积起来,重新计算一次应纳的移居转移税额,但以前缴纳的税额可以扣除。
(4)实行回流退税制
为鼓励财富的回流,已纳移居转移税的富豪如将转移出境的财富再转回国内,可以申请退还该部分财产已纳的移居转移税。
2、移居转移税的基本功能
由遗产税的辅助税种性质与制度设计所决定,移居转移税具有这样的基本功能:一是这一税种能在富豪将财产移出国门这一特别情况下,使其留下拟移出财产中应属于本国社会公众的部分,实现遗产税“归还”的目标,能防止本国公众利益的损失;二是该税的征收能增加富豪将财产转移出国门的成本和负担,能在较大程度上减少富豪向国外转移财产的行为,减少本国生产消费资金的流失;三是该税的征收仅仅是收回富豪占有的应属于社会公众的财富,并没有对富豪自己应得的财产有所剥夺,这就能保障富豪携自己的财产自由迁徙的基本权利;四是该税种实行回流退税制,可以在以后富豪财富回流时予以退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富豪财富回国。移居转移税这些功能的发挥,能较好地减轻富豪移民潮对一般民众和其他企业家的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一般民众的不满和不平,增强其他企业家的安全感,使一般民众和其他企业家对我国经济前景保持信心,为改善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法治环境,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富豪移民潮问题,赢得宝贵的时间。因此,移居转移税是我国政府应对富豪移民潮的必然选择。
四、遗产税疑虑与移居转移税消解
移居转移税只是遗产税的一个辅助税种,但事实上,我国的遗产税至今尚未开征,因此,为使政府能运用移居转移税应对富豪移民潮,就必须先解决遗产税的开征问题,否则,讨论移居转移税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国遗产税之所以至今未能开征,根本原因就在于开征遗产税的种种疑虑的存在。比如,国外纷纷取消遗产税,我国是否应开征此税?开征遗产税是否会阻碍民营经济发展?开征遗产税是否会造成资金外流?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水平和配套条件是否适应开征遗产税的要求?遗产税收入少,成本高,开征遗产税是否得不偿失?目前中国连财产税都没有,不具备基本的条件,怎么能开征遗产税?对于这些问题,早在多年前,刘佐、高培勇、刘植才和刘荣等学者就作了很好的回答。[4][5][6]这些研究很有价值,对消除我国开征遗产税的种种疑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有必要从遗产税延伸的角度做两点补充。
1、我国开征遗产税并不是逆势而上
近30多年来,加拿大 (1972年),乌干达、乌拉圭 (1974年),阿根廷 (1976年),澳大利亚 (1977年),孟加拉国 (1982年),肯尼亚 (1982年),印度 (1985年),斯里兰卡 (1985年),萨摩亚 (1987年),埃及(1989年),马来西亚 (1991年),斐济 (1991年),新西兰 (1992年),巴布亚新几内亚(1992年),巴拉圭 (约 1993年),赞比亚(1996年),塞浦路斯 (2000年),意大利(2001年),以色列 (停征时间不详),中国澳门 (2001年),[7]中国香港 (2006年),新加坡(2008年),奥地利 (2008年),瑞典 (停征时间不详)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取消遗产税。从这份名单上看,取消遗产税的国家和地区明显有三类,第一类是移民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瑞典、意大利等;第二类是国际避税地,如塞浦路斯、马来西亚、乌拉圭、奥地利、新加坡等;第三类是一些国土面积很小或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或地区取消遗产税的共同原因,就是为了吸引外国财富。而在世界有重要影响的更多国家和地区如美英法日德等都没有取消遗产税,也不可能取消遗产税,[8]就是美国等一些国家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废除遗产税的活动,也无非是虚晃一枪,是要提高遗产税的起征点,以免课及中产阶级,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税率,而不是要真正取消遗产税。因此,取消遗产税只是一些特别的国家和地区吸引国外财富的策略,并不是世界潮流或遗产税的发展趋势,我国既不属于那些特别的国家,开征遗产税也并不是逆势而上。
2、开征遗产税既不会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不会造成资金外流
遗产税只是在特定环节帮富豪归还其占有的应属于社会公众的那部分财富,而不是对富豪的剥夺。作为社会的精英,那些正当致富的人能因为遗产税的这一法理心情畅快。因为在这样的法理下,他们的天赋、能力和努力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敬,他们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成就和社会的关系,能够接受遗产税是归还而不是剥夺的道理,不再因此生气,而是乐意生前关心和帮助穷人,回报社会,死后以遗产税的方式,把社会公众应得的财富归还给社会,而不是留给衣食无忧的后代。这样就能很好地保护社会创造之心,而此即民营经济发展之源。而且,如前所说,遗产税的辅助税种移居转移税还能较好地减轻富豪移民潮对一般民众和其他企业家的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一般民众的不满和不平,增强其他企业家的安全感,使一般民众和其他企业家对我国经济前景保持信心。同时,我国开征遗产税,其辅助税种移居转移税能较好地抵消移入国取消遗产税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缓解富豪移民潮,减少财富和人才的流失。所有这些都无疑有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总之,分析表明,我国开征遗产税不仅不应心存疑虑,而且非常必要,明确移居转移税的功能,能更好地消解有关遗产税的疑虑,促进其早日开征,因而讨论移居转移税非常有意义。正在我国兴起的富豪移民潮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尤其是潜在影响,绝不能小觑,但政府不能采取“设限”措施予以阻止,而移居转移税作为遗产税的一种延伸制度,其功能的发挥能较好地减轻富豪移民潮对社会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使社会公众对我国经济前景保持信心,为改善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法治环境,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富豪移民潮问题,赢得宝贵的时间。因此,移居转移税应成为政府应对富豪移民潮的必然选择,我国应努力消除种种疑虑,尽快开征遗产税。
[1]王若翰,贺莉丹,陈 冰.六成富豪考虑移民背后严重的精英流失 [DB/OL].http://news.qq.com/a/20111207/000464.htm,2011-12-07.
[2]蔡木子.武汉投资移民九成移“名”不移“钱”[N].长江日报,2011-11-30(6).
[3]张永忠.遗产税的法理依据新论 [J].兰州商学院学报,2011,(6):62.
[4]刘 佐.关于目前中国开征遗产税问题的一些不同看法[J].财贸经济,2003,(10):76-77.
[5]高培勇.新一轮税制改革评述:内容、进程与前瞻 (续)[J].财贸经济,2003,(10):15-16.
[6]刘 荣,刘植才.开征遗产税须消除的疑虑与制度设计[J].现代财经,2008,(1):13-14.
[7]刘 佐,石 坚.遗产税制度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61.
[8]张永忠.西方国家遗产税缘何废而不除 [J].北京:现代经济探讨,2012,(2):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