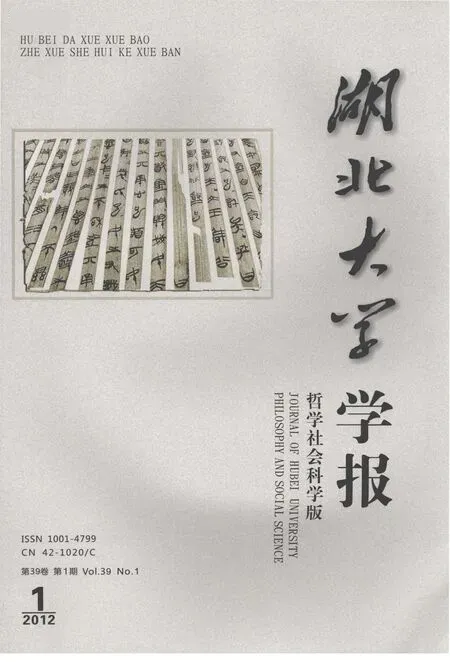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
谭德兴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
谭德兴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将《诗经》与金文互证,此法滥觞于北宋,至清代达到高峰。与《诗经》发生在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地下材料如今亦只有金文,而二者的互证,对解决《诗经》和金文各自的许多问题,诸如辨字释词、名物制度考证以及诗篇与铭文断代等无疑有巨大作用。清代金文与《诗经》的对比研究成果颇丰。在文字方面:通过互证,发现汉代四家诗诗文的本字与假借;借助《诗经》来正确释读某些金文;通过邶伯等青铜器的出土地域,探讨《诗经·邶风》所涉地域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内涵。在名物制度方面:通过互证,揭示《诗经》学内部的某些分歧及其成因;正确阐释某些诗篇发生的文化背景与主旨。在史实方面:借助《诗经》中某些诗篇的发生时代,对相关的青铜器进行断代,或者借助金文纠正历代《诗经》阐释中的某些错误。《诗经》与周代金文往往涉及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比研究有助于认识周代一些历史事件真相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对探讨周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特别是铜器断代,以及诗篇创作背景等有重要意义。
清代;金文;《诗经》;互证
清代金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王国维所总结的二重证据法[1]2,即将传世文献与出土金文文献对比研究。在这种对比研究中,《诗经》无疑是被引用最多的传世文献之一,清代每种金文著述几乎都要涉及到《诗经》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在《诗经》学和金文学两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深入分析清代金文著述的引《诗》论《诗》,对开拓《诗经》研究的视野无疑有重要意义。
一、文字互证
今本《诗经》中,尚有很多字词含义不甚明确,且各家在这方面的分歧更是成为《诗经》学发展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弄清诗篇的字词含义,显然是《诗经》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解决《诗经》学领域的这些问题,仅靠内证或其他传世文献显然已经难以实现。故有时需要依靠新材料的发现来解决之。而金文的出土,无疑极大推动了《诗经》学的发展,特别在辨文释字方面,创获很大。
例如,《山左金石志》卷二论《宋戴公戈》曰:
今释其文曰“朝王,商戴公归之造”。何以知为“朝”字也?《诗》“惄如调饥”,《释文》作“輖”,今作“调”者,字形相近而误。輖音周,周朝一声之转,古字通借。此戈借为朝覲之朝,犹毛诗借为朝夕之朝矣,其右旁近舟,古钟鼎舟周每同字也。[2]16
又《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八论《宋戴公戈》亦曰:
案:“輖”当为“朝”,《诗》“惄如调饥”,《释文》作“輖”,今作“调”者,字形相近而误。輖音周,周輖一声之转,古字通借。此戈借为朝觐之朝,犹毛诗借为朝夕之朝矣。其右旁近舟,古钟鼎舟周每同字也。[2]179
毕沅、阮元在考释《宋戴公戈铭》时,均引用了《诗·周南·汝坟》“惄如调饥”句。毛传:“惄,饥意也。调,朝也。”郑笺:“惄,思也。未见君子之时,如朝饥之思食。”《释文》:“调,张留反也。又作輖,音同。”[3]108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
调,《释文》云“本又作輖”。今按,明赵灵均《说文钞》本及《五音韵谱》本引《诗》并《蜀石经》本正作“輖饥”。杨凝式《韭花帖》“輖饥正甚”亦作“輖”,惟《韩诗》及今《说文》二徐本作“朝饥”。輖、调俱从周声。《说文》:“朝,旦也,从倝,舟声。”周、舟古同声通用。故“朝饥”可借为“调”与“輖”也。传云“调,朝也”,正谓“调”为“朝”之假借。[4]66
又《易林·兑之噬嗑》:“南循汝水,伐树斩枝。过时不遇,惄如周饥。”则《齐诗》又作“周饥”。尚秉和注:“‘周’,毛诗作‘调’,传云‘朝也’。丁晏云,‘周’,《释文》作‘輖’,‘周’即‘輖’之省文。”[5]569又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诗》作“朝饥”[6]59。
综上可知,《汝坟》“惄如”句,各家诗文有“调饥”、“朝饥”、“周饥”、“輖饥”之说。为什么会形成如此的诗文差异呢?导致这种文字的差异背后肯定有一定原因。诗文差异的出现是伴随汉代《诗经》学分化而形成的,而从先秦文字发展演变来看,应以《鲁诗》“朝饥”说为正,其余皆为文字演变或《诗经》传播中形成的假借。这点可以在周代金文中得到印证。在周代金文中,“朝”字由形旁“倝”和声旁“舟”构成(见《利簋》、《朝歌右库戈》、《先兽鼎》、《大盂鼎》等)。《说文》“倝,日始出光”[7]140。此为象形,象日光刚刚从树丛露出,故为朝夕之朝。《说文》:“朝,旦也,从倝,舟声。”[7]140朝音舟,同音相通,故有调、周、輖之假借。《小臣继彝》铭:“惟十有三月王宅旁舟,小臣继即事王,锡贝五朋,扬天子休,用作父宝尊彝。”《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五论曰:
案:旁舟,犹言邦京也。舟古通周。《考工记》“作舟以行水”,注云:“故书‘舟’作‘周’。”《诗·大东》“舟人之子”,笺云:“‘舟’当作‘周’。”《左传》“申舟”,《吕览》作“申周”;“华周”,《说苑》作“华舟”,二字古通用也。[2]142~143
此亦可解释朝与调、周、輖的假借问题。《吕氏春秋·音初篇》说《周南》、《召南》为周公、召公采入[8]646,当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则西周时期的《汝坟》必作“惄如朝饥”。汉代四家诗中,《鲁诗》文最接近周代原貌,故《汉书·艺文志》说三家诗中“鲁最为近之”[9]1708。毛、齐诸家诗文作调、周、輖等属同音假借,实乃口耳相传的结果。《汉书·艺文志》说《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9]1708。《诗经》长期口耳相传,在汉初写定时,因方言、记忆等导致同音假借。故“朝饥”讹为调饥、周饥、輖饥。
又如《缀遗斋彝器考释》论《井仁钟》铭曰:
《说文》:“吊,问终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会敺禽。”[7]167“吊”只有悯意,何来善义?故朱熹以“愍吊”释之[11]88。且毛传“吊,至也”的训释实难理解。故郑笺、孔疏均未从之。郑笺改训为“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吊昊天”之“吊”属讹误,正字本应为“淑”。方濬益从金文与传世文献之二重证据,考释出“吊”当为“淑”。现代金文研究者多认为周代金文中的“吊”有两个义项,其一用为伯叔之“叔”,其二通“淑”,善也[12]786。殊不知,这种认识可能混淆了“叔”与“吊”的释文。据方濬益说来看,现代学者对金文中“吊”的释文实际上是有误的,凡释“吊”的,均应作“叔”。“叔”乃本字,根本不存在“吊”用为“叔”的,此字本来就是“叔”。
按:“北”字为二人相背之形,说详前《背父乙鼎铭》,释此曰“北伯”,自是国名,字又作邶,《说文》:“邶,故商邑,在河南朝歌以北。”《诗谱》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汉书·地理志》集注:“邶或作鄁。”是邶之命名正以其在殷都之北。武王克商,分纣城而封之者,特其事不详,得此铭,知其爵为伯,可补经传之阙。[10]80
《诗经》十五国风所涉地域及文化历史背景大多有历史文献清晰可考,只有极少数不清楚,而《邶风》就是其中之一。关于《邶风》的史料主要见于郑玄《诗谱》[3]15和《汉书·地理志》[9]1647,但其中许多问题实际上并不明朗,如邶是何等爵位,它的地理位置究竟在哪等。这些问题对《诗经》邶、鄘、卫三风的区分及相互间关系研究无疑有重要作用。而清人对《北伯鬲》的考释,首先从出土文献方面证实了邶的爵位乃伯,弥补了传世文献之不足。周代铜器中关于邶伯的主要有:《北伯作彝鬲》:“北(邶)伯作彝。”《北伯作尊鼎》:“北(邶)伯作尊。”《北伯邑辛簋》:“北(邶)伯邑辛作宝尊簋。”《北伯灭卣》:“北(邶)伯灭作宝尊彝。”[14]77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北伯鼎跋》曰:
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家洼又出北伯器数十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诸殷之境内。[15]548
再如,《邶伯鬲》铭:“邶伯作彝。”《古文审》论曰: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说:“北伯诸器出于燕地,乃西周初邶国之器,似无可疑。……北伯皆仅限于西周初期,可认作武、成间殷遗的铸作。成王诛武庚,更封卫、宋、燕而北器遂亡。北伯器出土之地,或以为邵公封地。”[14]78
关于邶、鄘、卫的分封问题,先秦文献没有提及。《史记》中无论《殷本纪》还是《周本纪》都没有三分邶、鄘、卫之说。相关的分封有两次,其一,周武王克殷后:“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16]126其二,成王平息武庚叛乱后:“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16]132据《史记》,根本没有三分殷畿内之地为邶、鄘、卫之说。且具体武庚封于何地也言之不详,而且很明显封卫与封武庚根本不是同时期的事情。《帝王世纪》说:“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16]127此说与《史记》、《诗谱》、《汉书地理志》的说法皆各不相同。这说明,三分殷畿内为邶、鄘、卫之说中传说附会成分不少。司马迁去古未远,而班固、郑康成又去司马迁几百年,则似乎当以《史记》为信。而按《史记》说,前后两次分封中,封于殷都以北的只有燕,这与北伯诸器在燕地的出现十分吻合。因此,对于邶之地理位置,似乎可以肯定王国维“邶即燕”之说。
二、名物制度互证
由于时空隔阂,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今天的人们认识如《诗经》这样的作品时,对其中的名物制度往往十分陌生,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而周代金文研究中也存在相同难题。借助金文与《诗经》之比照,有时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研究效果。
例如,《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论《周饕餮罍尊》:
右罍尊……兽高四寸五分,满身饕餮兽,云罍花纹,无铭。《说文解字》:“櫑,龟目酒尊,刻木作云雷象,象施不穷也。或作罍。……《诗》:‘酌彼金罍’。”毛传:“人君黄金罍。”《五经异义》:“韩诗说,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诸侯大夫以金。”毛诗说,金罍,酒器也,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金饰龟目。蓋刻为云雷之象。[2]439
《两罍轩彝器图释》卷四论《周齐侯中罍》:
罍,《说文·木部》:“櫑,龟目酒尊,刻木作云雷象,象施不穷也。从木,畾声。”……罍,古用木。郑君《司尊彝》注云“‘山罍亦刻而画之’为山云之形”。《诗·卷耳》“正义”引此申之曰:“言刻画则用木矣,故《礼图》亦云刻木为之。”许氏《五经异义》引韩诗说“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诗说“金罍,酒器也”。许不从韩说谓以玉。经策明文则金玉亦就其饰言之,其实皆用木也。故《解字》以从木之櫑为正字。[17]55
金罍为《诗·周南·卷耳》中器物名,毛传与韩诗在训释时存在明显差异。按毛诗说,此诗主人公当为天子;而据韩诗,则此诗主人公当为诸侯或大夫。王先谦说:“《周南》之诗,是文王未称王时作,无嫌于金罍为诸侯之制。”[6]27此为调和之说。弄清器物的形态与使用制度,无疑有助于认识诗篇之主旨。造成分歧的原因,在于毛诗与三家诗对《周南》产生的历史背景理解有异。毛诗有正变之说,《诗谱序》说:“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3]6这里所谓的“集大命于厥身”、“为天下父母”,实际上是认为文王已经受天命而王。故有金罍人君之器说法。而三家诗多认为《周南》为刺诗,故金罍只能是“下以讽刺上”的大夫之器。实际上毛诗的文王受命说存在严重漏洞的。《诗本义》之“二《南》为正风解”说到:
虽恶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尔,亦曰服事于纣焉,则二《南》之诗,作于事纣之时,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岂所谓周室衰而《关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诗,在商不得为正,在周不得为变焉。[18]118
《毛诗李黄集解》也有类似论述[19]48。毛诗的文王受命称王说,从历史事实来说,可能没有此事。这不过是春秋笔法之类的后人创作。正如汉代辕固与黄生争论汤、武到底是受命称王还是弑君一样[16]3122。三家诗学者似乎坚持的是历史真相。故对于金罍之说,王先谦亦说:“毛传统言‘人君’,所以成其曲说,不若韩之得实也。”而大量文献也充分证明,夏殷周之爵制,天子确以玉也[6]27。
又如,《攀古楼彝器款识》论《斿形妇鬺》引张孝达说:
此器乃大夫妻庙见时所作祭器,上作旗形者,著其夫之爵,《礼》所谓“妇人无爵,从夫之爵”也。熊旗六斿,上大夫所建。《周官》疏所谓“祥大夫六命得建六斿”也。此器六斿,故知为上大夫。妻称妇者,《礼》所谓“三月而庙见,成来妇也。择日而祭于庙,成妇之义也”。……《诗》所谓“于以湘之,维筥及釜。谁其尸之,有齐季女”也。毛传:“湘,亨也。”……此器之义即在《采蘋》之诗。[20]599
又《从古堂款识学》论《周季彝铭》曰:
亚屋有四阿形,庙室之象。……季,非叔季之季。《诗·召南》“谁其尸之,有齐季女”,传:“尸也,主季少女也,女,微主也。”又《左》襄二十八年传“季兰尸之”,注:“使服兰之女而为之主,盖主妇之称。”[2]316
此与《斿形妇鬺》一样,均反映了“三月庙见”之礼制。亚形屋正象庙室之形,中有一人持器物,当是正在主持祭祀仪式,而主祭很可能是一名女子。此类铜器形象描绘了“三月庙见”的场面,与《召南·采蘋》相印证。另,此铭云“作季”,则“季”显非叔季排行之季,而似乎应指祭祀之名。此铭正与《昏义》等礼法同。《昏义》:“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之祭,牲用鱼,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妇顺也。”[3]124这是嫁前三月在女子祖庙的活动。而嫁后三月,在夫家祖庙也有一场祭祀活动。《魏风·葛屦》毛传:“夫人三月庙见,然后执妇功。”孔颖达《正义》:“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妇也。《曾子问》云:‘三月而庙见,称来妇。’又云:‘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则知既庙见者为成妇也。……妇入三月,乃见于舅姑之庙。”[3]307《斿形妇鬺》铭既称妇,又著夫爵,则显然应为嫁后三月庙见。而《周季彝铭》有“作季”语,与《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维筥及釜。谁其尸之,有齐季女”语同,当为嫁前三月庙见。且《召南·采蘋》既然称“女”,则恐怕描绘的也应该是嫁前三月庙见仪式,而非嫁后之事。
三、史实互证
此所言史实,主要指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诗经》与周代金文往往涉及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这有助于认识周代一些历史事件真相与历史人物的身份等,对探讨周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特别是铜器断代,以及诗篇创作背景等有重要意义。
例如,《周太保鼎》:“太保虎作宝尊彝。”《宁寿鉴古》卷一曰:
《江汉》之诗曰:“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又曰:“釐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毛传云:“召虎,召穆公也。召公,太保召康公也。”郑笺云:“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宣王欲尊显召虎,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赐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礼。是鼎当是虎受赐,因作鼎以祭其始祖太保召公奭也。[20]18~19
《大雅·江汉》描写的是周宣王命召伯虎平淮夷之事。《诗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3]857诗文颇有周代铜器铭文之风格。周代铜器中还有《召伯虎簋》二器,郭沫若认为《召伯虎簋》(其二)铭文所载即《大雅·江汉》之事。《两周金文辞大系》说:“此铭所记与《大雅·江汉》篇乃同时事,乃召伯虎平定淮夷归告成功而作。诗文‘告成于王’即此之‘告庆’,诗之‘锡山土田,于周受命’,即此之‘余以邑讯有司,余典勿敢封’,邑即所受之土田,典即所受之命册,‘勿敢封’者谓不敢封存于天府也。诗之‘作召公考,天子万寿’即此文‘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烈祖召公尝簋。”[21]307据《大雅·江汉》之召伯虎事迹,不难判断《周太保鼎》、《召伯虎簋》的铸作时代。
又如,《南仲鼎》:“惟王命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国……”《商周文字拾遗》论曰:
是铭,《博古图》疑为南宫括,又疑为南宫毛,或曰其名曰仲,盖即《诗》所谓南仲。窃谓是言得之,但合南宫与仲为一人,则不然。其文曰王命南宫,即继之曰王命仲,则非一人可知。审其文义,更合下二铭参之,南宫者,盖仲之考也,其曰王命南宫伐叛虎方之年,曰于归生原,皆追溯之辞也。盖是时南宫已卒,仲追叙其事以作庙器。[2]30
又《无专鼎》:“惟九月既望申戌,王格于周庙,燔于图室,司徒南仲右无专入门,立中廷……”《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论曰:
考南仲有二,《诗·出车》篇之南仲,毛传以为文王之属。《常武》篇之南仲,毛传以为王命南仲于太祖,是宣王之臣也。此铭不类商器,当是宣王时臣。[2]120
关于历史人物南仲,在周代金文与《诗经》中均有二位南仲。据《南中鼎》来看,南宫中显然是南仲之祖辈,而非父考。鼎铭云南宫中事迹实乃追述之词,这样的体例在周代金文中比比皆是。后代因功作器,往往在铭文开始要称述祖辈功业,以示己辈能不殄先祖之绪,能发扬光大先辈业绩。这也是孝道之体现。如此,南宫中伐虎方之事当为周初“薄伐西戎”,而鼎铭之南仲则就是《常武》之南仲无疑矣。《南仲鼎》的铭文正与《诗经》之二南仲相印证。
再如,《留君簠》二器,《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论曰:
《王风·丘中有麻》毛传:“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国,子嗟父”[3]249。毛传以《诗》中“留子嗟”、“留子国”皆为人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云:
“彼留子嗟”,传:“留,大夫氏。”瑞辰按:留、刘古通用。薛尚功《钟鼎款识》有《刘公簠》,《积古斋钟鼎款识》作《留公簠》。留即春秋刘子邑。[4]245
这是充分利用金文的研究成果来解释《诗经》。两相印证,很有说服力。而忽视金文的互证,则往往导致在解诗时穿凿附会。如《诗本义》论曰:“留为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诗人之意,所谓彼留子嗟者,非为大夫姓留者也。”[18]25于是《本义》曰:“唯彼贤如子嗟子国者独留于彼而不见录。”[18]26欧阳修居然将“留”解释为停留、留下。姚际恒更是走向极端,《诗经通论》:“愚按,此诗固难解,然‘留‘字是留住之留;子嗟、子国……亦必非人名;‘嗟’、‘国’字只同助辞。”[22]115《诗经原始》亦说:“中间‘彼留’、‘彼留’云者,乃虚拟之辞耳。‘嗟’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耶?其国不可久留也。”[23]201现当代学人的误释就更不用多举例了。《留君簠》二器,不但印证了毛传说的正确,也说明地下材料对于《诗经》研究的重要性。
又如,《愙斋集古录》论《毕狄钟》:
是钟无作器者之名,亦编钟之文不完者。铭文有“毕狄不龚”语,当即纪北伐玁狁之事。《诗·采薇》“玁狁之故”,传云“玁狁,北狄也。”《采薇》、《出车》,《毛传》皆以为文王之诗。《说文》:“毕,毕尽也”;“歼,歼尽也”,毕与歼同意。龚,古恭字,《书·甘誓》“女不恭命”,《左》氏僖二十七年传“杞不共”也,《释文》“共本作恭”。毕狄不龚,言北狄不恭而击尽之。首云“侃先王”,前钟当有“喜”字……阮氏以为成王所作,此云“先王其严在帝左右”,“先王”谓文王也,《诗》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铭颂文王伐狄之功,当亦成王时所作器。[24]186
《诗经》中有很多篇章记录了与玁狁的战争。而周代金文中也有不少铭文记载伐玁狁之事。除此铭外,又如《兮甲盘》即记载了尹吉甫随宣王征伐玁狁之事[21]304。按毛诗说,《诗》中记录与玁狁战争主要分两个时期,一为文王时,一为宣王时。由于此钟无作器者之名,不像《兮甲盘》有尹吉甫可与《诗经》互证,因此,很难判断其时代。清人依据“先王其严在帝左右”判断先王为文王,而作器者为成王。这种认识未免有些武断。此钟铭曰:“……侃先王,先王其严在帝左右,毕狄不龚,丰丰勃勃,降……”,而类似话语在西周晚期铜器铭文中很多:
《宗周钟》:“先王其严在上,勃勃丰丰,降余多福……”[25]279
《虢叔旅钟》:“皇考严在上,翼在下,丰丰勃勃,降旅多福……”[25]296
《井人钟》:“用追孝侃前文人,前文人其严在上,丰丰勃勃,降余厚多福……”[25]272
特别是《井人钟》铭,无论句法,还是字体皆与《毕狄钟》同,且皆为钟铭,二器当为同时期产物。因此,将《毕狄钟》定为周宣王器可能更合理些。
[1]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刘庆柱,段志洪,冯时.金文文献集成:10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5.
[3]孔颖达.毛诗注疏[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4]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尚秉和.焦氏易林注[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6]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8]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刘庆柱,段志洪,冯时.金文文献集成:14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5.
[11]朱熹.诗集传[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12]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13]刘庆柱,段志洪,冯时.金文文献集成:11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5.
[14]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5]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刘庆柱,段志洪,冯时.金文文献集成:8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5.
[18]欧阳修.毛诗本义[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19]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20]刘庆柱,段志洪,冯时.金文文献集成:7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5.
[21]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8)[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2]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3]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4]刘庆柱,段志洪,冯时.金文文献集成:12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5.
[25]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K204
A
1001-4799(2012)01-0045-06
2011-07-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BZW0BZ
谭德兴(1968-),男,苗族,湖南麻阳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