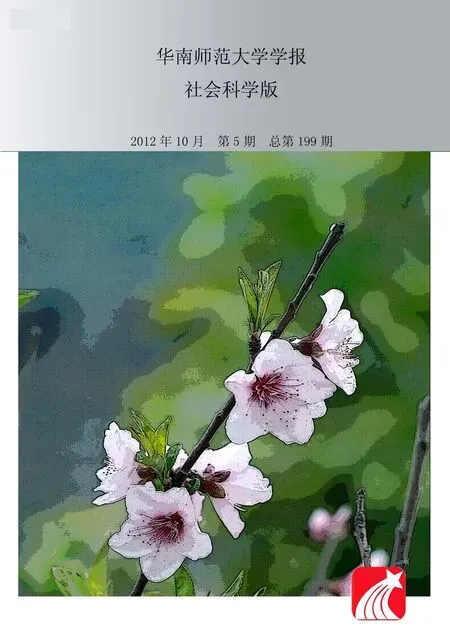从“诗味”到“文味”——宋代文章学之“味”范畴论析
刘春霞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 文化产业系,广东 广州510091)
“味”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它与“韵”、“趣”、“格”等一起被用来概括文学的审美特征。“味”首先被运用于诗学批评领域,后来又被运用于词学批评领域。宋代文章学正式成立,①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参见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载《复旦学报》2009年第2期;祝尚书:《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1期。文人将“味”范畴移植到文章学中:他们以“味”作为品评文章的审美标准,从理论上探讨文“味”之创造与生成,并提出“玩味”的接受方法。宋代文人将诗学“味”论移植到文章学,包含了对文章审美特质的肯定,同时又认识到“文味”与“诗味”有本质区别。
一、以“味”作为品评文章的审美标准
以“味”品藻衡量文章,在宋代已经大量出现,其表述形式有“味”、“风味”、“意味”、“滋味”、“余味”等多种情况。现就几种典型表述作一简要例举与分析,借以一窥宋代文人以“味”论文之大概。
首先,以“味”品评文章。如苏洵《上欧公书》:“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惟李翶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逊,有执事之态。”[1]341认为李翶文章因有“味”而达到了较高的成就,且其“味”似于欧阳修。晁补之序《变离骚》,在评论宋玉、曹植、王粲、鲍照、陆机、江淹等人诗文风貌之后总结道:“要曰群言之异味,亦可贵也。”[1]346“味”指自屈原以来受到《离骚》影响的各家诗文的艺术风貌。苏轼赞赏鲜于俊的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2],赞赏其文章的“风味”。南宋后期著名文论家楼昉将“味”作为一个重要标准评论古今文章。如评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铭》:“叙事有法,辞极简严,而意味深长,结尾绝佳,感慨伤悼之情见于言外。”[3]470评欧阳修《祭元珍文》:“讥贬虽近乎太过,然一时之毁誉,决不能掩千古之是非。观此文,然后知枉之语为有味也。”[3]484楼昉所谓的文章之“味”指具有深婉委曲、不落言筌、见于言外的意味。楼昉以“味”来品评文章,其学生陈森在《崇古文诀》跋文中称他为知文章之“味”者:“……子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先生之于文,其知味也欤?”[3]510陈森曾为楼昉馆下生,他引孔子之语,借饮食之“味”喻文章之“味”,准确指出了楼昉对文章之“味”的推崇与追求,是真正的知“味”者。
其次,以“滋味”品藻衡定文章。吕祖谦推崇文章之有“滋味”者,将有“滋味”的文章视为最高等,并认为文章之“滋味”由含蓄不露的技巧表现出来,与平直铺写、一览无余相对。他在《丽泽文说》中称:“文字有三等:上焉藏锋不露,读之自有滋味,中焉步骤驰骋,飞沙走石;下焉用意庸庸,专事造语。”[4]329
“滋味”说最早出现于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中:“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风力穷于和韵。”认为文章之“滋味”是由文辞声律的抑扬顿挫和音韵节奏的和谐铿锵表现出来的。后来钟嵘《诗品》提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将“滋味”说与五言诗结合起来。钟嵘《诗品》是一部重要的诗学理论专著,对后世诗歌批评影响甚大,“滋味”说亦因之成为后世诗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诗学理论的逐步成熟与影响扩大,“滋味”说几乎成了诗歌的专有审美属性,却忽视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滋味”说其实涵盖了一切文章的原初观念。
颜之推提出了文章“滋味”说:“夫文章者,原出于五经……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诵,入其滋味,亦乐事也。”[1]373但由于其时诗文不分,他所谓的“文章”是包含诗、赋、文各类文体在内的“文翰”。唐代张说首次以“滋味”品藻文章,他在《与徐坚论近世文章说》云:“韩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则而薄滋味。”[1]406但还仅就感觉上予以描述,未说明“滋味”的具体表现。吕祖谦之后,谢枋得也提出了文章“滋味”说,他在韩愈《答李秀才书》“今者辱惠书及文章,观其姓名,元宾之声容,恍若相接;读其文辞,见元宾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于吾元宾也”句下批道:“文有情思,有滋味。”[5]指出优秀的散文像好诗一样,往往评不尽、谈不完,充满情思、耐人咀嚼,这是对散文艺术感染力的强调,体现了宋末文论家普遍开始认识到文章沉重的道德功能之外的审美特性。
另外,以“余味”评价文章高下。楼昉评王震《南丰集序》:“自少至壮,自壮至老,凡三节,曲尽南丰平生涉历,既可以见朝廷之用不用,又可以见文之老壮,学之进退。结尾一节,叹息其用之不尽,尤有余味。”[3]506永嘉文派陈傅良称:“结尾正论关锁之地,尤要造语精密,遣文顺快。盖精密,则有文外之意,使人读之而愈穷;顺快,则见才力不乏,使人读之而有余味。……首尾贯穿,无间断处,文有余而意不尽。”[6]1084“余味”指文章“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尤其是文章结尾处表现出来的余音缭绕、一唱三叹的蕴味。
二、对文章之“味”的创造与生成的探讨
诗学、词学批评领域的“味”主要指作品言不尽意的悠远韵味及虚空灵动、不可凑泊的优美意境。作者空灵悠远之情思与诗词委曲深婉之结构、平淡天成之语辞等,都是“味”形成的重要技巧手段。文章学移植了诗词批评领域之“味”说,其内涵与诗词之“味”有本质区别,包含了一定的儒家义趣、道理属性。宋代文人对文章之“味”的创成予以探讨,认为文章之“味”常由作品所表达的敦厚情感、深刻义理表现出来;文章之“味”由抑扬起伏的结构与变化多端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来,取法《史记》叙事简而有法、人物刻画生动毕肖等技巧与形成文章之“味”之间有密切关系。“文味”不同于“诗味”的创成方式,正是“文味”区别于“诗味”之内涵的根本原因。
(一)有“味”的文章必须具有敦厚深沉的情感与深刻独到的义理
首先,文章之“味”与作品包含的感人至深的情感有关,但这一情感具有鲜明的儒学色彩。如黄震评价韩愈《送孟东野序》称:“自‘物不得其平则鸣’一语,……终之曰:‘不知天将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也?’归宿有味,而所以劝止东野之不平者有道矣。”[7]613认为韩愈由物及人、由古及今、由远及近,层层递进议论,最终以设问作结,表达对东野不平遭遇的深切同情,情深感人。所谓“归宿有味”,即语末含情、情意悠远,劝诫之意符合儒者中庸之道,意味悠长。
这一点与诗歌之“味”有相通之处。诗歌是有“味”的文学,其“味”主要由作者之情志表现出来。但形成诗歌之“味”的“情”、“志”内涵具有较大的包容性,除了指符合儒家中庸之道的情志外,还可以指纯粹个人化的人生理想、喜怒哀乐,甚至不排除郑卫之声、绮靡艳情,是严羽所说的非关“理”与“识”的纯粹情感,是通过“镜中月”、“水中花”般空蒙意境表现出来的“别趣”(《沧浪诗话·诗评》)。较之诗歌之情志,黄震所评韩愈文章之情志无疑具有更鲜明的儒学色彩。早在梁代萧统就在《金娄子·立言》中说道:“至如文章,惟须……情灵摇荡”,已经模糊认识到了文章因“情”而有“滋味”。宋代文人从文章包含的“情”去体会文章之“味”,体现了对文章审美情感特征的认识;但在儒学一尊的时代里,“情”也无疑也带上了与六朝不同的儒学色彩。
其次,文章之“味”与作品包含的深刻“义理”、“道理”有关。如黄庭坚《答王周彦书》:“如足下之作,深之以经术之义味,宏之以史氏之品藻,舍之以作者之规模,不但使两川之豪士拱手也。”[1]358“味”是经义所包含的深广的“义趣”。谢枋得评柳宗元《送薛存义序》:“章法、句法、字法皆发,转换关锁紧,谨严优柔,理长而味永”[8]1054。“理长”则有“味”,“理”指儒家义理、道理。张耒称:“作文以理为主,……故学文之道,急于明理。……若未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反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9]1592“味”与“理趣”有关,“味”是咀嚼“理”时获得的审美感受。谢枋得评苏轼文章有“味”:“东坡作史评,必有一段万世不磨灭之理,……文势亦圆活,义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长。”[9]1595认为文章结构、义理与意味密切相关。
另外,宋末文人周密还认为文章因禅意而有“味”。他称:“蒋重珍伯父能禅,其亡也,重珍祭之以文云:‘不必轻生前以为空,不必重死后以为实。’此语极有味。”[10]1122周密认为重珍祭文包含了对生死认识的某种禅悟境界,故有“味”。南宋后期,以禅喻诗的现象十分普遍,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洪驹父都有以禅喻诗的论说;严羽作《沧浪诗话》,提出了诗歌“别趣”论,主张通过“妙悟”的方法去欣赏诗歌,是禅学思想观照下的典型论调。联系周密之论文“味”与江西诗派、严羽等人论诗“味”可知:同是以禅为喻,诗歌之“味”偏向空灵悠远、不可凑泊、不可言说的境界;文章之“味”则具有更深厚的哲理思辨性。不过,周密以禅意喻文境之“味”,与宋代江西诗派将禅语、禅意引入诗学批评及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具有思维的一致性,可见一种新的批评思维本身具有文体的包容性,并不限定于某一体式。这也是宋代文章学借鉴诗学理论的深层原因所在。
(二)文章之“味”通过变化多端的艺术技巧表现出来
有“味”的文章是作者精心构思、运用丰富高妙的艺术手段与表现技艺形成的。这包含两方面内容。
首先,文章之“味”的形成与篇法、句法、字法等技巧有关。
有“味”的文章通过起伏委曲的篇章结构表现出来。如宋元间人李淦《文章精义》中道:“文字有反类尊题者,子瞻《秋阳赋》,先说夏潦之可忧,却说秋阳之可喜,绝妙。若出《文选》诸人手,则通篇说秋阳,斩无余味矣。”[11]1168认为文章应该在结构上抑扬曲折、起伏变化,才不至于通篇平铺直叙而无“余味”。欧阳起鸣论时文写作中的“腰”时道:“变态极多,大凡转一转,发尽本题余意,或譬喻,或经句,或借反意相形,或立说断题,如平洋寸草中,突出一小峰,则耸人耳目。到此处文字,要得苍而健,耸而新。若有腹无腰,竟转尾,则文字直了,殊觉意味浅促。”[6]1088文章结构思理委婉曲折、开阖变化,则具有一唱三叹、余音绕梁般的意蕴,故有“味”;如果文章平直,一露无余,则无“味”。
有“味”的文章由灵活丰富的句式表现出来。诗词含蓄不尽的“意味”往往由有限的字词包含丰富的、多层的意蕴形成,具有以少胜多、以少涵多的特点。文论家认为文章含蓄蕴藉之“味”的形成与文章繁简、用辞多寡无必然联系,倒是与造句技巧有关。如陈模批评时人学作古文以“减字”为妙着,未能真正理解古人为文之法,古人作文“有多而少之者,有少而多之者”,不以字数多寡来衡定文章高下,而运用恰当的表达方式蕴含丰厚意旨,使文章具有无穷“意味”。他举《孟子》道:“‘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一段,许多事只将‘若此’两字括之,若更重叙过,则不胜费辞,且无意味。”用“若此”两字避免了很多重复内容,使文章有意味。又举韩愈《麟解》道:“‘有圣人者出,必知麟,麟之出果不为不祥也。’若以减字减之,当云:‘有圣人者出,必能知麟之非不祥也。’然此须重出麟字,而衍作一句,则冷语婉娈,且饱满充壮而有余味。”[12]521-522此处又必须不惮重复,将圣人识祥瑞以知天下的修性很好地表现出来,文章重复一“麟”字,却使结构思理反复曲折、发人深思。
有“味”的文章由畅达自然、新颖拙朴的文字表现出来。陈模称:“谓以艰深之辞,文浅陋之说,一读能钩棘人喉舌,仔细玩嚼,则枯槁全无意味。”[12]523古奥艰涩之语使文章无“意味”。陈模称文章善用“冷语”则“有味”:“欧文好处多在于冷语。如《春秋论》云:‘甚高之节,难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欤!’……又如东坡‘封建非圣人意也’,后又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亦是冷语。但欧文平淡中下冷语,人都不觉。人不晓者,则以为此等语似冗长,可以去之,却不知极有味……欧文中间拙处,他却不是不会作好语,但他不做,故意下此等拙语。”[12]527“冷语”与“拙语”相提并论,“冷语”应指冗长生疏之语,让人有咀嚼味,犹如橄榄,愈嚼愈有味。这一点又与文章学中崇尚“拙朴”的美学追求一致。正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言:“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诗文皆然。”[4]313
其次,取法《史记》之艺术技巧对形成文章之“味”有重要作用。
宋代文人在接受《史记》时,认识到了《史记》因高妙的表现技巧而有“味”,并对其“味”予以理论总结。如陈模称:“班固《赞》引《过秦论》,马迁亦引。但是班固中略改了数字,皆不及马迁者。优劣只此亦可见。前辈言,马迁载孝文时,‘廪廪改正服封禅矣,谦谦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此无限意味,而班固乃言:‘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呜呼仁哉。’便都尽了。”高度赞赏《史记》之“味”。陈模认为不用绝对的判断、议论之语,而是点到即止、引起人们的思考的语言表述才有“无限意味”,否则只是“都尽了”,意蕴发露,没有“意味”。陈模进一步分析,认为《史记》之“疏爽”、《汉书》之“密塞”风貌的形成,并不由文字寡富造成,其高下之别主要在于司马迁用语简练却给读者留下无穷思考余地,文章具有无穷意味;班固以密塞详尽之语说尽情事,文章意味都尽、了无蕴趣。[12]520吴子良评《史记·贾谊传赞》云:“曩见曹器远侍郎称止斋最爱《史记》诸传赞,如《贾谊传赞》,尤喜为人诵之。盖语简而意含蓄,咀嚼尽有味也。”[13]577准确地指出了《史记》简而有法、言简意丰的特征,并将《史记》的这种艺术表现与其“有味”的审美特征结合起来,从理论上对《史记》之“味”的生成予以总结。这正是宋代文章学“味”论与《史记》之关系论的理论基础。
宋代文人独具只眼地认识到后世文章因取法《史记》叙事简而有法、纪人形态毕现等技巧而有“味”。楼昉评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铭》“叙事有法,辞极简严,而意味深长,结尾绝佳,感慨伤悼之情见于言外”[3]470。“简而有法”是《史记》最富成就的表现手法,楼昉评韩愈文章之“味”与叙事方法、用辞技巧有关,显然已经认识到韩文与韩愈接受《史记》分不开。评曾巩《〈战国策〉目录序》:“议论正,关键密,质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亚也。咀嚼愈有味。”[3]498认为曾巩文章有“味”,具有与《史记》一样醇正的思想内容与深刻的义理趣味,是受《史记》影响的产物。评张耒《书五代郭崇韬卷后》:“说尽古今固位吝权者之情状,思深计工,反成浅拙。此论极有理,意味深长,尽可索玩。”[3]500认为张耒人物传能够刻肖人物情态,具有耐人寻味的无穷意味,离不开《史记》传状类人物的影响。
宋代文人开始认识到文章之“味”与继承《史记》简而有法、言简意丰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深厚情感力量与独特美学风貌有关。这种从“味”范畴角度对《史记》艺术技巧的探讨、从“味”范畴角度接受《史记》的思维向度,为后代文章学视阈中的《史》、《传》接受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文章学史意义。如明代唐宋派取法唐宋文章,从理论上总结唐宋八大家与秦汉史传文学的关系,认为唐宋古文家在取法秦汉文章时,继承了《史记》“风神”,形成了澹宕多奇的艺术风格,从而使文章具有无穷意味,并从理论上论述文章之“味”、“风神”与《史记》等史传文学的关系,即是对宋代文章学理论的直接继承与发展。
三、“玩味”:文章之“味”的接受方法
从接受学角度来看,“味”是文章包含的含蓄不尽的美学意味,具有多义性、动态性、丰富性。对于如何去认识文章之“味”,宋代诸多论文者都提出了“玩味”的接受方法,主张通过“玩味”、“熟味”、“详味”,充分理解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思理意旨和蕴含于字句之外的无穷韵趣,获得思想境界的陶冶与审美艺术的享受。宋代文章学中“玩味”的批评方法与诗学中的“涵泳”说有相似之处,从诗学“涵泳”说来观照文章学“玩味”说,可见其理论意义。
(一)“玩味”文章获得思想的提升与审美的享受
首先,通过“玩味”体会领悟文章包含的丰富意理,提高识见与修性,获得思想境界的陶冶。如朱熹《朱子语类·论文》:“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若其义理精奥处,人所未晓,自是其所见未到耳。学者须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见。”[14]224朱熹强调学者应该对文章仔细“玩味”,体悟领会圣人文章言辞后面的“义理精奥处”。元代继承宋代以经义取士的科举制,故论文者亦继承宋代,要求作文须“玩味”四书五经之义味,获得思想的提升与精神的修性。如倪士毅主张作文时,“须将文公《四书》子细玩味,及伊洛议论大概皆要得知,则不但区处性理题目有断制,凡是题目皆识轻重,皆区处得理到”[15]1499。
宋代文人强调于“玩味”中领悟文章所包含的“议论”,“议论”亦指作品包含的思想观念、道德义理。宋人好发议论,不仅在诗、词中议论,一些具有明确纪事、记人、抒情性质的文体如序、记、题、跋等文章,也融入了作者丰富的议论。“以议论为诗”、以议论作文是宋代文坛的普遍风尚。宋代文论家对这种新风尚是予以肯定的,并提出了于“深味”、“玩味”中体会“议论”、提高识见的观点。如楼昉评张耒《送秦少章叙》:“此皆老于世故之后方有此等议论,凡学文当知此理,深味然后有进益。”[3]500评唐庚《议赏论》:“议论精确,文词雅健,意有含蓄,能发明他人所不能到。不可以浅近求,宜深味之。”[3]507评胡宏《假陆贾对》:“议论正大,规摹开阔,不可独以文字观。而抑扬起伏,假设高帝、陆贾问对之辞,尤可玩味。”[3]509习文者“味”“议论”方有进步;读者不应只停留在文章表面形式,而应仔细体会作品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意旨。
其次,通过“玩味”体会文章技巧、字句之外所蕴含的无穷言外之意,获得审美享受。如楼昉评司马迁《自序》:“家世源流,论著本末,备见于此。篇终自叙处文字,反复曲折,有开阖变化之妙,尤宜玩味。”[3]466要求人们于结尾处看其结构起伏开阖之妙,体会作者作文之高妙境界。评孔稚圭《北山移文》:“此篇当看节奏纡徐,虚字转折处。然造语骈俪,下字新奇,所当详味。”[3]469要求人们品赏孔稚圭文章遣词用字处体现出来的“味”。评江淹《诣建平王上书》:“自始至末,似无不平处,须是子细详味,方见得文通托此自雪。”读者只有通过“详味”作者起伏纵敛的意脉结构,才能明白江淹作文时“心曲间事”[3]469,获得情感的愉悦与满足。朱熹强调学习欧阳修文章,应着意于文章遣词用字、结构曲折反复、文意深婉委曲等技巧方面仔细“玩味”,体会作品溢于言外的丰厚意旨:“六一文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字模样。……然有纡余曲折,辞少意多,玩味不得已者,又非辞意一直者比。”[14]213
(二)从诗学之“涵泳”观照文章学之“玩味”
宋代诗学接受中有“涵泳”的鉴赏方法,其产生与宋代追求“平淡”之“味”的整体诗学思潮有关。宋人认为“澹泊出至味”、“简易闲澹”而有“深远无穷之味”、“句雅淡”而“味深长”,提倡从平淡简易、朴实无华的语言、艺术风格等方面获得诗味,加之宋代诗歌的这种“味”往往包含于“筋骨思理”中,就要求接受者在欣赏诗歌时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细细地体会、长久地品味。这样,一种新的鉴赏方式——“涵泳”就产生了。“涵泳”即深入诗歌意境之中,仔细体会、反复吟咏,在诗歌有尽的字句与有穷的形式中,体会到悠远无穷的优美意蕴与空灵蕴藉的言外意趣,并从其高妙的艺术表现中获得审美感受。
诗歌鉴赏中有“涵泳”的接受方法,文章品藻中则有“玩味”的接受方法。元代苏伯衡在指导后学作文法时,就是将“讽咏”与“玩味”相提并论的。他在《述文法》中称:“欲作文字,且未可下笔,先取古人文章,熟读详味,再三讽咏,使心有所感触,思有所发动,方可运意。”[16]1578王顺娣《宋代评学平淡美的基本特征》一文中称,“诗学意义上的‘涵泳’,首先是体会与玩味”[17]63。“涵泳”与“玩味”实有相通之处。
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称:“从接受角度看,‘涵泳’与宋代追求‘平淡’、‘自然’、‘外枯中膏’的诗歌风格有直接关系”,“在宋代诗学中是个相当重要的范畴,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既是学诗和品诗的主要方式与心理过程,又与宋代诗学价值取向有着紧密联系,同时它还标志着道学向宋代诗学的观念渗透与话语转换。”[18]120-129从李春青关于诗学“涵泳”理论观照宋代文章学中的“玩味”说,可知“玩味”是文章品赏的心理过程,与宋代文章学的价值取向相关,体现了宋代文章学对文章之“味”这一审美特征的重视;从“玩味”的具体内容可见,宋代文章学依然摆脱不了儒学思想的影响。
宋代诗学之“涵泳”与文章学之“玩味”,都是通过一定的鉴赏方法体会作品之“味”,两者虽在思维、学理上有相通之处,但所品赏的诗、文之“味”的内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宋代诗学之“味”将“淡”作为审美理想广泛推崇,读者“涵泳”的主要是诗歌空灵凑泊、兴象朦胧、意旨悠远的情趣韵味;文章学之“味”的内核精神侧重指深刻的思理、意旨,读者“玩味”的是文章曲包余蕴、含蓄不尽、发人深思的“意味”、“义味”。①马茂军师认为中国古代的义理散文,“往往代表了一个民族理性精神的最高水平与深遂境界”,“义味”说“是对义理的审美,且与佛教渊源深厚”,指出古典散文因“义理”而具有“味”的特征。见马茂军:《中国古典散文义味说》,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就品赏的方法理路来看,“涵泳”诗歌强调深入其中去体会,在反复吟咏中“披文入情”,读者需要通过“妙悟”、“顿悟”获得“不落言筌”、“不睹文字”般的意趣韵味;“玩味”文章,强调深入思考体验作品所包含的思辨性义理与高妙的文境之美,读者可以通过寻绎文章思想内涵、表现技巧去探讨文“味”,文“味”的获得较之诗“味”具有明显的形而下特征,因之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另外,与“涵泳”诗歌之味不同,宋代文章学中“玩味”说还包含了一层“揣摩”的含义,强调对文章写作技巧、前人作文法度的反复学习、精心模仿。这与宋代文章学用于指导科举时文的实用目的分不开,习文者“玩味”文章正是出于科举的功利驱动。王水照先生指出:“文章学成立于宋代,其中的文化动因是非常复杂的……而时文讲习作为推动士人讲求文章法度的重要契机,其作用尤其不应忽视。”[19]31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宋以后明清时期八股文兴盛的时代,对文章之“味”的探讨、通过“玩味”学习古代文章就成为文章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了。
“味”范畴是一个具有突出美学特征的理论范畴。宋代文人普遍以“味”品藻衡量文章,探讨文“味”之创作与生成的原因,并对接受者提出了“玩味”的鉴赏批评方法,这三方面内容一起构成了宋代文章学中完整的“味”范畴论。宋代文章学中的“味”论由诗学之“味”论发展而来,但“文味”与“诗味”有本质区别。“味”范畴进入文章学,一直影响到明清复古理论和八股理论,具有较重要的文章学史意义。
[1]王正德.余师录∥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苏轼.与鲜于子骏三首(其二)∥东坡全集:卷七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楼昉.崇古文诀评文∥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魏天应.论学绳尺·行文要法∥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7]黄震.黄氏日抄·读文集:卷一∥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8]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文∥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9]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0]周密.浩然斋雅谈·评文∥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1]李淦.文章精义∥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2]陈模.怀古录∥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3]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四∥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4]朱熹.朱子语类·论文∥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一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5]倪士毅.作义要诀∥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6]曾鼎.文式:卷下∥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第二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7]王顺娣.宋代评学平淡美的基本特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18]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9]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