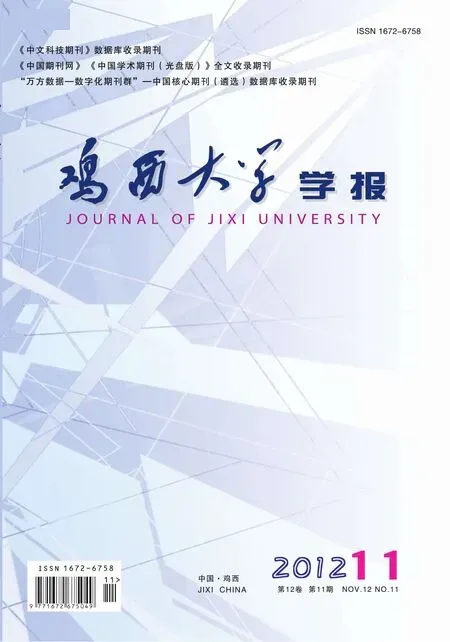论《世说新语》中竹林七贤放诞不羁的审美理想
张富翠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世说新语》是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部著作。它以生动的笔触,优美而精炼的语言,分别记载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趣闻轶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特别是士族阶层,广泛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更是魏晋风度的审美产物。“竹林七贤”生逢在动荡不安的魏晋时期,《世说新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竹林七贤”放诞不羁的审美理想。本文所谓的审美理想,就是竹林七贤追逐的名士风度,包括: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崇尚清谈、蔑视权贵等几个方面。
一 对自由人格的追求
“竹林七贤”对自由人格的追求,从他们酗酒佯狂、傲啸山林的生活方式上以及内在学识上都有所体现。
1.酗酒佯狂,傲啸山林。
魏晋时期是一个纷繁动乱的时代,“竹林七贤”就生活在这个时期,他们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通过酒可以向我们展现当时的现实状况。酒对于文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酒不仅是他们生活中的伙伴,更是他们精神上的朋友。纵酒是“竹林七贤”的一大特征,他们对酒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们看来醉酒不仅可以使人超脱荣辱和生死,也可以净化人的精神世界并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世说新语》中很多门都记载了有关七贤饮酒的故事。七贤中,有山涛的嗜饮能饮,一饮八方方有醉意;有刘伶的纯粹嗜酒如命;有阮籍的借酒消忧,蔑视礼法和一醉六十天借酒避祸。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的那样:“整个魏晋时期就是一个迷醉的时代,翻开这一段历史,似乎页页都有酒香。”[1]《世说新语·排调》载:“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阮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耶?”[2]饮酒则成为他们每天的乐趣。七贤中的山涛擅饮酒以交友,他的饮酒一面为了自身的怡情遣性,另一方面也是想保持人格上独立。
在《世说新语·任诞》篇所讲“刘伶病酒”的故事,表面上看刘伶纯粹是一个酒鬼,而且过度饮酒在某种意义上有损他们的“名士风度”,但是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酒能成为他们情感最好的表达方式与政治上的避难方式,因为在那个险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是危险的,消极抵抗同样也会招来杀生之祸,就只好为自己寻找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即终日大醉、不问世事。因此纵酒成了名士们想要保全性命的唯一方法,因为即使说错什么做错了什么也可以说是醉言无忌、醉行可谅了。因此当他们无法实现对自由人格的追求时,酒就成了他们最好的伙伴,也是抒发苦闷心情的最佳方式。
2.内在的学识。
(1)文学。
七贤中阮籍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其《咏怀诗》在文学史上就有很高的地位,这些诗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生活态度,尤其是对于人生问题的反复思考。只是,由于处境的危险,他只能用隐蔽的象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对自由人格的追求,用笔曲折,含蕴隐约。
读其诗似乎能感受到一种悲哀的意蕴、一种强烈的生命孤独感,同时还传达出一种想反抗却找不到方向的迷茫感。比如第一首就流露出了这种感情。“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3]月色如水,寒风拂衣,孤鸿悲鸣,宿鸟惊飞,在这一片冷漠枯索的气氛中,主人公独处空堂,徘徊忧思。此诗用象征的手法,寄托一种绝对的孤独感,一种幽深而难以名状的愁绪。所以才会有“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的举动。因而阮籍的放诞不羁、酗酒佯狂的言行举止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掩饰自己的孤独与无奈。同时,在《大人先生传》这篇散文中他假托“大人先生”之口,表述自己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揭露封建礼法的虚伪的本质。议论十分尖锐而透彻。从中可以看出阮籍不想与所谓的礼法君子们同流合污,表现出他对自由的向往并始终想保持人格上的独立。
(2)音乐。
七贤中嵇康崇尚老庄,性格高傲刚直,不拘礼法。又受道教影响,喜谈服食养生之事。通音乐,善奏琴。曾官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在《世说新语·雅量》门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嵇中散临刑东市,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长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2]嵇康因“吕安事件”牵涉被杀,面对生命的终结尚能纵情谈乐,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音乐的痴迷,另一方面,“临刑奏琴”可以算是他的最后一次反抗,面对死亡他依然用冷静的方式保持着他独立的人格,不仅现出他坦荡无畏的气节,更体现出他对自由人格的追求。
阮咸可以算是一个杰出的音乐天才,有一种乐器的名称用他的名字固定下来,这就是“阮”即“月琴”全称“阮咸”,魏晋时期它又叫“琵”“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精通弹奏琵琶。
总之,弹琴赋诗、酗酒佯狂、傲啸山林是七贤的重要标志,也是他们怡志遣情的重要手段,更是他们追求自由人格之体现。
二 崇尚清谈
魏晋时期,政治上的高压促使文人朝不保夕,因而纵酒佯狂,挥毫谈玄,成为了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精神庇护所。玄学的兴起,动摇了两汉以来的经学独尊的地位,淡化了文人以从政为人生归宿的意识,使老庄哲学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完成了它对古代文人的思想启蒙,从而对文人的价值观、思想作风、人生态度、审美情趣及文学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竹林七贤”弃儒家经典而崇尚老庄,每个人都才华横溢,清谈则成为他们放诞不羁的方式之一。《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2]
“竹林七贤”是十分热爱清谈的,而且他们的谈玄论道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清谈不仅成为他们彰显名士风度的方式之一,更是他们放诞不羁的表现。清谈在当时自然是评价颇高,名士们崇尚自然,讲究无为而治。而清谈本身也有其审美的价值,竹林七贤轻裘缓带、饮酒的风度,论辩叙致、辞令声调的优美,会让其他人觉得这才是名士的风度。
“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他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而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三人交往甚密。一方面种田、栽培蔬菜可以满足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借此陶冶情操谈玄论道,他们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在那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清谈既可以达到精神世界的满足,又能回避当时残酷的现实。加之清谈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又是名士风度的象征,并逐渐成为一种风气。善于清谈的名士也成了士族文人心中的偶像,所以竹林七贤选择用清谈的方式来表达其放诞不羁的审美理想也就容易让人理解了。
三 不拘礼法,蔑视权贵
竹林七贤厌恶黑暗的社会,想脱离传统礼教,于是放弃儒家经典而崇尚老庄,不拘礼法,蔑视权贵,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他们大多都借酒消愁,以求得到精神上的超脱,回归自然。
阮籍可以算是“七贤”中的翘楚。他蔑视权贵与不拘礼法的言行举止便是淋漓尽致的表现出他的放诞不羁,因而他的放诞不羁也更具代表性。《世说新语·任诞》中的阮籍总是一幅特立独行的样子,他为了能喝到酒,就申请去做步兵校尉。阮籍认为“礼岂为我辈设耶?”所以他送别嫂嫂,大醉后睡在邻居妻子的旁边。母亲去世后,他在母亲服丧期间纵情酒肉,虽然这不符合古人的观念,甚至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不被人们所齿,因此他受到了裴楷的弹劾:“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6]就在所难免了。
阮籍的行为与态度只是为了避开世俗礼教不想与虚伪的礼教为伍,这也只是他与礼法的一次较量而已,不是他内心的想法。因为从葬母的事件中我们会发现阮籍是一位孝子。还有文帝想帮阮籍求婚,阮籍打心里不想同意这门亲事但又不敢得罪文帝,所以醉了六十天,让文帝没有办法和他谈正事。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会发现阮籍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所以他不想与司马氏合作,更不甘心向虚伪的权贵低头的态度都体现出他对礼法和权贵的蔑视。
在刘伶的身上我们也会发现其对权贵的蔑视程度极深,在《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2]他把天地当作自己的房屋,把房间当作裤子可见他饮酒后性情十分的狂放,这也是一种反抗,一种对虚伪礼法及权贵的蔑视。刘伶的《酒德颂》赞美纵酒任诞、蔑视礼法的生活,也被世人所称赞。文中把“大人先生”和显贵公子、仕宦处事的言行进行对比,文章不仅突出了大人先生鲜明的个性——狂放、潇洒、不拘礼法、蔑视权贵,而且揭示出贵介公子们的迂腐不堪。所以《世说新语》称刘伶著《酒德颂》乃义气所寄。虽然过度饮酒对身体有很大的害处,但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方式是一种对礼教权贵的蔑视,甚至是一种反抗,所以“竹林七贤”的这种反抗值得我们肯定,因为这些名士们处于黑暗政治环境中,对自由的向往与现状的无奈形成强烈的对比,那时的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因而他们经常聚集在竹林,纵酒放任,愤世嫉俗就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了。
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行为举止反而促进了整个魏晋名士旷达不羁的风气的传播。因此竹林七贤对礼教的蔑视、不拘礼法体现了他们放诞不羁的审美理想。
四 情感的真实流露
竹林七贤放诞不羁的审美理想还从他们率性而为的一腔真性情,对亲情、友情的珍视里体现了出来。他们很看重骨肉亲情的。阮籍将要埋葬母亲时,与母亲诀别那一刻,一直哭号着说完了,紧接着就吐出鲜血以致病弱了很久。由此可见阮籍是很孝顺的。七贤中的王戎也是一个孝子,《世说新语·德行》就记载了“王戎死孝”[2]的故事。王戎、和峤同时遭逢父母死亡的大事,和峤行孝备礼合乎礼仪规范但神气并没有损伤,王戎不备礼,但他已经悲痛得只剩一把骨头。由此可见王戎的行为和孝心是真正的“孝道”的表现,也是他内心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七贤之间的友谊之情也特别深,七人常聚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语·伤逝》载云:“王濬冲为尚书令,……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未……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2]此条记述王戎触景生情,不禁悲感泉涌,回忆当初鸿鹄比翼悠游,是多么自适自在!可见王戎也是很重视七人之间的友情的;谈到七贤之间的友谊就不得不提到嵇康和山涛。尽管嵇康曾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这只不过是他不想与虚伪的权贵扯上任何联系、表明厌恶仕禄的态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交。因为在嵇康临死之前他依然让自己儿子去找山涛,可见他是非常信任山涛的,而且对这份友情很重视。
五 “竹林七贤”放诞不羁的审美理想对现代人的积极影响
“竹林七贤”放诞不羁的审美理想,实际上是他们追逐的名士风度。它包括从内到外的东西,不仅是内在学识,还有外在的言行举止。既包括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对清谈的热爱、对权贵礼法的蔑视,还包括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竹林七贤”言行举止上的放诞不羁是追求独立人格的一种表现,谈玄饮酒只是一种形式而并非竹林七贤的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追求人生的一种逍遥适意,并以此保持人格上的独立、精神上的自由、活出真正的自我个性。
“竹林七贤”虽然有不同的出生背景及经历,但是他们都追求自由的人格并且都崇尚清谈,而且对虚伪的礼法和权贵十分的蔑视,正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点才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魏晋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比较混乱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更是一个觉醒的时代。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物欲膨胀的社会中,传统的安贫乐道,像“竹林七贤”那样远离官场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的人已经很少了,人们对利益功名的追求变得极度实际。人们随波逐流,放弃了心灵上的修炼与提升,甚至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因而他们活不出像“竹林七贤”真正的自我个性,活不出他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的一腔真性情。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竹林七贤”的人格和行为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思考,促使我们淡化功名利禄追求和张扬个性;促使我们尊重内心的真情实感抛弃虚伪的东西;促使我们追求自由的人格得到精神上的充实。所以只有追求自由的人格、保持自我个性、尊重内心的真情实感,我们才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助于解决我们的个人利益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进而创造出更为多元灿烂的文化。“竹林七贤”的放诞不羁是一种对美、对真的追求,所以“竹林七贤”放诞不羁的审美理想对现代人是有积极影响的。
[1]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6.
[2]刘义庆.世说新语[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256,101,234 -236,05,203.
[3]倪其心.阮籍诗文选译[M].巴蜀书社,2000:67.
[4](南朝宋)刘义庆.杨美华,译注.世说新语精粹[M].海潮出版社,2009.
[5]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高谈文化.教你看懂世说新语[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
[7]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8]蒋凡.世说新语英雄谱[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王晓毅.张齐明.世说新语解读[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