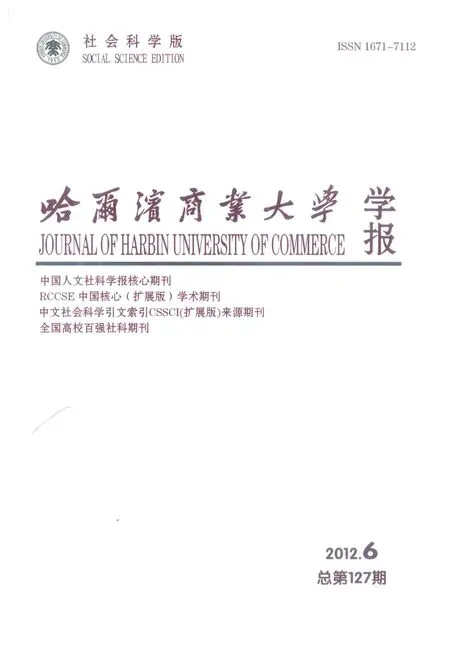国有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视角
刘儒昞,王海滨
(1湛江师范学院商学院,广东湛江524048;2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北京100081)
企业生产经营离不开自然环境,而且对自然环境还会产生巨大影响。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过程中,企业经营导致的环境污染事故进入了频发期,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使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严峻考验。企业应补偿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失,承担环境责任。新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价值最大化不仅仅是企业的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同时达到最优。2010年10月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两型社会”的建设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
一、文献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
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界定方面。加拿大环境污染调查组织(2007)从三个方面定义企业环境责任: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使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不会对环境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原材料和能源管理体系;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实现企业环境信息透明化。Arab Forum for Environment&Development(AFED)(2007)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要承担生产经营带来的环境影响,降低废弃物的排放量,增强资源的使用效率。美国经济伦理学家Graft Zivin(2007)提出:环境责任主要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让环境承受较少的废弃物[1]。
关于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福柯特、林登等(1998)认为,环境信息披露存在显著性波动,不能支持自愿性披露假设。诺拉·博尔(2002)认为公司通过发布环境报告可以改善自身的社会形象并确立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2]。马克(2006)发现强制信息披露可以克服环境信息披露相对公众需求的不足,并指出这能增加社会福利。玛若(2006)发现强制环境信息披露在能源、电力行业效果明显,不仅能提高环境方面的表现,还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降低平均能耗[3]。
关于组织合法性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Ramanathan(1976)最早将组织合法性理论运用于公司环境会计的研究。他提出,无论是发生合法性危机后的事后补救还是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主动预防,环境信息披露都是公司合法性管理的一种方式。Lindblom(1994)将合法性理论系统地运用于环境会计研究。她严格区分了合法性(legitimacy)和合法化(legitimation):前者是一种状态,而后者则是实现这一状态的过程。接着,她描述了公司在合法化过程中可能采用的四种战略。这四种战略都要借助社会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4]。Neuetal(1998)、Mobus(2005)研究表明在企业以持续提供正向信息作为合法性策略时,强制性披露不遵守环境规则信息数量的增加降低了不遵守现行环境规则的状况,提高了现时环境业绩[5]。
2.国内研究综述
关于企业环境责任的界定方面。白平则(2004)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自身及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当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樊英(2005)认为公司环境责任是指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遵守有关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尽可能地维护环境利益,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采取预防、治理等措施,使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吴真(2007)认为企业环境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当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科学生产和经营,以履行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1]。
关于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汤亚莉等(2006)研究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及影响因素。王建明(2008)认为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受到行业差异和外部环境监管制度压力的显著影响。鲁海帆(2010)分析了低碳时代环境信息的需求者和使用者,提出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的建议[3]。高红贵(2010)基于“生态社会经济人”视角分析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周一虹等(2010)指出绿色经济政策为环境信息披露目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些解决途径,并为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了带有压力的外部环境,因此,企业要从各方面逐步完善环境信息披露[5]。
关于组织合法性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李朝芳(2010)研究指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可能产生于合法性的动机;在企业不同组织变迁阶段,由于其环境保护意识的不同,导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需求有所不同,对政府管制需求也不同[5]。毛江华、戴鑫(2011)运用组织合法性理论通过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的对比研究得出:政府应加强对企业的披露管理,鼓励企业自愿性披露环境信息;建立企业的规制合法性时应采用强制性环境披露,在建立规范和认知合法性时企业应更多地考虑采用自愿性环境披露;企业也可通过强制性与自愿性披露结合的形式,多维度、多方面地进行披露实践,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公众的认知,从而建立和巩固企业的组织合法性[6]。
现有研究文献显示,国内外对于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从最初的披露动机领域向披露的策略、影响因素和绩效等领域拓展;从理论基础来看,组织合法性理论对于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从研究对象来看,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企业是主要研究对象。
虽然近十年来该领域的论文数量发展迅速,但是从现有可检索到的文献中鲜见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研究;在理论基础上,虽然组织合法性理论对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信息披露现象有较好的解释作用,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偏少。
本文尝试运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对国有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必然性进行分析,提出改进国有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一孔之见。
二、组织合法性与国有企业环境责任
1.组织合法性
组织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组织研究领域中被广泛运用。合法性理论源自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关于企业和社会系统定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与政治、经济是分不开的,离开了政治和社会及制度框架,经济问题就不能被有意义地研究。普遍认同的组织合法性定义是由舒什曼(Suchman)提出的,即组织合法性是指一个实体的行动在社会建构起来的规范、价值、信仰以及解释系统中是合乎要求的、恰当的。也就是说,组织合法性是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或旁观者对组织的认可[6]。
归纳起来,组织合法性理论大致经历了萌芽、明晰、形成和应用四个阶段。萌芽期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此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保护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公众呼吁将企业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统一,此时人们开始思考企业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存在基础,但还没有形成组织合法性的明确定义。20世纪80年代为合法性理论的明晰阶段。这一阶段组织合法性的基本定义形成,同时对企业如何与社会利益相关者一致的价值体系的构建等问题展开了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合法性理论体系形成。在此阶段,学者们进一步发展了组织合法性的定义,并从制度基础、合法性鸿沟等角度丰富了组织合法性理论体系。进入21世纪以后为应用阶段。这一阶段,人们尝试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来解释企业行为,有学者运用该理论来解释企业年报和社会环境披露行为。
合法性是一般化的感知或假设,是关于一个企业的行动如何被社会现存系统的标准、价值、信念等认为是合理的、合适的、令人满意的理论。合法性理论认为一个缺乏持续地遵守社会标准、价值的企业不可能维持下去,即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在与社会价值观不一致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企业的信息披露政策被认为是企业内部管理者采用的一个重要手段,管理层可以用它来影响外界对于企业的认知,以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满足社会预期以取得合法性。
2.国有企业环境责任
近年来,国有企业频频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如2005年11月13日发生的中石油吉林化工分公司爆炸事故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严重的松花江水污染;2010年7月4日福建紫金矿业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事故造成汀江部分水域严重污染 ;再到2011年6月4日和17日,中海油渤海湾油田发生两起漏油事故,造成近840平方公里海域受到污染,对海洋生物的伤害或更严重。以上这些发生在国有企业的重大环境事件不但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严重的生态破坏,而且严重影响了国有企业的形象,将国企推到了环境保护的风口浪尖。用纳税人的钱创办的国有企业竟然成了污染大户,变成了环境违法的“钉子户”,引发了人们对国有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深刻反思。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作为“经济人”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企业公民社会理论认为,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组成单元,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公民不但要遵守法律法规作出经济贡献维系自身的存在发展,而且要承担起对人以及自然环境的责任[8]。“生态社会经济人”理论则认为,在现代经济科技环境条件下,企业作为“生态社会经济人”,其行为决策不仅要追求直接的物质利益,更要注意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不仅追求代内生态、经济和社会公平和谐,而且要追求代际的公平和谐[7]。
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的环境责任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在我国,国有企业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因此,国有企业承载着民众对社会主义企业乃至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向往,这是国有企业合法性所在。国有企业从建立伊始就赋予他强大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国有企业从一开始就并非单纯为“经济目标”而建立的,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性质的重要体现。国有企业实质上具备着“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双重性质。由于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用国有资产投资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理应更多地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责任,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应当考虑公共利益。因此在“公益性”和“营利性”双重属性中,公益性应当是首要性质,当公益性和营利性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公益性为优先。在这种意义上,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主体,更是特殊的政治主体,其行为不能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应当追求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国资委2008年第1号红头文件指出:中央企业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企业的表率,努力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和全社会企业的榜样。
国有企业的环境责任,既是国有企业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两型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国有企业满足社会期望以取得合法性的必然选择。这种企业环境的受托责任就要求其对环境信息予以充分披露,以从相关社会公众那里取得合法性地位,解除社会对其预期的环境保护责任。
三、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1.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主体并未涉及所有国有企业
根据2003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件《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为“超标准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企业”,“其余企业可以自愿参照本规定进行环境信息公开”[9]。在2010年环境保护部下发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中,也未对所有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作出强制性规定。可见,我国目前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主体仅限于上市公司(包括国有上市公司),而对于非上市公司(包括国有非上市公司)暂无强制性要求。
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不完整
根据“公告”,企业必须公开的环境信息包括企业环境保护方针、污染物排放总量、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环保守法、环境管理等5大类12小项,而且要求企业不得以保守商业秘密为借口,拒绝公开相关环境信息。但从目前上市公司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看,很多重要信息由于涉及企业的财务或战略利益而并未完整真实地予以披露[9]。
另外,我国目前对环境信息的披露基本上采用在传统报告(如年报、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中分散披露的形式,无法有效反映环境问题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如高污染行业的有色金属类上市公司在2007至2010年年报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中,几乎均未见到环境信息披露内容,也未见其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环境费用、环境收益和环境活动引起的现金流量的详细列示[10]。
3.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缺乏有用性
大多数公司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主要采用定性的文字表述方式,缺少数据支持,即使在定性描述过程中涉及一些数量指标(如公司年度资源消耗总量、公司环保投入等),也是分散在各个问题中,并非独立系统地进行披露。从收集到的462份200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发现,仅有21份报告披露了环保收入,比例只有4.5%[11]。由于缺乏可计量的数量指标,使得企业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对外部使用者的有用性大大降低。
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中,在每年的年报里连续披露相关的环境会计信息的企业也很少,即使进行了连续的信息披露,披露内容也比较随意,形式也不一致,致使信息使用者难以对此进行趋势分析,严重影响了环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12]
四、问题的原因分析
1.环境会计理论发展不完善
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研究起步较发达国家要晚一些,尚未形成完整的环境会计核算体系,没有建立统一的环境会计准则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规则,从而导致企业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难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因而容易出现企业信息披露中的随意性。在实务中,会计计量方面缺乏对环境对象的有效计量,使得需要货币计量、披露的环境资产与负债、环境成本与收益等信息缺乏可操作性的方法。如何突破环境会计理论障碍,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急需解决的问题。
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统一的规范
我国政府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管理仍然较为松散,证监会、环保部等都没有对企业在年度报告中必须披露的环境信息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环境会计核算和披露也未列入《会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制定相应的环境会计准则和制度,造成目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随意性太大。同时,由于缺乏强制性的准则规范,大多数企业不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使得披露信息的企业较少,诸如中石油、中石化等,环境敏感企业,仍然对环境信息的披露缺乏主动性。或者即使披露了一些,也无相关标准去衡量其信息质量,不能取信于社会公众,影响披露效果。
3.外部监管力度不够
发达国家在环境会计发展方面一般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作保障,环保执法严格,处罚力度很大,其中对上市公司和强污染行业的公司监管更严。我国虽有环境保护法,但对于环境违法的处罚态度不坚决、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直接影响了环境会计在我国的推行。再加上环境审计体制的不完善,即使对于被要求必须披露环境信息的重污染上市公司,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也并不理想。
五、完善国有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建议
1.提升国有企业环境责任意识
通过广泛的环境保护宣传,提升国有企业管理者对于环境责任的认知水平,认识到国有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履行环境责任与企业的长期发展并不矛盾,可能会损失眼前的经济收益,但这种牺牲有助于规避来自政府、商业伙伴、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压力,并与他们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提升了品牌价值,赢得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长远利益[8]。树立环境责任和经济效益并重(甚至是环境责任重于经济效益)的理念,不仅要服从环保法律法规,而且还要遵循生态伦理,将环境责任落实到企业经营、管理、生产的各个环节。淘汰旧的生产技术,促进材料和能源的循环利用,降低消耗和污染,实现企业、环境和社会的“多赢”。不仅要考虑整个生产过程的无污染、零排放,还要考虑产品设计、售后使用的环保节能以及废弃物的无污染性等等。
2.建立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强制披露,鼓励其他企业自愿披露的披露机制
目前,我国只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但是,环境保护不能单靠上市公司,所有企业都责无旁贷,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因此,有必要强制要求所有国有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同时,为提高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和积极性,弥补强制披露机制下存在的信息量不足和相关性差等缺陷,需建立激励机制以鼓励更多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缺乏激励制度是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执行力不高的一个原因。由于缺乏激励制度,使得会计信息披露多与少差异不大,难以调动企业环境保护和环境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加大执法力度的同时,做到奖罚分明,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优秀的单位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或精神奖励。通过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举的办法,推动环境信息披露的发展。
3.完善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
应该在相关法规中确定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内容,对需披露的环境信息的范围、形式、时间、内容等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以使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要加强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对违反相关环境会计制度的,除了追究民事责任外,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制度的严肃性,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权威,引导企业自愿进行环境保护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4.加强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尽快出台环境会计准则
会计准则是会计工作的准绳,因此制定环境会计和信息披露的相关准则,对于规范和推进环境会计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国目前还没有独立的环境会计及信息披露方面的准则或制度,环境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还缺乏科学的确认和计量方法,使得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可操作性。建议由政府组织,组建由会计学、环境科学、经济学等学科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对环境会计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环境会计准则以及实施细则,以规范环境会计的核算与信息披露。
5.强化外部约束,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监管机制
在目前没有环境会计准则规范的情况下,财政部、证监会和环保部应加强合作,严格监督检查国有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其次,要发挥政府审计机关在环境审计中的作用,就像审核资金一样对国有企业环境会计信息进行审核,确保信息披露的质量。同时,培植一批具有环境信息验证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在环境信息审核中的独立审计监督职能。最后,通过新闻媒体对不履行企业环境责任、披露虚假环境信息的企业曝光,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和谴责,对及时履行环境责任、正确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进行宣传,以有利引导其他企业。
六、结论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和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是社会发展对企业的一种必然要求。在我国,基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因此首先从国有企业开始,强化其环境责任的履行,再逐步向其他企业推开,不失为当下推进企业全面承担环境责任进而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和谐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强化国有企业环境责任,既是国有企业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两型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国有企业满足社会期望以取得合法性的必然选择。这种企业环境的受托责任就要求其对环境信息应予以充分披露,以从相关社会公众那里取得合法性地位,解除社会对其预期的环境保护责任。
但是除非有法律法规等进行强制性要求,大多数企业是不会主动增加环保支出、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因此,要解决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从宏观上说必须加强法律的制约,健全环境信息披露监管机制,完善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加强环境会计理论研究,尽快出台环境会计准则。从微观上说,国有企业管理者应当提升环境责任意识,认识到国有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既是大势所趋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主动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1]张晓丽,戴玉才.中外企业环境责任认识与制度研究的初步比较[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9,4:8-8.
[2]王珍义,方小红,刑 艳,等.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基于纺织行业的实证[J].工业技术经济,2009,(4):145-145.
[3]孙玉军,姚 萍.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以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J].财会通讯,2009,(6):78-78.
[4]沈洪涛.公司社会责任和环境会计的目标与理论基础[J].会计研究,2010,(3):89-90.
[5]李朝芳.环境责任、组织变迁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5):118-120.
[6]毛江华,戴 鑫.组织合法性理论视角下强制性与自愿性环境披露对比研究[J].生态经济,2011,(3):37-39.
[7]张保伟.国有企业环境责任问题分析[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1,(7):4-5.
[8]高红贵.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J].会计研究,2010,(12):30-32.
[9]胡 杨,邓婷婷.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156-156.
[10]陈 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问题探讨[J].中国证券期货,2011,(10):5-5.
[11]李 勤.谈完善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J].财会月刊,2010,(12):16.
[12]张淑惠,史玄玄,沈 咪.企业国际化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J].商业研究,2011,(12):70-76.